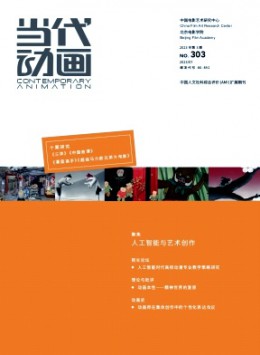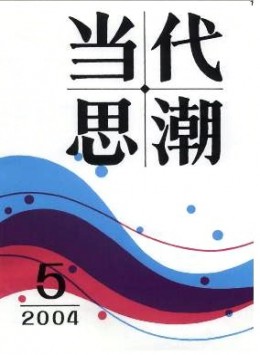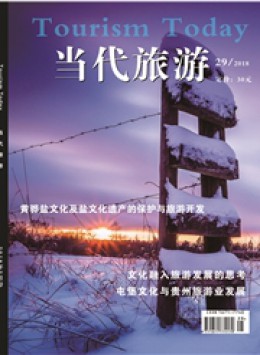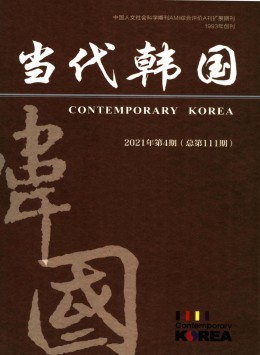當代政治哲學全文(5篇)
前言:小編為你整理了5篇當代政治哲學參考范文,供你參考和借鑒。希望能幫助你在寫作上獲得靈感,讓你的文章更加豐富有深度。

當代藝術創作政治符號化使用價值分析
摘要:政治符號性題材在20世紀80年代后開始逐漸被國內藝術家應用于藝術創作中,使政治符號化題材在新時期藝術作品中賦予了新內涵與藝術家本人的文化創作個性。
關鍵詞:當代藝術;政治符號化;使用價值
1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及界定
隨著1976年“”的結束,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逐漸步入了正軌。反映到文化藝術上,中國當代的藝術創作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星星美展、85美術思潮開始,一大批青年藝術家拿起畫筆結合全新的社會背景及對舊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思,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的藝術實驗,中國當代藝術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里幾乎重新走過了西方當代藝術三百年的探索路程。中國當代藝術的時間跨度,在廣義上講,是指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星星畫會大批探索性、叛逆性的藝術作品出現及傷痕美術人文主義作品創作為開端直至今日。而從狹義上講,所謂中國當代藝術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爆發于‘85新潮美術’,而終于1989年的‘現代藝術大展’的這一藝術演化進程一般被視為新中國藝術史上的現代主義藝術階段。”[1]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先鋒藝術家的藝術語言探索主要表現在從對“”回憶的悲戚中強化對人的本體性的情感表達,同時這一時期隨著西方哲學思潮的涌入,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美學現象對青年藝術家的藝術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藝術作品開始追求極富哲學意味的“前衛性”,出現了如“北方藝術群體”以“我們的繪畫并不是‘藝術’!它僅僅是傳達我們思想的一種手段,它必須也只能是我們全部思想中的一個局部”[2]為宣言的青年藝術群體。這一時期的先鋒藝術創作已不僅僅是用畫筆簡單的描述外界的景象,而是將藝術作品作為文化意義上的一種表現手法,創作總體上是完全服務與屈從于人的內心思想與哲學意識。90年代之后的中國當代藝術表現中,則有著與前輩們截然不同的落腳點,波普藝術、女性藝術、艷俗藝術等等一系列西方當代藝術表現形式使中國當代藝術家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西方的當代文化與藝術表現形式滲透成為這一時期藝術創作的主要語言。同時,藝術家開始對當代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體系進行了再思考。自星星畫會的創造性探索之后,中國當代藝術的開創性及模仿西方藝術語言的實驗開始在不同藝術門類展開,在具體的實踐創作過程中,藝術作品所展現的主題往往與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狀況有著重要的聯系,藝術作品的主題隱藏著藝術家在創作作品時的內心思想、價值觀念,是他們隱形觀念顯性表達的文化方式。在中國當代藝術創作中,近30年最主要的創作主題有玩世不恭的潑皮主義、具有中國傳統印記或特殊符號、對底層人群的關注、表現消費主義、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某種程度的滲透、關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聯系以及具有符號或領袖面孔的政治語言表述等等,這些創作主題在經過藝術家的藝術實踐及自身生活思考后,于不同藝術家手中逐漸形成各自不同的個人藝術符號。改革開放后,人民政治生活不再像“”時期嚴肅、封閉、不敢言語,對“”政治環境的反思與追問不停地在藝術家筆下呈現,“”題材與像等政治符號表現則是其中直接而又極具寓意的藝術語言。
2中國當代藝術中政治符號化藝術語言的運用
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最早使用政治符號進行先鋒藝術創作的可以追溯到1979、1980年王克平在星星美展中的雕塑作品《偶像》,作品以一個抽象化的頭像為主要表現內容,作品摒棄了中國領袖人物創作的高大、偉岸的傳統創作形式,作品中的“偶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仿佛在以狡黠的心態看著下面對其“朝拜”的崇拜者,然后露出一絲狡猾的微笑,整個作品政治寓意深厚,在廣大人民心中神圣的模樣仿佛在這里被消解掉了。此時,青年藝術家在經歷后“”時期理想主義消散的失落感之后,逐漸開始對之前的盲目政治崇拜進行反思,開始反思政治偶像與內心崇拜之間的距離。85美術思潮后,、等政治化符號被廣泛運用于當代藝術創作之中,期間出現了一些藝術家運用表現主義或波普主義手法表現政治化符號的藝術作品,而政治化符號在當代藝術中的運用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高潮,也正是這一時期,西方藝術界開始對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這一政治化符號藝術語言運用產生了密切關注,而隨著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之后,這種政治化符號題材開始在全世界受到追捧。中國的政治波普作為這一時期中國當代藝術的產物隨之誕生,一經出現便在藝術界、收藏界、評論界產生了一股震動。對于國內藝術家政治符號在波普藝術中的運用,在85美術思潮時期就有了實驗性創作,吳山專1986年的早期裝置作品《紅色幽默》進行了中國早期政治波普的探索,作品中運用了大量的“”時期的政治性口號進行拼貼,體現了青年一代對歷史反思的一場“紅色幽默”。王廣義、余友涵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運用安迪•沃霍爾波普藝術的創作形式,融入中國、領袖政治符號進行藝術創作,即為目前廣大意義上認知的“政治波普”,與安迪•沃霍爾對流行文化解構重構不同,中國的政治波普在一定意義上有了寓意更為深刻的內涵與批判精神。王廣義使用波普藝術的形式在標準像上打格子,隨后又在標準“批判”符號的基礎上進行政治波普化創作,創作了自己的代表作《大批判》系列。余友涵則將海報及領袖標準像基礎上加入了傳統民間服飾的花紋特點,之后又進行了大量的類似艷俗主義的領袖像創作。李山以作品《胭脂》系列成名,藝術家以青年時期標準像為題材,在嘴角加上一束桃花并運用對比色進行波普處理。劉大鴻的作品則運用民國月份牌及清代點石齋時事畫波普化,習慣性地顛覆舊有政治符號,展現歷史的荒謬和無奈。在政治波普之外,艷俗主義及一些后現代的表現手法中也加入了、領袖像等政治符號。祁志龍在早期作品中將各類標準像與歐美女郎畫像以艷俗主義的手法融合到畫面中,以側面暗喻消費主義時期偶像。俸正杰的《系列》,以翻白眼艷俗化表情的表現方式融入消費社會表現中,這一形式不再是政治隱喻,而更多的是對消費時代的一種反諷。尹朝陽代表作品《標準像》系列以天安門城樓標準像為原型進行了后現代的藝術處理,在對時代流逝思念的同時也表達出了青年至垂暮的某種人生歷程。石心寧則運用后現代的圖像處理方法將與不同人物進行了圖像融合,如與羅斯福等人參加雅爾塔會議,與瑪麗蓮•夢露在游泳池邊,與中國高層領導一起參觀杜尚作品《泉》。王興偉在作品《東方之路》中則將中國早期政治油畫作品《去安源》進行了圖像處理,將正面的形象處理成背對觀眾,以這種手法對美術史進行了借古諷今的調侃。
3中國當代藝術中政治符號化語言的使用價值
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分析
[摘要]卡爾·米切姆將技術哲學研究劃分為人文傳統及工程傳統,這一劃分得到了學界廣泛的認可。20世紀80年代技術哲學經驗轉向之后,面向社會的經驗轉向與面向工程的經驗轉向分別延續了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及工程傳統的技術哲學。無論從哲學發展、技術哲學學科建設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在強調技術哲學研究經驗基礎的今天,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研究仍具有首要性。
[關鍵詞]人文傳統;技術哲學;經驗轉向
一、技術哲學研究
傳統的劃分卡爾?米切姆(CralMitcham)通過對技術哲學研究的歷史考察,將技術哲學研究分為人文傳統與工程傳統。工程傳統的技術哲學的研究主體多為工程師,他們以技術為出發點,對技術進行考察與分析,由于其起點為技術,在看待其他事物時,也帶有技術思維的影子。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則以人為出發點,探究技術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以及技術與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要素如文化、政治等之間的聯系。盡管米切姆的二元劃分僅屬一家之言,且有過于簡單之嫌,但由于其概括性強,具有廣泛的通約性,因此得到了普遍的認可。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伴隨著對技術的懷疑與批判出現。在米切姆對技術哲學人文傳統的劃分中,主要包括了人類學———文化批判傳統的路易斯?芒福德、哲學———現象學批判傳統的敖德佳及馬丁?海德格爾和社會———政治批判傳統的埃呂爾等人的技術思想。芒福德考察了技術發展的歷史,考察了技術的起源,區分了綜合技術與單一技術[1]56,并對單一技術這種現代技術的主要形式進行了批判。海德格爾從他的存在主義現象學出發,區分了古代技術與現代技術,并指出現代技術的本質并非技術性的東西,而是一種真理的形式,是展現存在的一種手段。埃呂爾認為,自己是用“與馬克思研究資本相似的方法來研究技術”[1]75,他通過區分“技術操作”與“技術現象”對技術進行分析,指出技術是現代社會的統治力量。這些技術思想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是出于哲學的批判與反思精神,考察現代技術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由于環境污染、生產過剩以及經濟危機等問題日益嚴重,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傾向于認為現代技術是有害的,同時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一些哲學家諸如埃呂爾等認為技術是能夠自主發展的獨立系統,不是人類掌握技術,反過來很有可能是技術掌控人類。同時,這些技術哲學家也對如何面對技術引起的社會危機提出了一些見解,也“致力于探求人類怎樣才能與技術發展一種更好的關系”[2]9-10。這種技術哲學研究在多個方面受到批判。首先,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家大多對技術持有悲觀態度,他們的技術思想是出于對技術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批判,因此較少關注技術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其次,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家在對技術的本質認識中賦予了技術主體性,傾向于把技術當作一種人類無法控制的獨立自主的力量,技術對社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與人類使用并無太大關系,而是由技術本身決定。再次,在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的研究中,“技術被作為整體研究,……幾乎沒有注意到不同技術之間的差異性”[2]11。因此,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很少關注具體的技術,并不能對現實中的各種技術問題提出有效的建議。
二、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的當代體現
鑒于人文傳統的技術哲學中存在的種種問題,20世紀80年代歐美技術哲學研究發生了經驗轉向。技術哲學“經驗轉向”的概念由荷蘭技術哲學家提出并進而在歐美技術哲學研究中得到認可和發展。漢斯?阿卡特胡斯概括了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三個特點:
第一,它不把技術人工物看作是先天給定的,而是試圖打開黑箱,對技術的具體發展和模式展開分析。
“上善若水”的思想政治教育啟示
摘要:老子以水喻“道”,其“上善若水”思想,將水性與人性相結合,闡述了“利萬物而不爭”的生命哲學。“上善若水”所內蘊的哲理,既對當代大學生具有積極的道德教育意義,又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教育方法。
關鍵詞:老子;上善若水;思想政治教育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蘊含著豐富的哲理與智慧,正如所說:“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1]道家思想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蘊崇尚無為、追求本真的自然人本主義思想,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對于以德育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而老子作為道家哲學思想的創始人,有感于世人一味逞強好勝、不肯謙讓而引起無數紛爭的社會現實,而提出居守柔弱的處世之道。[2]他的“上善若水”理論,富含深厚哲理,既對當代大學生具有積極的道德教育意義,又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教育方法。
一、“上善若水”思想的基本觀點
“上善若水”出自《道德經•道經》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其中“上善”即是最好的品德與德行。老子以水性比喻人性,他認為最上等的品行就如同水一樣,既滋養萬物又與世無爭,甘心位居低處,卻能心向高潔。上善之人要像水一樣,處世謙遜不驕,思慮深邃寧靜,與人交往仁愛有禮,言談真誠守信,為政精于治理,處事以柔克剛,行事張弛有度。老子之所以將“上善”與“水”相聯系,是由于水作為生命之源,體現了生命的本源價值。“水”作為老子哲學思想中的一個特殊意象,代表了老子的“道”,通過“水”的自然規律,老子揭示出了生命的規律以及對個體生命的關注,“上善若水”思想代表著老子的處世哲學,其和諧、誠信、友善等價值內涵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對當代大學生具有積極的道德教育意義,有利于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二、“上善若水”思想內蘊的道德價值
(一)“居善地”的謙遜態度
中國經濟生態化發展
【摘要】解決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普遍難題,也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必須應對的嚴峻挑戰。作為一個唯物的、辯證的、實踐的、歷史的科學范式,馬克思生態哲學有關人與自然的分析既有哲學理論層面的關注,又有生態政治經濟學、生態社會主義層面的關注,三個視角的統一賦予馬克思生態哲學認識和改變世界的強大力量。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自覺踐行馬克思生態哲學,初步形成了一套推動經濟生態化發展的政策模式,為實現經濟與環境、人與自然永續發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關鍵詞】馬克思生態哲學;范式;經濟生態化
一、馬克思生態哲學的多維界定
生態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人與自然。馬克思生態哲學的深刻之處在于,在別人只看到人與物之關系的地方,馬克思看到了人與人的關系。圍繞著人、自然、經濟、社會等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觀點、科學論斷,建構了一個唯物的、辯證的、實踐的、歷史的生態哲學理論。
1.馬克思生態哲學的本體論根基:唯物的自然觀。在馬克思之前,長時間以來占據統治地位的世界觀是目的論的“存在之巨鏈”思想,即自然神學。在自然神學中,人與自然沒有先后之分,都歸于上帝意志。這種自然神學的最大敵人,“從一開始,就是古代的唯物主義,特別是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1]。早在還是一名大學預科生的時候,馬克思就開始研究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后來又把伊壁鳩魯主義選定為博士論文主題,最終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旗幟鮮明地肯定了自然對人的先在性,強調人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在人類產生之前,自然就已經存在。作為自然界進化結果之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人始終“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由此,先在的、客觀的自然,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與自然之關系的唯物主義特征。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人是自然的奴隸,與之相反,人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2],擁有對自然的巨大能動性。
2.馬克思生態哲學的方法論構架:辯證的自然觀。辯證法,就其根本來說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3]的方法。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形而上學的見解”與“辯證法的見解”[4]兩種對立的宇宙觀。形而上學總是在日月不同輝、水火不相容的對立中進行思維,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各種事物的聯系和區別、生成和消逝、前進和后退之間,都有著普遍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5]。比如在人對自然的勞動中,“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6]。這一觀點貫穿于整個馬克思生態哲學,既強調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又強調對其的否定理解,既強調對立又強調統一,既強調量變又強調質變。可以說,辯證法賦予馬克思生態哲學超越時代的穿透力。
3.馬克思生態哲學的實踐論取向:人化的自然觀。在馬克思生態哲學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實踐的關系。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具體化為一種對象性的關系,這種對象性關系包括了“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的人化”,而實踐則是兩者統一的中介。人對自然的實踐,是多種形態的對象性關系的綜合運用,不論是人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還是直觀、愿望、互動、愛等等,每種形態都是在展現人的實踐力量。人通過實踐占有了的、正在占有的自然界,就是人化的自然。馬克思生態哲學所考察的自然界,正是這個人化的自然。只有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2]那些與人類主體不存在對象性關系的自然界,則“是抽象的東西”[2],事實上等于無。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
一、馬克思人學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學基礎
在思想上任何教育都有自己的哲學基礎。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當代社會的進步,哲學在逐漸的研究中慢慢明晰了本學科在人學本質上的清晰思路和立場。隨后,哲學便主動向人學方向轉變,在形態上也逐步地靠近人學。高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肩負著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的艱巨任務,要實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這一目標,首先必須牢固夯實自己的哲學研究基礎,也就是明確以馬克思主義人學的觀點來指導自己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就必須:“從哲學的角度出發,理清人的本質屬性,梳理出人在發揮主觀能動性時的方式和方法,找出人在發揮主體作用時的過程,從本質上講就是要研究探索出人的主體性能力的發揮問題。特別是在適應和改造自然事的人格轉型問題。”“因此,把人當做行為主體,就必須進一步解決人的主體性的正確發揮的問題。這是研究人的基礎性工作,是研究人的現代化實現全面發展的理論出發點。因為人的主體性是與人的被動性、消極性相反的行為,只有正確發揮人的主體性,人的現代化和全面發展才有可能實現,只有把人作為一切行為的主體才能體現出其積極能動的作用”。馬克思認為人始終是一切活動的主體,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重視人要通過實踐來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提出人的主體性要以實踐活動為基礎。人的主體性是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過程中所發揮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整個過程中具有明顯的主觀能動性。人的主體性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主觀能動性,這是主體性的最高層次,而積極性和創造性是對客觀物質實現方式的認知和超越過程。在人的主體活動中還有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即人格,人格是人的主體性的一種表達,表達方式是在人的活動過程中從主體到客體以及從主體到主體的一種轉換。這種人格表現是人作為活動主體最基本的一種資格條件。發揮人的主體性否定了把人當做消極被動的客體的錯誤理論,為處理解決國家、個人、集體的相互關系,確立人作為人的基本地位,維護人的基本權利,實現人的自我發展,發揮人的潛力,沖破封建社會所強調的人的附屬和依附關系,從而為解放人的思想完善人的主體人格提供基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二、對馬克思人學思想觀照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思考
馬克思主義人學的興起對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明確提出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實現人的現代化這一目標和任務,表明了當代追求人的現代化的潮流和趨勢。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創新理念與實踐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2.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上的轉變
在我們的傳統教學中,思想政治教育更多關注的是對政治覺悟和道德觀念的教育,培養人的服務和服從意識,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教育目標局限教育與人才于要求受教育者順從組織要求、服從組織管理,而完全忽視個體的特點和特長,個體所具有的創造能力、突出個性、特殊才能都完全不受重視,忽略了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對個人性格和能力的培養,阻礙了個體的全面發展和思想上的百花齊放,在這種環境中的個體往往失去了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在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的指導下,新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應從傳統的“政治道德教育至上”向“突出個體能力”轉變,實現現代化和各方面能力的全面發展。人的自由和現代化是哲人從未停止追求的目標,這是人的發展最理想的狀態。哲學導師恩格斯在向外界描繪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未來時說:“到了那個時代,人可以成為自然界的主人。主宰自然,發揮自身所具有的創造性和能動性,成為屬于自己的自由的個體和社會的主人”。“個體的全面發展”是我們現代社會教育的最終目標,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教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目標還是為了促進人思想上的進步和提升,他的客體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最終指向是人之本質的生成和人性的完善、人之全面而自由發展。呼吁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實現向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觀念的轉變,構建更加科學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轉變價值取向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