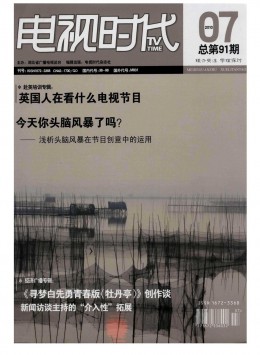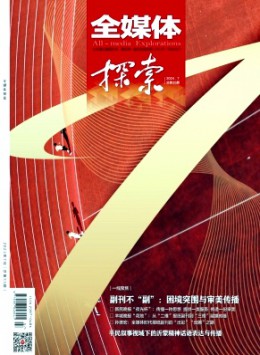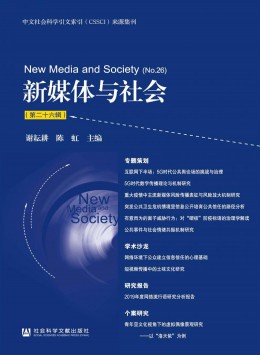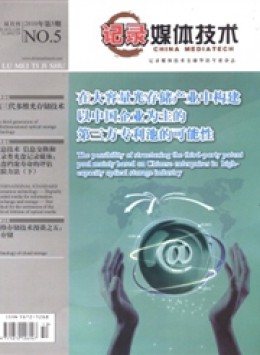自媒體下商標惡意搶注行為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自媒體下商標惡意搶注行為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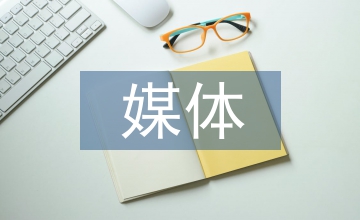
摘要:近年來網絡市場急劇發展,但部分網紅姓名遭到他人惡意搶注,造成經濟和名譽上的損失。目前我國《商標法》對于認定公眾人物姓名權惡意搶注行為有所缺失,司法實踐中遇到類似情況通常適用“在先權利”和“不良影響”兩個條款予以規制,但二者的側重點不同、又因為相關概念界定范圍不清晰,導致法官適用錯誤而當事人無法維權。對此,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修正:(一)在考慮認定因素上,對于惡意搶注名人姓名行為,主觀要素應當認定為惡意;(二)在法律規制方面,應當明確“在先權利”條款的界定范圍以及“不良影響”條款的含義;(三)從美國和日本兩國對該行為的立法借鑒,完善本國法律的缺失;(四)對于自媒體人而言,完善網絡平臺制度是必要的,以增強維權意識。
關鍵詞:惡意搶注;公眾人物;姓名權
一、案情引入
2017年9月,網紅敬漢卿表示,某公司將其名字作為商標完成了注冊,并以郵件的形式收到了鏡湖區知橋電子產品銷售部的通知。此公司表示,敬漢卿目前使用其姓名運營的微信公眾號、騰訊以及頭條公眾號均已侵權,若繼續使用,則本方可以提告。而這一切并非敬漢卿本人所為,甚至在收到郵件后的第三天,當他登錄其運營的公眾號時,卻收到一條侵權投訴。此時方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他人惡意搶注了。隨著敬漢卿主動在網上曝光其遭遇,不少自媒體人紛紛站出來表示自己遭受過同樣的情況,也有部分自媒體人開始查找自己的名字是否遭到搶先注冊。不幸的是,只要稍有名氣的自媒體人的姓名幾乎都被搶注成為他人商標了。其中,我們熟知的知名網紅“papi醬”的名稱已被不止一家公司搶注,而至今仍有多件搶注商標存在。可以說,商標搶注行為已經在自媒體領域蔓延。此前不少惡意搶注名人姓名的商標糾紛案件為我們所熟知,如“方大同胡辣湯案”“喬丹案”等。在筆者看來,“網紅”與此類名人的性質是相同的,即被公眾所知并在社會中有一定影響的人,均屬于公眾人物,可以一并討論。而該類事件頻繁發生的原因,依舊在于我國現行法律的不足與漏洞。從數據分析可知,我國惡意搶注名人姓名的案件呈遞增趨勢[1],而司法實踐中由于此類案件沒有一個固定的判決依據,導致判決結果因人而異,甚至因案由而異。基于公眾人物的特殊性,應當首先探討惡意搶注名人姓名的要件。
二、惡意搶注認定
(一)惡意搶注認定要件
對公眾人物姓名的惡意搶注行為的認定要件與一般搶注行為相同,即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分析。其中,客觀上,搶注人真實地進行了商標搶注的行為,且此種行為對原權利人的基本權益造成了損害。客觀層面是沒有異議的。對于“惡意搶注”的主觀層面,學界有一定的爭議。有觀點認為,搶注行為有些并不是惡意的,惡意的商標注冊有些是不屬于搶注的,也就是說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交叉的[2]。另有觀點認為,搶注行為中,惡意是對搶注人主觀方面的判斷,其所進行的商標的注冊行為通常會造成原權利人利益的損害。筆者更傾向第二種觀點,通過查閱資料并歸納可知,在惡意搶注他人姓名的主觀惡意表現在:首先是注冊他人姓名作為商標卻不實際使用,而是轉手以高價賣給他人;其次是可以通過“搭便車”方式獲利[3];再則是如敬漢卿案,注冊公眾人物姓名作為商標致使該公眾人物因未知而使用該商標導致侵權,再通過侵權訴訟獲得利潤。因此,通過歸納,惡意的是該文主觀方面的要件。若注冊人注冊的商標正是姓名權人名氣大漲之時搶先進行的,那么主觀故意是一般都具有的,相反的則沒有[4]。
(二)公眾人物姓名被搶注的特殊要件
從身份上來講,公眾人物與普通民眾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對于其姓名被搶注的特殊因素是需要進行考慮的。首先,公眾人物,顧名思義一定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如本文所述,搶注人利用名人的“知名度”而搶注其姓名作為商標從中獲利,這樣方屬于主觀的惡意。但是,如何衡量公眾人物的知名度,法律并未給出明確界定[5]。對于“知名度”的界定可以很廣,如演員、歌手或者本案所提及的具有較多粉絲的網紅等,都可以被定義為知名的公眾人物。對此,筆者認為“知名度”應當以一般公眾的認知作為標準,即在特定領域影響較大,并且被多數公眾所知曉的人為知名度較高的公眾人物。換句話說,如果該名人具有一定“顯著性”,那么大部分的公眾對他是知曉的。其次,被搶注名與該公眾人物之間的關聯性是需要考慮的。如果搶注人直接將名人的本名注冊為商標,那無疑就是惡意搶注行為。但是現在許多知名人物,如網紅papi醬、一條小團團等,所呈現給大眾的名字僅僅是網名。盡管是網名,仍然需要保護,因為他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為公眾所知,只要提到此類化名就立刻能想到這個名人,具有明顯的指向性。因此,若公眾人物使用了化名,其姓名權一樣應當受到保護。最后,被搶注的姓名作為商標與該公眾人物的關聯程度。此公眾人物在某領域的知名度是搶注人所看重的,通過利用,進而放大并使用搶注的商標在該領域的特征,使一般公眾陷入誤區,具有“搭便車”行為。因此,應當考慮姓名商標與公眾人物之間的關聯程度。
三、法律規制
(一)《商標法》的規制
目前,有關公眾人物姓名惡意搶注行為,主要由《商標法》第十條以及第三十二條進行規制。但是,由于這兩個條款的側重點不同且不同的法官對條款理解不同,因而會造成適用不當而出現類似案件有不同判決的情況。因此,應當對《商標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八項“不良影響”與第三十二條的“在先權利”條款進行分析。首先是“不良影響”條款。司法實踐中,在處理惡意搶注姓名商標時,許多法官適用不良影響條款來作出判決,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結合《商標法》第十條分析可知,該條款指的是對國家的政治、民族、宗教、社會等利益產生消極影響。因此,除非搶注人搶注的姓名商標有關國家領導人姓名,或者對民族、宗教等有不良影響的姓名,否則不會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不良影響。筆者認為,公眾利益與社會利益不能一概而論,公眾利益的范圍應當小于社會利益,因此不能達到《商標法》第十條所述“不良影響”。此處,其無關于具體的某個權利,對社會公共和國家利益的維護是其目的,而不是對個人權利的維護[6]。其次是“在先權利條款”。“在先權利”條款更側重維護個人利益,旨在保護私權。商標的注冊申請要以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不受到損害為基礎,這是《商標法》中明確規定的①,但由于目前我國《商標法》對于在先權利的范圍并沒有明確的規定[7],因此其爭議點為被搶注人姓名權是否屬于在先權利的范疇。有觀點認為,他人已擁有的在先合法權利,以及在線注冊或受保護的商標、著作權、人身權,特別是肖像或姓名權,這些都是申請注冊的商標不可侵犯的[8]。另有觀點認為,在先的利益和權利都屬于在先權利,但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在先利益[9]。在先權利的范疇中不需要將姓名加入。筆者認為被搶注的姓名權可以直接通過民法典來進行保護,不一定要將其劃進第三十二條“在先權利”的保護范疇。民事或其他應保護的合法權益都屬于在先權益,所以盡管在先權利中未包括姓名權,但仍能夠用在先權利來規制公眾人物姓名遭惡意搶注行為,只不過是對于經濟利益的在先權利的保護。綜上可知,“不良影響”是一個彈性條款,而“在先權利”更具有針對性。因此,在適用了“在先權利”條款之中還存在解決不了問題的情況下,再對“不良影響”條款的適用與否進行考慮。應駁回目的不是使用的惡意商標注冊申請,這是2019年所進行了第四次修改之后,《商標法》中添加的條款,加強對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注冊商標的打擊力度,公眾人物甚至自媒體人在發現該情況時,也可以適用第四條進行保護。針對商標被惡意搶注的情況,該法律中的第三十三條、第四十四條和第四十五條中也提供了權利人的法律救濟途徑。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制
惡意搶注名人姓名作為商標并實際投入某領域進行使用的行為很容易使公眾產生混淆、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從而破壞市場競爭秩序。那么,《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第二款也是此行為所適用的,該項直接列舉了姓名的范圍,即姓名包括筆名、藝名、譯名等②。但《反不正當競爭法》畢竟調整的是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間的關系,實踐中證明不正當競爭行為比較困難,因此對于姓名惡意搶注行為,實踐中主要依據商標法進行規制。
四、借鑒域外立法來完善本國法律缺陷
在美國,事前審查和事后救濟制度是針對惡意搶注名人姓名商標行為所制定的兩種制度。前者即進行商標的申請注冊過程中,通過對意圖使用說明程序的使用以確保申請注冊的商標不會損害他人的在先權利,從而在注冊申請階段制止那些明顯的惡意注冊行為;事后救濟制度是指,當公眾人物姓名被惡意搶注后的侵權救濟方法,只要確定了他人的公開權受到了此搶注行為的侵犯,法院就會對侵權人發出立即停止商標侵權的行為,并且要將此商標撤銷,之后被侵權的損失以其所提供的證據來進行確認[10]。日本在公眾人物姓名惡意搶注方面同美國一樣,也是使用意圖說明制度。在申請注冊商標時應當證明該商標的真實使用目的,甚至需要證明該商標是否用于正常經營以及如何利用;日本還有姓名授權許可制度,國內全部擁有此姓名的人表示同意之后,申請人才能夠對此姓名進行商標的注冊申請[11]。我國現行法律可以適當參考以上的域外立法,創立意圖使用說明程序,以此在申請注冊商標階段及時遏制明顯的惡意搶注行為,完善現有的商標體系。
五、完善保護建議
自媒體時代,為了市場需求而惡意搶注公眾人物姓名的“搭便車”行為應當被禁止,由敬漢卿案所引申的一系列問題值得人們思考,而且讓更多自媒體人以及名人正視惡意搶注姓名商標這一情況。由于自媒體人的知名度以及其自身所擁有的名譽,搶注者的惡意搶注行為不僅奪取被搶注者的商業機會,使其造成經濟損失,更可能因被搶注者對商標的使用不當而給被搶注者帶來負面影響,造成其名譽的損害。從2019年《商標法》第四次修改中新增第四條第一款內容可看出,我國對于惡意注冊這一行為的重視以及正在不斷加強打擊惡意搶注行為的力度。除了在相關法律法規上進行完善之外,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修正。首先,在考慮認定因素上,對于惡意搶注名人姓名行為,主觀要素應當認定為惡意,且在司法實踐中可以適當將部分惡意搶注姓名行為列舉出來。為了更好地規制該情況,應當明確將上文所述的特殊考慮因素納入立法。因為公眾人物身份特殊,在實際中應當多將公眾人物知名度、姓名與其關聯程度等方面考慮進去。其次,在法律規制方面,應當明確“在先權利”條款的界定范圍以及“不良影響”條款的含義。因為這兩個條款的側重點不同,在適用方面不應該有交叉,若未能明確二者界限,則會經常出現適用錯誤的情況,造成司法實踐混淆。因此,建議法律對兩個概念作出明確的判定標準。再次,我國由于在商標注冊申請前的審查不嚴格,導致搶注名人姓名商標行為頻繁出現,因此可以從美國和日本兩國對該行為進行立法借鑒,以完善我國相關法律。最后,對于自媒體人而言,完善網絡平臺制度是必要的。部分自媒體人因為維權意識較薄弱,加上自身姓名因素以及自媒體平臺維權程序冗長復雜,導致自媒體人維權困難。這種情況下,建議相關平臺尤其是網紅所屬平臺,應當建立完善的平臺網紅商業價值開發管理制度,并且增強平臺網紅的知識產權布局規劃,增強網紅名人以及相關公關團隊的維權意識,及時制止惡意搶注事件的發生。
作者:李佳怡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