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茶技術(shù)論文: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的價(jià)值思考
前言:想要寫(xiě)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制茶技術(shù)論文: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的價(jià)值思考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lái)靈感和參考,敬請(qǐng)閱讀。

本文作者:劉馨秋、王思明單位: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
據(jù)陸羽《茶經(jīng)•六之飲》記載,飲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餅茶,是指將鮮葉用甑蒸后,再經(jīng)搗碎、拍壓、干燥等工序而制成的一種蒸青緊壓茶。而粗茶、散茶、末茶與餅茶的制作原理和方法大致相同,都是蒸過(guò)的不發(fā)酵茶,其差別僅在于所用原料的老嫩,以及成茶外形的整碎和松緊程度。也就是說(shuō),末茶在唐代即已產(chǎn)生,其制作過(guò)程較餅茶簡(jiǎn)單,只需將鮮葉干燥后入磨細(xì)碾即可。由于末茶未經(jīng)拍壓成型,因此烹煮之前無(wú)需再進(jìn)行炙烤、研磨,極大簡(jiǎn)化了烹煮程序。生產(chǎn)和烹飲的簡(jiǎn)化既得到茶葉生產(chǎn)者的認(rèn)同,又符合消費(fèi)者對(duì)茶葉產(chǎn)品類型的需求。因此,末茶在入宋以后逐漸成為茶葉市場(chǎng)上的暢銷產(chǎn)品,不僅茶戶紛紛自發(fā)開(kāi)設(shè)磨茶坊,連官府亦“修置水磨”,并規(guī)定“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許赴官請(qǐng)買(mǎi)”,2以此壟斷磨茶和出售末茶之利。元代“金字末茶”即是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lái)的。金字末茶產(chǎn)于宜興與長(zhǎng)興交界處,與紫筍茶同產(chǎn)區(qū),是元代著名貢茶之一,位于長(zhǎng)興縣北水口鎮(zhèn)的“磨茶所”即是元朝統(tǒng)治者為督貢金字末茶而專門(mén)設(shè)立的貢茶官署。金字末茶的制作方法與唐宋時(shí)的末茶制法相同,即將鮮葉用甑蒸殺青,然后以茶磨碾磨成末狀而成,如王禎《農(nóng)書(shū)》所載,“先焙芽令燥,入磨細(xì)碾”。3據(jù)方志記載“,元貢薦新茶九十斛,貢金字末茶一千斛,芽茶四百一十斛。”4表明元代金字末茶在江浙貢茶中占據(jù)最為重要的位置。明洪武八年(1375),磨茶院(即磨茶所,明初改為“磨茶院”)罷院,金字末茶隨之被芽茶、葉茶徹底取代。
岕茶是產(chǎn)于宜興和長(zhǎng)興一種蒸青綠茶的總稱。“岕”,是指兩山之間的凹陷部分。就產(chǎn)地來(lái)看,岕茶與紫筍茶同屬宜興與長(zhǎng)興交界處的茶區(qū),其茶樹(shù)資源應(yīng)屬同種。據(jù)屠隆《茶箋》載“,陽(yáng)羨,俗名羅岕,浙之長(zhǎng)興者佳,荊溪稍下。”5《茶疏》亦有“長(zhǎng)興之羅岕,疑即古之顧渚紫筍也”6的記載。表明岕茶與紫筍茶確實(shí)同種,僅在加工方法上有所差別而已。岕茶制作工藝精湛細(xì)致,主要包括采摘、攤涼、揀茶、蒸茶、焙茶等程序。岕茶的采摘有別于他茶的“以初出雨前者佳”,而是“非夏前不摘”,必待“正夏”時(shí)才“開(kāi)園”采摘,稱為“春茶”;也有在“秋七八月重摘一番”,稱為“早春”。7采茶需要在“風(fēng)日晴和,月露初收”的清晨進(jìn)行,如果在烈日之下,則“須傘蓋至舍”以防止“籃內(nèi)郁蒸”;采回的鮮葉需要迅速攤涼,并“細(xì)揀枯枝、病葉、蛸絲、青牛之類”。鮮葉在經(jīng)過(guò)攤涼、萎凋和挑揀之后才能進(jìn)入到蒸茶工序。蒸茶時(shí)“須看葉之老嫩,定蒸之遲速。以皮梗碎而色帶赤為度,若太熟則失鮮。其鍋內(nèi)湯須頻換新水,蓋熟湯能奪茶味也。”蒸茶之后需焙茶,即將茶葉干燥。據(jù)《岕茶箋》記載“,茶焙每年一修,修時(shí)雜以濕土,便有土氣。先將干柴隔宿熏燒,令焙內(nèi)外干透,先用粗茶入焙,次日,然后以上品焙之。焙上之簾,又不可用新竹,恐惹竹氣。又須勻攤,不可厚薄。如焙中用炭,有煙者急剔去。又宜輕搖大扇,使火氣旋轉(zhuǎn)。竹簾上下更換,若火太烈,恐糊焦氣;太緩,色澤不佳;不易簾,又恐干濕不勻。須要看到茶葉梗骨處俱已干透,方可并作一簾或兩簾,置在焙中最高處。過(guò)一夜,仍將焙中炭火留數(shù)莖于灰燼中,微烘之,至明早可收藏矣。”焙好的茶葉在貯藏時(shí)需要用干凈的新磁壇,壇周用干燥箬葉密砌,將茶葉裝進(jìn)壇中并搖晃扎實(shí),再以干箬葉覆蓋,并用干燥木炭鋪在壇口扎固以吸濕氣,最后需在壇口壓上“火煉候冷新方磚”才能放置在干燥陰涼處保存。1岕茶采制工藝精細(xì),且因無(wú)需像餅茶、末茶一樣經(jīng)過(guò)拍搗、碾末等程序,從而保留了茶葉原本的清香淡雅。明代周慶叔曾作《岕茶別論》感嘆,“恨鴻漸、君謨不見(jiàn)慶叔耳,為之覆茶三嘆”;2清代冒襄對(duì)其亦有“味淡香清,足稱仙品”的高度評(píng)價(jià)。3
碧螺春茶產(chǎn)于蘇州吳中區(qū)境內(nèi)的太湖洞庭山。洞庭山包括東山和西山兩部分,兩山遍布數(shù)目眾多的山塢,即為碧螺春茶的地理標(biāo)志產(chǎn)品保護(hù)產(chǎn)地。據(jù)《隨見(jiàn)錄》載,“洞庭山有茶,微似岕而細(xì),味甚甘香,俗呼為嚇殺人。產(chǎn)碧螺峰者尤佳,名碧螺春。”4《太湖備考》載“,茶,出東西兩山,東山者勝。有一種名碧螺春,俗呼嚇殺人香,味殊絕,人矜貴之。然所產(chǎn)無(wú)多,市者多偽。”5另?yè)?jù)王應(yīng)奎《柳南續(xù)筆》載,“洞庭東山碧螺峰石壁,產(chǎn)野茶數(shù)株,每歲土人持竹筐采歸,以供日用,歷數(shù)十年如是,未見(jiàn)其異也。康熙某年,按候采者如故,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fā),采茶者爭(zhēng)呼嚇殺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后,每值采茶,土人男女長(zhǎng)幼,務(wù)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正元獨(dú)精制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康熙己卯,車駕南巡,幸太湖。巡撫宋犖購(gòu)此茶以進(jìn)。上以其名不雅馴,題之曰碧螺春。”6
由上述史料分析,碧螺春為洞庭東、西兩山所產(chǎn)之茶,以東山為勝,因其香氣特異,故俗稱“嚇殺人”。清圣祖康熙于三十八年(1699)南巡至太湖時(shí),江蘇巡撫宋犖進(jìn)此茶,康熙因其名不雅,而題“碧螺春”。此后,每年“谷雨節(jié)前,邑侯采辦洞庭東山碧螺春茶入貢,謂之茶供。”碧螺春屬炒青綠茶,其采制工藝在清末民初朱琛的《洞庭東山物產(chǎn)考》中有詳細(xì)記載,“茶有明前雨前之名,因摘葉之遲早而分粗細(xì)也。采茶以黎明,用指爪掐嫩芽,不以手揉,置筐中覆以濕巾,防其枯焦。回家揀去枝梗,又分嫩尖一葉二葉,或嫩尖連一葉為一旗一槍。隨揀隨放,做法用凈鍋入葉約四五兩,先用文火,次微旺,兩手入鍋急急炒轉(zhuǎn),以半熟為度,過(guò)熱則焦而香散,不足則香氣未透,炒起入瓷盆中,從旁以扇扇之,否則色黃香減矣。碧螺春有白毛,他茶無(wú)之。碧螺春較龍井等為香,然味薄,瀹之不過(guò)二次,飲之有清涼醒酒解睡之功。”7可知碧螺春茶的采摘時(shí)間為清明至谷雨,采摘標(biāo)準(zhǔn)為一芽一葉初展至一芽二葉,采摘后的鮮葉需先揀剔去不符合標(biāo)準(zhǔn)的芽葉之后再進(jìn)行炒制。碧螺春茶的炒制方法較為特殊,需“兩手入鍋急急炒轉(zhuǎn)”,以“炒轉(zhuǎn)”的手法使茶葉卷曲如螺、顯露白毫,與當(dāng)代碧螺春茶“手不離茶,茶不離鍋,揉中帶炒,炒中有揉,炒揉結(jié)合,連續(xù)操作,起鍋即成”8的炒制特點(diǎn)極為接近。碧螺春茶條索纖細(xì),卷曲成螺,香氣濃郁,滋味鮮醇。清代書(shū)法家梁同書(shū)曾題《碧螺春》詩(shī)贊之“,此茶自昔知者稀,精氣不關(guān)火焙足。蛾眉十五采摘時(shí),一抹酥胸蒸綠玉。纖褂不惜春雨干,滿盞真成乳花馥。”時(shí)至今日,碧螺春茶以其獨(dú)特的制茶工藝和“嚇殺人”的香氣,仍為傳統(tǒng)名茶中的珍品。
云霧茶產(chǎn)于連云港東北部的云臺(tái)山。連云港,古屬海州,據(jù)《宋史•食貨志》載,“宋榷茶之制,擇要會(huì)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錢(qián)之?dāng)?shù)厚于他州。”1說(shuō)明早在宋代,連云港所產(chǎn)之茶即因品質(zhì)優(yōu)良而易于販?zhǔn)郏⑦€特此向海州茶商征稅詔書(shū),而海州也成為當(dāng)時(shí)重要的茶葉集散地。據(jù)清代方志載“,茶,出宿城山,味似武夷小品,以悟正庵者為最。”悟正庵位于宿城山頂,“庵多茶樹(shù),東海茶以此地為最”。2表明嘉慶年間(1796-1820),云霧茶仍為海州所產(chǎn)茶中之精品。至道光末年,據(jù)許喬林在《海州文獻(xiàn)錄》中記述,“今惟宿城山有云霧茶,歲采不及一斤,山麓居民則以山楂之葉代茗蘚,別無(wú)茶樹(shù)也。”3表明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之后,云霧茶品質(zhì)優(yōu)良、易于販?zhǔn)鄣氖r已不復(fù)存在。直至清末民初,廣東候補(bǔ)直隸知州宋治基聯(lián)合海州士紳沈云霈等招商集股成立“樹(shù)藝公司”,并于云臺(tái)山擇68處向陽(yáng)山地栽種茶樹(shù),其所出云霧茶獲得南洋勸業(yè)會(huì)獎(jiǎng),云霧茶才又恢復(fù)往日輝煌。云霧茶的制作工藝主要包括采葉、攤放、殺青、揉捻、做形、干燥。采葉需在清明前后進(jìn)行,選擇一芽一葉初展芽葉為原料,經(jīng)攤放、揀剔后,進(jìn)行殺青、揉捻、做形。做形包括理?xiàng)l、搓條和抓條三個(gè)過(guò)程,成形后的云霧茶形似眉狀、條索緊結(jié)渾圓、鋒苗挺秀、白毫顯露。云霧茶以其香高持久,滋味鮮濃,湯色綠而清澈,葉底細(xì)嫩成朵、勻整、明亮的品質(zhì)特征,與洞庭山碧螺春茶、南京雨花茶并列為江蘇三大名茶。
雨花茶原產(chǎn)于南京中山陵園茶場(chǎng)和雨花臺(tái),是1958年江蘇省委為紀(jì)念革命烈士而組織人員研制的一種針形炒青綠茶。雖然雨花茶的歷史較短,但自其問(wèn)世以來(lái),曾多次獲國(guó)家和部省級(jí)優(yōu)質(zhì)名茶稱號(hào),并于2006年被評(píng)為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的地理標(biāo)志產(chǎn)品。制作雨花茶所用的茶樹(shù)品種主要有祁門(mén)櫧葉種、宜興小葉種、鳩坑種和龍井43號(hào)等,加工流程主要包括采摘、攤放、殺青、揉捻、整形干燥等。雨花茶在清明前后開(kāi)采,以一芽一葉初展為標(biāo)準(zhǔn),要求芽葉嫩度均勻,長(zhǎng)度約2~3cm,通常500g特級(jí)雨花茶約含芽葉50000個(gè)。鮮葉采回后,需揀剔不符合標(biāo)準(zhǔn)的芽葉,然后在室溫20℃左右的條件下,以2~3cm的厚度攤放3~4h,使鮮葉散發(fā)部分水分,促使茶多酚等生化成分發(fā)生輕微變化,從而消除成品茶的青澀味,增加鮮醇度。將攤放后的茶葉以“高溫殺青、嫩葉老殺、老葉嫩殺、嫩而不生、老而不焦”的原則進(jìn)行殺青,殺青采用“抖悶結(jié)合,以抖殺為主,適當(dāng)悶殺”的方法,鍋溫約140~160℃,歷時(shí)約5~7min,至葉質(zhì)柔軟,折梗即斷,透發(fā)清香時(shí)即起鍋攤涼。4殺青后的芽葉需進(jìn)行8~10min的揉捻,目的是使茶汁微出,并達(dá)到初步成條的效果。整形干燥包括理?xiàng)l、搓條和抓條,是形成雨花茶獨(dú)特外形的關(guān)鍵工序。整形干燥的初始鍋溫為85~90℃,待茶葉稍干時(shí)降至60~65℃,待六七成干時(shí)再提高至75~85℃。1在此過(guò)程中,茶葉在鍋內(nèi)被反復(fù)拉條、摩擦、搓緊,從而形成細(xì)緊、渾圓、光滑的外形,歷時(shí)約10~15min。成型的雨花茶毛茶還需進(jìn)行分級(jí),并用50℃左右的文火烘焙30min,至足干后才為成品茶。雨花茶的品質(zhì)特點(diǎn)是“緊、直、綠、勻”,即形似松針,條索緊直、渾圓,兩端略尖,鋒苗挺秀,茸毫隱藏,色澤墨綠,香氣濃郁高雅,滋味鮮醇,湯色綠而清澈,葉底嫩勻明亮。經(jīng)過(guò)50多年的發(fā)展,如今雨花茶產(chǎn)區(qū)已擴(kuò)大至雨花、棲霞、浦口、江寧、江浦、六合、溧水、高淳等三郊五縣。其中,南京市城區(qū)、江寧區(qū)、浦口區(qū)、溧水區(qū)、高淳縣等被列為地理標(biāo)志產(chǎn)品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生產(chǎn)區(qū)域。雨花茶成茶品質(zhì)和產(chǎn)量亦逐年提高,其制作技藝已收錄于江蘇省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活態(tài)的文化遺產(chǎn),強(qiáng)調(diào)技藝、經(jīng)驗(yàn)、精神的活態(tài)流變。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屬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范疇,則必然具備活態(tài)流變的特征,因此具有重要的傳承價(jià)值。此外,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亦屬于茶文化的研究范疇,因此又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而且茶葉本身也是一種具有地理標(biāo)志的產(chǎn)品,其質(zhì)量取決于特定原產(chǎn)地的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2綜合上述特征,江蘇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的傳承價(jià)值主要體現(xiàn)在地域和歷史文化兩個(gè)方面。
1、地域文化傳承
江蘇位于中國(guó)東部的長(zhǎng)江三角洲,介于東經(jīng)116°18′~121°57′,北緯30°45′~35°20′之間,屬溫帶向亞熱帶的過(guò)渡地帶,具有明顯的亞熱帶季風(fēng)氣候特征,四季分明,光、熱、水資源豐富,無(wú)霜期較長(zhǎng),適于多種作物生長(zhǎng)。憑借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條件,江蘇自古即是產(chǎn)茶重地,六朝時(shí)期其茶葉種植和生產(chǎn)已聞名全國(guó),唐代江蘇的茶樹(shù)種植以近太湖的蘇州、無(wú)錫、常州等地最為密集,種植范圍一直北延至連云港。植茶、制茶歷史悠久的江蘇更是名茶輩出,如宜興的岕茶,蘇州的虎丘茶、天池茶,揚(yáng)州的蜀岡茶,南京的棲霞寺茶等。這些歷史名茶不僅在品種和名稱上帶有茶文化固有的鮮明地理標(biāo)志性,而且在其傳統(tǒng)的制作技術(shù)和工藝演變中也蘊(yùn)含了深厚的地域文化元素和內(nèi)涵,具有珍貴的地域文化傳承價(jià)值。例如宋元時(shí)期,在其他茶區(qū)仍限于餅茶生產(chǎn)時(shí),江蘇的制茶技術(shù)以當(dāng)?shù)夭铇?shù)品種所適合的茶類生產(chǎn)為依據(jù),率先完成了由傳統(tǒng)餅茶向芽茶方向的轉(zhuǎn)變和發(fā)展,并通過(guò)較高的制茶技術(shù)水平創(chuàng)造出多種優(yōu)秀名茶品種。以此為基礎(chǔ),在明代“罷造龍團(tuán),惟采茶芽以進(jìn)”的貢制轉(zhuǎn)變之際,江蘇制茶技術(shù)獲得進(jìn)一步發(fā)展,其工藝更加先進(jìn)、精細(xì),炒青及蒸青技術(shù)均達(dá)到傳統(tǒng)制茶工藝的最高水平。江蘇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的發(fā)展及其在漫長(zhǎng)歷史時(shí)期中所取得的成就,均是在地域文化的影響下所產(chǎn)生的,因此在其千百年的傳承過(guò)程中必然伴隨了地域文化的傳承。
2、歷史文化傳承
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作為茶文化遺產(chǎn)、農(nóng)業(yè)文化遺產(chǎn)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組成部分,其形成和演變是在歷史發(fā)展的大背景下,在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產(chǎn)生的,因此在其傳承過(guò)程中保存并積淀了大量歷史信息。僅就餅茶至芽茶制作技術(shù)的轉(zhuǎn)變而言,即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統(tǒng)治階級(jí)的政策變化,生產(chǎn)力、科學(xué)技術(shù)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發(fā)展程度,以及普通人民群眾的經(jīng)濟(jì)生活水平和日常基本需求,此外,由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衍生出的飲茶文化、茶具文化、茶詩(shī)詞曲賦以及豐富多彩的茶俗文化等內(nèi)容,也極具歷史文化傳承價(jià)值。例如,專著宜興岕茶的茶書(shū)即有明代熊明遇的《羅岕茶記》、明代馮可賓的《岕茶箋》、明代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明代周慶書(shū)的《岕茶別論》等,而涉及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的史料更是不勝枚舉。再如歷代文人墨客以茶為題,將茶事內(nèi)容用詩(shī)詞、繪畫(huà)、歌舞等茶文學(xué)、茶美術(shù)的文化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正是茶文化吸收并向其他傳統(tǒng)文化浸滲的直接反映。這些茶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中所包含的歷史文化信息,無(wú)疑具有弘揚(yáng)民族文化,延續(xù)中華文明的價(jià)值和意義。
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中有條件轉(zhuǎn)化為文化生產(chǎn)力的文化資源之一,它不僅為現(xiàn)代制茶工藝的發(fā)展提供了詳實(shí)的借鑒依據(jù),而且還為當(dāng)?shù)芈糜伍_(kāi)發(fā)提供了珍貴的文化資源,并帶來(lái)了豐厚的經(jīng)濟(jì)效益。
1、為現(xiàn)代制茶工藝發(fā)展提供借鑒
結(jié)合不同茶樹(shù)品種及其適合生產(chǎn)的茶葉品類,我國(guó)古代勞動(dòng)者創(chuàng)造了眾多細(xì)致的茶葉加工方法,積累了豐富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yàn)。這些方法和經(jīng)驗(yàn)在史籍資料中得以沿傳至今,有些方法在當(dāng)今的制茶工藝中仍然發(fā)揮著積極作用,甚至仍然保持著最初的工藝流程。以洞庭山碧螺春茶為例,清代傳統(tǒng)工藝流程為:采茶,揀去枝梗,用凈鍋入葉,兩手入鍋急急炒轉(zhuǎn),炒起入瓷盆中,從旁以扇扇之;現(xiàn)代碧螺春茶制作技術(shù)(包括手工和機(jī)械)的主要流程則為:鮮葉采摘、揀剔攤放、殺青、揉捻、做形、提毫、足火提香。對(duì)比現(xiàn)代與清代的制茶方法,從殺青、揉捻、干燥的工藝原理,到茸毫顯露、卷曲如螺的成茶品質(zhì)特征都基本一致。而且在機(jī)械制茶中所使用的碧螺春茶成型機(jī),也是依照傳統(tǒng)工藝中“成形提毫”這一形成碧螺春茶外形關(guān)鍵工序的技術(shù)原理而研制開(kāi)發(fā)的,充分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對(duì)現(xiàn)代制茶工藝發(fā)展所起到的指導(dǎo)和借鑒作用。
2、為茶文化旅游開(kāi)發(fā)提供文化資源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載體。”近年來(lái),人們對(duì)文化遺產(chǎn)的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均大幅擴(kuò)大,因此以茶與茶文化為主題的旅游項(xiàng)目以其深厚的歷史積淀和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而備受青睞,并成為多地旅游業(yè)與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的新熱點(diǎn)。以碧螺春茶產(chǎn)地蘇州吳中區(qū)為例,全區(qū)從事碧螺春茶種植的農(nóng)戶約1.7萬(wàn);碧螺春茶產(chǎn)量和產(chǎn)值為154.5噸和13564.0萬(wàn)元,分別占茶葉總產(chǎn)量和總產(chǎn)值的49.5%和75.5%。22010年,吳中區(qū)茶文化景區(qū)接待游客數(shù)量高達(dá)110.99萬(wàn)人次,3極大促進(jìn)了當(dāng)?shù)氐慕?jīng)濟(jì)發(fā)展。
隨著茶文化旅游的不斷升溫,人們對(duì)其內(nèi)容的要求也不再滿足于僅是參觀茶區(qū)景觀或購(gòu)買(mǎi)相關(guān)產(chǎn)品,而是更加注重從體驗(yàn)和參與的過(guò)程中獲取知識(shí),并達(dá)到精神層面的滿足。在此趨勢(shì)下,挖掘和開(kāi)發(fā)既具有文化內(nèi)涵,又能使人們參與其中的旅游資源就顯得尤為迫切,而集教育功能、科研功能于一身的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則完全符合人們對(duì)新型旅游資源的要求。首先,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是在數(shù)千年的茶業(yè)與茶文化發(fā)展過(guò)程中慢慢積淀下來(lái)的,其中所蘊(yùn)藏的文化價(jià)值是茶文化旅游的核心要素和重要資源,能夠滿足人們對(duì)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此外,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又是一種可以再現(xiàn)的生產(chǎn)實(shí)踐活動(dòng),是體驗(yàn)型的旅游產(chǎn)品。我國(guó)茶葉種類繁多,每種茶葉的制作方法都有其獨(dú)特性,人們可以參與其中,從不同茶葉的制作過(guò)程中切身感受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這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特色與魅力,在達(dá)到對(duì)旅游產(chǎn)品體驗(yàn)和參與目的的同時(shí),獲得對(duì)當(dāng)?shù)匚幕恼J(rèn)同感和歸屬感。
江蘇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歷史悠久、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具代表性的有唐代宜興陽(yáng)羨茶制作技術(shù)、元代金字末茶制作技術(shù)、明代宜興岕茶制作技術(shù)、清代洞庭山碧螺春茶制作技術(shù)、近代連云港云霧茶制作技術(shù)以及當(dāng)代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術(shù)等。其中,蘇州洞庭山碧螺春茶制作技術(shù)、連云港云霧茶制作技術(shù)和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術(shù)已收錄于江蘇省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而碧螺春茶制作技術(shù)更于2011年被中國(guó)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收錄。
這些傳統(tǒng)制茶工藝再現(xiàn)了歷史時(shí)期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集成了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重結(jié)晶,蘊(yùn)藏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群體智慧和思想精髓,是珍貴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資源。然而隨著現(xiàn)代制茶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機(jī)械制茶的普及,手工制茶遭受到嚴(yán)峻挑戰(zhàn),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正在慢慢消失或已經(jīng)消失。雖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課題已獲得越來(lái)越多的社會(huì)關(guān)注,其傳承與保護(hù)工作也在努力進(jìn)行中,但在高速發(fā)展的城市化、工業(yè)化和全球一體化的潛在威脅下,傳統(tǒng)制茶技術(shù)的傳承仍面臨眾多挑戰(zhàn)。仍以洞庭山碧螺春茶為例,據(jù)統(tǒng)計(jì),目前茶葉炒制人員的市場(chǎng)需求量至少為4萬(wàn)人,然而登記在冊(cè)的茶農(nóng)數(shù)量?jī)H1.75萬(wàn)戶,且每戶基本只有1人掌握手工制茶技術(shù),缺口達(dá)一半以上。1榮獲中國(guó)馳名商標(biāo)稱號(hào)的“洞庭山碧螺春”的情況尚且如此,其他茶葉制作工藝的傳承工作必定更為艱難。
如何在國(guó)家政策支持下將傳統(tǒng)制茶工藝與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jì)相結(jié)合;如何在展現(xiàn)其價(jià)值的同時(shí)使之進(jìn)入市場(chǎng),從而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效益;如何使我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既能服務(wù)于現(xiàn)代社會(huì)又能弘揚(yáng)于未來(lái)社會(huì),實(shí)現(xiàn)傳承和可持續(xù)發(fā)展,都是需要思考并亟待解決的問(wèn)題。
相關(guān)熱門(mén)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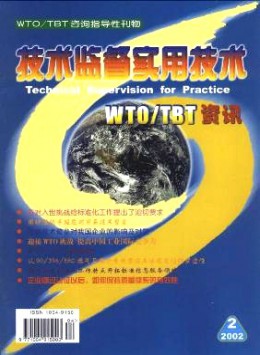
技術(shù)監(jiān)督實(shí)用技術(shù)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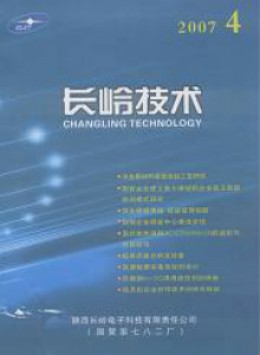
長(zhǎng)嶺技術(shù)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
-

綠洲技術(shù)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
-

特鋼技術(shù)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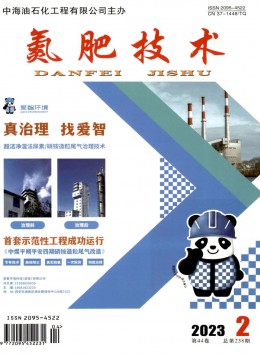
氮肥技術(shù)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