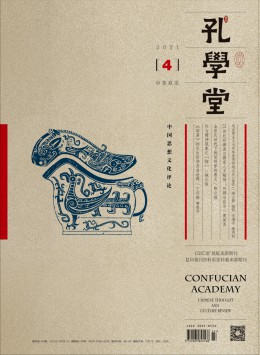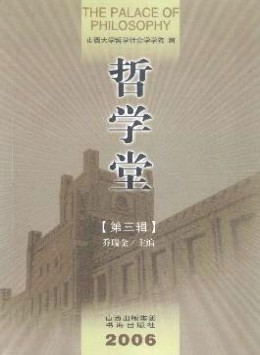學堂樂歌的藝術魅力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學堂樂歌的藝術魅力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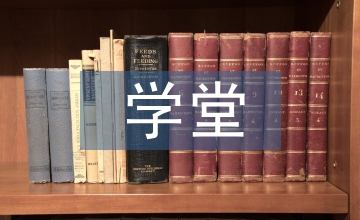
本文作者:何霜華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音樂舞蹈系
在學堂樂歌的創(chuàng)作史上,李叔同占據(jù)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因其獨特的音樂藝術創(chuàng)作和影響深遠的音樂教育,而被當代音樂學界公認為學堂樂歌的首創(chuàng)者之一,并與沈心工、曾志忞并列為學堂樂歌的“三駕馬車”。李叔同學貫中西的文化藝術底蘊,使他的學堂樂歌具有非常獨特的藝術魅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音樂藝術價值,但學界對此關注很少,本文對此做一簡要探討,以拋磚引玉,求教方家。
一、以民族文化熔煉藝術內核
在李叔同創(chuàng)作音樂的時代,中國還沒有精通西方作曲技術的音樂人才。那時的音樂人主要從日本學習學堂樂歌的創(chuàng)作手法。他們一般采用日本的甚或西方的音樂曲調,按照曲調形式來填詞,這樣創(chuàng)作出來的樂歌占到學堂樂歌的大部分。后來,隨著創(chuàng)作能力的提升,也開始出現(xiàn)采用中國民間音樂或傳統(tǒng)音樂曲調進行創(chuàng)作的,甚至有的音樂人可以自己作曲作詞。在這個逐漸學習和轉換的過程中,學堂樂歌從創(chuàng)作的根本上就必須融合西方音樂形式和中國文化內涵。因而,學堂樂歌創(chuàng)作的成敗,不僅取決于創(chuàng)作者對西方音樂技法的掌握,更取決于創(chuàng)作者的文化涵養(yǎng)。因為文化是音樂作品的靈魂,而曲調及技法只是形式。李叔同出身于書香門第,自幼飽讀詩書,且天賦文才,因而他在創(chuàng)作學堂樂歌時,非常自然地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氣質融入其中。李叔同廣受贊譽的一點,是他在創(chuàng)作學堂樂歌時對古體詩詞的嫻熟運用。他的學堂樂歌有不少選題出自中國古代的《詩經(jīng)《》離騷》,以及唐宋詩詞等。例如,標志李叔同音樂起步之作的《國學唱歌集(》結集于1905年6月),在當時維新派一味拒斥傳統(tǒng)音樂的喧囂中,李叔同堅持倡導國學,并主張用音樂來喚醒國民精神,這既體現(xiàn)了他對本民族音樂的自信,也凸顯出跨越時空、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像《祖國歌》和《我的國》這樣作品,充滿了豪邁的愛國熱情。《春游》、《西湖》等樂歌又洋溢著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氣質,采用借景抒情的藝術手法,表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人特有的內涵與志趣。李叔同的文采風范不僅表現(xiàn)在這些傳統(tǒng)的古雅詩詞上,而且在民間曲調的采納上也是信手拈來。譬如他的《祖國歌》和《夕歌》創(chuàng)作中,就都使用了江南絲竹曲牌《老六板》。而且他非常注意保持曲調的節(jié)奏平穩(wěn)對稱,從中國音樂的審美習慣來進行構思創(chuàng)作。因而,我們今天廣為傳頌的李叔同的樂歌,都有一種內在的民族精神和國學文化意蘊,正是這樣的音樂藝術內核使李叔同的音樂具有獨特藝術感染力。
二、音樂語言質樸簡潔
真正的大師不會炫技,李叔同毫無疑問是運用音樂語言的大師,他雖然擁有深厚的國學底蘊,但卻以質樸、簡潔的音樂語言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一個基本原則。尤其在解除了大量日本和西方音樂之后,李叔同追求質樸簡潔音樂語言風格的意識就愈加明顯。有時,即使他的樂歌運用了文雅的詞匯,但也會保持非常通俗明了的旋律,甚至他會注意選用一些已經(jīng)被人們所接受的西洋樂曲的曲調來創(chuàng)作,以便于人們更容易地記憶和接納樂歌。而且,他對于本來復雜的外國曲調中的復雜部分,還會選擇割愛,以保持器音樂的簡潔性。例如,《送別》的原曲是美國音樂作曲家約翰•奧德威創(chuàng)作的《夢見家和母親》,李叔同在選用這首曲調時并未全部照搬,而是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做了更改。在《夢見家和母親》一曲中,每句結尾處的旋律都有一個好像長嘆一樣的強拍上的切分倚音。結尾上帶一個切分倚音本是當時很多美國通俗歌曲中常見的一個特點,但李叔同認為這個特點在《送別》的樂歌中顯得多余。為了讓《送別》的曲調更加簡潔精煉,李叔同大膽地將每四小節(jié)就會出現(xiàn)一次的切分倚音刪去,從而形成了更加明了暢快的曲調旋律。《送別》曲調的成功,對比另一位學堂樂歌代表人物沈工心的《昨夜夢》,就更容易明了。沈工心的《昨夜夢》也是選用奧德威的《夢見家和母親》的原曲調,他保留了切分倚音,雖然詞作也不俗,但在后來的傳唱中就湮沒無聞。由此可見,質樸簡潔的音樂語言對于樂歌的傳唱有一定的功用。其實,不獨《送別》這樣廣為傳頌的樂歌,就是李叔同創(chuàng)作的其它很多學堂樂歌也都語言簡潔易懂,易于傳唱。比如旋律歡快而明朗的《春郊賽跑》,曲調源自德國的《木馬》。原曲是赫林(KarlGottliebHering,1765-1853)為哈恩(KarlHahn)的《木馬》歌專門做的曲。李叔同仿《木馬》曲調時,就是看中了它簡潔明快的特點,因而創(chuàng)作出的《春郊賽跑》也擁有相同的藝術特性。《春郊賽跑》歌詞:“跑!跑!跑!看是誰先到。楊柳青青,桃花帶笑。萬物皆春,男兒年少。跑!跑!跑!跑!跑!錦標奪得了。”不僅語言簡練,而且意興飛揚,歌唱也給人暢快淋漓之感。李叔同還有很多多聲部合唱作品,盡管曲調結構比《春郊賽跑》這樣的樂歌要復雜,但仍然不改其簡潔洗練的音樂語言風格。他在創(chuàng)作中,切忌沉迷于音樂技巧,而是在整體上把握音樂曲式結構,使之清晰方正,在和聲與復調的運用上也力求干凈利落,因而形成了李叔同特性鮮明的音樂語言風格。
三、音樂審美意境豐富而深邃
在近代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剛剛碰觸時,當時的音樂家就發(fā)現(xiàn)了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的一個根本差異:中國音樂重視神韻,而西方音樂則以理性的技法見長。中國自唐宋以來,就已經(jīng)形成了音樂“意境論”的審美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到李叔同的時代仍然完好地保留著。李叔同創(chuàng)作學堂樂歌時大量采用了西方和日本曲調,但是他同時也非常好地保留了中國音樂特有的意境美學特征。在《送別》一曲中,幾乎每一句歌詞都有很強的畫面感,讓人能聯(lián)想到一幅美麗的詩歌畫境。例如“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一句,描摹出中國傳統(tǒng)文人經(jīng)常傷懷歌詠的山巒夕陽之景,無論是李商隱的“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還是馬致遠的“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都與《送別》中的意境相應,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意境聯(lián)想,生發(fā)出豐富的文化想象和美學感受。又如李叔同另一首廣受贊譽的樂歌《春游》,也是音樂曲式、語言與意境完美統(tǒng)一的代表作。春游歌詞中有這樣四句:“游春人在畫中行,萬花飛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黃。柳花委地芥花香。”李叔同巧妙地運用減5度和純5度的對比音程,以鮮明的調性色彩形成開放性的樂段,形成豐富的聽覺效果,而這又與“梨花淡白菜花黃,柳花委地芥花香”所白描的自然景物相輔相成,有力地表現(xiàn)了花香彌漫游人醉的春游意境。曾有人批評李叔同的音樂情感消極、曲調較為低沉等,實際上這些觀點都沒有注意到李叔同樂歌意境表達的美學需要。李叔同的樂歌,尤其是后期創(chuàng)作的樂歌,大多具有深邃的哲理思想,而這種思想恰恰是中國傳統(tǒng)樂理原則的繼承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音樂對“意境”的重視,導致了對“氣韻生動”美學價值的推崇。明朝徐上瀛在《溪山琴況》中指出,情、理、形、神在“意”的貫通下達到一致,才能形成“無限深微”的“弦外”之韻。李叔同的很多樂歌恰恰體現(xiàn)了這種意境論音樂美學的特征。也正是由于這一點,李叔同的學堂樂歌不僅受到學生們的喜愛,而且也得到很多文化大家的贊美。《春游》就因為歌曲所描繪的淳樸自然的音樂之美,加上工整的旋律、和聲與無懈可擊的曲式,被豐子愷稱頌“李叔同是用畫家的眼睛觀察春游之景的妙處。”雖歷經(jīng)數(shù)十年,《春游》的魅力依然不減,時至今日仍是專業(yè)院校合唱的保留曲目,并曾在1992年被評為“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jīng)典”。
綜上,李叔同無疑是一位從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汲取了深厚營養(yǎng)的文化大師,他不僅按照西方音樂作曲曲調和技法進行學堂樂歌的創(chuàng)作,而且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氣質巧妙地熔煉成樂歌內在的精神靈魂,其中精粹又以簡潔質樸的音樂語言表現(xiàn)出來,并傳達出如詩如畫的音樂意境,充分表現(xiàn)出國學文化精粹與現(xiàn)代音樂藝術的雙重魅力。也正因此,李叔同的學堂樂歌開創(chuàng)了中國近代學堂樂歌的先河,為中國現(xiàn)代音樂按照自己的文化品格創(chuàng)新式發(fā)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