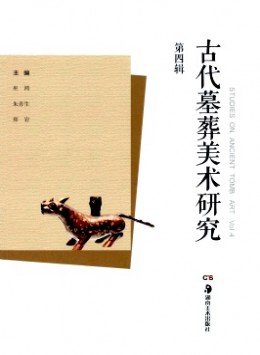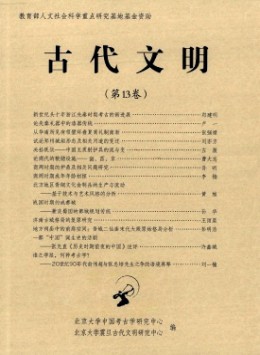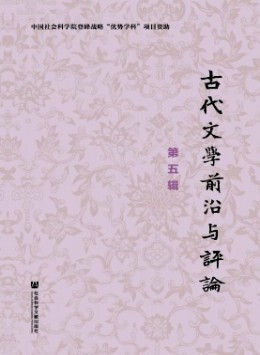古代戲曲文學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古代戲曲文學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研究述評
戲曲文學在國際國內都因戲曲藝術的獨特表演形式而備受關注,也不斷得到學術界的闡釋,形成了相對厚實的學術積淀,成為我們提出“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研究”的學理基礎,并對我們開展這一問題的討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西方,戲曲文學起源早,影響深,并且對西方哲學、文學、繪畫以及當代電影藝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受到西方社會的普遍認可,特別是隨著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化和文化產業發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應對成為西方學術界關注的一個話題,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沖突》、約翰•湯姆林森的《全球化與文化》等論著,讓我們聯想到從本土文化藝術研究可以獲得應對外來文化入侵的應對策略。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鄧啟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鳩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韓國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較早些時期便對云南戲曲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進行考察,對云南戲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月》、馬丁•艾斯林的《戲劇剖析》、萊辛的《漢堡劇評》、魯道夫•阿恩海姆的《藝術與視知覺》、烏格里諾維奇的《藝術與宗教》等對我們關注和討論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相關問題提供了全球化的這一全新的視角和間接材料。
在我國,戲曲與詩歌、散文、小說一起并列為我國古代四大文學樣式,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東方化的審美取向和綜合眾多藝術樣式的表現手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標志。自20世紀初期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開啟了古代戲曲文學的研究以來,經過一個多世紀幾代學人的努力,《中國戲劇史》《元曲家考略》《南戲拾遺》《古劇說匯》等著作,無論是在劇目整理、作家考辨、戲曲史等基礎研究方面,還是在社會學、民俗學、語言學、文化學、藝術發生學等深層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戲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戲曲志•云南卷》對云南的戲曲歷史以歷史性觀點作了梳理,列舉了云南戲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劇種等,是一部較為翔實的對戲曲藝術進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戲曲劇種史料匯編》系列叢書按劇種、劇目、音樂、藝人等系統,分別對云南地方戲曲中24個劇種的形成和發展史況以及音樂特色等作了詳略得當的介紹;李安志、徐志強等主編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戲曲史作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著重介紹了元代昆明水滸戲、明代關索戲、少數民族雜劇作家作品,但該書并未以云南戲曲為主要研究對象;王勝華的《云南民族戲劇論》,從民族文化的自我傳習、保護與發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此外,尚有對某些具體的劇種,如白劇、傣劇等戲曲作品、流派群體的研究著作、論文等,這些研究成果構成了我們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的基礎,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顯然我們從以上對國際國內研究現狀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學者在研究中更為關注的是作為一種表演藝術的戲曲,從其劇種、劇本、表演及傳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視了從文學樣式的角度探討其文本文化、文本創作、文本發展歷程及其與地方、民族的關聯。
討論分析
從目前來看,在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研究中,研究范圍狹窄和文獻資料不足這兩大問題嚴重困擾云南戲曲文學研究的深入。盡管我們在整個戲曲研究層面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處邊陲,相對于發達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則顯得封閉和落后,廣大研究者在云南戲曲文學研究中很難找到切實可靠的研究資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導致文學研究與民族文化研究處于一種脫節的狀態。故而關于云南戲曲文學研究的科學性和實用性亟待提高。所以從長遠看,選取云南戲曲文學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為視點,有利于從內涵方面和外延兩方面促進云南戲曲文學在云南經濟文化建設中趨向能力發展的均衡、公平,促進云南戲曲文學在云南文化建設及教學科研中的實效性。開展“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研究”應以基礎理論研究為主,重在對云南古代戲曲孕育、形成、發展的系列問題進行探討,通過文化和比較的方法,針對云南戲曲文學研究中的缺漏與不足以及云南地處邊陲、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等現實,結合西部大開發及橋頭堡建設戰略的實施,選取文學研究中地域與民族文化特征為切入點,通過對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的系統研究,解剖各個時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發生的一般現象、基本條件、規律與特點,著重闡釋云南戲曲文學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戲曲文學發展與經濟文化發展的一般性規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發掘與構建、旅游文化的開發與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與出路,為云南戲曲文學的研究與地方文化建設提供有益的經驗,為地方文化教材開發與建設創造有利條件。具體來說應主要關注以下內容:
一是關注云南古代戲曲作家與作品研究。“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文化傳統的重建越來越受到重視,但這是非常細致的事情,短時間內不容易見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發展中,從公元前3世紀楚人莊蹻率兵入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開始,直到魏晉南北朝,云南的戲曲藝術活動見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術禮儀活動。公元738年,唐冊封南詔首領皮羅閣為云南王,唐賜南詔胡部、龜茲音聲各一部,794年南詔遣使到長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詔奉圣樂》以及1116年大理國隨使藝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與中原進行戲曲表演藝術活動交流及云南早期戲曲活動的痕跡。此后,在中原戲曲發展的繁盛時期,歷史文獻中卻沒有關于云南戲曲活動的記載,只有一些詩句中提到了儺舞和梁王府蓄養的優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戲曲逐漸繁盛并奠定了“滇劇”的地位,但作為文獻研究的云南古代戲曲仍然顯得十分單薄。因而,作為戲曲文學研究的根本性內容的云南古代戲曲作家與作品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也只有通過對云南古代戲曲作家與作品的梳理,我們才能進一步厘清戲曲文學發展線索,重建云南古代戲曲文學體系。具體來說要重視對云南戲曲文學的歷史沿革及發展變化分析,重視對云南古代戲曲作家梳理與分析,重視云南古代戲曲作品與同時期中原文化的淵源及比對,重視對云南古代戲曲不同劇種作品的歸納與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關注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區域文化產業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鮮明的文化特色的東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軍隊及大量移民進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規模開礦后帶來的經濟繁榮,各種戲曲聲腔也紛紛傳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種聲腔、戲班繼續進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戲班和藝人劉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現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們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聲腔表演藝術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劇三大聲腔中襄陽、二簧兩種,至此之后云南戲曲文學得到逐步豐富,為“滇劇”的形成繁榮奠定基礎。可以說,每一種文化藝術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環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戲曲文學在發展過程中既有對外來戲曲藝術的接受也有對地方文化傳統的繼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戲曲文學就不能忽視對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體來說要關注對云南古代戲曲文學地域分類的調查與分析、關注對云南古代戲曲文學地域性特征分析、關注云南古代戲曲劇種的空間分布、關注外來文化對本地文化影響的地區、時間差異、關注對云南古代戲曲文學地域性特征的現代啟示的研究。
三是關注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擁有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這也是云南這一區域范圍內最為傳統、最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發展歷程中,正如民間的社火觀燈活動漸趨與云南民族民間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風俗融合而成為祭祀性的花燈歌舞活動并演出《瞎子觀燈》《包二回門》等劇目一樣,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間傳統祭祀儀式、節日禮儀、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與云南古代戲曲走向了融合。特別是在康熙道光年間,出現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語為之”、“靜夜華燈演苗戲”的白劇、苗劇等少數民族戲曲表演樣式;以“哎咿呀”腔流傳的壯劇;把《封神演義》譯成傣語演出的傣劇;從語言到音樂等都彝族化的彝劇花燈《打花鼓》等,標志著白劇、苗戲等少數民族戲曲的出現。到咸豐同治年間,更有張銘齋等在杜文秀帥府演出了《二進宮》《絕纓會》《取高平》,這三部劇在滇劇中分屬“胡琴”“襄陽”“絲弦”三個聲腔的劇目,這既說明滇劇聲腔的成熟,也說明云南民族文化與戲曲文學發展的結盟。我們始終堅信“民族藝術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為一種符號它表現了民族文化的內涵。因此,要了解每個民族的藝術,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戲曲文學發展與云南民族文化建設、旅游文化開發與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與出路,必須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戲曲文學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別是要加強對云南古代少數民族戲曲文學作品的分類與梳理、少數民族戲曲文學對主流文學的繼承與發展、少數民族戲曲文學作家的身份認同及創作研究、對云南古代戲曲文學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對云南古代戲曲文學民族性特征現代啟示的討論。
四是關注少數民族特色劇種劇目的研究。云南是一個多民族的邊疆省份,有漢、彝、白、拉祜、哈尼、壯、傣、納西、傈僳、佤、回、瑤、苗、藏等26個民族,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滇劇、傣劇、白劇、彝劇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劇種,它們和川劇、評劇、京劇等外來劇種共同構成了云南的戲曲系統。但各民族劇種的發展是不均衡的,造成這種不均衡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長期以來我們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學術界重視和研究程度不夠。另外,從現有劇目資料來看,不管是彝劇、云南壯劇,還是白劇、傣劇等都和中原戲曲劇目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我們缺少細致的分析和整理,對其繼承和發展關系的討論不甚了了。再次,我們在討論戲曲文學民族性時,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不夠,導致在翻譯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甚至舛誤。尤其是古代用少數民族文字創作的作品的翻譯整理工作,幾乎沒有突破和進展。
結語
云南是一個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與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聯系,不僅和漢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個東南亞、南亞文化都有關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從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資源,獲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贏得發展機遇。”[5]86云南戲曲文學作為云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匯聚了云貴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鮮明的邊疆色彩,探討云南戲曲文學的創作狀況、發展歷程,可以使其藝術、文化價值得到新的闡釋,從而揭示云南戲曲文學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揚民族文化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學景象與時代價值,通過對云南戲曲文學在民族認同、沖突、融合、互補中的現象梳理與分析,可以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啟迪民族和諧意識,促進云南地區社會的和諧穩定,為全球化背景下戲曲文學的發展尋找可資借鑒的理論材料與創作經驗。這對于云南增強競爭軟實力乃至其可持續發展以及“兩強一堡”發展戰略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意義。(本文作者:呂維洪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