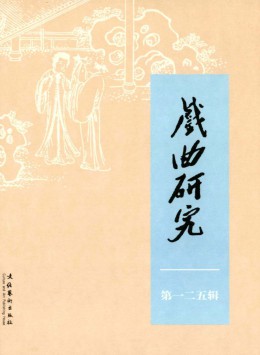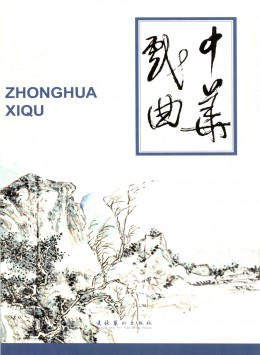王仁杰戲曲創作的劇種特點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王仁杰戲曲創作的劇種特點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鄭傳寅 單位:武漢大學藝術學系
地方劇種眾多是我國戲曲在形態上的特點與優勢。據我所知,世界劇壇之中,只有中國戲曲才擁有眾多地域特色鮮明的地方戲,其他國家的傳統戲劇雖然有的也受方言和地方音樂的影響———例如印度梵劇、朝鮮半島的唱劇和越南的嘲劇等,但并沒有形成劇種學意義上的地方戲。戲曲的這一特點不僅能滿足觀眾對文化多樣性的要求,強化戲曲對當地民眾的吸附力,也使得戲曲一直維持著“一體而萬殊”的龐大的生態系統,這種特殊的生態系統使古老的戲曲能夠保持此消彼長、生生不息的頑強生命力。這也正是世界上的古老戲劇大多已經消亡,而擁有幾百個地方劇種的戲曲卻能追隨時代前進,至今仍有百余個劇種活躍在舞臺上的重要原因。換言之,如果沒有“一體而萬殊”的眾多地方戲的存在,戲曲獨特的藝術魅力、抵抗時間殘酷淘洗不斷蛻變更新的頑強生命力都將遭受重創,戲曲有可能像世界上的其它古老戲劇一樣,早已消亡。
然而,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文化傳播與文化交融日漸深入,不同戲曲劇種間的借鑒學習自然展開,西方戲劇文化對戲曲的影響也不可避免,戲曲劇種“趨同”的問題也就日益嚴重,不同地方戲的地域性特征逐漸淡化,話劇化、歌劇化的傾向日漸凸顯,這已經是當代戲曲史的一個普遍現實。這種傾向固然與戲曲音樂創作拋棄“依字行腔”的傳統,忽視乃至輕視音樂的地域性元素,強調音樂創作的“主體性”,向京劇等大劇種和西洋歌劇“看齊”有關,也與文本創作中忽視方言元素,主要用“共同語”———漢語普通話語匯編寫劇本的創作思潮大有關系。現在大多數戲曲編劇是不同劇種“通吃”的———以漢語普通話語匯編寫劇本,以適應不同劇種的搬演。不同劇種在將這種具有“普適性”的劇本搬上舞臺時,用其方言語音唱念便變成了地方戲。然而,由于地方戲的地域特色不僅是靠音樂和方言語音所承載的,方言語匯和方言中的某些特殊的語法現象也是地域特色的重要載體,許多方言語匯以及某些特有的語法現象所承載的文化意蘊和美感是普通話語匯和語法所無法承載的。再者,普通話語匯未必都能在不同的方言中找到對應的語匯,因此,有時用方言唱念用普通話語匯寫成的劇作時,會顯得生硬別扭,有的還會造成對劇種規范的破壞。
例如,昆曲的用韻遵循的是《中原音韻》,而且保留南戲入聲單押的傳統,屬于近代音系的《中原音韻》與現代漢語普通話的音韻系統是很不相同的,①如果用漢語普通話寫昆曲劇本,再用蘇州官話唱念,還是會背離昆曲語言的音韻系統和格律規范,弱化昆曲的劇種特色。又如,南昆的丑角通常用蘇白,如果用漢語普通話語匯寫成臺詞,再讓丑角用蘇州方言念出來,那也不是真正的蘇白。可見,方言是地方戲的“根”,用不同的方言為不同的地方戲編寫劇本是保持劇種特色的重要保證和措施,否則,劇種的地域性特征就會逐漸淡化,最終會因“根”離“土”而導致地方戲的枯萎衰亡。
福建劇作家王仁杰長期致力于保護、發展家鄉的梨園戲,在戲曲文學領域做出了不俗的貢獻。王仁杰劇作的語言是當代戲曲文學的一個亮點,它不僅簡潔、準確、生動,而且富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能恪守不同劇種的音律規范,體現曲體文學的詩性之美,這在當代劇作家中是并不多見的。
用泉州方言寫梨園戲劇本
別具一格的梨園戲是我國戲曲文化寶庫中的珍貴遺產,從她身上我們得以窺見古代戲曲———特別是古老南戲的神韻風采。難懂的泉州方言和獨特的“泉腔”是梨園戲劇種特色的主要承載體,保護、發展梨園戲不能離開泉州方言和“泉腔”。
王仁杰堅持用家鄉泉州的方言為梨園戲編寫劇本,其多數劇本都是用泉州方言寫成的,這使得其劇本創作體現出濃重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時也彰顯了劇作家保護梨園戲劇種特色的自覺意識。例如,《董生與李氏》一劇就攬入了大量的泉州方言語匯。第二出《每日功課》梅香賓白:“人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到來各自飛,割吊什么愁腸呀!再一說,我家員外……那個老泡頭,死就死,眼睛還不愿閉,分明是買囑那個老古董,托他來監視我夫人!夫妻到這份上,有乜恩義?”①又如《皂吏與女賊》第一出《放簽》中的皂吏對白:“兄弟呀,近來可‘好面’否?說來相分聽一下。”“這人有錢,又大手面,好牌,至少自摸。”“不用打醒他的眠,等一下看他吃股。”②再如《陳仲子》第一出《辟兄離母》門子等人的對白:“二老爺今來了,臭死狗呀,看你吃‘閂槌’我才歡喜。”“老爺吩咐也是不去,緊去回話。”③除在賓白中使用方言之外,唱詞亦間用方言。例如《節婦吟》(新版)第三出《闔扉》中顏氏唱【二調•一封書】:“立地無顏,羞恥愧難言!乜溫存繾綣,頃刻化云煙?”④《節婦吟》(舊版)第六出《詰母》中顏氏唱【中滾】:“你衣錦還鄉,正該春風得意歸。為乜臉色蒼黃,愁悶鎖雙眉?為乜低頭,默默無一語?”⑤陸郊唱【中滾】:“說到先生,媽親為乜心慌忙?”⑥
王仁杰同時還寫有昆曲、京劇、閩劇、越劇劇本,這些不同劇種的戲曲劇本雖然也體現了作者駕馭語言的功力,大多準確、精練、生動,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詩性之美令人陶醉,但就運用方言而論,其不足顯而易見。例如,昆曲《琵琶行》,男女主人公倩娘和白居易均操中原“官話”,丑角江西茶商吳一郎和居于社會下層的艄公、艄婆也都與方言俗語無緣。這里試舉一例以明之。第二出《商別》,當倩娘為吳一郎彈唱一曲之后,吳一郎問:“適才所唱,乃何人何詩?”倩娘答曰:“詩名《寒閨夜》,乃左拾遺白居易所作。”吳一郎說:“未聞,未聞”,倩娘告知:“豈不聞,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其詩者?”艄婆補充說:“又豈不聞,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其詩者?”吳一郎說:“如此說來,竟與龍井、鐵觀音齊名。只是名字起得怪,人道長安居,大不易,他老人家竟能白居易,好不逍遙自在?那一句,通宵不滅燈,也未免太耗油了吧?”⑦這里看不到方言俗語,就連艄婆的賓白也是中原文人聲口,吳一郎的賓白雖然活現出其腹內草莽,渾身銅臭,但也并無方言俗語,大體上還是普通話語匯。越劇《柳永》也少見越地方言,大體使用普通話語匯。這與作者長期生活在泉州,很熟悉泉州乃至閩南方言,但不熟悉吳越方言或許有關。由此可見,如果不熟悉劇種所在地的方言,要想寫出有地域特點的賓白和唱詞并非易事。如果劇作家大多用漢語普通話寫劇本,我國地方戲劇種特色的保持也就要大打折扣。
堅持用方言寫戲曲劇本既是一個理性認知問題———認識到方言俗語關涉劇種特色和命運,有保護地方戲的自覺意識,同時又是一個能力問題———要用方言寫地方戲劇本首先得懂方言,不但能聽懂當地的方言,而且很熟悉當地的方言語匯,對其特殊的表現力和美感有深入的體驗,做方言俗語的有心人乃至研究者,會準確熟練地使用方言,否則,心有余而力不足,還是無法用方言編寫劇本的。現在,像王仁杰這樣懂方言俗語,能堅持用方言寫地方戲劇本的編劇不多,許多文學青年能操一口純正的“官腔”,卻不了解當地的方言俗語,甚至鄙薄方言俗語,以為方言俗語是落后的東西。因此,在戲曲文學創作———特別是地域特色鮮明的地方戲的劇本創作后繼乏人的今天,堅持用泉州方言寫梨園戲劇本的王仁杰也就顯得格外耀眼。
恪守音律規范
我國古代戲曲是以曲牌聯套體為主的,近代以來,板腔體戲曲取代了曲牌聯套體戲曲的地位,成為了戲曲的主要樣式,但曲牌體或大體是曲牌體的戲曲劇種仍然存在,例如,昆曲、川劇高腔、湘劇低牌子以及在明清俗曲基礎上形成的有些劇種大多都是曲牌體。梨園戲也屬于曲牌體。板腔體與曲牌體并存的劇壇格局對當代戲曲創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企圖以板腔體文本“通吃”各個劇種的做法顯然是行不通的,對當代戲曲的健康發展也是一種破壞和威脅。
編寫曲牌體戲曲劇本,需要懂得戲曲音律,用李漁《閑情偶寄》的話來說,就是要“凜遵曲譜,恪守詞韻”:曲譜者,填詞之粉本,猶婦人刺繡之花樣也。描一朵,刺一朵;畫一葉,繡一葉。拙者不可稍減,巧者亦不可略增。然花樣無定式,盡可日異月新;曲譜則愈舊愈佳,稍稍趨新,則以毫厘之差,而成千里之謬。情事新奇百出,文章變化無窮,總不出譜內刊成之定格。是束縛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譜是也;私厚詞人,而使有才得以獨展者,亦曲譜是也。使曲無定譜,亦可日異月新,則凡屬淹通文藝者,皆可填詞,何元人我輩之足重哉!“依樣畫葫蘆”一語,竟似為填詞而發。妙在依樣之中,別出好歹。①
曲牌體戲曲文本———主要是唱詞的創作需要按照曲牌的格律規范進行,而這些規范一是相當苛繁,二是與當代漢語普通話語音系統頗有距離,不要說當今的一般人難以熟練掌握,就是古代劇作家也是備感艱難的。李漁《閑情偶寄》曾言及,曲牌體劇作是一種“艱難文字”,寫曲牌體劇本比按照詩詞格律賦詩填詞都要困難得多,因為曲不但講究平仄諧協,對仗工穩,還要尋宮數調,而且平要分陰陽,仄要別上去,如果要形容曲牌聯套體劇本創作之苦,“擬之悲傷、疾痛、桎梏、幽囚諸逆境,殆有甚者。”②這并非夸大其詞。當今許多戲曲作家是不懂戲曲音律的,但卻有人在自己的劇作中標示曲牌,然而,將這些標有曲牌的作品繩之以曲律,我們會發現,這些劇作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標示有曲牌的唱詞幾乎完全不合律,這在新中國建立后的新編昆曲中相當普遍。臺灣有戲曲學者曾將這種“新編昆曲”斥之為“偽昆曲”,可謂一語中的。這些編劇并不是不想“凜遵曲譜,恪守詞韻”,完全按照昆曲音律來編寫劇本,而是力有不逮,因為不懂戲曲音律,無法按照曲譜編寫昆曲劇本。梨園戲是曲牌體戲曲,由于其屬于古老劇種,至今仍保留使用帶過曲、集曲的古老傳統,其曲牌體式與昆曲有較大差異,許多曲牌在明清以來所編撰的曲譜中是找不到的,編寫梨園戲、昆曲劇本不但要懂泉州方言和蘇州方言,而且必須懂得梨園戲、昆曲的曲韻、曲譜,否則,寫出來的劇本有可能是“偽梨園戲”或“偽昆曲”。王仁杰先生在這方面可謂行家里手,他熟悉梨園戲、昆曲的文本創作規范,大體上做到了合律依腔。這沒有深厚的功力,沒有古代曲學的深厚學養是辦不到的。這里試舉幾例。王仁杰的昆曲《琵琶行》頭出《潑酒》白居易唱【粉蝶兒】:春日啼鶯,出墻東數枝紅杏。趁韶光正好曲江行。殘冰消,泉脈動,有綠楊掩映。則見俺廄馬朝纓,卻依然野老心性。③南北曲均有【粉蝶兒】,均在中呂宮,但格律不同,此為【北中呂宮•粉蝶兒】。據康熙年間王奕清等所編《曲譜》、吳梅《南北詞簡譜》等曲譜所示,此曲句格、字格譜式大致如下:×——,│——、│——去,│——、×│——。│×—,—×│,×——去。×│——,│——、上——去。④王仁杰填寫的【粉蝶兒】全曲葉“庚青”韻,三個仄聲韻均葉去聲,僅“趁韶光正好曲江行”句多一襯字,“有綠楊掩映”句的“有”字,“則見俺廄馬朝纓”句中“則見俺”三字均為襯字。“卻依然野老心性”句“老”字當平而用了上聲字,“殘冰消,泉脈動”兩句對仗,但“殘”字當仄而用平。第四、五兩句有押韻的,但不為方家所取,王仁杰懂得其中三昧,“殘冰消,泉脈動”兩句依譜守對仗格但不用韻。
曲譜是曲家對前人創作經驗的總結,既有不容逾越的規范性,也有一定的靈活性,例如,被康熙間王奕清等所編《曲譜》收入譜中的李致遠的散套【粉蝶兒•歸去來兮】最后一句“消磨了浩然之氣”中的“浩”字當用上聲,但這里卻用了去聲。可見,在一首曲子中偶有平仄不合并非個別現象。由此可見,王仁杰是熟悉曲譜與曲韻的,他劇作中的唱詞在句格、字格、韻格、對仗格上都大體合律,能分別何為正字,何為襯字,于仄聲能分別上聲與去聲之不同用法,三個七字句的音步結構大體符合上三、下四的要求———如“出墻東、數枝紅杏”,“卻依然、野老心性”,雖然全曲未能做到“無一字不合律”,但現在能達到這個高度的戲曲作家已經不多。元代以來,漢語中的入聲字派入平、上、去三聲,平聲則分為陰平和陽平,但南方方言中仍保留有入聲,故以南方方言演唱的南曲仍有入聲單押的曲牌。梨園戲屬于南曲之遺,入聲單押之曲多有。王仁杰對此相當了解,其劇作中成功地譜寫了多首葉入聲韻的曲子。例如,《董生與李氏》一劇有多首曲子以入聲單押,其中第三出《登墻夜窺》董四畏唱【逐流水】過【杜韋娘】是篇幅最長的入聲單押的套曲:把你行徑,俺看了真切;西廂房,原是你風流穴。一對野鴛鴦,好歡悅。捉奸,正大好時節。(白)只是呀———(接唱)此豈書生為,我又何太絕?(白,略,唱【短潮】)我心郁結,更與何人說?煞費躊躇,此時有計計亦拙。(白,略,唱【杜韋娘】)我心也如鐵,顧不得四體不勤,管不得手裂腳折。學一個張君瑞,我意已決。這是一個套曲,韻腳字切、穴、悅、節、絕、結、說、拙、鐵、折、決均為“車遮”韻中的入聲字,可見作者既熟練地掌握了南曲入聲單押的規則,對《中原音韻》的韻部以及入聲字派入三聲的規律也是了解的。曲牌體屬于長短句,句式有長有短,而板腔體則是上下句結構的齊言———兩個七字句或兩個十字句構成一個樂句;曲牌體唱詞須嚴守句格、字格、平仄格、對仗格和韻格,板腔體大體押韻則可,幾乎無“律”可守;曲牌體屬于古代戲曲之遺,其用韻主要遵循“平分陰陽,入派三聲”的《中原音韻》,如果編寫屬于南戲系統的曲牌體戲曲劇本,還需要懂得入聲單押之理,板腔體押韻遵循與漢語普通話接近的“十三轍”即可;曲牌體戲曲須講究聯套,何曲在前,何曲續后,往往不可亂其“輩類”,而且不同劇種有不同的聯套規則,苛嚴程度也各不一樣,板腔體戲曲則沒有聯套的問題。由此可見,企圖用板腔體文本“通吃”所有地方戲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戲曲文學創作不僅要重視思想內容和人物塑造,同時還需要熟悉不同劇種不同的文本形式,否則,就無法寫出合格的劇本。王仁杰熟悉屬于曲牌體的梨園戲的音律規范,他撰寫的梨園戲劇本大多標示曲牌,而且能大體上按梨園戲聯套規則將不同曲牌的曲子組成套曲,字格、句格、韻格、對仗格大體符合梨園戲的音律規范。有的劇作雖未標示曲牌,但也是按照曲牌體填詞,唱詞為長短句,不同于板腔體劇作,便于按梨園戲的聲腔演唱,例如,梨園戲《楓林晚》《皂吏與女賊》都是如此。我國不少戲曲劇種都被列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包括許多珍貴戲曲劇種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已成全社會的共識,而且也成為了國家行動。然而,要保護這些珍貴遺產首先就得熟悉這些被保護的對象,而要深入了解這些被保護的對象就得具有古代文化知識。編寫新的梨園戲劇本,是對梨園戲進行“動態保護”的有力舉措,但如果當代劇作家不熟悉梨園戲的音律規范,新編梨園戲劇本時就不可能做到遵循其文本創作規范,這種新編劇目也就像拋棄劇種的舞臺表演程式一樣,起不了保護和發展梨園戲的作用,而只能是對梨園戲劇種特色和藝術傳統的背離,是對這份寶貴遺產的破壞。由此可見,保護和發展梨園戲僅憑熱情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一批像王仁杰這樣懂得戲曲音律的行家。大體遵守劇種的藝術規范,既是王仁杰劇作的藝術特色,也是其對當代戲曲的寶貴貢獻。
文化底蘊與詩性之美
李漁《閑情偶寄》認為,戲曲劇本主要不是寫給人閱讀的,而是演給人看的,因此,其語言“貴淺不貴深”,以能讓不讀書的婦人小兒、愚夫愚婦一聽就懂為上,用典過多,過分講究藻飾的戲曲語言是不可取的。但戲曲是對生活的詩性表現,不追求再現生活形態的逼真性,但講究傳神寫意,營造美的意境。這就要求戲曲語言———特別是唱詞既明白曉暢,又蘊涵豐富,具有詩性之美。這一要求與“貴淺顯”是不矛盾的。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如果劇作家對我國深厚的傳統文化沒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缺乏深厚的語言功力,就無法做到為人所稱道的“費盡鍛煉,出之自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字字在聲音律法之中,言言無資格拘攣之苦”———既明白自然,又蘊涵豐富,且具有形式之美。
近代以來,我國戲曲發生了從以文學為中心,到以表演為中心的“轉型”,文學修養深厚的大作家大多遠離戲曲創作,劇作家變成了為名演員搭建展示絕活之平臺的“秘書”和“侍從”,戲曲文學文壇地位日漸邊緣化,劇本的語言不僅不美而且不通的情況并非個別現象。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戲曲創作的文學品位有所提升,但戲曲語言缺乏文化底蘊和詩性之美的問題并沒有太大的改觀,許多戲曲劇本的語言形同“白開水”,蘊涵瘠薄,索然無味,在獲得過“文華劇作獎”的劇目中也不難發現語言不但不美,甚至不通的例證。①王仁杰的劇作在語言上取得了較高成就,這主要體現在其語言的文化底蘊和詩性之美上。這里先列舉一段唱詞來加以說明。梨園戲《董生與李氏》寫教私塾的秀才董四畏與被“監護”的故員外寡妻李氏的戀情,李氏雖然不是飽學才女,但也是有身份的夫人,她的唱詞崇情尚雅,耐人咀嚼。例如,第二出《每日功課》李氏唱【短相思】:巫山云散,霜雪折雁行。角枕淚痕濕,五更鐘鼓獨自傷。雖每墳前細細訴,又一語何曾到冥鄉?只落得滿目萋萋芳草,長隨個迂腐秀才郎。空對著斷梗飄絮,古道夕陽。
短短數行文字,準確細致地揭示了新寡李氏的苦悶與傷感,也透露出她漣漪初起不耐寂寞的隱秘的內心世界。就其語言而論,它恰到好處地處理了述事與抒情的關系,既明白如話,朗朗上口,又蘊涵豐富,意境渾成,具有鮮明的詩性品格。如果作者沒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對巫山云雨、霜天雁行、五更鐘鼓、萋萋芳草、斷梗飄絮、古道夕陽等具有豐富美感、鮮明時代特征和獨特民族個性的審美意象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平時沒有積累,是不可能寫出這樣底蘊深厚,令人回味無窮的唱詞來的。戲曲的賓白與話劇的臺詞有相似之處,它偏重于“述事”,但又與話劇臺詞有明顯區別———戲曲賓白雖然是散白,不像唱詞那樣講究意境營造,但也要求節奏化和韻律化,這種講究形式美的賓白與現實生活中的口語并不相同,古代戲曲劇作多有登場詩和下場詩,正是為了凸顯賓白的韻律化和節奏化,話劇臺詞則力圖接近口語。因此,曾有人用“無聲不歌,無動不舞”來形容戲曲舞臺上的唱念做打。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特點不僅是屬于舞臺表演的,文本創作———包括賓白亦當如此。這里容我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昆曲《桃花扇》第二出《傳歌》小旦扮演的老鴇李貞麗首先登場,唱一曲【秋夜月】之后有如下賓白:梨花似雪草如煙,春在秦淮兩岸邊;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妾身姓李,表字貞麗,煙花妙部,風月名班;生長舊院之中,迎送長橋之上,鉛華未謝,豐韻猶存。養成一個假女,溫柔纖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轉嬌羞,未入芙蓉之帳。這里有位罷職縣令,叫做楊龍友,乃鳳陽督撫馬士英的妹夫,原做光祿阮大鋮的盟弟,常到院中夸俺孩兒,要替他招客梳櫳。今日春光明媚,敢待好來也。①這段賓白主要承擔述事任務,而且出自下層人物之口,通俗易懂,然而它同樣具有韻律化和節奏化的特點,與現實生活中的口語有明顯區別。
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學修養———相當熟悉駢文,恐怕是很難寫出這樣精練、具有形式美的賓白的。王仁杰劇作的賓白大多精練準確,而且具有節奏化、韻律化的特點。這里試舉兩例。《董生與李氏》的第一出《臨終囑托》有兩個勾魂的小鬼登場,彌留之際的彭員外的鬼魂與兩個小鬼有精彩對話:小鬼甲(念)持牒出酆都,小鬼乙(念)勾魂不含糊。小鬼甲(念)閻王要你三更死,小鬼乙(念)誰人敢等四更鼓?……彭員外魂鬼哥且從容,吾尚有一法。小鬼甲、乙你有乜法?彭員外魂吾托一人監管。小鬼甲你上無父母叔伯,下無昆仲子侄,誰人替你監管?彭員外魂有秀才董四畏,蒙館為業,與吾為鄰。……王仁杰撰寫的《唐琬》第三出寫唐琬被迫改嫁趙士程,新婚之夜,士程揭開唐琬的蓋頭,唐琬不能忘情仍然深愛她的陸游,竟把士程當成陸游,有如下道白:務觀!我該不是良禽另擇棲身處?殘花敗柳竟高攀?不,不,我是無端被休棄,無奈另結緣。央媒自嫁,我負氣在后,你負心在前!務觀呀務觀,你雖自許上馬擊強胡,下馬草軍書,報國情懷,溢于筆端,卻呵護不了結發的妻,忍教她寄人籬下,紅葉飄單……陸務觀呀陸務觀,鑒湖臨別,你信誓旦旦,而今夜呀,你那畫堂香暖,杯酒言歡,是何等溫存,何等繾綣!全不忘菊枕枯萎,舊人忉怛。你……②
這兩段道白分別出自不同人物之口,能展露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語言的風格并不一樣,雖然在節奏化、韻律化的程度上與古代戲曲仍有距離,但都具有節奏化、韻律化的特點,與話劇臺詞和生活化的口語有別。如果作者沒有較深厚的文學修養,對戲曲賓白與話劇臺詞的區別不了解,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賓白的。有人批評現在的戲曲話劇加唱的色彩越來越強烈,其實這不只是舞臺呈現的問題,戲曲文本創作同樣存在這種弊端,王仁杰的劇作在語言上是盡力追求戲曲化的,這既表現在唱詞的撰寫上,也表現在賓白的撰寫上。在話劇加唱越來越普遍的今天,他的這種追求顯得尤為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