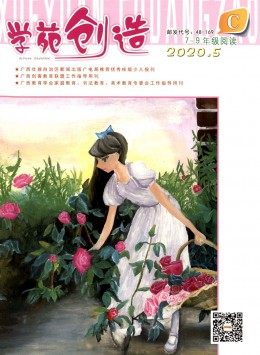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創(chuàng)造社諸君初赴日本的時間
基本集中于20世紀第一個十年,正是求知若渴的青年學子,資質聰穎,意氣風發(fā),甚至有些年少輕狂。又恰逢日本近代史上第二次民主思潮,以及由此而彰顯的時代新氣象,對天才的期許和崇尚、對個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謳歌、對人性的呼喚與伸張,這種開放的時代氛圍令來自封建傳統(tǒng)國度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滿心激蕩、心馳神往。正如郁達夫所描述的,“兩性解放的新時代,早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尤其是智識階層,學生群眾———里到來了。”置身在這樣的社會氛圍,創(chuàng)造社諸君也將目光投向男女戀愛、婚姻等兩性話題,再加上自身的性格和心態(tài),以兩性為主的創(chuàng)作占他們作品總量的大成。他們以大正時期的女性解放熱潮為背景和參照,讓他們所熟悉的中國女性成為作品的主角,批判的矛頭對準她們被壓抑的靈魂和被遮蔽的命運。在對光明和希冀的熱切渴望中,因時代、社會、個人等因素而難以調和的“靈肉分裂之苦惱”成為包括戲劇界在內的日本文壇頗感棘手的現(xiàn)實問題。日本惠特曼研究權威有島武郎就在《出生的煩惱》、《死及其前后》等作品中寫出靈肉分裂的深刻痛苦。這種矛盾糾結的苦惱情緒引起了創(chuàng)造社諸君的共鳴,他們在早期創(chuàng)作中也表現(xiàn)出“個人的靈活與肉體的斗爭”。
田漢在談論那一階段的創(chuàng)作時說:“無論創(chuàng)作劇,還是翻譯劇,都有一種共通的‘靈肉生活之苦惱’的情調。”《咖啡店之一夜》中的林澤奇,不知自己是“向靈的好,還是向肉的好”,他的生活“是一種東偏西倒的生活”,“靈-肉;肉-靈;成了這么一種搖擺狀態(tài),一刻子也安定不了”。《靈光》中的張德芬,也因婚姻問題上“靈肉的交戰(zhàn)”而感到難以擺脫的“煩悶”。同時,日本新劇在觀照人類情感命題的同時,還有很多題材直接源于日本民族的現(xiàn)實生活,精神上更契合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的創(chuàng)作,為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即如何將文學的藝術功能與社會功能結合起來。一向標榜藝術至上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婚戀題材之外也開始嘗試著用戲劇形式表現(xiàn)工農(nóng)大眾的生活狀態(tài),如田漢的《午飯之后》。還有一些作品,將戲劇的眼光投向下層民眾的苦痛和對社會黑暗的揭露上,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戲劇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能力。如郁達夫的《孤獨者的悲哀》、張資平的《軍用票》、成仿吾的《歡迎會》等。然而,日本文學畢竟是有別于中國的文學,因此,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接受日本戲劇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中國因素”的制約。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文學啟蒙是在中國本土完成,更在于中國文化在他們心理和情感塑造上所占有的“先機”。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審美情調的角度進行理解。日本新劇非常重視抒情,這種抒情不是郭沫若《女神》中撼天動地、響徹云霄的無節(jié)制的情感宣泄,而是承襲了日本“物哀”的美學精神。“物哀”是日本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和美學思想,講究“真情流露”,即情感主觀接觸外界事物時,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地產(chǎn)生的幽深玄靜的情感。“物哀”的美學傳統(tǒng)不僅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學,而且支配著日本民眾精神生活的諸多層面。創(chuàng)造社諸君敏感多情的心性、內在的藝術修養(yǎng)、以及中國漢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相通性,使得他們更容易領會“物哀”的美學精神,從而在創(chuàng)作中與之呼應,呈現(xiàn)出深沉淡泊的美學風格。
二、大正時期的日本文學界異常活躍
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個時期的文藝思潮和文學流派在這一時段集體涌入,對日本文壇造成極大的沖擊并呈現(xiàn)出活躍而紛繁的局面。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日本所受的影響,除了日本本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外,還有以日本為媒介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響。“日本在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比任何的國家都更為重要,它發(fā)揮了雙重的作用,既是啟蒙的導師,又是輸入西方文學的中間人。”這正是“日本機制”的第一重機制———環(huán)境機制之外,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中“日本機制”所發(fā)揮的第二重功能———中介機制,或稱媒介機制。自明治第二個十年之始,一股翻譯文學的風潮開始在日本文壇盛行,“在這個時期里,翻譯和介紹過來的有英國的莎士比亞、李頓、迪斯雷利和司各脫的作品,法國方面的有凡爾納、費爾隆、大仲馬和雨果,還有俄國的以虛無黨的活動為中心的虛無黨文學等等。”許多的日本作家和學者致力于翻譯的再創(chuàng)造過程。正是得益于這樣濃郁而開放的文化氛圍,不僅為創(chuàng)造社諸君打開了接觸西方文學的窗口,同時因日本文化界的推介,讓他們在西方文學的選擇上獲得某種導向性的引領作用。如他們所推崇的歌德、盧梭、尼采、惠特曼、泰戈爾、波特萊爾等,都是通過日本文壇的推介而進一步接觸的。這樣,創(chuàng)造社諸君通過日本這個窗口間接地向世界文學潮流靠攏。歷史劇是五四時期很受作者青睞的戲劇類型,創(chuàng)造社諸君中郭沫若和王獨清都有歷史劇存世。他們的歷史劇帶有鮮明的自我色彩,借“古事古詩”以表達個人對“今事今人”的思考。郭沫若在創(chuàng)作戲劇之前,曾閱讀莎士比亞、歌德、席勒、泰戈爾等人的作品。他將史劇分為兩類,“一種是把自己去替古人說話,如莎士比亞的史劇之類,還有一種是借古人來說自己的話,譬如歌德的《浮士德》之類。”并強調自己的史劇觀更多地來自歌德浪漫主義史劇觀的影響,目的是“借古人的皮毛說自己的話”,“借古人的骸骨來,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王昭君不再是歷史中那個被迫遠嫁的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悲情女子,而化身成一個封建斗士和理想女性。王獨清創(chuàng)作歷史劇的興趣也不僅限于歷史事實本身,他要“把這中間的主要人從那已死的形體中復活了起來,投以特殊的新鮮的生命”,“用我的清熱把生命的水力吹進它們的身中,使它們成為我的新的建筑的新的原料。”
楊貴妃不再是紅顏禍水的形象,而是以“甘為民族甘為自由犧牲的人物”。正是這種個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主觀感受,這種將個人抒發(fā)融于史劇創(chuàng)作的方法,形成了創(chuàng)造社史劇創(chuàng)作中反傳統(tǒng)的浪漫主義風格。在此還要提及的是創(chuàng)造社對“新浪漫主義”的美學追求。日本文論家廚川白村在《近代文學十講》中對新浪漫主義的源流、成因、特征的闡述,極大地影響了創(chuàng)造社諸君新浪漫主義文藝觀的形成。田漢在寫給郭沫若的信中談及自己是如何通過戲劇去體驗新浪漫主義的,“我看新羅曼主義的劇目從《沉鐘》起,至今羅登德蘭海因利希的印象還是活潑潑的留著,同時一股神秘的活力也從那時起在我的內部生命的川內流動著。”他將寫于1920年的《梵珴璘和薔薇》標注為“一部新浪漫主義的四幕悲劇”。陶晶孫自稱是“一直到底寫新羅曼主義作品者”。他的劇作《黑衣人》是用日文寫成的作品,后被譯成中文發(fā)表于《創(chuàng)造季刊》。劇中的“黑衣人”痛恨毫無公道可言的社會,手握武器,卻無所適從。社會在劇中被描繪成一個“無物之陣”,無論采用什么方法與之對抗,依然難逃宿命。“在這個很短的劇本里,他描寫孤獨,寂寞,恐怖和瘋狂,描寫在特殊時候的凄涼和失望的,而仍然含著神秘的美麗的向往的心情是值得贊賞的。里面的情調,非常緊張而且靜默,而從這緊張與靜默中傳出美和理想和現(xiàn)實底幻滅。”他的另一劇作《尼庵》則表現(xiàn)的是人物在夢境與現(xiàn)實沖突中的迷惘與覺醒。兄長苦勸萬念俱灰的妹妹,妹妹雖然聽從兄長的勸告從尼庵中走出,卻不愿再入塵世的紛擾,“寧肯進第二的尼庵”———湖水之中。兩部劇作都是以新浪漫主義手法造就,劇作手法之新穎,反映之深刻,無不映射出作者的藝術積累,以及對所學創(chuàng)作手法的自覺運用。確認地說,創(chuàng)造社諸君接受的西方文化,是經(jīng)由日本“過濾”或“中轉”后的西方文化,不論這個過程中存在怎樣的轉換過程,其實現(xiàn)的重要途徑正得益于“翻譯”的手段。許多的日本名家,佐藤春夫、谷崎潤一郎、森歐外等在創(chuàng)作之余都極為重視對以西方文學為主的外國文學的翻譯和推介。創(chuàng)造社諸君目睹了日本文壇對西方文藝的積極譯介從而對本國文壇所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和促進作用,也開始重視“翻譯”的功效,身體力行地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他們通過“日本之橋”完成了離開第一文化語境(母語文化語境)后,思想觀念和文學修養(yǎng)在第二文化語境中的二次積淀和儲備,郭沫若就曾翻譯過歌德的重要詩篇、小說及戲劇。田漢也“目睹了日本話劇家接受外來話劇樣式的經(jīng)歷和艱辛”,非常重視譯介在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促進和啟發(fā)作用,他出版翻譯劇本15部、改編外國劇本原著5部,還發(fā)表外國文學評論50余篇。
三、外界因素可以承擔觸動和啟發(fā)的功能
但自我精神的內在訴求卻是無法被替代的。深刻的人生體驗,是文化環(huán)境、藝術交流這些外因所不能悉數(shù)詮釋的。只有從這樣的角度,或許才有可能將創(chuàng)造社諸君進行獨立精神創(chuàng)造的過程給予生動描繪。正如王富仁對文化互動的一種描述那樣,“文化經(jīng)過中國近、現(xiàn)、當代知識分子的頭腦之后不是像經(jīng)過傳送帶傳送過來的一堆煤一樣沒有發(fā)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只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chuàng)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chuàng)造物。”筆者在此討論的正是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中“日本機制”的第三重———體驗機制。這一機制也可以概括為“留學體驗”或“海外體驗”。這是一種“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生存、發(fā)展、成就以及歷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的留居他國學習的經(jīng)歷,以及這種經(jīng)歷經(jīng)過學人個體特殊的精神轉化后所形成的,對現(xiàn)代作家人生道路和創(chuàng)作領域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一種支援意識和背景因素。”創(chuàng)造社諸君的留學體驗是以出生國(中國)為基礎的內在知識、思維、情感,以某一個外在機緣(留學)為契機,通過另一個文化語境(日本)重新選擇、整合、塑造的精神活動過程,而這個新的文化語境正是現(xiàn)代生活、現(xiàn)代思維、現(xiàn)代文化的一個新的傳播地和創(chuàng)造地。初涉異域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出國前大多生活在封閉保守的鄉(xiāng)鎮(zhèn),受教的是傳統(tǒng)儒家文化,來到日本后他們的內心無疑受到一股與既有思想體系全然不同的心靈沖擊。“他們的文章和見解,難免受到留學所在地時髦的思想或偏見所感染。”日本社會的都市化刺激了他們年輕敏銳的神經(jīng),他們流露出對現(xiàn)代都市、物質主義的認同和傾心,看時報、泡溫泉、觀電影、談戀愛,甚至去酒坊買樂。郁達夫、田漢等人就對作為“日本的風俗漸漸歐化的象征”的咖啡館充滿了想象,暗香疏影的咖啡館成為他們早期創(chuàng)作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空間設定。如田漢的劇作《咖啡館之一夜》就是“以咖啡情調為背景,寫由頹廢向奮斗之曙光。”這樣的精神體驗已經(jīng)不僅僅是生存空間的變更或者延伸所能簡單解釋的,而是“從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西方的轉換中所產(chǎn)生的雙重或多重情感空間、價值空間、審美空間的對立轉化、矛盾發(fā)展或者自我超越。”內心所經(jīng)歷的復雜的心理體驗和精神活動,就不可避免地讓從“老中國”走出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時刻處于一種時空變換所造成的比對中。他們直面日本社會的資本主義化,社會風尚開放、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再反觀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中國,新文化運動落入低谷、新文化陣營已然分化,以及身為被侵略國子民所受的屈辱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行動所造成的民族自尊心的極大傷害。因而,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日本機制”下的創(chuàng)作心理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充滿了矛盾的復雜性。其實,日本文化和文學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遠在創(chuàng)造社之前。“創(chuàng)造新文學之一人”的梁啟超在晚清文學改良運動中提出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就是蒙受日本留學經(jīng)歷的啟示。新文化運動的指導者中,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皆是20世紀初期的赴日留學生。
他們在日本所受到的思想啟迪直接影響了他們回國后所引領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思潮。啟蒙思想、自由平等思想、“人的思考”的時代意識、國民創(chuàng)造精神,在日本社會中備受推崇的新興思想如星星之火,在同時代的廣大青年學子間燎原。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赴日前后都與這些新興觀念擦碰出思想的火花。郭沫若在早期歷史劇《三個叛逆的女性》中,遵循批判的精神擊打封建綱常倫理的腐朽枷鎖,提出女子“三不從”的“新性道德”。郁達夫感嘆“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fā)見,以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xiàn)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特別是日本的國民創(chuàng)造精神,既與新文學所弘揚的“創(chuàng)造”精神一致,也與郭沫若所言“脫胎換骨地獨立自主地開始創(chuàng)造”的主張契合,是創(chuàng)造社同人集結的思想基石,更是創(chuàng)造社結社的根本精神。另一個原因則在于,“戲劇藝術本身的實踐性決定了中國的戲劇家不可能‘置身世外’作純文字的陶醉,藝術的實踐過程必然讓他們更多地‘進入’到日本當下的生存狀態(tài)。與他們頻繁交往的編導、演員與觀眾都是具體的人,頻繁而廣泛的人際交往令他們深入地體察到了生存與心靈的細微意義,對于當下生存與人類(觀眾)精神需要的準確把握才是戲劇藝術成功的保證,這一切都構成了留日中國戲劇家重要的戲劇資源,較之于小說家的純文學吸取,為日本戲劇資源包裹的中國戲劇家有了更為深刻的生存體驗。”這正是創(chuàng)造社諸君異域———故國雙重體驗的真實寫照。他們把“人的解放”作了富有個性色彩的張揚與渲染,顯示了獨特的文化心態(tài)。他們所擴張的自我,不再只是擺脫了身心枷鎖的“個體的人”,而是要讓這“個體的人”充滿主觀戰(zhàn)斗的激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在日留學期間被日本國內高漲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所感染,也開始自覺地將個體體驗和對國家、民族的思考緊密結合,不再囿于自己狹小的天地和多愁的心緒。有學者曾將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描述為“青年文學”,“代表了中國現(xiàn)代的青年文化和青年文學的獨立形態(tài)的形成。”創(chuàng)造社諸君無疑是20世紀初期青年群體中的幸運兒,他們的青年文學夢孕育且受哺于兩個不同的國度———中國賜予他們最寶貴的生命和情感的最初積累,日本賦予他們更全面的文化養(yǎng)分、更豐厚的生命體驗和他們結社之始就無比崇尚的先鋒精神與創(chuàng)造使命。文學創(chuàng)作是一個復雜的精神活動過程,是無法僅靠理論的鋪陳或概念的移植就可以“制造”出爐的,而是創(chuàng)作主體發(fā)自內心深處的體驗與表。
作者:譚蘇 單位:湖北民族學院 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