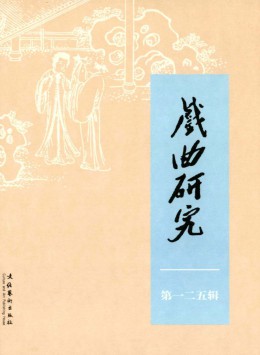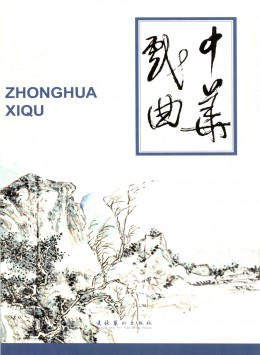戲曲服飾論文:漢樂舞服對戲曲服飾的作用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戲曲服飾論文:漢樂舞服對戲曲服飾的作用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張灝 單位:天津科技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廣義上講,樂舞服應該包括祭祀禮儀服飾、宮廷女樂舞服以及各種民間樂舞服的形式。“古代有巫必有舞”①,因此樂舞服的前身應該都是起源于巫術禮儀所用的舞衣,其長而及地的外形,飄灑遠去的衣袖,是舞服的基本形制,然而處于蒙昧時期的華夏民族的巫術舞蹈服飾,與后世宮廷乃至民間樂舞的舞服尚有著本質的區別。作為巫術舞蹈的服飾,都是模仿想象中神靈的模樣而創造的,因而也被稱為神衣。人在舞蹈的禮儀活動中,戴上象征著神的模樣的假面,穿上神衣,配上代表神意的飾物,通過身體的巨大運動而進入忘我的癲狂狀態,似乎就可以掙脫凡間的困擾,與神靈相通。“利用象征物與被象征物之間的某種類似或心理對應,使被象征物的某一內容得到含蓄而形象的表現”,②反映了中國古人在原始巫術時期豐富的文化心理活動,而這些象征物的使用也注定具有了一定的規范和宗教含意,代表著神的意志和形象的服飾符號明顯地具有著功利的目的,神衣的功利性因此獲得。
華梅在她的《人類服飾文化學》中曾精辟地指出:“服飾是巫術中最能強化神性的物質實物。”③可見神衣的功用對于巫禮的作用之重要。因此,神衣不僅要能承擔將人與世俗隔絕的裝扮作用,而且還要具有與神靈同等的圣潔與威嚴,這就要求神衣的設計需要呈現一種能給人心靈以震撼的特殊形式,這種形式雖源于生活,但又是生活中服飾形象的夸張和抽離,具有人神共通的特點。迄今為止能見到的最早的神衣形象的記載,是河南信陽出土的戰國時期楚墓中錦瑟瑟首漆畫所描繪的楚巫形象。從漆畫巫者扭動的纖纖腰肢,我們可以判定巫師的性別應為女性。巫師雙臂張開,似振臂疾呼,顯現出寬大而收口的衣袖,系帶的腰肢,衣長至足踝,與當時楚國盛行的深衣形制大致相同,只是神衣的袖袂更加寬肥下垂,隨著夸張的動作翩翩起舞,巫師頭上插羽毛,手中執法器,法器形式夸張,隨舞飛揚,與寬肥的衣袖相呼應,顯現出神的法力與威嚴。河北磁縣出土的東漢末年茹茹公主墓中一彩繪陶俑,也描繪了一正在做法式的巫師形象,舞者著紅色圓領廣袖曳地長袍,戴紅氈帽,左手執鋸齒法器,是北方薩滿巫師的典型形象。由于道教及讖緯學說在漢代的盛行,漢代的巫術之風比秦時更是有增無減,神衣的形制也得到了發展,神衣開始從帝王的祭壇蔓延到民間,成為民間儺舞的重要裝扮。遺憾的是,漢出土文物中關于漢代神衣的視覺資料并不多見,但據史料記載,漢代神衣的形制、色彩、配飾等大多是以模仿動物和神靈的形狀來設計的。“擬獸舞”的舞蹈形象在許多史籍中都可見到,如古樂府詩中就有“鳥獸倉倉”,“鳳凰來儀”,“擊石附石,百獸率舞”的記載,其中,“鳳鳥”、“百獸”,就是人們以鳥羽、獸皮作舞服的形象記錄,這種習俗后來形成了民間儺舞的藝術形式被保留下來,至今還在我國的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流傳。
漢代儺舞的舞服常采用紅黑兩色,具有明顯的漢文化的象征性。據王充在《論衡•訂鬼》中的記載:“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可見,紅色是驅鬼辟斜之用的。在卜千秋墓壁畫上的方相氏的面具也是紅色的,百二十帳子也一律“丹首玄制”,執事也是“披朱發,穿紅衣”,雖然它們不是穿神衣的巫師,但從他們驅邪避鬼的裝束上,我們不難推斷當時儺舞服的色彩也一定時以紅為主的。而黑色在巫術禮儀中更帶有蕭殺的意味,以惡克惡、以鬼制鬼是我們祖先通神辟邪、威懾驅疫的慣用思維,用儺舞舞服的假面、假形和驅邪的色彩,營造一種與邪惡殊死搏斗的激烈場景,在人神難辨的癲狂中獲得驅走惡魔的勝利感,這便是神衣乃至儺舞服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和意義。
漢代“角抵戲”中的《鳳舞》是借鑒巫舞而創作的一種儺舞形式,其舞服的設計明顯保留了神衣的形式特征。《鳳舞》又名《梧桐引鳳舞》,舞者將鳳鳥的假形道具穿戴系扎在身上,裝扮成鳳鳥的模樣,模擬鳳鳥的動作進行舞蹈,以表現吉祥如意、欣欣向榮的生活景象。山東沂南出土的漢畫像石就為我們清晰地展現了角抵戲中這種鳳舞的舞服形象,舞服用絲織物制成,身上羽紋清晰,雙翼后展,鳳尾用長長的彩帶裝飾,如鳳鳥飛騰的樣子,鳳頭上插滿了花飾,高高翹起,昂首挺胸,口中含有一條綬帶,隨著舞蹈動作向后飄起,鳳鳥的頭、尾、翼、羽、紋已經樣樣齊全,只露出一雙穿著彩褲的雙腳,隨引鳳人的引領而舞蹈。引鳳人戴假面,高鼻、大眼,頭戴軟腳幞頭,身穿荷葉領彩衣,腰間系帶,帶下垂流蘇,手執梧桐枝,鳳鳥隨梧桐枝翩翩起舞。這種鳳舞的舞服形象,是漢代儺戲舞服的典型代表,它既具有神衣的神靈意味,又兼具了世俗化的審美情趣,是從神衣到民間樂舞服很好的過渡形式。
從神壇走向民間的漢樂舞服,保留了亦神亦人的文化情結,把現實中的人以修長的袍身和寬肥的大袖進行裝扮,成為舞臺上供人觀摩和效仿的樣板。其修長的袍身、寬博的大袖、濃重的色彩,華麗的裝飾以及著裝者擬神擬鳥的形態和動作,都含有人類生活最本真的理想追求,承載著更多對宇宙上天的告問,對生靈骨肉的神思與遐想,而正是這種理想,也成為后世戲曲服飾的審美源頭。武官衣以及蟒服中被抽象化了的龍首、蟒爪、麒麟、獅尾等紋樣,都是來自現實,卻又超越現實的神的形象的化身,武生的靠衣及其夸張的雉雞翎更是意欲將人的形象加以神化的審美表達,是樂舞服中對神獸形象的理想追求的現實延伸,這種延伸使得后世在民間得以廣泛流傳的戲曲服飾,也一直沒能脫離其被神化的人物形象特征,而具有了來自生活卻又超越生活的審美初衷。
女樂舞服的抒情意境是戲曲服飾的審美升華
《說文解字》說:“‘巫’者,女能事無形。”可見,巫術和舞蹈,自古就是女性獨有的身體活動,因此,舞服也自然是以女性為穿著對象的服飾形式。漢代宮廷樂舞因此也被稱為“女樂”,“女樂”并從宮廷逐漸走向了民間,其服飾的典型形象是細腰曲折,衣長而曳地,袖長則問天,女性形象陰柔秀美、曼妙多姿,舞蹈的審美情趣遠遠勝于其社會象征意味,舞服的藝術內涵也遠遠超越了其禮儀的社會功用,樂舞服真正進入了人類的審美視野。
長袖舞是中國傳統樂舞的典型,因服飾中長袖的獨特形態而得名,《韓非子•五蠹》中有“長袖善舞”的說法,洛陽金村韓墓出土的戰國玉雕舞女及湖南長沙出土的戰國彩繪漆上的《教舞圖》中的舞女,都明顯表現出以袖為主的舞蹈形式,足見長袖舞的由來已久。然而漢代宮廷君王對長袖舞的獨特愛好,使長袖舞真正確立了它在舞蹈中的地位。漢代“女樂”舞蹈舞服的袖身更加加長,舞動的幅度因而也被增大,長袖在舞蹈中的作用明顯被加強,出現了著名的《長袖舞》、《對舞》和《盤古舞》,等專門以長袖為特點的完整的舞蹈形式,舞服的形態也因此大為發揚,在漢時期紡織印染工藝的技術支持下,樂舞服由春秋戰國時厚重的麻質材料演變為輕柔的絲質品,色彩也變得飽和鮮艷、柔美曼妙,同時因為裁剪技術的進步,出現了纏繞式、層疊式、搭接式等多種造型形態,舞姿因而不再受造型的限制,更加的大膽舒展,富有動感。這種長袖舞衣在漢代的畫像石磚上留下了大量的記載。如河南南陽出土畫像石中就清晰地記錄了長袖舞女的服飾和舞蹈形象,舞者下身著褲,雙腳跨開,頗似巫者動作的熱烈,其雙臂盡量展開,揮動著長袖,袖身窄而長,被拋至身后,線形飛舞,顯現出舞者的力度和熱烈的情感;廣州東郊出土的東漢彩繪舞蹈俑以及揚州“妾莫書”漢墓出土的玉雕舞人,都有一雙長長的舞袖,舞袖或飛過頭頂,或轉至身后,都明顯顯露了從手臂處開始加長的痕跡,足見漢代舞蹈的長袖動作是勝于漢前的。從各種出土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漢代長袖舞的形式大多是以兩人對舞為主,舞者服飾形制相差無幾,只是服飾的色彩或冠飾等稍有差別,兩雙長袖在空中對舞,更能產生相互纏繞、盤卷、抑揚頓挫的空間感,在一逗一和的交流中產生中國舞蹈獨有的身體語言特征。除此之外,漢代也有多人完成的群舞形式,這樣的舞蹈形式大多是為渲染環境氣氛而創作的,一般會用于大型慶典活動中,如漢末晉初時宮廷就曾流行一種被稱為《恒舞》的集體舞蹈,舞者數千人,頭戴倒龍玉佩、鳳凰金釵,衣袖綿長,相互挽接起來,形成一個圓形的陣列,繞著堂上的楹柱晝夜而舞,連綿不斷。④可見無論何種形式的舞蹈場面,長袖總是漢代舞蹈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長袖舞幾乎就是漢代女樂舞蹈的代名詞。因此長袖舞在漢代是十分風靡的,它不僅是漢代宮廷專業藝妓的專長,而且在漢代的命婦宮人之中,也多有善舞的能手,這進一步促進了長袖舞服這一典型樂舞服形式的風靡。
中國古代服飾裁剪的平面化,使得衣服的肩袖部位一體相連,沒有分界。因此,中國古代服裝中單獨的袖體,實際是指從小臂開始,長于手,又反屈至肘的部分,稱為“袂”。而長袖則是在袂之外再接上一段由白色絹綢接續的袖子,平時可呈疊排在手腕處,稱為延袖、假袖、或義袖,舞時按照動作需要甩出,以創造舞的觀感,所謂手舞足蹈,大概就是源于此。長袖舞蹈有甩袖、拋袖、翻袖、翹袖等許多種舞的動作,長袖拋向空中,舞畫出各種幻妙的空間造型,袖子拋起的高度、速度、角度、形態也表現出舞者的技術與情感,由于絲織絹綢的輕柔曼妙,拋出的袖形如游龍般在空中飛舞,似行云流水般上下翻飛,創造出以空寫實的獨特的藝術觀感。漢賦中對這種獨特的長袖舞多有記載。如張衡在他的《觀舞賦》中就寫道:“推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修袖以醫面兮,展清聲而長歌。”⑤左思在他的《蜀者賦》中也寫道了長袖之舞的景象:“起西者于促柱,紓長袖而舞。”長袖成了舞者抒發情感、渲染氣氛的重要手段,長袖舞成了中國傳統舞蹈的典型形式,造就了中國舞蹈的特質,并影響到后來的中國戲曲舞蹈形式的發展。
長袖舞的要旨是“振飛縠以舞長袖,裊細腰以務楊柳”,與長袖相匹配的是舞者纖細的腰身,因此,舞服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細腰結帶。戰國時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詩句,因為楚王有細腰之好,就連臣子們也都三飯為節,儐嬪女子更是競相效仿,這種習俗直到漢代一直被沿用和推崇,并滲透到女子的舞服中,成為漢代舞服的另一個重要特點。細腰的追求加長了舞者的身材,突出了肢體扭動的視覺表現,同時也加強了身體的輕靈,使飛舞的長袖與扭動的細腰相呼應,形成千姿百態的韻律美與婀娜曼妙的輕柔之美,因此又有“楚舞細腰掌中輕,纖腰舞飛春楊柳”的說法。
在《趙飛燕別傳》中,記錄了漢代著名舞姬趙飛燕“腰骨尤纖細,善踽步引,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的舞蹈形象,描述了她腰身纖細柔軟的舞姿與輕靈的體態。這種惹人愛憐的女性形象也一度成為漢代女性的榜樣,被紛紛效仿,細腰、長袖、衣長及地成為一時的服飾風尚。為了突出這種腰肢的嫵媚,配合長袖的舞蹈造型,漢代宮廷女樂中還推出了一種名為“折腰舞”的舞蹈動作,“折腰”的意思是指舞者在舞蹈時通過袖的甩動和腰肢的彎曲,使胸、腰、臂成前后向或左右向成“三道彎”,極盡優雅柔美的姿態,這種舞姿在漢代樂舞百戲畫像石中可以得到確實的印證。這種曾經在漢代盛行一時的舞步形式,充分展現了長袖與細腰的完美組合。《西京雜記》中也記載了劉邦寵姬戚夫人“善翹袖折腰之舞,長袖飄舉,儀態萬千”的曼妙身姿,這種自上而下的推動,更能見出折腰舞步在漢代時的流行之盛。在“折腰舞”中,曳地長裙覆蓋了舞者的雙腳,觀者看不到舞蹈者雙足的蹈動,如“足不在體下”,卻只看到靈活扭動的纖細腰肢,像是腰肢在帶動足下舞蹈一樣,這種忽略下體及足部的舞蹈形態,更能突出地表現舞蹈者袖身及腰部扭動的上體的動態,以更加突出女性的優柔婀娜之美。如北京郭公莊大葆臺西漢墓出土的玉雕舞人,就表現了這種長袖折腰的舞蹈形態。舞服衣裾曳地,行走時向后拖起,腰身高束,拉長了下體與上身之間的比例,舞蹈時扭動腰肢,上身左傾,下身右斜,兩臂一揚起一叉腰,恰到好處地維持了身體的平衡,揚起的臂膀長袖拋過腦后,飄至身后的裙裾處,叉腰的長袖則下垂曳地,與裙裾相接,并向上卷起,由于裙裾拖地,遮蓋了雙腳,使觀者感覺不到足部的蹈動,只感到腰身的扭曲帶動了舞步徐徐前行,優美婀娜的體態在這種舞步中淋漓盡現。這種“翹袖折腰舞”一方面表現了漢代舞蹈的獨特特點,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漢代舞服形態的獨特韻味。
為了突出女性題材的輕柔曼妙之美,漢代樂舞服在服飾形制的極度夸張之外,面料的輕薄柔軟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素紗禪衣,輕如煙霧,薄如蟬翼,就是漢舞服材料輕薄柔軟的最佳實物考證。漢末時,白紵麻織品在吳越一帶的長足發展,使本為吳地民間舞蹈形式的白紵舞很快就發展為宮廷樂舞,創作了直接以面料命名的《白紵舞》。《樂府詩集》中對這種新穎的樂舞形式及舞服形象作了專門的描述:質如輕云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余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清歌徐舞降抵神,回座歡樂胡可陳。⑥
如詩中所描繪,白紵舞舞服質料輕薄,色澤潔白,形制為長袍,光亮、滑爽、飄逸,襯托著曼妙輕歌,翩翩起舞,其輕盈飄逸如神如夢,清新柔美如仙如幻,表現出白紵舞服的輕柔質感,后世流傳著“輕軀徐起何洋洋“,“仙仙徐動何盈盈”,“體如輕風動流波”,“妙聲屢唱體輕飛,流津染面散芳菲”等許多有關白紵舞的詩句。白紵舞雖最初源于民間,但后來進入宮廷之后,更多地成為宮廷夜宴樂舞之用,服飾越來越奢華富麗,白紵舞服也從單純的白色衣身,發展為以翡翠腰帶,珍珠軟靴和玉瑤、釵環等首飾為佩飾的豐富樣式,曳地舞服修長輕薄,充分顯現出舞者的曼妙身姿,起舞時袍裾遮蓋雙腳,形成“似留又行”,“似退若止”的纖纖動態,疾行時身輕如燕,流動自然,止步時飄搖似仙,儀態萬千,面料的滑爽飄逸借助舞蹈動作的收與放充分表現了舞服的抒情意境。這一舞服形式最終脫胎為戲曲服飾中的花旦、青衣的服飾樣式,白紵舞的舞蹈動作也被沿用到戲曲中,形成碎步、滑步、水袖功等年輕女性角色專用的戲曲舞蹈動作。
白紵舞在舞袍之外還配有一條長巾,“制以為袍余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巾的質料與衣身相同,它進一步延展了舞袖的功能意義,在抒發情感、渲染氣氛方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舞袍的飄蕩與舞巾的拂撣交相成趣,共同營造出一種空靈、飄逸的藝術氛圍。許多漢代的畫像石磚中都記錄了這種舞巾或舞綢的舞蹈形象,說明巾的形式確在漢舞服中存在,這種形式影響了后來敦煌壁畫中飛天舞女的服飾形象,啟發產生了飛天舞服中狹長而盤卷的錦帶,如舞巾和長袖在漢舞服中的重要作用一樣,錦帶也成為敦煌飛天舞服中的重要內容,創造出飛天舞蹈的獨特特征,那就是充滿升仙和飛天幻想的裝飾韻味與飛動之美。而這種服飾形象就是今天許多戲種中的嫦娥形象的化身,長巾則化身為世俗人間活生生的個體悲憫生命,指問蒼天的戲曲舞蹈的道具。
樂舞服“質樸”與“生動”的雙重
境界是戲曲服飾審美的最高境界漢代樂舞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是被稱為“大禮”的祭祀舞蹈,天子都會親自“冕而摠干”,率而舞之,可見其地位在漢代之重要,另一種則是供宮廷貴族享樂之用的女樂樂舞,這兩種樂舞形式也都在民間有所發展,成為當時并存的兩種音樂舞蹈形式。由于功用、場合的不同,兩種活動中人物服飾形象所呈現出來的審美境界也截然不同,前者以“質樸”為追求,后者則以“生動”為追求,而兩種審美特征并存,也成為漢代樂舞服的一大特點。古人認為神靈和祖先都是質樸的,“祭祀之美,齊齊皇皇”。⑦“皇”即“往”,意思是心所系往,因此“祭祀之美”在于舞者的誠懇恭敬,心系鬼神,以樸素之質裝扮身體,就是接近鬼神心靈的手段之一。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古人平時是以帶有黼黻紋樣的華美裝飾為美的,在祭祀時卻要用又粗又稀的疏布覆蓋鼎俎籩豆,這是對人類紡織的原始的追溯……,如同美味的大羹并不加任何佐料調和,只追求它原本的味道;美麗的大圭并不雕琢多少花紋,卻美在其質樸天然的本色;就連祭祀所乘的車輛,也是簡單素樸,不加任何裝飾,這都是以質樸為尊,以無裝飾為貴的例證。由此可見,古人在祭祀時,所用的物品包括服飾,都是以質樸為上的。漢代祭祀舞服幾乎完全承襲了這一特征,表現出漢代帝王貴族尚未脫離對神靈的頂禮膜拜的意識形態特征。漢代劉安在《淮南子》中對此作過如下描述:“湯……乃使人積薪,剪發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燃,即降雨。”可見,周朝祭祀“質樸為尊”的習俗,在漢代是仍然被延用和尊崇的。
這種剔出形式的繁雜華麗,才能達到精神的真摯與深邃的文化心理,是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代表之一。其源頭應該追溯到老子的“光而不耀”的審美思想,老子曾提出過:“圣人為腹不為目”,“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圣人,光而不耀”,⑨都是說,真正的美不在于形式的華麗,而在于實質的內容,追求事物本身的、自然的質的內容,才是大美所在。漢代劉安繼續延用了老子的這種美學思想,再次提出“白玉不琢,美珠不文”的觀點,王充也在此基礎上大加發展,指出:“論貴是而不務華”,“養實者不育華”⑩,把老子的以“拙”為美的“真”的境界發展為以“實”為美,這里的“實”雖已明顯帶有實用的功用性,但也仍然不失真誠、自然之意,不失重視事物的質,并把這種質再次與自然連接在一起,崇尚質之樸的境界,漢代的祭祀舞服就尊承了這樣的境界,其服飾形制以兩塊方形的大布縫合而成,面料多為粗質的麻織品,著色單調素雅,不施粉彩,冷靜時以本白色素面裹身,熱烈時便以代表了華夏民族全部文化內容的黑和紅來表達,以示質樸尊實之道。
這樣的審美境界與祭者的生活心跡實質上是相仿的。那些王者貴族在歌舞升平、奢華享盡的世俗生活中,幾乎完全忘卻了生命的所來與所往,只有在祭壇上,身著與神靈相仿的舞服,才能暫時地擺脫世俗的纏繞與紛擾,重歸心靈的凈土。因此,形式的華美一定要在此時摒棄,精神之外的物質存在除了要達到與生命、天地、神靈自然的統一,別無可留,因此對原始的追溯、對自然形態的尊崇,對剔出了裝飾的最簡單樸素的質的形態的保留,才是祭祀物品與服飾的最高追求,這種追求無疑是向著內心的“空”和“淡”接近而行的。精神的虛空,“淡乎其無味”的心靈體驗,超出了眼前具體的審美對象的感官形式,使心靈直達宇宙的本體與生命,最終達到的是“道”的境界,這種質樸的境界直接影響了后世戲曲中多種人物的服飾形象,如老生角的藍衫、八卦衣、法衣,以及青衣角的罪衣、僧衣等,以單純的藍、黑或者灰為主色調,配飾白色的須髯、腰帶、短巾等,色與彩完全被抽離,剩下的是絕對空絕無彩的心靈世界,它不攜帶任何感官的刺激,是一種內心充盈著虔誠與莊重的質樸、空淡之美,成為中國戲曲服飾最高審美境界之一。
與之相對,漢樂舞服中的女樂舞服,則以其舒朗自由的造型、夸張的舞袖,傳達出的另一種生動鮮活的藝術境界,創造了中國戲曲服飾又一個審美高潮。舞袖是連接在樂舞服的袂口之外的一段長形的袖子,它就像畫家在紙帛上揮灑筆墨的畫筆,是舞蹈者在舞臺空間抒發情感的工具,善用長袖在空間的揮舞來寫意傳情,是漢代樂舞服的突出特征之一,這一特征被很好地沿用到了后世的戲曲服飾中,造就了傳統戲曲中許多濃重抒情人物的獨特藝術形象,利用長袖的飛舞代替肢體與語言,來訴說難以言狀的情感,成為中國戲曲的一大特點。長袖拋出時身體前傾,柔軟飄動的衣襟、袍身也隨著飛舞的長袖向前飄蕩,似乎要飛向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無邊的境界,這境界溝通著觀者的心靈,長袖拋甩的速度、方向和力量可以使人暫時突破衣袖的有形之度,而沖向一個無限飄遠的自由境界;長袖回旋,掠過頭頂,拋起又落下,在空中創造的是一個有形但無界的立體空間,這個空間到底有多大,我們無從想象,但在這抽象的線的一拋一收中,似乎可以擺脫這現實空間的經驗范圍,探刺到宇宙的冥渺幽微中去;袖與袖之間盤卷糾纏,如急風暴雨,是與現實磨難糾葛爭斗的生命能量的爆發;長袖垂落,猛然下甩,是無法征服現實存在的情感的憤然;長袖緊貼衣襟,空癟無力,長垂及地,則是生命無奈的悲切掃落。人物的語言與情感全表現在這兩條長長的舞袖之中了,其造型手法簡單抽象為了一條線,通過線的收放、頓挫、疾澀、虛實、抑揚,來與人的情感心靈接通,通化出更加無限浩渺的心中世界,讓人在舞蹈和舞蹈的觀看中忘卻了服飾本身的形式,只隨著衣袖運動的節奏、旋律,進入心靈的時空隧道。對故去往事的隨想,隨著衣袖的展開娓娓道來,時間的限制被突破了,對生命情感的領悟在這隨想中獲得,空間的構成與突破交替而來,與時間的流動渾然一體,觀者與舞者都在線的飛舞中與時間和空間一起優游。那帶有著生命內涵的袖線被凈化了,凈化為了藝術表達最簡單的形式,因此,樂舞服的長袖常常為最純潔的白色,雖然漢代服飾很講究文采刺繡,但唯獨“假袖”的袖面上不帶任何裝飾,它柔軟飄逸,呼之欲出,沒有重量,沒有體積,沒有色彩,把自身的形式占有退化到了極致,它只代表了一個符號,一種痕跡,是創化和書寫生命韻律的工具,這工具是樂舞服獨有的,現在又成為戲曲服飾的獨特道具。這樣的服飾形式是何等的生動,直通人的內心。袖線的飛動賦予舞者以生命和情感,舞服實際上已超越一般服飾的靜止性審美方法,而進入一種動感的、充滿生命張力的狀態,因其與舞蹈藝術的不可分割而達到了更加觀念化、哲學化的境地,而這種審美境界所連接的正是莊子所說的要沖破生命的局限,以“秋毫之末”,見到天下之大,以現實來勘透時空的審美境界⑨。莊子的這種時空透視觀雖然最初帶有對生命局限的悲哀情緒,但最終卻在生命無限擴張的體驗中,獲得了充滿激情與喜悅的生的力量,這與中國戲曲形象中充滿愁情困苦但又不甘命運羈絆的人物形象正相吻合,正應合了如嫦娥、竇娥、蘇三等這些為現實所冤,驚魂不屈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需求。發源于漢樂舞服的舞袖形式所創化的無形空間,常常因為人物故事內容的豐富而營造出一個綿延不斷、令人無限遐思的世界,它就如中國畫的“留白”,古琴的“無聲”,將人的心靈帶入最原初、最純粹的境界中,令人反省和沉思,悲憫生命、追問現實,因而產生巨大的審美效應與魅力,也賦予中國戲曲服飾以最高的審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