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民族化發展歷程淺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小提琴民族化發展歷程淺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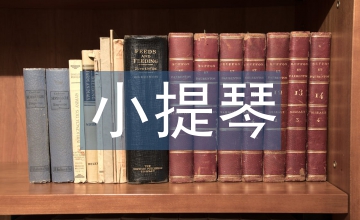
[摘要]小提琴本身具有極強的西方審美情趣,自傳入中國后,諸多方面都深受本土傳統音樂文化的熏陶與影響,眾多中國作曲家及小提琴家以傳統音樂為基礎,創編了許多凸顯民族特色的小提琴作品,以此將該樂器的民族化表現力極大提升,同時也為小提琴藝術在中國的發展開辟了全新道路。基于此,本文主要對小提琴民族化意義及其發展歷程全面闡述,并以此對中國小提琴民族化表現進行分析。
[關鍵詞]小提琴;民族化;歷程及表現
近年來,眾多知名音樂家堅持致力于民族化音樂的推廣,這是中國音樂人民族化意識的集體覺醒,在音樂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只有牢牢把握住民族音樂特色,才能使中國音樂在世界爭得更廣闊的天地。小提琴雖然為西洋樂器,但不可避免的受到具有極其深厚歷史積淀的中國民族文化影響,彼此逐漸融會貫通,催生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小提琴作品和創作技法。對中國小提琴藝術民族化的探索,促進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精髓,符合民族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與必然趨勢,理應成為每位中國音樂人的重要使命。
一、中國小提琴民族化重要意義
(一)推動中國的小提琴普及
小提琴其外形與音色都十分出眾與獨特,承載著西方審美藝術,在這一特點下導致該樂器引進后較長時間內都只是在教堂和學校中進行傳播,而基層大眾對于該項藝術則一直處于審美領域絕緣的發展狀態。所以,各作曲家為打破該現狀不斷嘗試著對小提琴創作加以改進,隨著長時間創新,民族化的創作路徑逐步成為小提琴在中國發展的主流基調。創作初期藝術家對小提琴這一西洋樂器的表現形式進行挖掘,其目的是使該樂器表演形式與內容能夠與中國本土審美相符,而在經過多番摸索、嘗試后小提琴在中國的認可度逐漸提高。隨著李四光《行路難》、冼星海《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馬思聰《搖籃曲》等音樂作品的誕生,開辟了民族化小提琴作品創作的先河,使小提琴樂器真正的走向了民族化創作道路,同時這一改變迅速吸引了眾多基層群眾關注,并推動小提琴在中國音樂血脈中真正融入。之后在音樂家的反復改進、探索與詮釋下,小提琴樂器及其曲目中的民族化細節更為深化,同時其演奏形式、風格也更貼近群眾情感及生活,也有更多中國人對小提琴所蘊含的藝術魅力領悟得更加深刻。
(二)將中國美學向世界展示
中國小提琴所作出的民族化改變,在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了自身的特色,促使小提琴在國內成為關注度極高的音樂藝術,并備受世界矚目。一方面,小提琴民族化使西方音樂在演奏形式與技巧上都有一定改變與創新。另一方面,具有濃厚中國民族特色的音樂題材不斷融入小提琴作品中。這些變化打破了西方對中華音樂審美及文化的詮釋,正因民族化創新后的小提琴將西方藝術音律和中國民族神韻兩者同時兼具,所以才能夠促使其真正的帶著民族特色走向世界,并獲得極高認可度,對世界音樂產生重要影響。1923年,美籍奧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克萊斯勒訪問中國時,演奏了他自己創作的《中國花鼓》,令人耳目一新,轟動一時。這首作品雖然是西方作曲家創作,但將中國風體現得淋漓盡致,鑼鼓喧天的熱鬧場景在小提琴的演繹下活靈活現。作品的旋律采用了中國傳統的五聲調式,利用切分音、顫音等創作技法準確地將花鼓元素展現出來,這首作品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音樂的喜愛與尊重,也象征著中國和世界音樂的有效結合,并為世界各民族了解中國音樂提供了絕佳平臺[1]。隨著時代的發展,這部作品并未退出音樂舞臺,反而呈現出更強的生命表現力及藝術感染力,在中外小提琴音樂界都處于經典地位,至今仍是國內外音樂會首選中國風作品之一,所贏得的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喜愛,更是使世界各地億萬聽眾為之傾倒。
(三)拓展中國民族音樂之路
當前世界各領域及行業發展皆十分迅速,音樂創作也同樣如此,信息時代下新的音樂藝術風格層出不窮,較為傳統的民族音樂皆面臨著被取代的發展危機。因此,民族音樂如何能在該背景下取得突破、穩住地位,已成為眾多民族音樂藝術家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2]。中國有很多民族音樂自衍生出現至今已經過百年或千年歷史,但因缺乏深入研究,忽視創新和推廣,導致社會大眾在審美上產生疲勞感和距離感。以戲曲為例,因其在表現形式以及唱詞曲調上都一直保持傳統,從而導致大部分青年人對于該類藝術作品無過多的欣賞熱情,這會使該藝術的傳播與發展被極大削弱。小提琴藝術民族化正是由此情況而生,在某層面上講,中國小提琴藝術民族化解救了傳統音樂的消亡命運。作為全新音樂表現形式,小提琴于民眾來講極具吸引力,所以用西洋樂器對傳統民族音樂進行重新編創與演繹,不僅使傳統民族音樂有更為新穎的改變,同時也為受眾群體帶來不同的視聽效果,這一創新使群體思維中的傳統音樂形式被革新,以古典音樂手法為依托,利用民族音樂元素進行創作,與新時代群眾藝術審美需求相符。
二、中國小提琴民族化發展歷程
作為西洋樂器,小提琴的產生與發展都植根于西方文化語境,要想小提琴能夠在中國的土地上萌根發芽,就需要在發展的過程中與民族文化互相滲透,并逐漸與中國觀眾的審美相適應。回顧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
1949年以前小提琴在中國的起步始于清朝康熙年間,傳教士將小提琴帶入中國。真正得到傳播和發展是在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小提琴藝術不再由西方殖民者把控,有了第一批小提琴留學生,學成之后相繼回國,他們是中國小提琴藝術發展的先鋒者,為小提琴表演、教學、創作、制作等方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1919年11月,正在巴黎留學的李四光先生創作了《行路難》,成為國內第一首具有中國特色的小提琴作品,同時也促使小提琴民族化創作步入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迎來了小提琴音樂創作的第一個高峰,誕生了一批優秀的小提琴音樂家,如馬思聰、冼星海、桑桐等,他們將西方作曲技巧與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進行結合,創作的作品體裁多樣,技法豐富,其中的一部分至今仍是藝術性最強、水平最高的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為小提琴的民族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3]。
(二)第二階段
1949—1966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政府對音樂文化事業的發展給予了一定重視,自1953年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由國家相關部門直接領導后,又在一些重要城市建立一批音樂專業院校,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為中國小提琴藝術的普及和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所有的小提琴曲目皆呈現出超高創新性,首先在素材汲取范圍上實現了進一步拓展,從廣東地方音樂逐漸擴大到了南北民歌,特別是對中國各少數民族地區獨有樂種的采集與吸收,從而使小提琴民族化創作素材更為豐富。表現形式上,除常見性獨奏演繹外,也同時衍生出齊奏和重奏的演奏形式。演奏手法實現了對二胡、古箏、琵琶等民族樂器的模仿,比如與西方音樂風格相差較大的滑音、弓法以及裝飾音等,該類技巧使小提琴在民族化發展過程中逐漸衍生出屬于中國小提琴藝術的全新特點[4]。這一階段創作的代表性作品,是1958年由何占豪、陳鋼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至今依舊可視為中西方音樂結合的完美典范,其所帶來的視覺與聽覺感觸都極為震撼。陳、何二人通過對民族藝術的不斷挖掘,并憑借自身對小提琴的理解及專業才華,將二胡演奏中較為常見的滑指、琵琶演奏中的掃弦等技巧在該作品中靈活運用,以此促使小提琴演奏的藝術感染力更為動人。此外,在中國越劇、京劇等表演中常用的倒板、囂板等手法,也被其首次應用,從而使整個音樂作品中國民族特色更為鮮明,尤其是表現形式上,民族化特征十足,由此小提琴民族化飛躍第一次實現。
(三)第三階段
1966—1976年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一時期小提琴的發展無疑受到了重大打擊。令人感動的是,音樂家們即使面對如此惡劣的社會環境,依舊沒有放棄對小提琴作品的創作。總體而言,這一時期小提琴民族化發展呈現出了如下特點:一是基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國內一些音樂家不得不選擇出國“避難”,或者停止作品創作;二是由于當時江青喜愛西洋樂器,因其個人喜好給西洋樂器在國內的發展帶來了翻身的機會,《紅燈記》的誕生改變了小提琴、鋼琴等西洋樂器在國內的發展環境。這一歷史發展階段中,創作成績最為顯著的音樂家是陳鋼,其主要作品有《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干》《金色的爐臺》《苗嶺的早晨》等。最后,基于“文革”的影響,不僅獨立作品產量少,且大部分作品呈現出了較為明顯的政治色彩,時代印記濃郁。
(四)第四階段改革開放以后
自此階段開始,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為小提琴的發展帶來了全新機遇,小提琴隨之進入了多元化發展時期。在創作上,將西方小提琴創作技巧嫻熟的與我國傳統音樂理論相融合,并在現代表現技法上大膽探索,在充分展現小提琴中國文化特色的同時,更加追求鮮明的個性。同時在取材方面,不僅對民族樂曲進行了改編,還將中國傳統戲曲文化進行了創作與融入,充分彰顯民族文化內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楊寶智《廣陵散》、韓鐵華《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宗江與何東《鹿回頭傳奇》等。
三、中國小提琴民族化具體表現
從發展本質上分析,中國小提琴的民族化創新本身則屬于中西方音樂兩大不同藝術體系的深入融合過程,其中融合階段必然會有各種多元化、復雜化特點出現,其主要在以下幾個層面體現。
(一)小提琴創作題材民族化
作品題材屬于音樂藝術形成及其不斷發展的基礎所在,同時更是小提琴這一藝術能夠充分實現民族化發展的關鍵性重要因素。中國經歷了近五千年發展周期,其中所能夠運用的音樂元素及歷史文化眾多,如此則可作為支撐小提琴民族化創新的動力源泉,也正是因其為小提琴曲目創作提供多樣的文化素材,方使得具有民族特征的中國小提琴作品不斷涌現[5]。中國經典的小提琴作品多是以民族民間音樂為基礎進行編創,如民族器樂曲調以及傳統地方戲等。例如,1937年由馬思聰創作的《內蒙組曲》,全曲共三個樂章,分別采用《跑馬溜溜的山上》《城墻上跑馬》和《虹彩妹妹》的音調進行創作,通過對節奏、調式、演奏技巧等方面展開處理,將濃郁的民族氣質與高超的專業技巧完美結合。此外,《紅軍哥哥回來了》《漁舟唱晚》《紅麥子》《喜相逢》《春節序曲》等經典小提琴作品,皆立足于中國民族音樂題材上進行創編加工而形成,這一類作品不僅將中國文化充分弘揚,同時也在小提琴與傳統音樂融合時注入了全新藝術元素,使整個作品更具有藝術價值和民族價值。
(二)小提琴作品風格民族化
所謂作品風格,通常指小提琴作品所體現的典型性代表特征,對世界音樂歷史整體發展進程進行回憶即可發現,不同國家民族音樂皆具備其自身風格特征,而該風格特征正是源自于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背景、經濟狀態、宗教習俗和所處地理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中國音樂存在時間較長,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韻味,音樂形態上多以單旋律線條態勢呈現與發展,與小提琴單旋律的線性思維有著較為復雜化的聯系,正因如此,中國民族音樂在歷經長時間的發展和沉淀后,配上小提琴歌唱性與抒情性的表現特征,才使得兩者的融合將民族音樂風格韻味表達得更為精準。以《牧歌》為例,該作品是沙漢昆于1953年進行改編的,以同名內蒙古民歌為基礎進行創作,主題主要以G宮調為主,裝飾音、泛音等技法與五聲性旋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舒緩的節奏使音樂更加優美,全曲展現了濃郁的草原氣息。除單旋律特征之外,節奏方面中國傳統音樂多采用散板,為小提琴民族化創作提供更多的發揮空間。例如《漁舟唱晚》,以古曲《歸去來》為素材發展而成,樂曲形象地描繪了夕陽西下,漁夫滿載而歸的喜悅情景。該作品引子部分由兩個寬廣的樂句組成,利用散板的方式進行演奏,細致地刻畫出水天一色的風光、愉悅開朗的心情。通過音樂家的努力,小提琴藝術真正實現了在不影響藝術美感這一前提條件下,將旋律、節奏、調式等音樂元素注入中國文化,從而使群眾僅是傾聽即可對其風格進行分辨,由此中國小提琴在世界音樂領域影響力也有所提升。
(三)小提琴演奏技巧民族化
作為小提琴表演中的重要構成部分,演奏技巧也是其民族化體現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在演奏技術上應注意中西結合,通過小提琴演奏使民族音樂風格完美呈現,并將其民族性全面彰顯。小提琴演奏技巧民族化主要在四個方面體現:第一,音響與力度,中國傳統音樂所講究的是“中正平和”,中國傳統音樂常表現出空靈悠遠的意境,小提琴由此對傳統民族樂器的音響和演奏力度加以借鑒,可呈現出弱奏及泛音等音效。第二,節拍速度變化,西方樂曲中所注重的是穩定、均衡的節拍演奏速度,但相比之下中國樂器更常見于以散板的方式進行表現,這一習慣更符合中國群眾的審美。因此演奏者對散板的演奏方式加以探索和應用,不僅可以使小提琴演奏中的民族特色更為明顯,同時也可進一步提高小提琴演奏水平。第三,滑音與裝飾音,滑音本是民族拉弦樂器的重要技巧之一,移植到小提琴上拓展了其表現手段,在風格、韻味、情感等方面極大增強了民族化色彩。西方小提琴音樂雖然也有裝飾音,但在創作技法和演奏要求上有嚴格規定,在中國小提琴音樂中,裝飾音更像是一種即興演奏的狀態,自由隨性,且重音的位置與西方要求截然不同。第四、五度手型,西方小提琴音樂以四度手型為主,中國作品由于五聲調式的特征,演奏中常運用到五度的伸張手型。
四、結論
綜上所述,盡管小提琴屬于西方藝術,但是在對其進行中國民族化發展之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績。所以,中國小提琴藝術想要進一步發展,更需要把民族化發展作為根本方向,用西洋樂器講好中國故事,在繼承以往成功經驗的同時,探索出更加具有“中國風”的發展之路。
注釋:
[1]李昊坤.中國小提琴演奏的民族特色研究[J].參花(下),2021(07):140—141.
[2]梁寒琰.中國小提琴音樂民族化創作題材研究[J].藝術教育,2021(04):86—89.
[3]孫婷婷.小提琴藝術中國化的歷程及其啟示[J].閩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3):118—120.
[4]遲源.小提琴民族化發展路徑分析[J].劇作家,2020(04):130.
[5]侯曉春.當代小提琴藝術民族化發展的回顧與展望[J].藝術品鑒,2020(03):348—349.
作者:符沁瑜 單位:上饒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