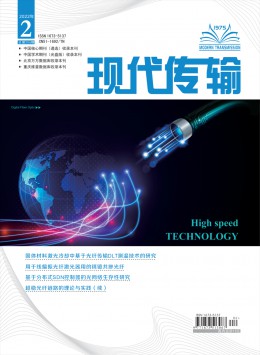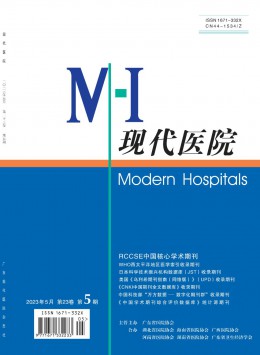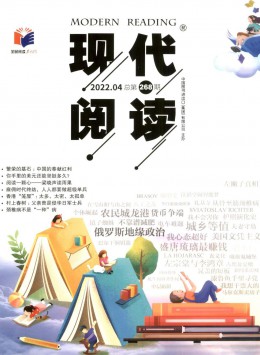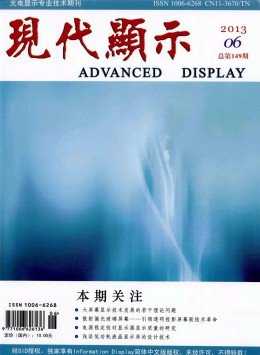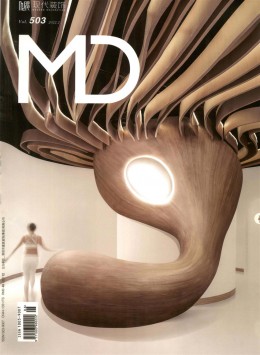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技術(shù)單向性倫理觀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技術(shù)單向性倫理觀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1.文學(xué)作品的生態(tài)倫理教育功能
人類對文學(xué)內(nèi)在含義的研究在不斷變化,人類的文本研究經(jīng)歷了不同的范式轉(zhuǎn)換,對文學(xué)作品審視的角度也一直處在不斷重新界定的不確定狀態(tài)。這種范式的轉(zhuǎn)化和不確定性,為從新的角度來研究文學(xué)發(fā)展提供了來自自身的動力。生態(tài)危機的信號使我們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重新審視文學(xué)作品,進行文化批判,解釋生態(tài)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并力圖尋找一種臨界點的反動。在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和生態(tài)危機嚴重惡化的當今時代,現(xiàn)代生態(tài)倫理研究者認為,現(xiàn)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基本都可以歸因為一個破碎的世界觀:我們?nèi)狈σ粋€統(tǒng)一的觀點,這使我們的世界變成了支離破碎的,斷代缺層的和被異化了的世界。因此,他們主張,現(xiàn)在所需的是某種系統(tǒng)理論的定向,這種理論提供給我們一些方法,讓我們?nèi)ビ^察和感覺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已經(jīng)被編織進了一個單一的模式和命運之網(wǎng)中。然而打破這種思維定式的網(wǎng)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僅僅依仗生態(tài)倫理學(xué)的傳播,也依賴多種學(xué)科共同努力來改變這種斷裂和異化了生態(tài)倫理觀的狀態(tài)。格倫•洛夫在《重新評價自然:走向一種生態(tài)學(xué)文學(xué)批評》中曾經(jīng)這樣聲言,“當今文學(xué)的最重要功能是將人類意識重新指引向?qū)ψ约涸谧匀唤缰械奈恢玫某浞终J識。”洛夫所主張的“文學(xué)功能生態(tài)化”彰顯了文學(xué)在生態(tài)倫理意識普及方面的教育功能。當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變的時候,文學(xué)作品中折射的社會背景具有“物理向度”和“心靈向度”雙重功能,其生態(tài)訴求也比較明顯。在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人類對科技的控制欲不斷膨脹的歷史背景下,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中也呈現(xiàn)了多重的科技態(tài)度,很多作家表現(xiàn)出了對技術(shù)發(fā)展的擔(dān)憂。
2.《寂靜的春天》對現(xiàn)代技術(shù)的批判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寂靜的春天》并不是一部文學(xué)作品,而是一部以文學(xué)特有的細膩筆觸來寫作的生態(tài)科學(xué)報告。該書以科學(xué)事實為基礎(chǔ),以科學(xué)家的視角和邏輯嚴謹?shù)恼Z言,表達了地球共同體的概念,要求尊重生態(tài)共同體本來的面目,反對破壞環(huán)境的行徑。荷蘭科學(xué)家貝爾金形容說,人類在自然界中的行為就像碩大的大象闖入擺滿了一碰即碎的瓷器店,這恰恰是卡森在書中描寫的人類使用殺蟲劑等時候造成的對自然界的影響:由于廣泛使用“2,4-D”除草劑去控制闊葉草,野草已成為對谷類和大豆產(chǎn)量的一種威脅;控制豚草進行地毯式噴灑的結(jié)果是豚草更多了。人類狂妄的使用科學(xué)手段來完成自己的任務(wù),“也許我們尚不了解其他的一些植物正在起著對土壤有用的作用,可是我們過去殘忍的將它們根除”[1]。這是因為人類忽略了一個完整生態(tài)系統(tǒng)內(nèi)自發(fā)的種群控制能力、濫施人類的干預(yù)而造成的,正確利用自然自我平衡的力量而不是化學(xué)試劑,能夠達到萬物和諧的目的。但是短視的人們不愿意使用這種天然的除害方法,相反,大量的化學(xué)殺蟲劑進入了自然循環(huán)系統(tǒng),卡森以確鑿的證據(jù),闡明了這些化學(xué)試劑對生態(tài)圈的破壞:噴灑——人類、家禽、野生動物中毒——河流——降雨——土壤,通過自然的循環(huán)作用,殺蟲劑進入了自然界各個環(huán)節(jié)。“褐色長尾鶇鳥、燕八哥、野百靈鳥、白頭翁和雉都消失了。一場細雨后,可以看到很多死去的蚯蚓,可能知更鳥就是吃了這些有毒的蚯蚓,降雨在毒物的邪惡作用下,進入了鳥類的生活,因而變成了一種毀滅性的藥劑了”,類似這種的描述貫穿于《寂靜的春天》的始末。《寂靜的春天》成為環(huán)境保護運動中的圣經(jīng),因為越發(fā)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使很多人相信,“我們關(guān)注宇宙中自然奇觀和客觀事物的焦點越清晰,我們破壞它們的嘗試就越少。”
3.愛德華•艾比與“生態(tài)性故意破壞”
愛德華•艾比(EdwardAbbey,1927—1989)是美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充滿爭議性的一個作家,被冠以“自然主義寫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名號,這是對他寫作風(fēng)格最有代表性的總結(jié)。艾比的代表作《有意破壞幫》于1975年出版,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反響,奠定了他在美國生態(tài)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小說以現(xiàn)實為基礎(chǔ),揭示了為促進美國西部大開發(fā)而投資數(shù)億美元的巨型水壩(格蘭峽谷大壩)建成后,對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的不可修復(fù)的損害。小說的主人公海都克(GeorgeWashingtonHayduke)在越南戰(zhàn)場上作戰(zhàn)兩年,回國后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已經(jīng)面目全非了,工地、垃圾、推土機、沙漠、毒氣、巨型水壩將河流截斷。他和他三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有意破壞的方式阻止人們破壞生態(tài)平衡,目的是讓自然保持原色,他們毀掉代表人類強制力的推土機,割斷電纜,炸斷橋梁,甚至要用炸藥炸毀耗資7.5億美元的大壩。他們這種近似瘋狂的行動顯然是破壞社會秩序、違背法律的,有很多評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生態(tài)原教旨主義,為保持生態(tài)原貌而不擇手段。這本小說創(chuàng)造了“生態(tài)性有意破壞”的概念。所謂“生態(tài)性有意破壞”,是指環(huán)保者為了保護自然環(huán)境而摧毀破壞自然環(huán)境的工具等的運動。生態(tài)性有意破壞的前提是用暴力摧毀機器和設(shè)備的同時,不造成任何人身傷害。面對主人公海都克為首的四人組為“讓自然保持原樣”而進行的“生態(tài)性有意破壞”活動,輿論一片嘩然,贊成者是一個陣營,而反對者亦比比皆是。當從立法或者政策保障方面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時候,若文明方式的抵抗也無法解決問題,《有意破壞幫》中的粗暴解決方式就成為民眾解決矛盾的方式的一種嘗試。小說的主人公海都克試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打破技術(shù)作為“強求”的屬性。海德格爾曾經(jīng)提出過,如果強行向自然界提出不屬于自然界本來屬性的要求,這種強求會嚴重侵害事物存在的特征;在這種嚴重侵害中,事物被迫放棄它本真的存在,海都克和他的伙伴們想恢復(fù)自然被人異化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堤壩所代表的技術(shù)已經(jīng)成為一種框架,為了謀求人類的最大利益,水壩、水渠工程代表的技術(shù)手段,已經(jīng)蒙蔽了人類的眼睛。
4.《瑪拉與丹恩歷險記》與科技放逐
作為見證了兩個世紀文明發(fā)展的女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Lessing,1910—2013),其百年生涯中見證了人類發(fā)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運動過程,并將與環(huán)境相關(guān)的主題帶入自己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瑪拉與丹恩歷險記》在開頭營造了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被摧毀的自然環(huán)境背景,北半球被冰雪覆蓋,南半球被沙暴席卷,而人類能居住的低緯度地區(qū)的大地則到處是干涸的景象。馬拉和丹恩姐弟兩人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了險象環(huán)生的自然環(huán)境和生存危機的挑戰(zhàn)。惡人、巨龍、蝎子的攻擊總是伴隨著險惡的自然環(huán)境,挑戰(zhàn)了姐弟二人的人性和忍耐。萊辛通過瑪拉的語言闡明這樣的道理,如果要獲得救贖,人類的意識必須要上升到和平、環(huán)保的高度:“每一座展館的展品都是各色武器。而恰恰是這些武器結(jié)束了前度文明,這樣看來,即使沒有冰川時代的到來,文明還是要結(jié)束的,戰(zhàn)爭就是其中的一種手段。”人類的暴行表現(xiàn)為無度的使用武器,也表現(xiàn)在無度的摧殘自然。萊辛通過描寫大象的尸骨,警告人類破壞自然的結(jié)局:“干旱持續(xù)的太久了,所以這些巨象死了,如果干旱再繼續(xù),人類也要滅亡了。”姐弟兩人最終到達綠洲,生活在一個綠色生機的世界中,馬拉說:“我再也不帶這些武器了,我再也不想看到刀子、匕首和武器了。”萊辛的故事情節(jié)安排是充滿了深層次含義的,當瑪拉達到了這種思想境界的時候,圍繞她的環(huán)境變成了“到處都是藍色,藍藍的大海和明媚的天空。藍天中漂浮著大片的白云”。[4]《瑪拉與丹恩歷險記》中的矛盾關(guān)系如果上升到生態(tài)倫理學(xué)的角度來分析的話,明顯呈現(xiàn)出深層生態(tài)學(xué)的生態(tài)倫理思考的特質(zhì):將人從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心的神壇上趕走,用一種整體和非人類中心的看法來對待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萊辛在對《瑪拉與丹恩歷險記》的記者訪談中說過,“人生就是一場旅行”,在這場本我、自我和超我交織的旅行中,萊辛完成了她的生態(tài)倫理思想傾訴:如果破壞了環(huán)境,人類挑戰(zhàn)的就是自己的生存。只有將人類利益與自然利益結(jié)合起來的時候,人類才有真正的生存。
5.《羚羊與秧雞》與技術(shù)異化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的小說《羚羊與秧雞》(OryxandCrake)呈現(xiàn)的是一個被基因工程技術(shù)摧毀的未來世界。該小說的創(chuàng)作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背景,表現(xiàn)了對從1973年起第一例DNA實驗成功后不斷進步的基因科技的憂患意識。這部生態(tài)預(yù)警小說圍繞著科技的放縱發(fā)展對人類世界帶來的災(zāi)難而展開故事情節(jié):在科技發(fā)展到盡頭的時候,世界唯一的幸存者“雪人”(吉米)和其他的變態(tài)生物品種(器官豬、狼犬獸、秧雞人)共同生活的情景。故事有兩條主線:一條是講雪人面臨著太陽的炙烤、饑餓的肚皮和怪獸的追逐;另一條是講雪人回憶自己如何淪落到絕境中。這部小說中基因技術(shù)是貫穿全文的主線,阿特伍德以雪人的遭遇揭示了技術(shù)至上的價值觀導(dǎo)致的結(jié)果:基因工程對自然本來面目的改變;改變自然的過程中造成的人的異化以及與自然的疏離。這部小說的情節(jié)是荒謬而丑惡的,阿特伍德選擇了一種極致夸張的丑陋方式描寫了人類改變自然本來面目所導(dǎo)致的毀滅性后果,這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式和羅丹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途徑不謀而合:羅丹認為,選擇丑的對象來表現(xiàn)生活,往往要比美的刻畫雕塑更能表現(xiàn)事物的本來狀態(tài)。這也是為什么眾多作家從破壞自然造成的后果的角度來表達自己的生態(tài)倫理理念的原因。阿特伍德選擇了從文化墮落、人性墮落帶來的惡果的角度來撰寫小說,強烈譴責(zé)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走向功利化帶來的毀滅。技術(shù)的性質(zhì)本來是作為人類擺脫自然賦予人的生理弱勢而改變世界的工具,但是現(xiàn)代技術(shù)越來越深入發(fā)展,不斷的改變和支配人類固有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文化傳統(tǒng)。《羚羊與秧雞》表達了社會上廣泛存在的一種焦慮,面對著愈發(fā)先進的科技,這種科技發(fā)展需要一種配套的人文價值觀,使得科技的發(fā)展維持在一定的界限內(nèi),否則其后果難以預(yù)料。阿特伍德曾擔(dān)心,人們對于科技發(fā)展的把握猶如兩歲的孩子面對著電動割草機一樣無措。問題的解決不在于科技的本質(zhì),而在于如何把握科技和社會的和諧相處,如何不讓科技發(fā)展的高度超過了道德邊界、打破責(zé)任的束縛。有人認為阿特伍德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在夸大技術(shù)的反作用力。阿特伍德評價道:“請不要誤以為《羚羊和秧雞》是反科學(xué)的。科學(xué)是一種認知的方式,也是一種工具,正如所有其他的認知工具和方式。它可以被用來作惡。它也可以被收買和出售,人們常常這樣做,但是科學(xué)本身并無害處,正如電那樣,它是中性的。”作者在結(jié)尾設(shè)計了開放式的結(jié)局,讓讀者按照自己的理性程度去設(shè)計故事的走向,在文明的廢墟面前,吉米發(fā)現(xiàn)了另外三個幸存者,“他們會和諧相處嗎?”作者實質(zhì)上在質(zhì)問,人類在廢墟上重建文明的時候,該以什么樣的生態(tài)觀來面對發(fā)展。
6.總結(jié)
在科技膨脹發(fā)展、技術(shù)力量對自然的異化愈發(fā)嚴重的時代背景下,文學(xué)作品中融入這種視角體現(xiàn)了人類對科技理性發(fā)展的憂慮和對生態(tài)系統(tǒng)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的期望。當正確的生態(tài)倫理觀逐步形成但是卻無法貫穿到人類生活、生產(chǎn)的各個層面的時候,卡森、艾比、阿特伍德等在作品中用危機論的眼光對待“技術(shù)”這把雙刃劍。當代文學(xué)作品的一個常見話題是人類技術(shù)進步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保持之間的矛盾,反映的是技術(shù)文化的危機性特征。技術(shù)和環(huán)境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的解決,不能靠一味排斥技術(shù),也不能靠單向度的技術(shù)理性,必須要在以技術(shù)改變生活的同時,不破壞自然的統(tǒng)一和和諧。
作者:劉春偉 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