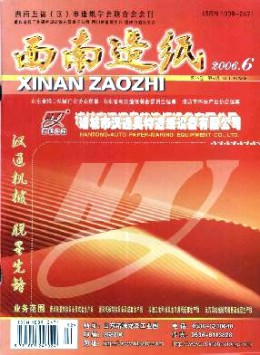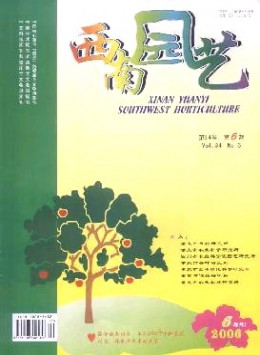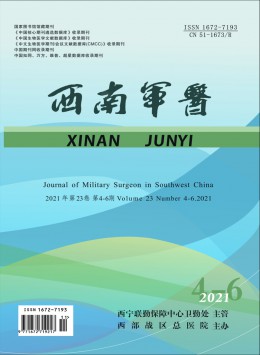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現(xiàn)代中國學(xué)界對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進(jìn)行了一定發(fā)掘整理,不少現(xiàn)代作家與文學(xué)研究者也將邊地歌謠與現(xiàn)代文學(xué)進(jìn)行對照,期望以此豐富現(xiàn)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研究。在現(xiàn)代文學(xué)語境中,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樣式豐富,呈現(xiàn)出鮮明的地域文化共性,具有質(zhì)樸靈活的表現(xiàn)形式、執(zhí)著求真的美學(xué)風(fēng)格等特點(diǎn)。它是西南邊地傳統(tǒng)文學(xué)的代表,也起到溝通主流知識界與邊地、少數(shù)民族、民間、民間文學(xué)的媒介作用,并由此進(jìn)一步充實(shí)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
關(guān)鍵詞:西南邊地;民間歌謠;少數(shù)民族歌謠;特點(diǎn);充實(shí)豐富;現(xiàn)代文學(xué)
中國文學(xué)是多元文學(xué),包括民族多元、地域多元等。作為一個遠(yuǎn)離中原的多民族文化區(qū)域,西南邊地及其文學(xué)也一直是中國文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南邊地主要指西南地區(qū)多民族共存的區(qū)域。據(jù)《史記》、《華陽國志》等記載,西南地區(qū)在古代就生活著多個民族,其中少數(shù)民族主要集中在古“西南夷”區(qū)域。“西南夷”文化區(qū)域大致包括今天云南、貴州兩省及四川省大渡河以西(原民國時(shí)期西康省),并向南延展至中南半島北部、向東延展至湘西地區(qū)(雪峰山以西)。這個區(qū)域自古以來被視為中國的邊疆,也是大西南地區(qū)的外圍部分,被視為“西南邊地”。西南邊地有悠久和獨(dú)特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文學(xué)語境中,西南邊地傳統(tǒng)文學(xué)與新文學(xué)之間的對話、互動使雙方都煥發(fā)了新的生命力,這使中國文學(xué)的內(nèi)涵顯得更為豐富。西南邊地傳統(tǒng)文學(xué)主要包括(口傳與書面的)神話、傳說、歌謠等。其中,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具有獨(dú)特的文學(xué)和文化價(jià)值。近現(xiàn)代以來,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逐漸被主流學(xué)界注意,如20世紀(jì)20年代的“歌謠運(yùn)動”就特地收集與整理了不少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據(jù)統(tǒng)計(jì),在“歌謠運(yùn)動”前期,《歌謠周刊》收錄的一萬多首歌謠中,僅云貴兩省就貢獻(xiàn)了兩千多首[1]。至抗戰(zhàn)及戰(zhàn)后,西南邊地歌謠更是得到多方關(guān)注,不少邊地歌謠被搜集成冊并公開出版,如劉兆吉的《西南采風(fēng)錄》、陳國鈞的《貴州苗夷歌謠》等。隨著相關(guān)研究的推進(jìn),現(xiàn)代西南邊地民間歌謠、少數(shù)民族歌謠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中的價(jià)值越來越得到重視它不僅是西南邊地地域文化、文學(xué)傳統(tǒng)的結(jié)晶,還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學(xué)、民間文學(xué)、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與現(xiàn)代“中心、主流”文學(xué)之間的媒介。通過這個媒介,邊地文學(xué)傳統(tǒng)、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傳統(tǒng)為主流文學(xué)話語所感知,并對主流文學(xué)產(chǎn)生某種反作用力,從而進(jìn)一步充實(shí)了現(xiàn)代文學(xué)。
一、現(xiàn)代文學(xué)語境中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的幾種形式
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歷史十分悠久,但由于遠(yuǎn)離中原文化中心,它在歷史上較少受到官方及主流知識分子注目。直至“五四”前后,特別是北京大學(xué)掀起“歌謠運(yùn)動”風(fēng)潮之后,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才逐漸被“主流”較為系統(tǒng)地了解。可以說,成文的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在現(xiàn)代是以“被發(fā)掘”的被動態(tài)勢進(jìn)入主流學(xué)界視野的,它們基本上都經(jīng)過了知識分子的翻譯與改寫。翻譯與改寫自然有力度的區(qū)別。若按“被翻譯與改寫力度”由弱到強(qiáng)的線索來考察現(xiàn)代文學(xué)語境中的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它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1.主要是指深入邊地的知識分子采集的、大致上還保留著本來面貌的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
如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diào)查報(bào)告》(1939年成書,恰逢抗戰(zhàn),至1947年方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收錄有41首湘西苗族歌謠,這些歌謠被翻譯為漢語,同時(shí)都標(biāo)注了苗語讀音和直譯讀法。陪同凌純聲在湘西進(jìn)行苗族調(diào)查的湘西人石啟貴于1940年編寫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bào)告書》,書中也收錄了大量湘西歌謠。與此類似的是,抗戰(zhàn)期間內(nèi)遷到貴州的大夏大學(xué)教授陳國鈞等人編成的《貴州苗夷歌謠》,以及貴州本土少數(shù)民族知識分子楊漢先著成的《大花苗歌謠種類》、《威寧花苗歌樂雜談》等文(收入?yún)菨闪亍㈥悋x編著《貴州苗夷社會研究》一書)。在云南,張靜秋的《云南僰民唱詞集》、薛汕的《金沙江上情歌》等則對云南(主要是滇南、滇西)少數(shù)民族歌謠進(jìn)行了收集、整理。在西康,劉家駒(格桑群覺)整理康藏民歌并將之翻譯成漢語,并于1948年編成《康藏滇邊歌謠集》(西康知止山房,1948年)出版。除此以外,還有一些邊地歌謠是被零散收錄的。如北大《歌謠周刊》收錄的幾千首西南邊地歌謠。沈從文將湘西歌謠整理成《筸人謠曲》,西南聯(lián)大學(xué)生劉兆吉將湘西、貴州、云南歌謠整理成《西南采風(fēng)錄》等。這類歌謠并未在搜集和刊出的過程中被大幅度改寫,總體而言,它們大體上保持了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的原生態(tài)面貌。
2.主要是指知識分子在原生態(tài)歌謠基礎(chǔ)上改寫的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
在這些經(jīng)過改寫的歌謠中,較廣為人知的是光未然改寫云南彝族歌謠而成的《阿細(xì)的先雞》。光未然坦言,原作的一些內(nèi)容“也是經(jīng)過了我的苦心經(jīng)營”[2]。光未然的這種做法是典型的將少數(shù)民族歌謠“文人化”的做法,但大致上保留了原作的味道。與光未然相比,有一些知識分子對邊地歌謠的改寫就是更為純粹的文人化改寫了。如云南作家趙銀棠將納西族歌謠改寫成五言舊體詩:“上峰三峰雪,/下峰三峰柏。/柏雪常相思,/相思情脈脈。”[3]230-231除了形式上的改寫,另有一種改寫是吸收歌謠的內(nèi)核之后,將歌謠的敘事原型和美學(xué)傳統(tǒng)融入到新的創(chuàng)作中。如云南詩人梅紹農(nóng)的敘事詩《奢格的化石》,取材于云南彝族傳說(以歌謠形式流傳于民間),詩人將民間歌謠轉(zhuǎn)化成新式白話詩。沈從文也曾將湘西苗族、土家族歌謠改寫成新詩,如《鄉(xiāng)間的夏》、《鎮(zhèn)筸的歌》等,他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湘西歌謠的形式改寫楚辭(《還愿》)和《詩經(jīng)》(《伐檀章今譯》),以此讓邊地歌謠煥發(fā)出別樣的生命力。從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屢屢“被改寫”來看,可見歌謠內(nèi)蘊(yùn)著文學(xué)與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所以它才能不斷被發(fā)掘和改造。
3.主要是指作家或模仿邊地歌謠創(chuàng)作的、或生造而成的“陌生化”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
這些歌謠大多散落在新文學(xué)作品中,讀者一看到這類歌謠就知道它們與邊地有關(guān),而實(shí)際上它們卻不在邊地流傳。如沈從文《鳳子》里鎮(zhèn)筸女子所唱的歌:“誰見過天邊有永遠(yuǎn)的虹?/問星子星子也不會承認(rèn)。/我聽過多少蟲聲多少鳥聲,/謊話夠多了我全不相信。”[4]這首歌很可能就是沈從文虛構(gòu)的,因?yàn)殒?zhèn)筸(鳳凰)苗族并沒有這樣的山歌(無論是沈從文的記錄還是凌純聲等人的田野調(diào)查都沒有錄入類似歌謠)。《神巫之愛》、《龍朱》等文中幾乎是西洋歌劇形式的歌謠更只能歸結(jié)為沈從文的“再創(chuàng)作”。另有一些與邊地真實(shí)歌謠相近,但也可推論出是作者生造的歌謠。如馬子華小說《月琴》出現(xiàn)的那首:“阿妹,/哥哥真想你,真想你!/請個畫師來畫你。/把你畫在月琴上,/抱著月琴如抱你。”[5]《月琴》最早收錄在馬子華1936年的短篇小說集《路線》中,該篇小說典型地“表現(xiàn)出馬子華早期小說創(chuàng)作的特色”[6],即往往如其他年輕左翼作家的作品一般淪為與實(shí)際生活相距甚遠(yuǎn)的“急就章”。這篇小說雖以故鄉(xiāng)為表現(xiàn)對象,但當(dāng)時(shí)馬子華并沒有切實(shí)的邊地底層經(jīng)驗(yàn),他早期主要生活在省城昆明,并在上海創(chuàng)作,這種歌謠只是為了增添“邊地風(fēng)味”而已。當(dāng)這些“生造”歌謠出現(xiàn)在小說、散文中,它們并不是獨(dú)立存在以供唱或頌的邊地歌謠,而是為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增添邊地風(fēng)味的佐料。當(dāng)然,這類歌謠的生成基礎(chǔ)仍是邊地傳統(tǒng)歌謠,只不過它們與原生態(tài)歌謠有較大差別,有時(shí)就難免變得陌生,以至于讓人不敢直接斷定是否就是實(shí)際存在的邊地歌謠。僅從上述歌謠形式來看,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是十分豐富的。當(dāng)然,多樣的邊地歌謠并非雜亂無章,而是具有一些共同特點(diǎn),這些特點(diǎn)反映了西南邊地這個文化區(qū)域的獨(dú)異性。
二、現(xiàn)代文學(xué)語境中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的基本特點(diǎn)
西南邊地歌謠雖繁雜,卻是雜而不亂。無論在整體上、形式上還是思想內(nèi)容、審美取向上,現(xiàn)代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都可概括出一些共同的基本特點(diǎn)。
1.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共性。
西南邊地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態(tài)各有不同,但西南邊地不同民族從古至今就相互交流、融合,這也形成了西南邊地文化的地域共性特點(diǎn)。地域文化共性使不少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超越了民族之別而成為地域性文學(xué)。如劉兆吉《西南采風(fēng)錄》收有云南曲靖的一首歌謠:“隔河望見妹爬坡/桃紅帶子順地拖/有心等哥站著等/無心等哥快翻坡。”[7]110《貴州苗夷歌謠》也收有十分類似的一首貴州安順一帶的仲家(布依族或云南壯族的舊稱)歌謠:“老遠(yuǎn)望見姐翻坡/情姐主意等情哥/有情有義坐起等/無情無義快翻坡。”[8]黔西與滇東是多民族雜居的地方,這首歌謠在不同民族之間流傳,可見它已經(jīng)是一種地域性文學(xué)了。甚至有的歌謠超越了民族和國界,成為某種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的經(jīng)典性文學(xué)。如云南傣族等少數(shù)民族流傳的“松帕敏”長詩。張鏡秋曾將其譯成漢語,并命名為《天王松帕敏奇遇唱詞譯》。張鏡秋在“注”里說明:“松帕敏系為四大佛典之一。”[9]164據(jù)相關(guān)研究者考證,這些歌謠“故鄉(xiāng)在印度,是佛教之風(fēng)把它的花粉播撒到這里來了。”[10]總體而言,西南邊地歌謠體現(xiàn)了這個文化區(qū)域的文化共性,它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態(tài)共同培育而成。
2.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具有質(zhì)樸、靈活的表現(xiàn)形式。
朱自清認(rèn)為,歌謠有“自然民謠”與“假作民謠”之別,后者往往向著“高雅”或“文人化”方向發(fā)展,而自然的民謠一直保持“單純質(zhì)樸”[11]。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就是典型的“單純質(zhì)樸”歌謠,即使被改造成“文雅”的或“現(xiàn)代”的詩詞形式,它依然保留了質(zhì)樸的本性和形式。如趙銀棠將納西古歌改為舊體詩詞,遣詞造句盡量向“雅馴”靠攏,然而“女兒愛戴花,戴花會情郎”[3]235等句仍是典型的納西族民間用語。邊地歌謠的質(zhì)樸深得沈從文推崇,他也從這種質(zhì)樸里吸取營養(yǎng),“用筆寫出來的比較新鮮,俏皮,真實(shí)的話”[12]。同時(shí),邊地歌謠在成文形式上十分靈活。如1936年貴州作家壽生指出流傳在貴州的一些歌謠有共同的“歌母子”(母題),在傳唱過程中人們可以隨性更改,因此就生成了多首歌謠:(一)買米要買一斬白/連雙要連好角色/十字街頭背鎖鏈/旁人取消也抵得!(二)買馬要買四蹄白/聯(lián)雙要聯(lián)好角色/那年那月犯了岔/旁人恥笑也值得[13]!這種質(zhì)樸、靈活的歌謠形式十分普遍。所以即使被改寫為舊體詩詞或現(xiàn)代詩,這些“歌謠詩”在遣詞造句上仍保留了鮮明的西南邊地民間和民族色彩。
3.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具有執(zhí)著求“真”的特性。
西南邊地遠(yuǎn)離中原,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往往保持著不受漢儒思想束縛的初民色彩。因此,在此文化土壤中生成的邊地歌謠相對內(nèi)地文學(xué)來說,也就保留了更為“真”的一面,同時(shí)更為執(zhí)著地追求“真”。最能體現(xiàn)邊地歌謠追求人性本真的是情歌。西南邊地情歌文化特別發(fā)達(dá),在現(xiàn)代成文的一些西南邊地歌謠集中,情歌占有很大比重。如《西南采風(fēng)錄》收錄各類歌謠771首,其中情歌就有641首。陳國鈞《貴州苗夷歌謠》把貴州苗夷歌謠分為七類,情歌一類在數(shù)量上遠(yuǎn)超其他六類之和。劉家駒《康藏滇邊歌謠集》原本就叫做《西藏情歌》。在情歌中,邊地人民毫不掩飾對原初生命意識的追求,也不壓抑對兩性結(jié)合的渴望,更表達(dá)了對世俗束縛的蔑視與反抗。當(dāng)邊地男女相遇,女子愛慕男子時(shí)不用掩飾自己的情感:“君細(xì)腰,眼睥睨/妾一見傾心,神魂飄蕩/儂心陶醉,精神錯亂了呀/真?zhèn)€白嫩的皮肉兒!”[9]9-10當(dāng)兩者得以結(jié)合,則滿心高興地唱:“好女好男好風(fēng)光/好女今晚配好郎/好日好時(shí)生貴子/好心好意比鴛鴦。”[7]520如果戀愛婚姻受到束縛,邊地男女更會勇敢地喊出反抗的呼聲:“怪七怪八怪我娘/拿我八字許配郎/等到三年我大了/只有隨我不隨娘。”[14]可見,邊地情歌“既不同于剝削階級仿作中的那種無病呻吟,也沒有市民階層所編俗曲中的低級趣味,所表現(xiàn)的感情是那樣的純真,那樣的真摯,那樣的深沉,這些作品與地主階級文人扭捏做作的‘情詩’和小資產(chǎn)階級虛夸、矯飾的‘愛歌’不能同口而語。”[15]當(dāng)然,現(xiàn)代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仍有很多值得剖析的特點(diǎn)。只不過總體來說,鮮明的西南邊地地域性、質(zhì)樸與靈活的表現(xiàn)形式、執(zhí)著追求“本真”的思想內(nèi)涵與審美風(fēng)格等算是其基本特色。當(dāng)這具有邊地色彩、少數(shù)民族色彩的歌謠遇到現(xiàn)代文學(xué),它就對現(xiàn)代文學(xué)產(chǎn)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三、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相遇
近現(xiàn)代以來,隨著歌謠運(yùn)動及類似歌謠采集活動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邊地、邊地少數(shù)民族及其文學(xué)在現(xiàn)代中國語境中呈現(xiàn)出更為客觀、立體的一面。同時(shí),歌謠采集活動還促使現(xiàn)代文學(xué)從邊地歌謠中汲取“民間”、“蠻夷”的活力與養(yǎng)分,以此豐富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內(nèi)容、形式與美學(xué)風(fēng)格。
1.現(xiàn)代中國從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中發(fā)現(xiàn)了西南邊地的“人”。
歷史上,西南邊地一向被忽視,邊地人往往被視為非人的“蠻夷”。而歌謠運(yùn)動重新定義了“民”的含義,邊地少數(shù)民族也被納入現(xiàn)代中國“民”的范疇。徐新建指出:“大體而論,在民國前期中國歌謠學(xué)的相關(guān)研究中,‘民’的含義與以下幾組命名關(guān)聯(lián):民間、民眾;平民、鄉(xiāng)民;俗人、蠻人。”[16]作為“蠻人”、“鄉(xiāng)民”的一部分,邊地少數(shù)民族在“五族共和”或類似政治表述中沒有一席之地,卻在歌謠運(yùn)動等文學(xué)語境中受到了重視。凌純聲在調(diào)查湘西苗族時(shí)明確認(rèn)識到“(苗族歌謠)或?yàn)楸憩F(xiàn)內(nèi)心現(xiàn)象的抒情歌,或?yàn)楸憩F(xiàn)外界現(xiàn)象的敘事歌。……其內(nèi)容雖似淺薄粗野,然很值得我們深刻的注意,因?yàn)榭梢詭椭覀儗τ谒麄兊那榫w生活,有一種直覺的覺察。”[17]這里雖還有“我們”與“他們”之分,但已經(jīng)看出“我們”確認(rèn)“他們”也是有喜怒哀樂的“人”,“他們”的情緒也值得“我們”去注意。黃鈺生在給《西南采風(fēng)錄》作序時(shí)也講述了自己對邊民的真切感受。邊民和他一路同行一路高歌,雖身負(fù)重物一步一喘仍歌聲不絕。黃說這并不是因?yàn)檫吤瘛胺侨恕保且驗(yàn)樗麄円愿杪晛矸謸?dān)勞累,唱歌之后“也覺得在綿綿長途上,還有同伴,還有一樣辛苦的人。他們所唱的歌,與其說是情歌,不如說是勞苦的呼聲。”[18]若沒有發(fā)現(xiàn)這些歌謠,有幾個人能知道邊民也是掙扎在勞苦的底層呢?薛汕更是把邊地歌謠當(dāng)成“生命的一部分”,因?yàn)樗麖倪叺馗柚{里看到了活生生的邊地民眾。邊地民眾“正如金沙江上的青年男女,充沛著豐富的生命力一樣……他們用火熱的感情,毫無顧忌地使山光水色,為之一變,使茂林巨石,為之動容……假如有人想抹殺他們的這些真實(shí),甚至侮辱了他們,他們絕不是只曉得沉湎于私情,不曉得是非的。”[19]邊地歌謠凝結(jié)了西南邊地民眾的喜怒哀樂,采集歌謠也就是把這喜怒哀樂給“采”出來,并把真實(shí)存在卻幾乎不為人所知的邊地少數(shù)民族展示給世間: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也是活生生的人。若沒有這些歌謠,邊地少數(shù)民族留給現(xiàn)代“中國”的印象或許只是面目模糊或猙獰的,如野獸一般的蠻夷罷了。只有在邊地歌謠中,邊地民眾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才有了更為客觀、立體的面貌,才能使“中心之國”更為平實(shí)地看待邊地。正如林同濟(jì)在認(rèn)識到真實(shí)的“苗夷”之后呼吁:“讓我們大家不要無條件地?cái)[出高等民族態(tài)度,動不動就高喊要‘同化’這些苗民!”[20]
2.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發(fā)現(xiàn)了“邊地”和“邊地文學(xué)”。
劉兆吉在談及民歌研究時(shí)不無遺憾地說道:“記載西南幾省尤其是黔、滇民歌的,可說是太少了,這實(shí)在是一種憾事。”[21]這其實(shí)反映出以滇黔為主的西南邊地文化區(qū)域被忽視的現(xiàn)實(shí)。對西南邊地歌謠的采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狀況,從北大《歌謠周刊》所收錄的西南邊地歌謠到中山大學(xué)《民俗》周刊、《民間文藝》等收錄的西南邊地歌謠身上,這個文化區(qū)域逐漸受到外界的認(rèn)識和重視,特別是這些歌謠采集者將少數(shù)民族歌謠翻譯成漢語并集結(jié)出版,這就使得在以往中國文學(xué)范疇里模糊不清、甚至被忽視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以“漢化”的姿態(tài)進(jìn)入主流視野。這些“漢化”的原生態(tài)邊地文學(xué)使得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一方面發(fā)現(xiàn)了一種“異域情調(diào)”文學(xué),另一方面以這種“異域”文學(xué)來觀照自身、充實(shí)自身。比如聞一多以西南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來考證伏羲女媧神話就是典型例子。在《伏羲考》中,聞一多特地強(qiáng)調(diào)中國西南各族洪水故事、瑤族圖騰舞樂等少數(shù)民族文化、文學(xué)對中國神話考證的積極作用。這些被聞一多作為觀照資源的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學(xué)大多是流傳已久的口傳文學(xué),歌謠是這些口傳文學(xué)的重要載體,其中的洪水神話更是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學(xué)、邊地歌謠一個重要主題。從聞一多等人對邊地歌謠的重視來看,邊地歌謠與中國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正如胡適所言:“歌謠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學(xué)擴(kuò)大范圍,增添范本。”[22]這就可看出,邊地歌謠使中國文學(xué)的范圍進(jìn)一步得到擴(kuò)大,同時(shí)使其內(nèi)涵更為充實(shí)。
四、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互動
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相遇影響了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方方面面,兩者之間的互動更是使現(xiàn)代文學(xué)擴(kuò)展了創(chuàng)作視野。可以說,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在新時(shí)代為新文學(xué)不斷提供營養(yǎng)。
1.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為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西南邊地書寫、少數(shù)民族書寫提供了某種文化、文學(xué)原型。
如沈從文《月下小景》寫苗族青年男女在山洞中幽會之后服毒殉情,按照作者的解釋,殉情的原因在于當(dāng)?shù)匾环N古老的風(fēng)俗:女子不得嫁給奪取了其初夜的男子,必須要嫁給他人。但《月下小景》對“奪取初夜”與殉情之間關(guān)系的描述并不一定依據(jù)現(xiàn)實(shí)習(xí)俗,而是從某種古老習(xí)俗、傳說中脫胎而來,其中的要點(diǎn)就在于“被迫嫁人”這個“原型”。實(shí)際上,湘西苗族婚戀歌謠里一直存在“被迫嫁人”與“反抗被迫嫁人”這個母題,沈從文極有可能在無意識中化用了這一原型。在這里,可參考一首古老的苗族古歌《苗族史詩》對苗族祖先姜央娶親過程的描寫。史詩敘述:大洪水過后,人類都滅絕了;姜央被天神命令娶自己的妹妹,以重新繁衍人類;妹妹不同意天神的安排,姜央就想了一個辦法意圖困住妹妹:“聰明的姜央,來到小橋西,編了九個鐵籠子,捉來九只土畫眉,放進(jìn)籠子里,叫妹妹去取。”當(dāng)妹妹被籠子困住后向姜央求救,姜央說:“我娶你作妻,答應(yīng)不答應(yīng)呢?答應(yīng)才救你。”[23]這首古歌一方面反映了遠(yuǎn)古時(shí)期的兄妹通婚風(fēng)俗;另一方面其實(shí)描寫了苗族“搶親”習(xí)俗的源頭,即姜央對妹妹的刁難便是遠(yuǎn)古苗族男子搶奪女子的手段。“搶親”在后來不再盛行,但“搶親”及“反抗搶親”故事卻在苗族口傳文學(xué)中流傳,故事中具體的主人公及行為已經(jīng)不限于姜央及其妹妹,而是成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文學(xué)原型:被迫嫁人、進(jìn)行反抗。那么,回到《月下小景》的“被迫嫁人”這一主要結(jié)構(gòu),可發(fā)現(xiàn)小說所述的“規(guī)矩”女子必須離開與自己過“初夜”的男子實(shí)質(zhì)上就是女子被迫離開情人而嫁給搶親者:這可能就是“姜央妹妹必須嫁給姜央”這一傳統(tǒng)文學(xué)原型的再現(xiàn)。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2.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還影響了現(xiàn)代文學(xué)西南邊地書寫、少數(shù)民族書寫的文學(xué)形式與審美情趣。
比如在作品結(jié)構(gòu)上,邊地歌謠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邊地書寫之間便有某種呼應(yīng)。以馬子華《他的子民們》對比彝族民歌《阿細(xì)的先雞》,會發(fā)現(xiàn)該小說與彝族創(chuàng)世歌謠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有一致性:《阿細(xì)的先雞》包括“創(chuàng)世記”、“開荒記”、“洪水記”、“談情記”和“成家記”,恰好是彝族對本民族歷史的理解;《他的子民們》的主體結(jié)構(gòu)包括“自在生活、土司壓迫、反抗土司、反抗失敗、逃進(jìn)深山”這與歌謠中彝族在創(chuàng)世紀(jì)與開荒之后,遭遇洪水、躲過洪水,然后在山上繁衍的結(jié)構(gòu)是一致的。這類“走出困境”式的故事原型不止存在于《阿細(xì)的先雞》中,更幾乎是西南邊地不同民族創(chuàng)世神話的共同主題,這無形中就影響了包括《他的子民們》在內(nèi)的部分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除了結(jié)構(gòu)上的聯(lián)系,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也在文學(xué)形式與審美風(fēng)格上充實(shí)了現(xiàn)代文學(xué)。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西南邊地書寫有一個特點(diǎn),即作品中常常混雜不少邊地歌謠,這些歌謠帶給文學(xué)作品以別樣的風(fēng)味。如埃德加•斯諾和周輅等人的“馬幫文學(xué)”加入云南歌謠,使“馬幫文學(xué)”呈現(xiàn)出某種邊地傳奇色彩;沈從文構(gòu)建湘西世界總要寫男女對歌,“對歌與音樂的插入,使沈從文的神話傳說故事洋溢著少數(shù)民族的浪漫與絢爛,也使故事充滿著獨(dú)特詩意和韻味,從而呈現(xiàn)出沈從文小說的優(yōu)美的風(fēng)格。”[24]更有一些邊地新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生期的邊地詩歌)直接就脫胎于歌謠,這使新文學(xué)與邊地傳統(tǒng)文學(xué)的關(guān)系變得更為密切。如貴州《鐸報(bào)》1919年6月刊登的《銷國貨歌》不乏“國貨勸他銷/偏說恐惹禍/比如我的房/空起我不坐”[25]等句,這些句子與邊地民間歌謠并沒有很大區(qū)別,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看成邊地新詩誕生期的獨(dú)特風(fēng)格。可以說,邊地歌謠使現(xiàn)代文學(xué)邊地書寫、少數(shù)民族書寫的文學(xué)母題、文學(xué)結(jié)構(gòu)和審美風(fēng)格都呈現(xiàn)出獨(dú)異色彩。正因?yàn)槿绱耍F(xiàn)代作家筆下充滿活力與生機(jī)的西南邊地艾蕪絢麗的滇緬邊境、沈從文沖淡的湘西世界、蹇先艾沉重的黔北民間、周文殘酷的川康雪地、馬子華奇詭的熱帶滇南以別樣的風(fēng)姿為“老氣沉沉”的“舊中國”及中國(中心之國)文學(xué)注入了一股“野蠻人”的新鮮血液。而且,邊地歌謠不僅充實(shí)了現(xiàn)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它甚至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學(xué)史的面貌,一些學(xué)者在考察邊地民間歌謠與其他口傳文學(xué)之后就提出“中國文學(xué)并不缺少英雄史詩”等觀點(diǎn)①。當(dāng)然,某些邊地歌謠是否該被歸為“史詩”暫且不論,但它毫無疑問是邊地民族文學(xué)傳統(tǒng)、邊地生存經(jīng)驗(yàn)的結(jié)晶,它對中國文學(xué)的貢獻(xiàn)是毋庸置疑的。
3.除了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直接互動,在邊地歌謠中還可看到邊地“民間”之于現(xiàn)代中國的重要意義。
“歌謠運(yùn)動”目的之一是知識分子為了確證自我與“民”的身份,這種確證的內(nèi)在邏輯就在于認(rèn)定有一個屬于“民”的生存空間它與“廟堂”相對,也與知識分子構(gòu)建的“知識廣場”相對,它被稱為“民間”。陳思和指出“民間”具有幾個基本特點(diǎn):一是它產(chǎn)生并存在于國家權(quán)力控制相對薄弱的位置。二是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審美風(fēng)格。三是它的內(nèi)涵十分復(fù)雜,“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性的糟粕”交織,構(gòu)成了獨(dú)特的藏污納垢形態(tài)[26]。現(xiàn)代新式知識分子在確證“民間”之時(shí),往往有“改造”大眾與民間的動機(jī)。作為“鄉(xiāng)民”、“土人”生活的區(qū)域,無論是地緣上還是文化上,西南邊地都是典型的民間。作為“民間”的一部分,邊地歌謠以“民間文學(xué)”的面貌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認(rèn)識,于是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把邊地作為解讀與“改造”的“民間”對象。在這層意義上,西南邊地與五四知識分子的“啟蒙”、左翼話語的“階級”及1942年延安講話之后的“人民”等現(xiàn)代文學(xué)關(guān)鍵詞緊密相連,也就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現(xiàn)代中國形成了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在“五四”啟蒙知識分子看來,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體現(xiàn)了自由也蘊(yùn)含著糟粕,他們從歌謠里看到啟蒙的迫切性;對左翼知識分子來說,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體現(xiàn)了“人民”的智慧與苦難,它是“人民文學(xué)”的一部分,還可從中延伸出“階級斗爭”的多種解讀。有學(xué)者就此認(rèn)為,對堅(jiān)持啟蒙立場的知識分子來說,“民間文化形態(tài)總是與知識分子已有的價(jià)值系統(tǒng)發(fā)生碰撞。這種沖撞使知識分子對現(xiàn)實(shí)思考的深度有了歷史縱深感”;對沈從文等堅(jiān)持“民間立場”的知識分子來說,則是“把自己融于民間的文化世界中,以‘下層人’的眼光去理解社會、人生、政治,去體悟民風(fēng)民情,把自己的心交給那一浸潤著民間文化精神的大地,敘說‘鄉(xiāng)下人’的心理內(nèi)涵、生命渴求與行為方式。”[27]總而言之,無論是何種立場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從民間去觀照現(xiàn)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他們都不可能繞開西南邊地這個典型的“民間”。西南邊地和邊地歌謠如其他“民間”及“民間文學(xué)”一般,從中可看到“新文學(xué)生成、發(fā)展的重要的精神資源和審美資源。”[27]綜上所述,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民族多樣、文化多元、歷史悠久的國家,中國文學(xué)是多個文化區(qū)域、多種文化形態(tài)共同塑造而成的多元文學(xué)。僅就現(xiàn)代文學(xué)而言,它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多元傳統(tǒng),在新的時(shí)期又有新的多元內(nèi)涵,所以絕不能以單一觀念(如以中心話語遮蔽邊緣話語、以雅文學(xué)遮蔽俗文學(xué)、以漢族文學(xué)遮蔽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等)去認(rèn)識現(xiàn)代文學(xué)。民間與官方及知識廣場的關(guān)系、雅俗文學(xué)的關(guān)系、中心與邊緣的關(guān)系、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的關(guān)系等,都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需要理清的要點(diǎn)。在理清這些關(guān)系之時(shí),重視歌謠(包括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在內(nèi))等民間文學(xué)傳統(tǒng),這有助于研究者以承認(rèn)并尊重多元的態(tài)度去認(rèn)識現(xiàn)代文學(xué)和中國文學(xué)。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語境下的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樣式紛繁、特點(diǎn)突出,重視并探討西南邊地少數(shù)民族歌謠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關(guān)系,這也是“重審”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一個角度。唯有認(rèn)識到民間文學(xué)、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重要性,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和中國文學(xué)的闡釋才不至于落入“一言以蔽之”的籠統(tǒng)概括中。
參考文獻(xiàn):
[1]劉錫誠.20世紀(jì)中國民間文學(xué)學(xué)術(shù)史[M].開封: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6:385.
[2]光未然.阿細(xì)的先雞解題(代序)[M]//光未然.阿細(xì)的先雞.昆明:北門出版社,1944:16.
[3]趙銀棠.玉龍舊話新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4]沈從文.鳳子:在栗林中[M]//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4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359.
[5]馬子華.月琴[M]//馬子華.他的子民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7
[6]吳重陽.邊地民族生活的絢麗畫卷:論馬子華的小說創(chuàng)作[J].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91(2).
[7]劉兆吉.西南采風(fēng)錄[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46:110.
[8]陳國鈞.貴州苗夷歌謠[M].貴陽:文通書局,1942:222.
[9]張鏡秋.云南僰民唱詞集[M].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164.
[10]王國祥.傣族長篇敘事詩與佛教[J].華夏地理,1981(3).
[11]朱自清.中國歌謠[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9.
[12]沈從文.鄉(xiāng)間的夏(鎮(zhèn)筸土話):話后之話[J].國語周刊,1925(5).
[13]壽生.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M]//壽生.壽生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51-52.
[14]陳國鈞.貴州苗夷歌謠[M].貴陽:文通書局,1942:78.
[15]張景華.論《西南采風(fēng)錄》的情歌文化[J].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92(4).
[16]徐新建.民歌與國學(xué):民國早期“歌謠運(yùn)動”的回顧與思考[M].成都:巴蜀書社,2006:40.
[17]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diào)查報(bào)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76.
[18]黃鈺生.序[M]//劉兆吉.西南采風(fēng)錄.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46:2.
[19]薛汕.序[M]//薛汕.金沙江上情歌.昆明:春草社,1947:5.
[20]林同濟(jì).千山萬嶺我歸來[J].戰(zhàn)國策,1940(13).
[21]劉兆吉.西南采風(fēng)錄的經(jīng)過[M]//劉兆吉.西南采風(fēng)錄.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46:2.
[22]胡適.復(fù)刊詞[J].歌謠周刊,1936(1).
[23]馬學(xué)良.苗族史詩[M].今旦,譯注.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3:247-248.
[24]楊劍龍.神話傳說故事與少數(shù)民族文化:讀沈從文作品[J].民族文學(xué)研究,2012(1).
[25]毛宅三.銷國貨歌[M]//尹伯生.貴州新文學(xué)大系(1919-1989)現(xiàn)代文學(xué)卷(下冊).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384.
[26]陳思和.民間的浮沉[M]//陳思和.陳思和自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7:207-208.
[27]王光東.“民間”的現(xiàn)代價(jià)值[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3(6).
作者:彭興滔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