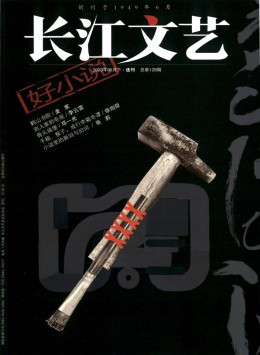文藝功利觀的反思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文藝功利觀的反思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隨著文藝的發(fā)展和各種體裁的完整化,文藝的功利性開始提到理論的層面進(jìn)行探討。早期的論述仍將文藝的娛樂功能放在首位。古希臘哲學(xué)家德謨克利特主張文藝的功能就是快樂:“大的快樂來自對美的作品的瞻仰。”而且認(rèn)為:“不應(yīng)追求一切快樂,應(yīng)該只追求高尚的快樂。”[2]蘇格拉底則是將美善統(tǒng)一作為文藝的最高功用:“每一件東西對于它的目的服務(wù)得很好,就是善和美的。”[3]8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早期文藝功利觀的集大成者,他在《政治學(xué)》中指出:“音樂應(yīng)該學(xué)習(xí),并不只是為著一個目的,而是同時為著幾個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凈化,(3)精神享受,就是緊張勞動后的安靜和休息。”[4]古羅馬的賀拉斯也認(rèn)為:“詩人的愿望應(yīng)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5]古代哲人所提出的不論是“高尚”也好,“服務(wù)得很好”也罷,還是“對生活有幫助”等,其實,已將文藝的功利性加以明確指出,只不過更多是精神與審美方面的,尚未政治功利化而已。
我國將文藝功利觀與政治教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論述比較早的是古代的大音樂家?guī)煏?“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左傳•襄公十四年》)就是說,早期的詩歌具有對政治進(jìn)行批判箴諫的價值功用。這就是孔子后來提出的“興、觀、群、怨”中之“觀”,因為統(tǒng)治者從中可以考察政事措施之得失,“以補其政”。這一點對后世也有長遠(yuǎn)影響。“箴諫”在后來發(fā)展為諷諭說,影響更為深遠(yuǎn)。但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貫穿文藝發(fā)展史上的功利觀,始終在政治道德教化作用和娛樂消遣作用互相排斥或互相影響的關(guān)系上左右搖擺。拿西方為例,前者如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他認(rèn)為詩可以幫助人們建立起“崇高的”“政治和道德信仰”;詩是使“一個偉大民族覺醒起來”的“最為可靠的先驅(qū)、伙伴和追隨者”[6]等,表現(xiàn)了強烈的政治功利性。后者如意大利的卡斯特爾維屈羅,他就明確反對文藝的教化功能,“詩的發(fā)明主要是為著提供娛樂和消遣給一般人民大眾”,“主要地為娛樂、而不是為教益”[3]194。這種種觀點雖相對立,但因站的角度不相同,也大致反映出文藝發(fā)展的價值規(guī)律,即文藝功利觀的多層次化、多闡釋化與多元化,都從不同角度指明文藝功利觀的社會內(nèi)涵與審美內(nèi)涵。
歷史發(fā)展到近現(xiàn)代,特別是我國,由于社會的激烈動蕩,文藝功利觀的天平明顯向政治化傾斜。高倡文藝具有認(rèn)識現(xiàn)實功能的梁啟超,同時也極力夸大小說的價值功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7]當(dāng)然,這里梁啟超用一種偏激的語言,目的是達(dá)到一定的修辭效果。但在改良運動時期,將文藝納入政治功利性體系的急切性和緊迫性也顯而易見。幾乎是同一個時期的普利漢諾夫,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文藝?yán)碚摷遥种匾曃乃嚨墓浴_@對后來的列寧、斯大林都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列寧,他的無產(chǎn)階級的文藝事業(yè)要像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shù)闹摂?他的關(guān)于列•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的評論,都在無產(chǎn)階級文學(xué)事業(yè)的大旗上標(biāo)示了鮮明的政治功利色彩。20世紀(jì)30年代蘇聯(lián)“拉普”派文學(xué)和我國的左翼文藝運動,都是文藝政治功利觀的最好體現(xiàn)。發(fā)展到的經(jīng)典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以鮮明的無可辯駁的政治功利色彩,取得了文藝功利觀的正統(tǒng)地位。歷史實踐證明,在波譎云詭的革命時代,鮮明的政治功利觀配合著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斗爭事業(yè),促進(jìn)了無產(chǎn)階級文藝的順利發(fā)展,其歷史價值和地位是難以抹殺的。
觀念反思
英國歷史學(xué)家湯因比說過:“人類因為在其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所以我們知道自己被賦予了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尊嚴(yán)性,并感覺到必須維護它。”希臘哲學(xué)家蘇格拉底也說過:“我是欲望的主宰,而你是欲望的奴隸。”這些都說明人類是理性的動物,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鮮明的自我意識,就是能夠?qū)⒆陨淼囊庵竞退枷胪渡涞剿袑ο笊希拐麄€可以反思的對象成為“人化的自然”。西方哲學(xué)家大多是通過對人性的經(jīng)驗事實的描述,來建構(gòu)其社會功利觀體系的。葛德文在《政治正義論》中把人看成“能感受到刺激的生物、知覺的感受者”。邊沁更是明確地說,自然把人類置于兩個至上的主人“苦”與“樂”的統(tǒng)治之下,“功利原則承認(rèn)人類受苦樂的統(tǒng)治,并且以這種統(tǒng)治為其體系的基礎(chǔ)”。因此他認(rèn)為人的本性就是求樂避苦,人的行為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和快樂,行為對象是那些能帶來幸福的外物,也就是利益(功用)。而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歷史唯物主義則認(rèn)為,人性是“人———自然———社會”相關(guān)聯(lián)統(tǒng)一的產(chǎn)物,是社會性、歷史性、實踐性的統(tǒng)一。人性是在社會生活中成熟并發(fā)展起來的,社會性是人性的主要表現(xiàn)。人身上的自然性也是以社會化了的形態(tài)呈現(xiàn)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功利觀也是放置于人與自然、社會的關(guān)系中來全面考察的。不僅對無產(chǎn)階級文學(xué)如此,就是對古希臘神話,對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世界公認(rèn)的文學(xué)大師,也都是如此。比如恩格斯就特別喜愛《德國民間故事》一書,并給予高度的評價,指出它的價值功用,就在于培養(yǎng)人的“道德感,使他認(rèn)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權(quán)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們的勇氣,喚起他對祖國的愛”[8]401。馬克思主義的文藝?yán)碚摷移樟袧h諾夫說得更為具體:“所謂功利主義的藝術(shù)觀,即是使藝術(shù)作品具有評判生活現(xiàn)象的意義的傾向,以及往往隨之而來的樂于參加社會斗爭的決心,是在社會上大部分人和多少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真正感興趣的人們之間有著相互同情的時候產(chǎn)生和加強的。”[9]829他反對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理論,概括地說:“藝術(shù)作品的價值歸根結(jié)蒂取決于他的內(nèi)容的比重。”[9]836
文藝的功利觀并不等同于文藝的政治觀,盡管其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以我國的古代文論為例,可以明顯看到一條文藝功利觀逐漸趨同于文藝政治觀的傳統(tǒng)。孔子曾提出詩歌有著“興觀群怨”的功能,但他要求學(xué)生學(xué)詩的最終目的卻又是“事父事君”。這可以說是在自覺地倡導(dǎo)并實踐著文藝為政治倫理化服務(wù)。即使孔子的文藝美學(xué)觀點,也是從政治主體之美出發(fā),如他所贊的《韶》是歌頌舜的音樂,是對仁德為本的“揖讓”政治的肯定。至于商鞅提出的文藝要為耕戰(zhàn)服務(wù),韓非提出的文藝要為政治服務(wù)這些主張,也都強調(diào)著文藝的工具角色。而產(chǎn)生于漢代的《樂記》,則受董仲舒所宣揚的神秘化和政治化了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yīng)”論的影響,提出了“禮以導(dǎo)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樂記•樂本篇》)很明顯地把樂(文藝)看做是與禮相配套的,是與政和刑同樣重要的維護統(tǒng)治的一種手段。之后像劉勰的“原道宗經(jīng)”;孔穎達(dá)的“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xùn)”;梁肅的“文章之道與政通”;韓愈的“文以載道”;李覯的“治物之器”;直到顧炎武的“明道”、“紀(jì)政事”等,一條政治工具論的主線在我國古代文論中是非常清晰的。正如劉淮南先生所指出的:“文藝的政治功能也就被更加狹隘化、極端化了。”[10]
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在闡釋文藝功利性的同時,又特別強調(diào)屬于藝術(shù)的獨特的審美屬性。即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藝術(shù)家不應(yīng)當(dāng)把傾向特別指點出來,也不必要把他所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要讓它從情節(jié)和場面中自然流露出來,而且“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shù)作品來說就愈好”[8]462。所謂“隱蔽”,就是把作者的見解隱蔽在藝術(shù)形象之中,讓讀者自己去品味,去體會。讀者從作品中體會出來的內(nèi)涵越多,得到的審美享受也越多,從而藝術(shù)價值也就愈高。藝術(shù)的消費者就是通過這樣一個獨特的審美渠道,來走進(jìn)藝術(shù)世界,從而認(rèn)識自我、認(rèn)識世界,并精神變物質(zhì)地去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因此文藝的功利性不是直接的、實用的,而是間接的、精神化了的。
文壇走向
從蘇聯(lián)20世紀(jì)30年代以來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政策,到我國的“左翼”文藝運動、的《講話》,以及建國后的歷次文藝斗爭和爭鳴,文學(xué)藝術(shù)的政治工具論,始終是革命文藝發(fā)展的指導(dǎo)思想。作為一個特定的時期,文藝功利性的外化、物化,乃至政治化,參與整個革命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文論家,對無產(chǎn)階級文藝的功利性都有精辟論述。但文藝畢竟是文藝,隨著那個斗爭年代的過去和新時期的到來,我們強調(diào)其功利性,更多地是看其作為文藝本質(zhì)屬性的存在,對整個現(xiàn)存社會的整合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主義文藝20年的發(fā)展歷史,已經(jīng)印證了這一點,即過去實用的政治功利性已開始轉(zhuǎn)化。這是一個新的趨向,同樣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但我們也同時看到有兩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走向。第一個走向是文藝市場功利觀的形成。文藝市場是社會主義文藝傳播中的重要途徑。我國現(xiàn)階段的文藝市場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發(fā)展起來的,即以商品形式向人們提供文藝產(chǎn)品和文藝服務(wù)的場所;通過文藝市場可以讓文藝產(chǎn)品的藝術(shù)價值,達(dá)到文藝傳播的目的。文藝市場的建立,從表面看來,似乎是文藝功利性的直接化和物態(tài)化(比如說消費者須用貨幣的形式來交換接受文藝產(chǎn)品的權(quán)利)。其實這不是問題之所在,就是在古代藝術(shù)產(chǎn)品的消費也是要付費的,只不過渠道不同罷了。文藝市場化的意義主要在于使得生產(chǎn)者與消費者的直接溝通,特別是強調(diào)了接受者(消費者)在整個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地位:接受者不是被動地感知對象,而是整個文藝創(chuàng)作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主體,是閱讀和產(chǎn)生意義的基本要素。事實上,沒有一個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中完全無視接受者的存在。“每一部文學(xué)原文的構(gòu)成都意識到它的潛在的讀者,都包含著它寫作對象的形象。”[11]不論是書刊市場、影視市場、還是音像市場、演出市場等,文藝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者始終將消費者作為自己進(jìn)行全部創(chuàng)作活動中最重要的伙伴和參照系。這從理論上,從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點上,從社會主義對文藝的要求上,都是無可厚非的。文藝市場功利觀的形成,是社會和文藝發(fā)展的大趨勢,是社會進(jìn)步的表現(xiàn),我們完全不必驚嘆。我們驚嘆的可能是來自另外一面,就是文藝世俗化、文藝弱化的傾向,這是發(fā)育尚不太成熟的文藝市場功利觀所帶來的負(fù)面影響。雖然我們認(rèn)識到文藝世俗化傾向是當(dāng)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曾長期生活在宗教般的社會氛圍中,被政治功利性熏陶的中國人,在改革開放、物質(zhì)生活日益豐富后,渴望“瀟灑走一回”,渴望盡情地享受人生,滿足不能滿足的欲望;因此,世俗化傾向在沖擊傳統(tǒng)的經(jīng)院哲學(xué)和保守觀念方面具有一定作用。[12]但對創(chuàng)建精神文明,重塑民族靈魂,特別在弘揚崇高的藝術(shù)精神,確立主流審美文化在當(dāng)代社會的地位諸方面,又有值得我們思考和擔(dān)憂的一面。
第二個走向是接受體驗功利觀的形成。表面看來,這是一種潛在的功利,或者說是無功利的功利,但與我們所說的審美的超功利性又有著質(zhì)的不同。審美的超功利性追尋著審美“意義”的形成,即從物態(tài)化的功利性轉(zhuǎn)入精神的功利性。但接受體驗的功利性,則只是沉溺于所謂的體驗“過程“,不去進(jìn)行話語“意義”的追尋。比如無情節(jié)、無主題,乃至無結(jié)構(gòu),包括一些“另類”文藝、網(wǎng)上虛擬文藝等。好像只有如此,才可拒斥“媚俗”傾向,才稱得上真正的文藝或“純文藝”。如果說世俗文藝還重視一些感官的體驗的話,那么這一類文藝似乎連感官的體驗也不屑一顧,只能是一種“接受”,使傳統(tǒng)的接受只剩下一個無規(guī)則“游戲”的外殼罷了。當(dāng)代文壇這些種種不同的文藝功利觀,是社會主義文藝在新時期下所遇到的新問題,但又是文藝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當(dāng)前,我們?nèi)蕴幵谝粋€社會體制的轉(zhuǎn)型期,市場經(jīng)濟所帶來的巨大沖擊,泥沙俱下,必然會使一些原先我們就倍感困惑的文藝功利觀問題,再度成為關(guān)注的焦點。
掘進(jìn)與重建
社會主義文藝的功利性,完全不排除文藝的娛樂功能;恰恰相反,“寓教于樂”說,既是文藝接受的本質(zhì)特征,也是社會主義文藝功利性的基本要求。其實,任何社會形態(tài)的文藝都具有功利性,只不過是間接功利與直接功利的區(qū)別罷了。我們所說的“超功利”、“無功利”不過是相對而言,絕對的“超功利”、“無功利”是不存在的。盡管如此,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仍然反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這方面都有精辟的論述。在建設(sh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當(dāng)代社會,為促進(jìn)社會主義文藝的健康發(fā)展,對于這種獨特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我們必須處理好輿論導(dǎo)向與文藝的特殊表現(xiàn)、精神內(nèi)省與政府管理、文藝自律與社會制約的辯證關(guān)系,包括對主流文藝思潮的監(jiān)督與改善,營造寬松的文化環(huán)境;處理好文藝的娛樂功能、宣泄功能與社會批判功能的辯證融合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社會主義的文藝功利觀應(yīng)該充分汲取和正視市場經(jīng)濟所給精神文明帶來的一些暫時的負(fù)面效應(yīng),既肯定在藝術(shù)生產(chǎn)中生產(chǎn)者與消費者的有機溝通可以刺激藝術(shù)生產(chǎn)的良性循環(huán),又承認(rèn)這樣一個事實:黃色的、粗糙的、格調(diào)不高的文藝作品往往能獲得比高雅之作更好的經(jīng)濟效益。這就說明文藝消費者的素質(zhì)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待提高。“媚俗”文藝的后果,則是為低劣文藝提供了市場,誘發(fā)了一些文藝家和書商的私欲,使文藝界的精神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這都印證了實用功利觀對社會主義文藝發(fā)展的弊端。因此,高尚的精神需要弘揚,高雅的藝術(shù)作品需要扶持,應(yīng)成為我們重建健康純正的社會主義文藝功利觀的必要措施。掘進(jìn)與重建需要開闊的視野。
總之,隨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深入發(fā)展,當(dāng)代中國的文藝事業(yè)也呈多元化、多極化、多媒化的趨勢,網(wǎng)絡(luò)文化、影視傳媒的沖擊,以及“純文學(xué)”的再度復(fù)興,使文藝的“功利性”問題更加敏感與突出。通過對社會主義文藝功利性的歷史與現(xiàn)狀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社會主義文藝功利性的特殊表現(xiàn),在社會主義文藝宏觀的理論框架下,主觀的無功利性與客觀的功利性,顯在的無功利性與隱性的功利性,形象的無功利性與抽象的功利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是現(xiàn)代社會和新時期文學(xué)對我們以新的要求,也是文藝在整個發(fā)展歷程中的真切呼喚。文藝就是文藝,在它真正而全面體現(xiàn)出作為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特質(zhì)時,其價值才能同樣得到真正而全面地實現(xiàn)。(本文作者:李建東 單位:南通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