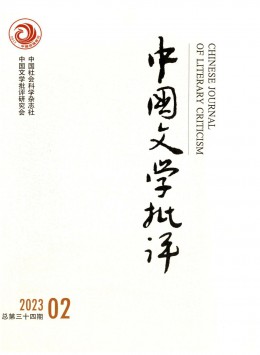韓柳文學批評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韓柳文學批評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前邊我們說過
韓柳的目的,最先是要行其道,如果不能行其道于當時的話,這才從事著作,以傳于后世。但是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所以也得注意文辭。然文辭如何才能好呢?其方法也是學古。韓愈在他的《進學解》里自己吹自己說:“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里也有同樣的意思,說道:“本之《書》以求質,本之《詩》以求恒,本之《禮》以求宣,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動。”中國的學者要對于社會有所改革的話,照例是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如孔子想行自己的學說,然又怕自己人微言輕,所以假托到三皇五帝。現在韓柳想改革那一時代的文學,于是又復古到孔子,他們既以孔子為標的,那末,作文當然也要根據孔子的五經。文宗五經的主張,本發之于揚雄《吾子篇》的“說經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揚雄的主張,后來劉勰著《文心雕龍》的時候,又大為解釋,在他的《宗經篇》里說的最為透澈。“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系》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范,章條纖曲,執而后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鹢,以詳略成文。”劉勰把《易》、《書》、《詩》、《禮》、《春秋》五經的性質解釋清楚以后,又得一個結論說:“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原。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傅銘檄,則《春秋》為根。”他把一切的文章,說是都出于五經。后來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文章篇》說的“文章者原出于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之說,也是由揚雄的主張而來。我所以引證以上幾句話的意思,是想示出韓柳論文的淵源,并可知道他們這些人都是孔源,而揚雄開其先路。所以從揚雄而后,中國的模擬與復古之風大開。我以為韓柳文學批評的淵源,受劉勰的《文心雕龍》的影響為最大,雖說他們不常提到他,所受揚雄的影響,恐怕只是復古的思想。然而韓柳的復古,決不能與揚雄的復古相提并論,因為韓柳想借復古的名義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是一種手段。并且韓愈在《答劉正夫書》里還說“能者無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他要“能自樹立”,自成一家風格,換言之,不去模擬外表之形式。不像揚雄那樣沒有主張,一味地迷古,所以他效《易》而作《太玄》,象《論語》而成《法言》,處處要拿孔子作個偶像,一步一趨地去學,只求形貌的相似,而把真正的精神失卻了。
二、無論是表現自我或是表現社會的文學
在作者寫的時候,都是內中有一種沖突,不得不寫的緣故。E.Bruneliere說“Nostruggle,nodrama”者,固然是為解釋戲劇,然而一切的文學都是這樣。換言之,就是在內我們有一種個性表現的欲望,而和這正相反的,在外卻有社會上種種的束縛與壓迫,結果,苦惱、煩悶,以及一切的不如意事都產生出來了。經文學創作把她表現出來,就謂之文學。這是廚川白村解釋文學的產生的話,而韓愈之解釋文學的產生,也是放在這個基礎上。他所謂說的“不平”,就是內心與外界的沖突,他所謂說的“鳴”,就是表現。他在《送孟東野序》里給我們的比喻的“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撀之鳴”,都是受外界的刺激而始表現。實在人類的文化,就是從這種沖突產生得來的,一方面有生的要求,而一方面又有種種的壓迫,于是人生萬花鏡就展開來了。我們受社會壓迫最利害的,就是經濟,所以韓愈特別把窮苦與文學的關系拿出來討論一下。他的《荊潭唱和詩序》里說“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的確是見道之語。我們看古今中外有幾個真正的文學家不是窮的。正因為窮,才能味嘗到社會上各種人的真正面孔,而給他一種很強烈的刺激,不能不從事于吐露。富人的生活大都是麻木的,從何會有刺激去使他去創作。我們都知道托爾斯泰是生于貴族的,但要不是他后來舍棄貴族的生活而去過那鄉村的貧苦生活,也不能認識人生那樣的深刻,而為世界的偉大的作家。正因為有強大的刺激,才有偉大的文學作品產生,所以韓愈說“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不過,韓愈所說的“鳴”,不但“自鳴其不幸”,還“鳴國家之盛”。本來韓柳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文學,他們所注意的完全是道,他們既然要想行其道于當時,于是不得不拍當時君王的馬屁。韓愈在他的《進撰平準西碑文表》說:竊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柳宗元也有同樣的意思說道:文之用,辭令褒貶尊揚諷論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于用。然開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后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經;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喻,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于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意,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以上的二段文字,是韓柳對于文學的態度的口供。他們認為文章除過“詞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外,沒有別的用處。即令再有別的用途,也就是自己不能行其道于當時的時候,則著述立說,以傳于后世,這是前邊已(竟)〔經〕說過的話。不過這二段文字我們應當注意的有一點,就是柳宗元把文分為著述與比興二類,前者是注重邏輯,后者是比較注重情感,所以他說二者不能得兼。實在,理智強烈的人很難寫一篇情感的文字,反是,情感豐富的人也很難寫一篇條分理(柝)〔析〕的文字。我們不必遠處舉例,即就韓愈、柳宗元而論,他們固然成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先鋒,可是他們太注重行為與理智,所以他們的文字,要以純文學的眼光來看,在文字藝術上有價值的很少。然而他們根本就不注重感情,所以我們也勿須怪他。
三、韓柳文學批評的主張
大概已如上述,我們現在把他們的最錯誤的兩點來討論一下。第一,就是混淆了純文學與雜文學。固然他們的目的是在改革六朝時代只注重形式而不注意內容的文學,可是因為太過火了,他們所主張的,我們反不能承認是文章。無論中外,在理論上我們總承認文學只是文學,不是其他的東西,然而批評家們總想把文學作為表彰真理或獲得知識的工具。如果這位批評家是比較喜歡哲學或宗教的話,則他希望文學是哲學或宗教的直覺的表現。如果他是比較理智的,他就認為文學是一種材料去發現心理的事實,或社會史的演變。總之,他們喜歡那一種學問,就希望文學是那一種學問的表現工具。即令如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所著名的WallerPater,但我們細讀他的《SludieaintheRenaissance》一書的結論,就知道他所說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意義,關于情感和感覺的用途,給于藝術的還不及給于人生的為多。這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然而不像韓柳那樣的過火,以致幾乎沒有抒情的文學的立腳點。第二,是拿文學作為宣傳的工具。我們知道文學的目的是在表現,而不是在宣傳,這是世人說舊了的話。易卜生劇作中所描寫的大多是婦女問題,好多婦女就以為他是在提倡婦女的地位,于是去找他對于婦女有什么意見,可是他回答說:“我還沒有想到這一點。”可見他只是表現內心的沖突,并沒有一種先見。如果文學要是表現的話,則你不論什么題旨都好,道德也好,自然科學也好,社會科學也好,甚而至于國家主義,以及三民主義,都無不可。然而這些題旨要以文學的形式去表現的話,就得以文學的標準來判斷,而不得以宣傳的目的來決定。因為表現,只是表現我內心的情感與意象,表現完了,則文學的目的就隨之而終。然宣傳是預先有一種目的,于是只求其如何能達到這目的,至于文學的藝術如何則就不問,所以我們只能謂之宣傳品,而不得謂之文學。如韓柳的目的,只在“詞令褒貶,導揚諷諭”,因為想達到這種目的,于是才去注意文辭,其在文學上的價值,就可想知。所以韓柳的文論,也只可以說是宣傳論,而不能說是文論。
作者:李辰冬(原著) 彭二珂(整理) 單位:湖南科技學院
- 上一篇:作文教學文學素養論文范文
- 下一篇:語文教育漢語言文學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