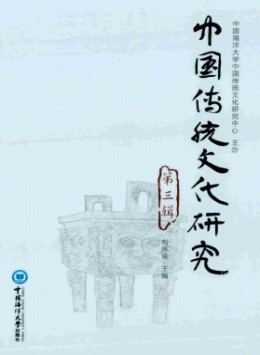傳統文學論文:分析天賦與俄羅斯文學傳統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傳統文學論文:分析天賦與俄羅斯文學傳統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邱靜娟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納博科夫于1937年創作完成并推出《天賦》并非偶然,這一年正值他衷心熱愛的詩人-作家普希金離世100周年。納博科夫此舉是作為對紀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獻禮,也是“最為公開地向現在和過去侵害普希金宗旨的行為發出了挑戰”[4]70,以批駁巴黎俄僑文學“數目派”對普希金的無知和虛無主義態度。小說鮮明地表達了納博科夫對普希金的崇敬仰慕之情,以及他堅定繼承普希金傳統的決心,確認并維護了普希金在俄羅斯文學史上崇高神圣的地位。作家依照對待普希金的態度來衡量俄羅斯批評家的優劣,更重要的是,借文學青年費奧多爾勤奮學習文學傳統(尤其是普希金傳統)以發展壯大自己文學天賦的流亡生活,普希金的文學遺產多次出現在《天賦》中,它們或是普希金作品的引文、題詞、主題,或是能引人聯想到其作品的相似物,或是對普希金藝術手法的發展等等,不一而足,普希金由此成為這部多主題小說的主要主題,并與費奧多爾尋父的主題交融在一起。納博科夫讓讀者感受到了普希金生機勃勃的氣息,領略到這位俄羅斯民族文學奠基人的恒久魅力。作家為筆下男主人公取名費奧多爾•戈都諾夫,它或多或少與普希金的作品(普希金的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相聯系。納博科夫同時讓費奧多爾的保姆來自與普希金的保姆阿琳娜•羅季昂諾夫娜相同的地方。小說第一章展示了費奧多爾詩歌學徒期的部分詩篇,它們都依照四音步抑揚格書寫而成,這是由羅蒙諾索夫創立、并經普希金之手使之不朽的韻律。費奧多爾對文學道路上的對手孔切耶夫暗懷類似沙萊里的妒忌心理(普希金的小悲劇《莫札特與沙萊里》),想象只有用毒酒方可遏制對手的天資(當然,這只是費奧多爾心地卑劣時的想法,后來,已經成熟自信的費奧多爾與孔切耶夫成為文學上的知音)。費奧多爾還通過假想的對話表達了對普希金的敬意,確認并維護了后者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宗主地位。第二章是費奧多爾對父親的回憶。戈都諾夫•切爾登采夫的普希金主題與父親的主題基本吻合。費奧多爾受普希金作品的啟發,想象出追隨父親———一位著名的昆蟲學家和旅行家去中亞和中國的旅程。費奧多爾早就有意寫一部與父親有關的作品,只是時機尚未成熟,閱讀普希金的散文,激發了年輕詩人的創作力,也使他找到了適合自己天賦的文學體裁,他從寫詩轉向寫作散文。在揣摩散文創作藝術的過程中,費奧多爾把普希金的作品當成學習的范本,繼而把現實生活與普希金作品、父親與普希金混淆在一起。因此,父親的形象其實融合了父親本人和普希金兩個人物。費奧多爾想象中的中國之行,可看作是納博科夫對普希金和自己曾懷有的夢想的補償。第三章是費奧多爾被迫搬家,他從研讀普希金作品轉向學習果戈理作品。柏林的俄羅斯僑民和當地居民給費奧多爾提供了“庸俗性”的絕佳樣本,他見識了形形色色的庸俗人物,他的新居生活是一次發現“庸俗性”的旅程,而果戈理的藝術則為如何嘲笑“庸俗性”樹立了榜樣(在《尼古拉•果戈理》一書中,納博科夫挑出“庸俗性”作為果戈理藝術攻擊的主要目標),納博科夫讓年輕的作家費奧多爾繼承了果戈理的藝術成果———嘲諷庸俗。但甚至學習果戈理的主題仍然多少與普希金有關,因為是普希金首先發現了果戈理諷刺庸俗的才華:在《關于<死魂靈>的第三封信》中果戈理寫道:“外界對我有不少議論,在分析我的這個方面那個方面,但沒有人指明我的主要的本質。唯有普希金一人早有覺察,他總是對我說,還沒有一個作家具備這樣的才能,把生活中卑下庸俗的品質表現得這樣鮮明,把卑劣者的卑下庸俗之態刻畫得這樣有力,使得那些極易在眼前滑過的細微之處能在大家眼中呈現為龐然大物。這就是我所獨具而為其他作家所缺少的主要稟賦。”[5]151-152很明顯,費奧多爾實際是透過普希金的蒸餾器汲取著果戈理的精華。第四章是費奧多爾滑稽模擬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傳記。這里,費奧多爾用果戈理的手術刀,對傳主這位自由知識界的寵兒施行了殘酷而有趣的活體解剖。在19世紀60年代俄羅斯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革命民主主義者以普希金的《現代人》作為主要論壇,開展反對純藝術的運動,旨在推翻普希金的權威地位。因此對崇尚純藝術的費奧多爾(維護藝術的純潔也是納博科夫的信念)而言,普希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代表了俄羅斯文化史中兩條對立的路線,車爾尼雪夫斯基代表了美學上的功利主義,對普希金的評價是他最脆弱的部位。費奧多爾對這位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進行惡搞,并稱其為“參觀阿佩里斯畫室的靴匠”,這個評價來自于普希金1829年創作的寓言詩《鞋匠》:鞋匠對畫家的作品指手畫腳,畫家最終忍無可忍,讓他別對補鞋外的事橫加評論。費奧多爾以此來嘲諷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懂藝術。《天賦》里費奧多爾的傳記被拒絕發表,納博科夫《天賦》的第四章同樣被俄僑雜志禁止發表,其原因都是因為蓄意嘲弄了19世紀60年代俄國最進步的人士。但費奧多爾比現實中的納博科夫幸運,他的傳記雖經波折卻很快出版,《天賦》完整的版本卻是此書創作完成十幾年后才得以在美國問世。納博科夫認為這是“生活不得不模仿它譴責的藝術的一個絕佳的例子”[6]413。作家可能預見到作品所要遭受的命運,好像要預先采取防止刪除的措施,在第五章中對被清洗的章節加以戲擬式的評論,評論嘲諷了評論者學識淺陋。這種技巧就像普希金當年所為,他在《魯斯蘭與柳德米拉》的第二版前言中沒為自己辯解,卻復制了某些對他的作品所作的評價。費奧多爾表達了自己對死亡的態度:在宴飲狂歡中微笑著迎接死神,使人聯想到普希金的《瘟疫流行時的宴會》。《天賦》結尾的段落以在韻律上模仿奧涅金詩節收束全書。對普希金傳統的學習、借鑒、利用、改造與評價貫穿了費奧多爾的整個學習成長生涯。因此,閱讀中讀者始終能夠真切感受到這位早已辭世的詩人活生生的存在。普希金仿佛從來未曾離開,在他暫時隱去100年之后,在納博科夫的《天賦》中,普希金歸來了!
針對果戈理的影響問題,1966年納博科夫在答記者問時說道:“我那時很小心,盡量不學他。作為一個老師,他疑點很多,很危險。”[7]106其實,對納博科夫的一面之詞讀者盡可不必完全相信。早在納博科夫俄語創作時期,就有僑民批評家發現了納博科夫與俄羅斯諷刺大師果戈理、謝德林在創作上的共同性。自傳體作品《天賦》更是暗示了作家對果戈理諷刺藝術的學習。在費奧多爾的學習生涯中,果戈理這位俄羅斯文學的散文之父,是他繼普希金之后要借鑒的一個重要對象。《天賦》第三章描述了費奧多爾學習果戈理的經過。費奧多爾借著《死魂靈》的翅膀,踏上了發現庸俗的旅程。路途終點,他已是一名初步形成自己風格的作者了。費奧多爾以果戈理為典范,學習借鑒果戈理的諷刺藝術,嘲諷了各種庸俗,后來,他還接過前輩作家的手術刀,對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進行了“活體解剖”(費奧多爾認為車氏誤導了俄羅斯文學)。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納博科夫綜合并發展了白銀時代作家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觀點,把果戈理和他的作品從社會歷史批評的模式中解放了出來。納博科夫認為,果戈理完全不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欽差大臣》、《死魂靈》等作品也完全不是忠實反映生活、暴露生活中一切腐朽丑惡和不合理現象的現實主義杰作,“把他的戲劇當作社會諷刺和道德揭露作品意味著錯過了它主要的東西”[8]59,“在《死魂靈》中尋找真正的俄羅斯現實生活是無益的”[8]78。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納博科夫有意忽視了果戈理作品大量的現實內容,而認為他的世界是由眾多次要人物組成的“夢幻世界”[8]68,他的作品充斥了形形色色這樣的人物,在戲劇中,這些次要人物由出場人物提及;在小說里,果戈理通過“各種補充說明、隱喻、比喻和抒情插敘使小說中的次要人物活躍起來”[8]83。這些次要人物,有些是作者創造出來、在作品中存在但從未出場的,還有一些人物是由作品中的人物杜撰出來的,“他們不是影子,而純粹是幻影了”[8]64。他們不具有情節意義,經出場人物提及后,在后文中絕不會再出現。果戈理無疑有別于契訶夫必讓懸置的槍走火的精簡手法,而納博科夫認為次要人物的魅力就在于“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現實化”[8]61。納博科夫指出,果戈理的夢幻世界也不是完全與現實生活絕緣,它的道德內涵是對庸俗的批判。“指斥什么為庸俗,我們不僅作出了審美的評斷,還建立了道德的法庭。”[8]388庸俗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惡習”,在納博科夫眼里,它是“假理想、假同情和假聰明。欺騙是真正的市儈的忠實同盟”[8]385,“俄羅斯自從學會思考以來,所有受過教育的、敏感的和自由思考的俄羅斯人,就深深領略過它的賊頭賊腦和糾纏不休”[8]73,“在與俄羅斯有緊密聯系的民族中,德國是這樣一個國家,那兒不僅不嘲笑庸俗習氣,它還成為民族精神、習慣、傳統和社會氛圍的一個主要品質”[8]73-74,納博科夫還從歌德的《浮士德》里嗅出了庸俗的氣息。納博科夫認為《死魂靈》誕生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百年前,當由黑格爾和施勒格爾(加上費爾巴哈)調制的醉人的雞尾酒影響彼得堡的時評家時,果戈理在那篇故事里,用自己巨大的天才順帶提及了滲透德意志民族的不死的庸俗的幽靈。”[8]74納博科夫還從文學作品中開據了一連串的庸俗之徒,并指出在果戈理的夢幻世界里也不乏這樣的人,“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死魂靈》中有一些傲慢的死魂靈存在,他們是市儈”[8]78,如乞乞科夫。這樣,納博科夫自出機杼地解讀了果戈理的作品,并為自己的作品尋到了傳統的“根”。《天賦》里,果戈理諷刺藝術的種子在納博科夫的作品里發芽生長,最終枝繁葉茂。在第三章,納博科夫借果戈理藝術的東風,讓讀者見識了俄僑眼中德國社會生活里的“當代死魂靈”。費奧多爾通過學習果戈理,獲得了果戈理式的慧眼,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庸俗分子(次要人物),又用果戈理式犀利的手筆,撕下了他們的偽裝,暴露了他們庸俗的本質。這些人物除了直接出場的外(濟娜的母親和繼父以及費奧多爾的一些熟人),大部分人是由濟娜提及的。在本章結尾部分還有從一個作家那里脫口而出的虛幻人物。他們正如果戈理筆下的次要人物一樣,一次出現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但這不妨礙他們在作品中活靈活現、躍然紙上。如為了表現一位叫特拉烏姆的市儈(他是濟娜所工作的律師事務所的幾個雇主之一),納博科夫所用的筆法就完全是果戈理式的。作家把他所理解的庸俗的種種表現諸如自高自大、自私虛偽、裝腔作勢、矯揉造作、老于世故等,都集中在這個酷似半輪月亮的矮子身上。而且納博科夫塑造的這個走樣的胖子,還多少具有了乞乞科夫的特點。
《天賦》是一部復雜的作品,它是“文學百科全書”[2]147,涵蓋了十九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的俄羅斯文學和納博科夫創作的幾乎所有主題[9]189,同時它也是“一部獨特的教育小說,描寫了藝術家創作的成長過程”[2]147,它敘述了俄國青年作家費奧多爾在旅居柏林三年多的時間里(1926,4,1-1929,6,29)創作才華的發展和成熟。小說結尾,雖然費奧多爾計劃中的寫作尚未付諸筆端,但他此時已經具備成為大作家的潛質,他還預見到了小說的成形,對完成作品充滿了信心。納博科夫借費奧多爾的學習生活告訴讀者,作家的才華并非天賦,才華是天才加上刻苦學習傳統,繼承、借鑒并超越傳統的結果。《天賦》具有很強的自傳性。雖然納博科夫一貫厭惡把作品中的人物與自己混為一談,但俄僑批評家還是很快從費奧多爾身上發現了作者的影子,納博科夫本人也在《天賦》一書和英文版前言中含蓄提到作品和自己的關系。可以說,雖然不能完全把主人公與納博科夫等同起來,但費奧多爾文學才能的成長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創作歷程,費奧多爾所表達的文學觀念、他對俄羅斯詩人、作家的評點則可以代表納博科夫本人的觀點。這些可從納博科夫的自傳、訪談錄和文學講稿中得到印證。納博科夫靈活地運用多種文體來表現費奧多爾作為藝術家的成長過程,大體相應于俄羅斯文學的發展軌跡:第一章展示了費奧多爾《詩集》里的詩歌和青年詩人的創作熱情和過程,他的詩歌創作時期對應于以普希金詩歌為代表的黃金時代;第二、三章費奧多爾轉向散文創作,他的散文學徒期對應于俄羅斯文學的普希金果戈理時代,他首先模仿普希金的韻律散文,然后學習果戈理的諷刺藝術,這部分的語言風格也由詩意抒情轉向揶揄諷刺;第四章費奧多爾為批駁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實用主義文學觀念,以車氏作為靶子,舉起果戈理諷刺藝術的火槍開火進行文學射擊訓練。納博科夫對這位批評家持雙重態度,他既欽佩車氏為公眾利益的獻身精神,又鄙棄他的文學實用主義,因而該章語體時而崇高莊重,時而譏誚挖苦;第五章費奧多爾在經歷傳統的洗禮后,邁進現代。于是本章成為現代主義文學形式手法表演的舞臺。費奧多爾對文學傳統博采眾長,去偽存真,吸取精華,剔除糟粕,憑作家和批評家對普希金的態度來裁決評斷他們的優劣,而且把他的每一個藝術成就都放在普希金的天平上來衡量。“普希金,他的生活和創作被認為是《天賦》的音叉。”[9]190《天賦》第一章費奧多爾借假想的談話,評說了俄羅斯文學的成敗得失,捍衛了普希金的崇高地位,表達了決心維護藝術純潔的態度。談話同時反映出未來作家對傳統孜孜以求的態度:以一流作家為榜樣,兼顧其他。這也是納博科夫本人的立場。《天賦》中歷數了大量的俄羅斯著名作家和詩人的優劣,還有對俄羅斯文學界和批評界知名人物的暗指或影射。俄羅斯作家還走進《天賦》,成為小說的人物,書中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并存,這些人物成為費奧多爾學習、緬懷或抨擊的對象。“作者公開從19世紀散文汲取養料,直接用它充實自己。”[9]189小說第一章描寫費奧多爾以詩歌起步,后轉向散文。費奧多爾首先以他崇拜的普希金為老師,對傳統狂熱的學習熱情甚至使普希金滲入到他的生活,他把普希金及其作品與現實混淆在了一起。后來費奧多爾被迫遷居,他從詩意的超現實墜入充斥形形色色庸俗的人世間,新居的環境庸俗不堪,新居的生活成為庸俗性的發現之旅,流亡者版的《死魂靈》則是旅行者的指南。掌握了果戈理的藝術后,費奧多爾用這把利器來抨擊與普希金藝術觀點相左、自認為是遺毒深遠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為寫作傳記,費奧多爾博覽群書,鉆研19世紀6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學習傳統積累知識的過程里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隨著《車爾尼雪夫斯基傳》的面世,吸收了傳統精華、被傳統充實提高的費奧多爾已經作為一個成熟作家浮出水面,他正醞釀著一部新的作品……相應于費奧多爾學習俄羅斯文學傳統促進了自己創作才能的增強,納博科夫在《天賦》中大規模引用文學作品,使其成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對文學傳統的有效借鑒利用充實了作品的肌體。這是納博科夫藝術創作的重要方法和技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普希金作品的形象、結構、思想、語言等被密密地織入《天賦》:“在《天賦》第二部分的檔案資料中,男主人公說,流亡的使命在于把父輩的贈品傳給后代。這樣的贈品首推普希金傳統。”
在覓得普希金的珍藏后,費奧多爾(或者說納博科夫)的文學探險之旅并未就此止步。果戈理、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別雷等,都是主人公和作家在探險歷程中挖掘的寶藏。旅程的終點,費奧多爾作為作家的創作才能日趨成熟和完善,納博科夫則為俄羅斯文學傳統譜寫了一曲深情的贊歌。如果說,祖國文學的傳統陪伴費奧多爾走過生命中最陰暗的日子,支持了他文學天賦的成長,主人公的創作道路表明:才華并非天賦,對文學傳統的學習是作家成長的基礎,那么“對納博科夫而言,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是幫助他確定自己創作和生活道路的基礎”[9]188。納博科夫在《天賦》篇首題詞“憶母親”,就充分表達了他對俄羅斯文學傳統的款款深情、摯愛、依戀和感激。“只有在《天賦》中納博科夫才完全表達了對俄羅斯文學傳統的忠誠”[9]190,“19世紀的作家留給他的文學世界,經過分散、豐富、重新認識和發展選題,影響了他虛構的形象”[9]188,“作家把引證作為方法,公開使用別人的言辭,就像自己的一樣。他不能拒絕天才的前輩作家”[9]189,“引證充滿了小說的所有層面———情節、風格、思想。……19世紀文學的例子撲面而至,作家仿佛信手拈來”[9]190。雖然《天賦》鮮明地體現出納博科夫與俄羅斯文學傳統的親緣關系,但是納博科夫沒有跟在傳統身后亦步亦趨,他充分吸取俄羅斯文學在經過19世紀輝煌發展后積淀的豐富多樣的經驗,進行加工、改造和完善的基礎上,實現了自己的創新追求。小說結尾主人公費奧多爾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路,納博科夫也找到了自己的創作風格———超越創新。承載著厚重傳統的《天賦》沒有被傳統的光暈所遮擋,它煥發著作家創新的光輝,“《天賦》在某種意義上是在領會19世紀俄羅斯文學風格經驗基礎上的新的詩學形式”[9]189,《天賦》是作家對自己在學習傳統基礎上所做的創新的回顧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