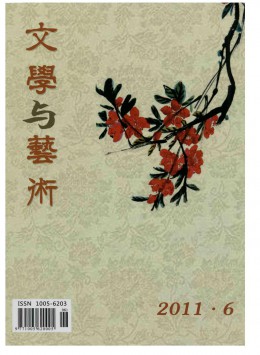文學作者論文:談?wù)撌吣晡膶W中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文學作者論文:談?wù)撌吣晡膶W中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李 旺 單位:南京大學
一、“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的出現(xiàn)
“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的寫作在一九四九年后蔚為大觀,他們的寫作貫穿了“十七年”和“”,在某些歷史時段他們甚至是唯一被推舉的寫作群體。如一九五八年“”、一九七三、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從一九四九年到“”結(jié)束這近三十年,“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扮演了既不同于國統(tǒng)區(qū)作家,又不同于解放區(qū)作家的獨特角色。他們的寫作行為被作為社會主義的寫作標本而受到贊揚。這和一九四九年后執(zhí)政黨可以完全貫徹《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著直接關(guān)系,把一種設(shè)想變?yōu)榱藢嶋H操作。此外,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其它三種因素與“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寫作之間,或者有或隱或顯的淵源關(guān)系,或者是彼此共享了近似的思想理念,在歷史軌跡中有著疊印與重合。這里先簡單解釋一下將要涉及到的幾個概念之間的關(guān)系:大眾、民眾、工農(nóng)兵。在新文學啟蒙者的眼中,大眾和民眾是指不具備現(xiàn)代意識的國民,范圍很廣。而工農(nóng)兵,則是建立在階級學說基礎(chǔ)上,以是否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同盟為標準而進行的劃分。前者所指要大于后者,包括后者。二者存在的交集與背離也可說明它們分屬的五四文學傳統(tǒng)與延安文學傳統(tǒng)有所因應但終又迥然有別的關(guān)系。一九二一年,文學研究會就曾在機關(guān)刊物《文學旬刊》發(fā)起過“民眾文學底討論”。這里的民眾文學研究會同人西諦(鄭振鐸)、俞平伯、朱自清、葉圣陶、許昂諾等人都撰文發(fā)表意見。“要想從根本上把中國改造,似乎非先把這一班讀通俗小說的人的腦筋改造過不可。”(西諦)[1]這里的“民眾”顯然是包括通俗小說的主要讀者———城市市民,以及所有可以識字看小說的人。“我們底目的原是要引導民眾,向著新的路途,換句話說,就是要打破他們沉淪底夢。”(俞平伯)[2]之所以提出“民眾底文學”這一議題來討論,是要喚醒民眾,達到啟蒙的目的。文學研究會同人在談到自己與民眾的關(guān)系時說:“但我不信人間竟有這樣的隔膜;同是‘上帝的兒子’,雖因了環(huán)境底參差,造成種種的分隔,但內(nèi)心的力量又何致不相通呢!”(朱自清)[3]“‘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我們與他們底中間,多少有些隔膜,這是不可免的。但我總相信以人們了解人們,要比莊周惠施去猜想魚樂容易得多。”(俞平伯)[4]“我們底目的是要引導民眾向著新的路途”,是引導者的昂然姿態(tài);“同是上帝的兒子”;但又是互相友愛的;“以人們來了解人們”,是人格平等的。與啟蒙者“我們”的引導姿態(tài)一并彰顯的是“我們”與“他們”平等的人權(quán)思想。在這次討論中,出現(xiàn)了在“民眾化底文學”和“為民眾底文學”之間進行選擇的躊躇(朱自清),以及為了讓農(nóng)人、傭工易于接受新思想,提出了簡化漢字的建議(許昂諾)。朱自清提出的問題在以后掀起的文學大眾化討論,文學形式之新舊爭論中將被反復提及,為誰與如何為的問題一直糾纏到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板上釘釘。一九三二年,《北斗》雜志發(fā)起“文藝大眾化”討論。這次討論的政治考慮要比文學研究會的討論濃烈得多。討論中對“工農(nóng)通訊員”的倡導和后來的業(yè)余作者培養(yǎng)有著耀眼的聯(lián)系,工農(nóng)不再是抽象的對象,而是和具體的政治任務(wù)發(fā)生了關(guān)系。還是“起應”時代的周揚就說:“工農(nóng)通信員的活動是和重大的政治任務(wù)相聯(lián)系的。這些任務(wù)不一定帶著文學的性質(zhì),但普羅列塔利亞的創(chuàng)造力,經(jīng)過工農(nóng)通信這個練習時期之后,是會達到文學的領(lǐng)域的。這是很自然的過程,因為政治通信可以使工人發(fā)展他的潛伏的文學才能。”[5]瞿秋白也有類似的意見:“要開始經(jīng)過大眾化文藝來實行廣大的反對青天白日主義的斗爭,就必須立刻切實的實行工農(nóng)通訊運動。工農(nóng)通訊員將要是一種新的群眾的文藝團體的骨干,這可以是很多種的小團體,在這種團體里面才能夠得到現(xiàn)實生活的材料,反映真正群眾的情緒,”[6]也是這次討論的發(fā)起者陳望道說:“因為不大眾化,將永遠只能這樣把守一角,不能大得群眾,盡其組織群眾的機能。”。[7]一九三二年也有工人通信員、工人作家的提法見諸報端。[8]高爾基的頻頻露面見出蘇聯(lián)文藝政策對中共文藝政策與日俱增的影響。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把文藝為工農(nóng)兵與否和道德優(yōu)劣聯(lián)系起來:“離開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須加以適當?shù)男拚!保?]他說:“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jié)經(jīng)驗,研究方法,在創(chuàng)作上就叫做表現(xiàn)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10]文藝為不為工農(nóng)兵是一個為哪個階級服務(wù)的問題;是正確還是錯誤與是否需要“修正”的問題、是一個有無“真正的好心”的問題。這種政治與道德同一的判斷方法在后來演變成為文藝界劃分敵友的普遍標準。如果說新文學發(fā)生之時對“民眾化底文學”還是“為民眾底文學”的考慮構(gòu)成了日后文藝為工農(nóng)兵方向的遠源,左翼文學的“工農(nóng)兵通訊員”倡導成為“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的前奏,的講話成為一種神諭般的指示,那么蘇聯(lián)的文藝政策則對中共文藝政策發(fā)生了直接且迅捷的影響。比如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七年五到六月間的講話《文學藝術(shù)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在九月被譯成中文刊登在《文藝報》上。佛克瑪認為,赫魯曉夫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蘇聯(lián)發(fā)展地方文化與地方勢力以削弱反對派(有自己主張并且藝術(shù)上不拘泥于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作家藝術(shù)家)的做法在中國得到更為廣泛更為成功的運用,那就是當時中國全國范圍內(nèi)的下放運動和業(yè)余文化運動。[11]赫魯曉夫還提出黨性與通俗性并不沖突的觀點。[12]對思想敏銳形式上先鋒的作家的警惕,倡導文學的通俗性,這種被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共享的文藝政策確實會對“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實踐和標本的推出
一九四七年冀南書店出版了一套“工農(nóng)兵叢書”,[13]文藝工作者把工農(nóng)兵所唱所說的歌謠、故事拿來,經(jīng)過改編加工而成。這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次較早的實際操作。《文學戰(zhàn)線》這份雜志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東北創(chuàng)刊,(先在哈爾濱出版發(fā)行,后轉(zhuǎn)到沈陽)該刊是中共進入北京前重要的文藝刊物,工農(nóng)兵的創(chuàng)作在《文學戰(zhàn)線》時期已經(jīng)進入在較大范圍推行的實踐階段,在“十七年”和“”中大行其道的“文藝小組”在這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且推出了“工人創(chuàng)作”特輯。嚴文井的文章《注意廣大工農(nóng)兵群眾的文藝活動和要求》,[14]提出工農(nóng)兵自身的寫作要求,比如從知識分子寫工農(nóng)兵到工農(nóng)兵自己寫。即將建立全國政權(quán)的中共在貫徹的文藝工農(nóng)兵方向時也日趨迫切激進。這篇文章發(fā)表后的第二年,該刊刊登了沈陽第一機械廠文藝小組給編輯部的信:文學戰(zhàn)線同志:我們很感謝貴社幫助我們成立了文藝小組,并于四月十八日收到一卷一期《文學戰(zhàn)線》一份。小組全體同志特向你們致敬。我們工人對于寫文章很外行,可是不能負了你們的好意,我們自己也愿意練習練習,拿筆桿,今天寫了兩篇又短又幼稚的東西,大膽地寄給貴社,望多指導與修正。全小組同志表示要經(jīng)常寫下去,下決心把文藝小組健壯起來,并擴展到全廠去。[15]以寫工人、工廠聞名的作家草明對工人作者全部是贊嘆:他們都是未來的工人文學家,他們有那么豐富的動人的生活內(nèi)容,他們有生動的語言,他們有那么高貴蓬勃的創(chuàng)作熱情。他們已開始認識文藝活動對他們生活的重要![16]在文藝政策的執(zhí)行者看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寫作要求,只有這些在工廠參加生產(chǎn)的工人是最有可能完成的,“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參加生產(chǎn)滿足了“源于生活”這一條件,至于“高于生活”所需要的潤飾加工這種技術(shù)活就只需那些脫離生產(chǎn)的作家?guī)鸵幌旅ΑR痪潘木拍旰蟮淖骷抑挥姓驹凇叭ブ行幕摹摺保?7]這一立場才能被中共文藝政策所接受,因此,在“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推出之前,作家只有通過不斷的思想改造才能獲得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資格;在“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推出之后,作家只能變?yōu)闉椤肮まr(nóng)兵業(yè)余作者”寫作服務(wù)的技術(shù)員。我們來看兩個“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的典型。幾乎不識字的作家高玉寶是一九四九年以來被國家宣傳機構(gòu)樹立起的第一個業(yè)余寫作的楷模。他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開始寫作《高玉寶》初稿。《解放軍文藝》在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選載了小說的部分章節(jié)。[18]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題為《英雄的文藝戰(zhàn)士高玉寶》的文章為其宣傳,一九五五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高玉寶》單行本。小說第九章《半夜雞叫》因長期入選小學課本而幾乎人盡皆知。高玉寶寫作行為的發(fā)生,與和奧斯特洛夫斯基作為他的精神資源而存在有關(guān)。有感于對才子佳人故事的厭惡,[19]高玉寶提筆寫作耕田漢故事。而來自蘇聯(lián)的道德楷模奧斯特羅斯基又是他的精神“老大哥”:“我想,人家是個瞎子都能寫出書,我們一個睜眼的,雖然沒有文化,慢慢學著習,總是比瞎子好的多吧。我更下定決心,非把書寫出來不可。”[20]讓我們看看幫他修改的作者是怎樣說的:“對于修改,高玉寶并不放心。最初,高玉寶同志對這點有很多顧慮的,他怕那些了解他的歷史的同志和鄉(xiāng)親們說他編造自己的歷史,改變了某些現(xiàn)在還活著的人的個性。可是,如果不這樣修改,作品就會大大降低它對讀者的教育意義。[21]與社會主義的強大通過高玉寶以及《高玉寶》的雙重故事得以生動地散播。高玉寶不再是真實的個人,而是一個社會主義文藝創(chuàng)作的一個幻象的載體。高玉寶是個農(nóng)民作者,胡萬春則是工人作者。他遠比高玉寶多產(chǎn)。并且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也還在寫。胡萬春的小說《骨肉》在一九五七年的世界青年聯(lián)歡節(jié)舉辦的國際文藝競賽中獲獎,被評為世界優(yōu)秀短篇小說。我們來看茅盾給他的一封信:“您在十一年的時間內(nèi),從一個半文盲達到今天的水平,的確是難能可貴的,雖然是受了黨的培養(yǎng)而致此,但是,您自己的努力該是主要的因素。十二年來,黨對于工農(nóng)子弟的培養(yǎng),其數(shù)量當以萬計,但能夠有所成而且鞏固下來,發(fā)展下去的,卻為數(shù)不多,而您是其中之一,這中間就有個自己努力不努力的問題。我常說,今天的年青一代的作家比我(或者同我同輩的作家們)年青時代要強得多;我在您那樣年齡的時候,寫不出您所寫的那些作品,在這一點上,就因為我那時是在反動政府壓迫之下,不用說得不到黨的培養(yǎng),那時連黨也還沒有成立呢!”[22]胡萬春這個只念過兩年小學的工人作者成為工業(yè)題材小說的代表人物。在茅盾的信中,共產(chǎn)黨的作用被突出出來,一個有深厚文學修養(yǎng)和成熟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五四”時代作家對這樣一個工人業(yè)余作者表達的卻是羨慕之情。三、業(yè)與余和公與私:一場假想的資產(chǎn)階級文藝與無產(chǎn)階級文藝對壘20世紀50年代的刊物《工人習作》、《群眾文藝》、《文藝月報》、《萌芽》、《新港》、《人民文學》等都推出了“工人創(chuàng)作專輯”、“群眾文藝特輯”,工農(nóng)文藝已經(jīng)成為了一九四九年后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必然部分。在宣傳、培養(yǎng)“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典型的同時,組織者又對那些不符合、越出培養(yǎng)規(guī)則的思想言行進行打壓和批判。在“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作為一項文藝政策和文藝制度逐漸固化的過程中,業(yè)與余的緊張,公與私的斗爭成為一場假想的資產(chǎn)階級文藝思想與無產(chǎn)階級群眾文藝觀念逐鹿爭鋒的焦點。這兩組對立的詞或話語象征其實是二而一的關(guān)系:脫離生產(chǎn)就是脫離人民就不再是工農(nóng)兵,那非工農(nóng)兵的寫作就不是為公和為社會主義的,那就是和資產(chǎn)階級的寫作沒有了區(qū)別,那就必然有資產(chǎn)階級的名利思想和個人觀念。這就是對無產(chǎn)階級和社會主義的背叛。這當然就是政治和道德的雙重錯誤。其實,這樣的定位如同在假想的對壘中一次次假想的試刃和自弒。對無產(chǎn)階級文藝圖景的塑造過程,在或以反面典型刺激或以光輝樣板引導的勸說、告誡中完成。
一九五六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者會議,會議報告有這樣的警戒:“某些青年作者受了這種思想的毒害,便想入非非地一心要寫出一部世界聞名的巨作來獵取地位、名譽和金錢,可是他忘記了文學創(chuàng)作為社會主義建設(shè)服務(wù)的目的,事實上,這種人是寫不出作品的,至少是寫不出好作品的。在黨的領(lǐng)導下,對于上述這些反動言論和錯誤思想,文藝界已經(jīng)給予了徹底的清算和批評,這對于培養(yǎng)青年創(chuàng)作者、繁榮文學創(chuàng)作是具有重大意義的。”[23]會議并且明確提出要加強“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培養(yǎng)的組織性和計劃性:“在培養(yǎng)工人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工作方面,還存在缺乏組織性和計劃性的混亂現(xiàn)象。這表現(xiàn)在把某些初露頭角的寫作者過早地從原有工作崗位調(diào)開,使他們脫離了哺育他們的土壤。這就是一些初學的寫作者中途夭折,結(jié)果不得不讓他們重新回到生產(chǎn)崗位,從頭做起。這一現(xiàn)象是應該糾正的。”[24]一九五八年“”時期對“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的推崇走向更為激烈的地步。地方省市也召開工農(nóng)文藝創(chuàng)作者會議,比如湖南,對此,《新苗》雜志的社論這樣寫道:“工農(nóng)文藝創(chuàng)作者是工人階級隊伍最可靠的新生力量。因為工農(nóng)文藝創(chuàng)作者本身,就是工農(nóng)勞動戰(zhàn)線上的一員,有豐富的生產(chǎn)知識和斗爭知識,和廣大勞動人民有著血肉的聯(lián)系,對社會主義的愛和對階級的恨,異常鮮明而熱烈,使用的是真正生活的語言……”[25]在這一年掀起的新民歌運動中,“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已經(jīng)成為產(chǎn)出的主力軍。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青年業(yè)余文學創(chuàng)作積極分子會議”,此次會議對于一九四九年后的“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寫作而言,有著歷史節(jié)點的意味。它以會議的形式為“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進行了最終命名、定性:“跟過去歷次的文藝會議不一樣,參加這個會議的人,是我們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支新軍。你們是從工農(nóng)兵群眾中來的。你們又會勞動又會創(chuàng)作,拿起槍來是戰(zhàn)士,拿起筆來也是戰(zhàn)士。你們既是生產(chǎn)的隊伍、打仗的隊伍,又是創(chuàng)作的隊伍。”[26]在周揚的講話中,無產(chǎn)階級文藝隊伍呼之欲出。即正確的工農(nóng)兵血統(tǒng),鮮明的階級斗爭意識,寫作者首先被規(guī)定為敵我陣營角逐中沖鋒的戰(zhàn)士。周揚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并闡述了“三結(jié)合”的寫作手法,這是“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寫作走向極端的變體,“為了迅速而又健康地發(fā)展社會主義的文藝創(chuàng)作,我們需要采取領(lǐng)導、作者、群眾三結(jié)合的方法。領(lǐng)導要向創(chuàng)作者指明方向,提出任務(wù)、在寫作過程中給以幫助和指點。許多青年業(yè)余作者從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中感到,如果沒有領(lǐng)導的指點和啟發(fā),沒有群眾的幫助,作品就寫不好。你們說,要請教領(lǐng)導,請教群眾,這是對的。這樣,政治統(tǒng)帥文藝,個人智慧和集體智慧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作就不再是單純的個人事業(yè),而真正成為黨的事業(yè)的一部分,人民群眾的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了。”[27]公而忘私的革命性,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崇高性,周揚的講話塑造出了無產(chǎn)階級文藝隊伍的圖景。這一圖景讓寫作完全喪失了個人性和獨創(chuàng)性。周揚雖在“”中被打倒,但這種寫作方式卻是“”中最為主流的方式。這說明了對無產(chǎn)階級文藝烏托邦的想象,不同的文藝政策施行者使用的邏輯沒有變。正是“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的業(yè)余性才造就了其寫作不可代替的專門性,這是這一無產(chǎn)階級文藝模型最耐人尋味的吊詭之處。周揚在業(yè)余作者積極分子大會上說:“我們的業(yè)余的文藝創(chuàng)作者,千萬不要想著專業(yè)化。我們文藝隊伍,包括專業(yè)和業(yè)余兩部分。業(yè)余是大量的,專業(yè)只能是少量的。”[28]同時期的這樣的觀點非常普遍:“在業(yè)余創(chuàng)作中,‘業(yè)’和‘余’的關(guān)系一定要處理好。既是業(yè)余作者,既要首先做好崗位工作,其次才是利用業(yè)余時間搞好文藝創(chuàng)作,要努力做到生產(chǎn)是能手,創(chuàng)作是積極分子。”[29]到會的積極分子也紛紛表態(tài)要杜絕資產(chǎn)階級寫作的名利思想,永遠不脫離生產(chǎn),堅決作思想的紅色宣傳員。[30]同類的文章都強調(diào)既生產(chǎn)又寫作。[31]此前的“湖南省工農(nóng)兵創(chuàng)作者會議”也有類似的警告:“現(xiàn)在有個別工農(nóng)文藝創(chuàng)作者,在報刊上發(fā)表了一兩篇作品,就驕傲自滿起來,不服從車間的調(diào)配和監(jiān)督,不愿意為中心工作服務(wù),迷戀于搞‘大’作品,想脫離生產(chǎn)當‘職業(yè)作家’,這顯然是要不得的。今后,應該通過勞動和群眾運動的鍛煉,使自己更健康更迅速地成長,成為工人階級的文藝家,才能寫出無愧于英雄時代的詩篇。”[32]是否有名利思想是“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培養(yǎng)政策最關(guān)注的問題,因為名利思想和個人的一己之私有關(guān),這對于一個強調(diào)集體公有的國家而言有著天然的危險性。這場假想的文藝對壘之所以綿延數(shù)十年之久,其動力是不斷革命的政治背景。“為了進一步抓好這一工作,我們首先要明確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用什么樣的方法培養(yǎng)。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階級斗爭,存在著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爭奪下一代的斗爭。資產(chǎn)階級和修正主義者總是要按照他們的面貌來改造青年一代,千方百計地要把青年拉到脫離革命斗爭,脫離革命群眾的道路,使他們變成為少數(shù)剝削階級和寄生蟲服務(wù)的‘精神貴族’,而我們要把青年作者培養(yǎng)成無產(chǎn)階級文藝的接班人。”“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們也表示要通過寫作捍衛(wèi)社會主義。“在這段過程中,不僅磨練了我的筆桿子,也提高了我的思想,我覺著,咱們工人翻了身,當了國家的主人,不僅要握緊鐵錘、焊槍,搞好生產(chǎn),建設(shè)咱們的新社會,也得要卡住筆桿子,保衛(wèi)和平鞏固咱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不管搞生產(chǎn),還是搞創(chuàng)作,都是干革命。為了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在生產(chǎn)上咱猛干活,在創(chuàng)作上猛寫猛編。”[33]“這個浩蕩的大軍大多是既會生產(chǎn)又會寫作的新型的勞動青年。這支新軍的出現(xiàn),將會給我國整個文藝創(chuàng)作打開一個新局面,將會使的文藝思想得到更廣泛、更深刻的貫徹,也將會大大促進我國整個文藝隊伍的革命化。”
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對壘的想象越偏激,這種爭鋒相對的火藥味就越濃烈。時期最有代表性:“一向把文學藝術(shù)看做神秘、特殊的精神產(chǎn)物的資產(chǎn)階級藝術(shù)觀點,被的新形勢給沖垮了。群眾文藝的時代真正開始了。”[35]一支無產(chǎn)階級文藝新軍的想象,建立在對同樣是想象的資產(chǎn)階級文藝的攻擊、批判之上,一個從未有過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隊伍就在這樣一種自說自話中產(chǎn)生。它成為了這樣一項文藝統(tǒng)治,以其虛構(gòu)性成就了游戲性,以其虛妄性行使了賞罰權(quán)。最后,我們有必要回到這一對壘的源頭及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里,我們可能察覺這種“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寫作以及這場鄭重其事的文藝對壘在始作俑者那里存在著的矛盾抵牾之處。李潔非先生在研究中寫到,在一九四三年在數(shù)月后,對獻禮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四人花鼓《七枝花》等為工農(nóng)兵的、工農(nóng)兵化的文藝表示了喜愛之情,然而他的喜愛是否是由衷的也頗令人懷疑,在戰(zhàn)爭年月過去后的閑暇時間,他“常招李何曾這樣的一流京劇演員到中南海為他唱堂會,而從未聽說把秧歌劇組找來給他唱《兄妹開荒》《夫妻識字》。”[36]把一個有著種種權(quán)用考慮[37]而言不由衷的策略性說法作為法則貫徹了數(shù)十年,這可以說明的是,“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寫作以其神圣性接近了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