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學(xué)的多層次性研究
前言:想要寫(xiě)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十七年文學(xué)的多層次性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lái)靈感和參考,敬請(qǐng)閱讀。

“十七年”文學(xué)具有比較統(tǒng)一的意識(shí)形態(tài)化特征,不過(guò),這仍是就總體上而言的,“十七年”文學(xué)的特征并不能就此而被攬括。於可訓(xùn)指出:“‘十七年文學(xué)’的多種闡釋、評(píng)價(jià)的可能和空間,亦即是它的新的歷史敘述的可能性,無(wú)須到這種高度政治化和高度一體化的歷史語(yǔ)境之外去尋找,它就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這種真實(shí)的歷史語(yǔ)境與文學(xué)文本的相互關(guān)系之中,是這種真實(shí)的歷史語(yǔ)境在生成這些文本的過(guò)程中同時(shí)也給我們留下的一種文本的間隙和裂縫。”(2)雖然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具有強(qiáng)大的塑造作用,但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那些給當(dāng)時(shí)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以及在今天看來(lái)稱(chēng)得上經(jīng)典的作品從來(lái)都不是極端政治化的作品,而是能反映特定時(shí)代生活豐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能體現(xiàn)政治和文學(xué)(人)的復(fù)雜關(guān)系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學(xué)文本中,政治與文學(xué)、個(gè)人與集體不可分離,它們?cè)谔囟〞r(shí)代中以“一幣兩面”而并非以分足鼎立的方式存在。按照政治和文學(xué)二元對(duì)立的思維模式,在面對(duì)文本的過(guò)程中我們永遠(yuǎn)都會(huì)疑問(wèn):對(duì)于“十七年”文學(xué)中存在的個(gè)人與集體的對(duì)立,我們到底應(yīng)該站在國(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角度發(fā)言,還是站在知識(shí)分子的立場(chǎng)發(fā)言?想給這樣的問(wèn)題找到一個(gè)正確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而運(yùn)用這種思維進(jìn)行研究既不能還原歷史的真實(shí)樣態(tài),也不能使新的文學(xué)史研究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因此近些年這種方式的研究已受到不斷的批判和清理。
“十七年”文學(xué)的復(fù)雜性在于它體現(xiàn)了政治與文學(xué)的豐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學(xué)必須擔(dān)負(fù)起弘揚(yáng)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這種“弘揚(yáng)”違反了文學(xué)的精神,那么,它勢(shì)必也對(duì)政治的宣傳無(wú)濟(jì)于事。因此,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必須從認(rèn)識(shí)“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政治與文學(xué)(人)的關(guān)系出發(fā),這里之所以不再關(guān)注政治中的“文學(xué)”和文學(xué)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種“歷史化”的思維下,對(duì)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學(xué)這樣一些本源性的問(wèn)題存而不論,而關(guān)注具體歷史語(yǔ)境中政治與文學(xué)的結(jié)合方式。“十七年”文學(xué)有它特殊的處理政治與文學(xué)、政治與個(gè)人的方式,其政治與文學(xué)的結(jié)合方式也是多樣的,正是因?yàn)檫@種特點(diǎn)才構(gòu)成了“十七年”文學(xué)的多層次性。具體地說(shuō),在“十七年”文學(xué)的作品中,既有政治化傾向明顯的作品,也就是政治性高于文學(xué)性的作品,也有政治和文學(xué)結(jié)合得比較好的作品,還有少數(shù)的注重個(gè)人文學(xué)表達(dá)的作品。而在每個(gè)作品的內(nèi)部,其政治和文學(xué)結(jié)合的方式和程度也同樣有各種各樣的表現(xiàn),有些地方的描寫(xiě)比較政治化、理念化,而有些地方又能夠把政治與人的關(guān)系處理得較好,還有一些地方也會(huì)比較富有生活情趣并暗含一定的個(gè)人立場(chǎng)。也就是說(shuō),這種多層次性即表現(xiàn)在“十七年”文學(xué)的整體創(chuàng)作上,也表現(xiàn)在具體的文本中。就拿“十七年”文學(xué)對(duì)情愛(ài)的表現(xiàn)來(lái)說(shuō),就既有被政治規(guī)范的革命化、階級(jí)化的情愛(ài)描寫(xiě),如《艷陽(yáng)天》中對(duì)蕭長(zhǎng)春和焦淑紅的愛(ài)情描寫(xiě)就是以強(qiáng)調(diào)革命對(duì)于情愛(ài)的絕對(duì)優(yōu)先性為前提的;也有對(duì)革命、階級(jí)中的情愛(ài)的合理表現(xiàn),如《創(chuàng)業(yè)史》中對(duì)梁生寶和改霞的愛(ài)情描寫(xiě),就既包含了革命理性對(duì)情愛(ài)的制約,也包含了情愛(ài)的力量和革命理性所構(gòu)成的沖突和矛盾;還有通過(guò)間接、婉轉(zhuǎn)的方式對(duì)情愛(ài)本能的正面表達(dá),如《山鄉(xiāng)巨變》中多次對(duì)盛淑君和陳大春在約會(huì)時(shí)不經(jīng)意的身體接觸的描寫(xiě)就傳達(dá)了作者對(duì)情愛(ài)本能的肯定;甚至也有對(duì)跨越階級(jí)陣營(yíng)的復(fù)雜的情愛(ài)關(guān)系的表達(dá),如《辛俊地》中對(duì)革命戰(zhàn)士辛俊地和地主女兒桂香的情愛(ài)悲劇的描寫(xiě)就包含了政治與人性的復(fù)雜糾葛……這些情愛(ài)描寫(xiě)方式都是“十七年”文學(xué)所特有的,表達(dá)的是作家在特定歷史語(yǔ)境中對(duì)愛(ài)情的認(rèn)識(shí)和體驗(yàn)。由此,我們不能再單純以“壓抑”和“被壓抑”的模式來(lái)看“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欲望表達(dá),政治中的個(gè)人有不同層次、不同形態(tài)的呈現(xiàn)方式,并且,它們可以和意識(shí)形態(tài)之間形成一種多維的張力關(guān)系。
“十七年”文學(xué)文本中存在多種政治與文學(xué)(個(gè)人)關(guān)系的表達(dá),有些是主流的、顯性的、與政治比較合一的文學(xué)形態(tài),有些是邊緣的、隱性的、與政治有一定差異的文學(xué)形態(tài),也有一些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文學(xué)形態(tài),但這并不意味著“十七年”文學(xué)文本內(nèi)部是各種不同性質(zhì)的內(nèi)容的雜糅。對(duì)此,詹姆遜的解釋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他認(rèn)為,“每一種文類(lèi)-敘事模式,就其存在使個(gè)體文本繼續(xù)發(fā)生作用而言,都負(fù)荷著自己的意識(shí)形態(tài)內(nèi)容。”“在一個(gè)文本內(nèi)部,不同的敘事形式或‘文類(lèi)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義的張力。”(4)“十七年”文學(xué)文本中各種敘事形式的共存,可以是一種和諧的張力關(guān)系,當(dāng)然對(duì)于具體的文本來(lái)說(shuō),是否能達(dá)到“和諧”以及“和諧”的程度如何,這又要具體分析。有人說(shuō):“十七年”文學(xué)“既是高度一體化的,又是充滿(mǎn)異質(zhì)性的,是一體與異質(zhì)之間的復(fù)雜纏結(jié)”(5)。我同意這樣的觀點(diǎn),正是因?yàn)檫@樣,不同的人才會(huì)看到不同的文學(xué)史風(fēng)景。而既然是“一體與異質(zhì)之間的復(fù)雜纏結(jié)”,那么,如何在這種“糾結(jié)”中對(duì)“異質(zhì)性”的內(nèi)容進(jìn)行把握就成了關(guān)鍵。所謂“異質(zhì)”,當(dāng)然“異”的是政治的“質(zhì)”,但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這種“異質(zhì)”只能是相對(duì)的,關(guān)注“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個(gè)人化的、審美化的表達(dá),并非是要以某一種固定的價(jià)值為標(biāo)準(zhǔn)。洪子誠(chéng)表達(dá)他對(duì)“個(gè)人”的理解具有啟發(fā)性,他說(shuō):“個(gè)體的價(jià)值選擇的獨(dú)斷性質(zhì)是合理的、正當(dāng)?shù)模遣粦?yīng)推論為普遍性的,進(jìn)而要求其他人無(wú)條件地接受……如果把價(jià)值選擇完全看成是個(gè)體的問(wèn)題,實(shí)際上也就取消了這個(gè)問(wèn)題的緊迫性質(zhì)。要是我們也認(rèn)同下面的這樣一種說(shuō)法,即知識(shí)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獨(dú)善其身的‘逍遙’,而且要有‘拯救’的承擔(dān),那么,在‘價(jià)值多元’的境況下僅僅強(qiáng)調(diào)選擇的個(gè)體性質(zhì),這是不大能解決問(wèn)題的。”(6)雖然不能說(shuō)任何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中“非主流”性質(zhì)文學(xué)的研究,就是剝離于特定時(shí)代語(yǔ)境的帶有主觀性的研究,但對(duì)這種文學(xué)存在狀態(tài)的闡釋是否符合文本的系統(tǒng)以及文本所處的歷史結(jié)構(gòu)卻是非常關(guān)鍵的。
同時(shí),由于我們慣用一些理論術(shù)語(yǔ)和文學(xué)史的線索對(duì)20世紀(jì)思想文化和文學(xué)的發(fā)展進(jìn)行評(píng)判,比如一說(shuō)到“個(gè)人”馬上就會(huì)想到“五四”啟蒙傳統(tǒng),雖然這樣一種聯(lián)系是基于歷史發(fā)展的客觀存在,但不能忘記的是,“個(gè)人意識(shí)”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等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和思潮,它也是人性本然的組成部分,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人們的意識(shí)中除了政治理性,也會(huì)有生命感性,作家也會(huì)有對(duì)人的感性世界表達(dá)的渴望和沖動(dòng),這并不都是來(lái)自于對(duì)“五四”傳統(tǒng)的自覺(jué)繼承。“十七年”文學(xué)是如何體現(xiàn)上述那種多層次性,或者說(shuō)在文本研究中哪些方面的特點(diǎn)特別值得注意?我認(rèn)為主要有以下三點(diǎn):
首先是“細(xì)節(jié)”比“主題”重要。對(duì)于“十七年”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作品所表達(dá)的主題通常是清晰明確的,作品在總體上的情節(jié)走向、人物命運(yùn)的安排是圍繞某一主題而設(shè)置的,但是作品所表達(dá)的主題并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在文本的無(wú)數(shù)細(xì)微處往往包含著主題所不能涵蓋的內(nèi)涵,這也就是人們常說(shuō)的“細(xì)節(jié)的政治”,“細(xì)節(jié)被界定為感官的、瑣細(xì)的與浮面的文本現(xiàn)呈,與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較為宏大的‘眼界’(vision)存在著矛盾關(guān)系,這些宏大的眼界企圖將這些細(xì)節(jié)納入其臣屬,但卻出其不意地為這些細(xì)節(jié)的反饋所取代”。(7)往往是在對(duì)細(xì)節(jié)的剖析中,我們能看到主題表達(dá)以外的內(nèi)容,這也是“十七年”文學(xué)的特殊性所在。
其次是“過(guò)程”比“結(jié)果”重要。對(duì)于探究“十七年”文學(xué)的多層次性而言,某些題材的文本具有更強(qiáng)的可解讀性。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往往是那些反映革命戰(zhàn)士成長(zhǎng)和小資產(chǎn)階級(jí)知識(shí)分子改造的題材的作品會(huì)充滿(mǎn)一種“多聲部”的特征,即體現(xiàn)不同話(huà)語(yǔ)的斗爭(zhēng)和糾葛。盡管最終的結(jié)果是確定的,但在對(duì)“成長(zhǎng)”和“改造”的過(guò)程的表現(xiàn)中,我們可以看到個(gè)人命運(yùn)和國(guó)家、民族的關(guān)系。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即使是那些將個(gè)人和政治被認(rèn)為結(jié)合得較好的作品如《三家巷》《青春之歌》《創(chuàng)業(yè)史》等,這種“結(jié)合得好”很多時(shí)候只是在文本的理性表述層面所取得的“勝利”,它帶有作家對(duì)人物主觀干預(yù)和塑造的性質(zhì),雖然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寶、林道靜等最后的人生選擇仍然是從屬于國(guó)家和集體,但人物在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流露出的感性、個(gè)人的力量,仍然給文本造成了縫隙,這也正是這些作品被反復(fù)批判的原因。
再者是“經(jīng)典文本”比“普通文本”重要。由于“十七年”文學(xué)總體上比較統(tǒng)一的特征,當(dāng)下研究展開(kāi)的重點(diǎn)仍然在對(duì)經(jīng)典作品的“重讀”上,因?yàn)榻?jīng)典的作品不僅能涵蓋同時(shí)代一般作品的思想和寫(xiě)作特征,而且由于其在政治性和文學(xué)性的關(guān)系上的有力平衡,它在對(duì)政治、人性關(guān)系的理解上也就能遠(yuǎn)遠(yuǎn)超越一般作品,由此,它所提供的文本的復(fù)雜程度也會(huì)大于一般作品。洪子誠(chéng)就坦言道:“我也是想能發(fā)現(xiàn)50-70年代許多被‘遺漏’的、‘另類(lèi)’的東西的。我不相信那個(gè)時(shí)期,人的情感、觀念、表達(dá)方法就那么統(tǒng)一為了尋找‘遺漏’的‘珠寶’,真花費(fèi)了不少時(shí)間。翻過(guò)不少作品集、選集,各種過(guò)去的雜志,從《人民文學(xué)》,到許多重要省份的雜志。結(jié)果非常失望……”(8)
當(dāng)然,以上“兩個(gè)重要”也都說(shuō)明“解讀意味著不再把這些文本視為單純信奉的‘經(jīng)典’,而是回到歷史深處去揭示它們的生產(chǎn)機(jī)制和意義架構(gòu),去暴露現(xiàn)存文本中被遺忘、被遮掩、被涂飾的歷史多元復(fù)雜性”(9),這才是文本研究的關(guān)鍵。當(dāng)然,以上所說(shuō)的這種多層次性對(duì)于文本來(lái)說(shuō)并非固定的,而是變化的,這是因?yàn)楹芏唷笆吣辍蔽膶W(xué)作品特別是那些當(dāng)時(shí)影響較大的作品大都再版、重版過(guò),而在再版和重版中,作者對(duì)原作進(jìn)行刪改也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只是這種“刪改”很多時(shí)候是根據(jù)現(xiàn)實(shí)要求而非文學(xué)要求進(jìn)行的。這樣看來(lái),“十七年”文學(xué)的不同版本與現(xiàn)實(shí)政治之間有一種確定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創(chuàng)業(yè)史》《青春之歌》《紅旗譜》《三家巷》《紅巖》等作品在不同的版本中所呈現(xiàn)的各種話(huà)語(yǔ)的強(qiáng)弱關(guān)系、組織關(guān)系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版本根據(jù)不同的現(xiàn)實(shí)需要進(jìn)行了調(diào)整,當(dāng)然刪改的方向只會(huì)是越來(lái)越靠近革命話(huà)語(yǔ)和階級(jí)規(guī)范,這就給我們的研究帶來(lái)了很大的復(fù)雜性。因此對(duì)于“十七年”文學(xué),我們不能籠統(tǒng)地就小說(shuō)發(fā)言,而必須根據(jù)具體的版本來(lái)發(fā)言。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學(xué)與現(xiàn)實(shí)之間強(qiáng)烈的對(duì)應(yīng)性,它才會(huì)有激烈的隨著現(xiàn)實(shí)變動(dòng)的不穩(wěn)定性,這也正是我們考察“十七年”文學(xué)的復(fù)雜之處。總之,對(duì)于“十七年”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在文本自身所反映的復(fù)雜性中,政治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結(jié)合的多種可能性所帶來(lái)的文本的多層次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學(xué)史研究中,保持一種客觀公正、科學(xué)理性的研究心態(tài)和價(jià)值立場(chǎng),努力還原歷史的真相從理論上來(lái)說(shuō)總是第一位的,這也被看作是每一個(gè)“治史人”的基本職業(yè)素養(yǎng)。詹姆遜在《政治無(wú)意識(shí)》中提出要“永遠(yuǎn)的歷史化”,他認(rèn)為有兩條實(shí)現(xiàn)的路線:客體路線和主體路線,即研究對(duì)象(文本)的歷史化和研究主體的歷史化。(10)所謂“歷史化”,即歷史研究的科學(xué)化、客觀化,福柯“知識(shí)考古學(xué)”方法對(duì)歷史的態(tài)度就是關(guān)注歷史形成的過(guò)程和肌理,而不作主觀的價(jià)值判斷。在這樣的歷史觀念的影響下,“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近些年的發(fā)展也顯示出“客觀化”的還原歷史的努力。不過(guò),我們卻不得不承認(rèn)純粹客觀的文學(xué)史寫(xiě)作幾乎是不存在的,這也是很多學(xué)者在實(shí)踐中普遍感到的困惑。洪子誠(chéng)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寫(xiě)作中就提倡一種“價(jià)值中立”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立場(chǎng),而李楊卻指出,其《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寫(xiě)作實(shí)踐,并未很好地貫穿這種立場(chǎng)。洪子誠(chéng)回應(yīng)說(shuō)自己的研究中確實(shí)存在主觀上的“啟蒙主義立場(chǎng)”,并解釋說(shuō):“我在《文學(xué)史》講到的對(duì)價(jià)值判斷的擱置與抑制,并不是說(shuō)歷史敘述可以完全離開(kāi)價(jià)值尺度,而是針對(duì)那種‘將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問(wèn)題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出來(lái),按照編寫(xiě)者所信奉的價(jià)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11)李揚(yáng)自身雖然在1990代末的研究中力圖貫徹一種科學(xué)、客觀的立場(chǎng),但他在對(duì)“十七年”經(jīng)典的重讀中也并非沒(méi)有價(jià)值判斷和立場(chǎng)。逃離價(jià)值立場(chǎng)也是一種立場(chǎng),對(duì)歷史客觀性的追求是必須的,但也必須認(rèn)識(shí)到任何一種方法的使用都不是絕對(duì)的。
“文學(xué)史”的特殊性在于它考察的對(duì)象既是歷史,也是文學(xué),西方新歷史主義把所有的歷史都看成文本,具有虛構(gòu)性,在我們的文學(xué)史研究中,進(jìn)入我們視野的“歷史”也是文本——文學(xué)文本,文本的呈現(xiàn)方式是語(yǔ)言化的,我們只能通過(guò)語(yǔ)言走近歷史,歷史在被我們“還原”或“闡釋”的過(guò)程中也需要通過(guò)敘述的方式進(jìn)行,而我們敘述歷史背后的方法、立場(chǎng)和語(yǔ)言卻是多變的,因此我們所呈現(xiàn)的“歷史”會(huì)呈現(xiàn)出多層次的狀態(tài)。對(duì)此,我將具體結(jié)合“十七年”文學(xué)具體的研究狀況進(jìn)行說(shuō)明。第一,進(jìn)入我們視野的“十七年”文學(xué)文本本身就具有多層次性,對(duì)此,通過(guò)上述“十七年”文學(xué)中政治與文學(xué)(人)關(guān)系的多層次性的論述已經(jīng)進(jìn)行了一定說(shuō)明,“十七年”文學(xué)政治與文學(xué)(人)關(guān)系的多層次性也必然會(huì)帶來(lái)通過(guò)文本重建歷史的多種可能性,這里的“歷史”既包括文本所指向的文學(xué)史,也包括文本外現(xiàn)實(shí)的歷史。有人認(rèn)為文學(xué)史主要是審美的歷史,而對(duì)社會(huì)生活沒(méi)有責(zé)任,我認(rèn)為這是值得商榷的。文學(xué)是一定時(shí)期社會(huì)和個(gè)人生活直接、間接的審美的反映和表現(xiàn),它的內(nèi)容不單包括審美的歷史,也應(yīng)包括現(xiàn)實(shí)的歷史,也就是說(shuō),不僅歷史事件在講述現(xiàn)實(shí)的歷史,文學(xué)文本也在講述現(xiàn)實(shí)的歷史,王德威說(shuō):“比起歷史政治論述中的中國(guó),小說(shuō)所反映的中國(guó)或許更真切實(shí)在些。”(12)而由于“十七年”文學(xué)與現(xiàn)實(shí)之間較強(qiáng)的對(duì)應(yīng)性,我們?cè)诿鎸?duì)“十七年”文學(xué)的時(shí)候,更容易自覺(jué)不自覺(jué)地把文學(xué)和歷史聯(lián)系起來(lái)思考。在考察文本的歷史性時(shí),除了普遍適用的文本細(xì)讀的方法之外,當(dāng)下學(xué)界所提倡的“知識(shí)考古學(xué)”“譜系學(xué)”的研究方法對(duì)“歷史性”的發(fā)掘顯示出特殊之處。這一研究方法的目的是重建文學(xué)史研究的歷史感,它傾向于透視文學(xué)史背后的形成肌理和組織方式,同時(shí)對(duì)剖析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話(huà)語(yǔ)如何被組織的過(guò)程有一定優(yōu)勢(shì),如洪子誠(chéng)《“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概念》一文的研究思路,關(guān)注的就是“當(dāng)代文學(xué)”這個(gè)概念是如何被構(gòu)造和描述的。在文本研究中,許多研究者也提倡這一思路,“當(dāng)我們面對(duì)一個(gè)復(fù)雜的文本時(shí),最重要的并不是從中尋找和發(fā)現(xiàn)某一個(gè)因素(如個(gè)體生命欲求等)并對(duì)其作出價(jià)值評(píng)判,而是闡釋各個(gè)因素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和組合方式。”(13)
也就是說(shuō),與以往文學(xué)史注重價(jià)值判斷不同,“譜系學(xué)”性質(zhì)的文本研究放在了“如何寫(xiě)”而不是“寫(xiě)什么”上,如果說(shuō)通常的文本細(xì)讀只是對(duì)文本的主題、情節(jié)、人物等表面結(jié)構(gòu)的分析,那么“知識(shí)考古學(xué)”“譜系學(xué)”的研究方法則重在對(duì)文本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分析,它能從另外的角度提供文本的歷史性,即文本在敘事上的特點(diǎn)是由何種機(jī)制形成的、何種話(huà)語(yǔ)操控的,如李楊的《抗?fàn)幩廾贰吧鐣?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1942—1976)研究》、藍(lán)愛(ài)國(guó)的《解構(gòu)”十七年”》等專(zhuān)著就體現(xiàn)了這樣的研究思路。不過(guò),總的來(lái)說(shuō),在近些年“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的文本實(shí)踐中,福柯在思想觀念上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的影響要比其在研究方法上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的影響大得多,這種“思想觀念”主要指的是福柯的“知識(shí)-權(quán)力話(huà)語(yǔ)理論”。由于“十七年”文學(xué)存在比較突出的政治話(huà)語(yǔ)對(duì)文學(xué)的組織和限制,福柯的這一理論看似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就具有了較強(qiáng)的可操作性。實(shí)際上,把“權(quán)力”等同于國(guó)家政治是對(duì)福柯“知識(shí)-權(quán)力話(huà)語(yǔ)理論”的簡(jiǎn)單化理解。福柯“知識(shí)-權(quán)力話(huà)語(yǔ)理論”中的“權(quán)力”與馬克思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中的“權(quán)力”有很大差別,它更多是指由知識(shí)、話(huà)語(yǔ)的生產(chǎn)所形成的權(quán)力網(wǎng)絡(luò),同時(shí),福柯對(duì)權(quán)力話(huà)語(yǔ)所作的歷史性的分析,說(shuō)明權(quán)力主體和客體的關(guān)系并非想象的那樣是“壓抑”和“被壓抑”的關(guān)系,不過(guò),他的這種學(xué)術(shù)思想?yún)s較少對(duì)我們的“權(quán)力”研究有啟發(fā)。與“十七年”文學(xué)高度政治化的語(yǔ)境相對(duì)應(yīng),很多研究者把福柯權(quán)力話(huà)語(yǔ)理論的一些研究結(jié)論作為研究的基本前提,即承認(rèn)權(quán)力話(huà)語(yǔ)對(duì)人的規(guī)訓(xùn),人只是權(quán)力的被動(dòng)服從者,這樣的研究思維不能體現(xiàn)作家及文本的感性主動(dòng)性,勢(shì)必會(huì)對(duì)具體的文本缺乏仔細(xì)分析和研讀,結(jié)果造成“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出現(xiàn)了和過(guò)去以階級(jí)標(biāo)準(zhǔn)為唯一標(biāo)準(zhǔn)的文學(xué)史研究同樣簡(jiǎn)單化的傾向。同時(shí),從思維特點(diǎn)來(lái)看,話(huà)語(yǔ)分析方法具有思想史、社會(huì)史、歷史研究的特點(diǎn),這對(duì)文學(xué)研究來(lái)說(shuō)存在著難以回避的缺陷,因?yàn)樗蛴诶硇院瓦壿嫞狈?duì)感性世界的細(xì)致感受和把握,用它來(lái)研究文學(xué)并不能顯示出其與其他人文學(xué)科的話(huà)語(yǔ)研究的區(qū)別來(lái),也就是說(shuō),話(huà)語(yǔ)研究更適用于研究普遍性問(wèn)題的抽象學(xué)科,而不太適用于個(gè)性突出的文學(xué)研究。所以,倡導(dǎo)“譜系學(xué)”研究方法的李楊在面對(duì)“十七年”文學(xué)文本的時(shí)候,仍然說(shuō):“在目前包括‘文學(xué)生產(chǎn)’‘一體化’‘知識(shí)-權(quán)力關(guān)系’等眾多新鮮有效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文學(xué)史研究方法之中,我仍然選擇十年前確定的‘再解讀’方式進(jìn)入歷史。”在面對(duì)文本的時(shí)候,如果說(shuō)感性層面需要的是研究者與文本之間的精神對(duì)話(huà),那么,在理性層面,需要的則是研究者對(duì)不同的文本所具有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的把握,這兩種文本研究方式都不是用權(quán)力話(huà)語(yǔ)理論把文本處理成單一的結(jié)論。第二,除了以上所說(shuō)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這種多層次性以外,文本的歷史性也與研究者所處的當(dāng)下語(yǔ)境、研究者的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和價(jià)值立場(chǎng)等有密切關(guān)系。沒(méi)有主體對(duì)歷史的介入就沒(méi)有歷史,這包含著歷史敘述無(wú)法擺脫的悖論:當(dāng)歷史已經(jīng)或者正在成為過(guò)去,歷史的真實(shí)只能通過(guò)語(yǔ)言的敘述來(lái)表達(dá)和獲得,當(dāng)代人對(duì)歷史的敘述和闡釋包含著他們自身的精神狀況對(duì)歷史的介入,在這一意義上,文本歷史性的多層次性也是由研究主體所賦予的。
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以來(lái)的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中,一種觀念的提出、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和立場(chǎng)的出現(xiàn)都是由當(dāng)下語(yǔ)境決定的,“復(fù)蘇五四啟蒙傳統(tǒng)”“重申民族國(guó)家的政治合法性”“尋找人文理想”“重塑時(shí)代精神”等一個(gè)又一個(gè)的文學(xué)話(huà)語(yǔ)類(lèi)型和研究熱潮實(shí)際上都隱含著置身其中的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境遇和價(jià)值立場(chǎng),對(duì)于文學(xué)史研究來(lái)說(shuō),福柯的那句“重要的不是話(huà)語(yǔ)講述的時(shí)代,而是講述話(huà)語(yǔ)的時(shí)代”仍具有真理性。因此,如果說(shuō)我們對(duì)歷史的理解和描述都多少包含和融入了闡釋者所處的當(dāng)下時(shí)代語(yǔ)境的因素,代表著在歷史中尋求答案的沖動(dòng),那么,歷史永遠(yuǎn)都不會(huì)只代表消逝的過(guò)去。在福柯那里,對(duì)歷史的知識(shí)譜系學(xué)的分析,就是源于現(xiàn)實(shí)的沖動(dòng):“我起初是從一個(gè)用當(dāng)代術(shù)語(yǔ)表述的問(wèn)題出發(fā),我想弄清它的譜系。譜系意味著我的分析是從現(xiàn)實(shí)的問(wèn)題出發(fā)的。”也就是說(shuō),所有“歷史性”的研究都會(huì)受到當(dāng)代文化語(yǔ)境的影響,“當(dāng)代性”賦予了歷史多層次的品格。實(shí)際上,正是上述一個(gè)又一個(gè)的“當(dāng)下語(yǔ)境”給近二十年來(lái)的“十七年”文學(xué)研究打上了各種各樣的烙印。同時(shí),由于當(dāng)下很多“十七年”文學(xué)的研究者都曾親自經(jīng)歷過(guò)那個(gè)年代,因此,對(duì)文本的歷史性研究也會(huì)受到研究者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影響。由于“十七年”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每個(gè)人對(duì)它的個(gè)人記憶是不同的,有些人對(duì)“十七年”有著深厚的“紅色”懷舊情緒,這些主觀的感情不會(huì)不影響到研究者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和判斷。有1950年代出生的學(xué)者對(duì)此發(fā)言道:“我們一方面試圖把文學(xué)史的寫(xiě)作變成一種冷卻抒情的‘?dāng)⑹觥⒃谶@一過(guò)程中盡量取客觀與超然的學(xué)術(shù)態(tài)度,同時(shí)又發(fā)現(xiàn),當(dāng)我們自己也變成敘述對(duì)象的時(shí)候,絕對(duì)的‘冷靜’和‘客觀’事實(shí)上是無(wú)法做到的。由此看來(lái),并不是‘當(dāng)代人’不能寫(xiě)‘當(dāng)代文學(xué)史’,而是當(dāng)代人‘如何’寫(xiě)曾經(jīng)‘親歷過(guò)’的文學(xué)史。它更為深刻地意味著,我們?nèi)绾卧谶@過(guò)程中‘重建’當(dāng)代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16)因此,在主觀和客觀、情感與理智之間如何保持一種良好的平衡,在對(duì)歷史的理解同情和對(duì)歷史的客觀審視之間如何保持一種良心和責(zé)任感,都無(wú)疑是對(duì)“治史人”的挑戰(zhàn)。再者,對(duì)文本的歷史性的研究也受到研究者在一些文學(xué)問(wèn)題上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的影響,這同樣是構(gòu)成文本歷史性的多層次性的重要方面。由于“十七年”文學(xué)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原則上的特殊性,它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原則和標(biāo)準(zhǔn)與其他時(shí)期相比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同時(shí),其他歷史時(shí)期如“五四”所形成的文學(xué)觀念也會(huì)影響到“十七年”文學(xué)批評(píng),因此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文學(xué)觀念及其差異在“十七年”文學(xué)批評(píng)中就會(huì)一起呈現(xiàn)出來(lái),如對(duì)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人物的評(píng)價(jià)無(wú)論是當(dāng)時(shí)還是當(dāng)下都存在這樣的問(wèn)題。
當(dāng)下研究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問(wèn)題,它們和上述問(wèn)題在本質(zhì)上仍是相同的。例如令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當(dāng)時(shí)引起很大反響,被認(rèn)為很真實(shí)感人的作品,現(xiàn)在看來(lái)卻是虛假的,我們?cè)撊绾螌?duì)待這一問(wèn)題?這顯然是由不同時(shí)代語(yǔ)境中的不同文學(xué)觀念所致,但這樣的解釋遠(yuǎn)遠(yuǎn)不夠,面對(duì)這樣的問(wèn)題,我們似乎仍然必須回答:對(duì)于文學(xué)史研究,我們需要的是歷史語(yǔ)境中的真實(shí),還是某種普遍性的真實(shí)?讓我們的研究回到特定的歷史語(yǔ)境,即意味著承認(rèn)歷史存在的合理性,但這樣也會(huì)帶來(lái)問(wèn)題,因?yàn)闆](méi)有價(jià)值立場(chǎng)就意味著失去批判立場(chǎng)。在我看來(lái),盡管由于上述不同的主體因素的介入會(huì)形成對(duì)文本不同的價(jià)值判斷,但這些不同的價(jià)值判斷不是非此即彼的對(duì)立關(guān)系,只能具有某種唯一的真理性,而是相對(duì)于還原歷史的可能來(lái)說(shuō),它們是可以共存的,因此這里我仍然認(rèn)為它們構(gòu)造了文本歷史性的多層次性。實(shí)際上,“純粹客觀”的歷史研究也不是沒(méi)有問(wèn)題,孫歌在研究日本批評(píng)家丸山真男時(shí)指出:“面對(duì)歷史現(xiàn)象,從外部對(duì)它進(jìn)行批判比較容易,但是這種外部的態(tài)度很難深入到對(duì)象中去,不具備瓦解它的內(nèi)在邏輯的功能。而‘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是深入到對(duì)象中去理解對(duì)象的內(nèi)在邏輯。”“這種歷史主義的方法,它的難點(diǎn)在于很容易被對(duì)象同化,因?yàn)檎J(rèn)同式的‘理解’而喪失批判精神。所以丸山說(shuō),‘理解他者’,‘理解’并不等于‘贊成’,它不包含把對(duì)方合理化和正當(dāng)化的意圖。”(17)當(dāng)代人的主體精神對(duì)歷史的介入,并不意味著非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而是意味著當(dāng)代思想文化、社會(huì)語(yǔ)境與歷史之間展開(kāi)一種積極對(duì)話(huà)的關(guān)系,從而使這一學(xué)科具有回應(yīng)現(xiàn)實(shí)的能力,歷史語(yǔ)境因“當(dāng)下”而變得鮮活而有意味,當(dāng)下語(yǔ)境也因“歷史”而獲得反思和批判自我的能力,這樣才能形成“歷史”和“當(dāng)下”的互動(dòng)。
綜上所述,無(wú)論是“研究客體”還是“研究主體”,它們的“歷史化”過(guò)程都充滿(mǎn)了多種可能,這些不同的因素共存在文本中,面對(duì)并承認(rèn)這種不同層面的文學(xué)表達(dá)在文本中的共存相對(duì)于拿一種對(duì)立的眼光去看它們之間的分歧是更理性的選擇,伽達(dá)默爾說(shuō):“作品呈現(xiàn)在讀者心目中的實(shí)際意義,并不是作者給定的原意,而總是由解釋者的歷史環(huán)境乃至全部客觀歷史進(jìn)程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18)他的這一看法與詹姆遜“把歷時(shí)性和共時(shí)性的區(qū)分納入一個(gè)整體”(19)的看法有著相通之處。這些觀點(diǎn)啟發(fā)我們,在面對(duì)文本的時(shí)候,我們不能只注重歷時(shí)性形成的各種觀念對(duì)研究立場(chǎng)的不同影響,也應(yīng)該注重這些不同的歷時(shí)性觀念在文本中所形成的共時(shí)性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本文作者:李蓉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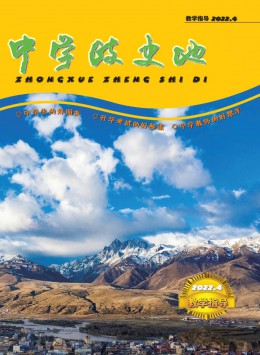
中學(xué)政史地·七年級(jí)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時(shí)代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七年級(jí)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中學(xué)課程輔導(dǎo)·七年級(jí)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中學(xué)生數(shù)理化·七年級(jí)數(shù)學(xué)·華師大版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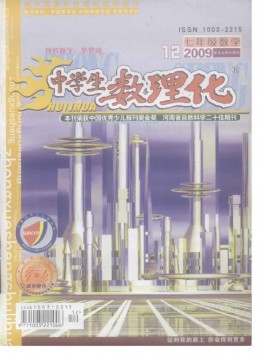
中學(xué)生數(shù)理化·七年級(jí)數(shù)學(xué)·北師大版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