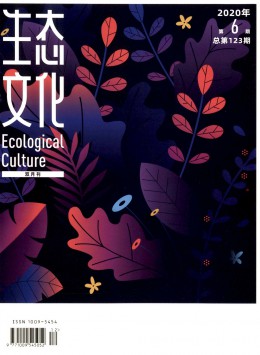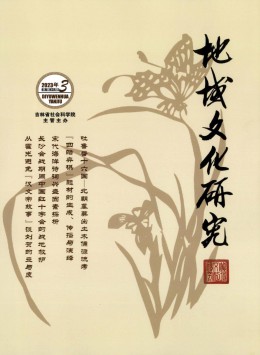文化研究理論創新啟發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文化研究理論創新啟發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興起與傳播:大眾文化與“美國化”威脅
從20世紀20年代起到二戰前后,在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諸多力量的推動下,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大眾消費社會的國家[2]P54并實現了文化轉型,大眾文化逐漸頂替了“白種人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徒”文化成為主流。這種文化以廣大的勞動人民和中產階級為主體,包容了一切與消費主義相關的生活要素,如通俗藝術、體育賽事等[3]P40-48,簡而言之,在當時的歐洲人看來,大眾文化即是美國生活方式。隨著美國經濟、政治、軍事的擴張,特別是在冷戰之后,大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被輸往世界各地,尤其是英、法、德等西歐國家,這些國家成了大眾文化輸出的最大場所。反映了“美國夢”的好萊塢電影、可口可樂等很快就占據了這些國家年輕人的心,它們成了美國傳播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世界觀、價值觀的載體,悄悄地引導著西歐國家走“美國化”(Americanism)的道路。[4]P157-163與美國相比,當時的西歐國家還未進入消費社會,等級分層比較明顯,因而“大眾”一詞主要指的是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普通百姓。另外,西歐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文化”在西歐社會主要指高雅的文學藝術和貴族氣派的生活方式,是只有通過良好的教育才能獲得的少數人的資源。因此對于他們而言,“大眾文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出于對作為“他者”的美國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對自身文化特權的維護和對本國前途的擔憂,西歐的精英階層對這種缺乏高度與深度,沒有歷史意識和崇高品質的文化形態[5]P57進行了曲解式的諷刺和挖苦,企圖引導大眾自覺抵御“美國化”的進程[6]P5-11。相比而言,西歐廣大人民則對給予他們愉悅和享受的大眾文化產品并不排斥而且愿意掏腰包,這與精英階層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精英與大眾,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在大眾文化問題上的對立性,使得大眾文化的合法性在西歐理論界那里被問題化(problematic),這樣就把一個新的理論空間推到了這些知識分子面前,這正是嚴肅的大眾文化研究發端于西歐而不是美國的原因。
二親知與批判:法蘭克福學派
與大眾文化的總體性話語諷刺的是,“推動”這項理論工作進一步發展的不是某個學科帶頭人,而是希特勒[7]P408。20世紀30年代,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遷往美國[8]P271,此后其成員紛紛進入到美國的媒體或政府部門,親眼目睹了大眾文化的生產和傳播過程[9]P24,因此對大眾文化有了更多設身處地的直觀與親知,其觀點的深入程度遠遠超過走馬觀花的文化旅行者,對西歐的“消極美國觀”也具有糾偏作用。[5]P541949年社會研究所遷回德國,這群學者發現,戰后西德就像當年他們在美國看到的那樣[8]P276,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已經成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重要事情,批判資本主義,需要對大眾文化進行批判。因此,嚴肅的大眾文化研究是由法蘭克福學派開啟的,而這項工作的第一本代表作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的《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在書的《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一章中,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考察了被納入到工業體系中的大眾文化,即文化工業。文化工業憑借強大的生產管理技術和傳播技術為消費者提供了大量廉價的文化產品以供選擇,表面上使得消費者有足夠的自由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商品和娛樂方式。實質上,消費者在文化工業的宰制力量下并無質的自由而僅有量的自由:可以選擇商品A或者商品B,卻無法選擇拒絕文化產品,否則便成為文化中的“他者”或者大眾中的異己分子。鋪天蓋地的文化工業體系扼殺了大眾的批判能力和否定性思維,造成了虛假的同一性和標準化的個性,最終還攻占了藝術這片自留地,導致了高雅藝術的邊緣化及其救贖功能的喪失,其后果就是將自由主義的社會推到了極權主義的深淵,把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捧為英雄。[10]P107-152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看待美國大眾文化和它的潛在形式——德國大眾文化是帶著三副有色眼鏡的,一是階級的,二是國家的,三是種族的,因此他們看待大眾文化的模式也刻下了時代的烙印,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是文化工業生產的參與者,對文化產品的制作和推銷過程那些不為人所知的陰暗面有所親知,因而對蒙在鼓里的大眾深感同情。另外,由于他們受過高雅文化的熏陶,對下里巴人東西的偏見阻礙了他們對這些產品做進一步的了解,更不愿意以一個消費者的身份對產品進行細讀,因此他們并沒有深入到消費者與文化產品的真實關系中,所得出的結論,想象和邏輯推衍的成分較多[9]P15-16,實證研究較少。其次,在德國,文化主要指的是精神創造物,如經典的文學和藝術,而在美國,文化不僅包括前者,也包括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加上前面的原因,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主要限定在藝術化的文化世界里,較少關注人類學意義上的大眾生活方式。再次,上述原因還導致了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將消費者看成文化工業的順從被動的客體,而不是多樣化的主體,所以他們看到的是極權主義的大眾文化而不是民主的大眾文化,因而過多地強調了羅斯福時代的美國大眾文化和希特勒統治下的法西斯文化的一致性。[12]P9最后,前兩副眼鏡加上特定時代的猶太人身份,又讓他們看問題的時候帶有濃厚的悲觀主義和憤世嫉俗色彩。作為左派人士和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歷史創造者”——普羅大眾的蔑視,也引起了后來人的不滿。[9]P38可以說,在三副眼鏡的視野下,文化工業理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研究定了基調——大眾文化的否定性話語。在英國學者的刻板印象中,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始終是精英主義的代名詞。不過,畢竟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通過“俯下身來”與大眾文化面對面地打交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西歐精英階層對大眾文化不屑一顧的看法,在將大眾文化與法西斯主義聯系在一起進行批判的同時,讓世人認識到大眾文化的重要性,提醒世人:文化非小事,它亦可成就人類,亦可毀滅世界,因此,大眾文化研究是嚴肅的,必要的,它需要被提升到社會總體性的高度進行批判,這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總體性話語,也為西方人文學界的“文化轉向”做了鋪墊。同時,他們在肯定大眾文化的重要性和全盤否定大眾文化的合法性之間留下了一個解構空間:既然大眾文化如此具有危害性,人民卻如此喜歡,而批判大眾文化是為了解放人民,那么從一種現實主義的角度考慮,我們就不能“單向度地”考察大眾文化(僅僅作為意識形態),而是應該將之置于大眾參與的總體社會關系中,把大眾作為文化主體來看待。
三懷舊與介入:利維斯主義與作為文化主體的人
與德法相比,英國與美國文化上是同源的,因而英國的文化反美主義并不典型,因而在文化工業理論盛行的40-50年代,英國并沒有類似的總體性理論出現。不過,當時英國的文學批評扮演了類似的作用,它是英國人文學科的中心;眾多的文學批評作品,建構了當時英國社會的總體性景觀[14]P112。當時英國著名的文學理論家F•R•利維斯創辦了雜志《細察》(1932-1953)季刊,形成了《細察》集團以及利維斯主義學派,統治英國文學批評近40年之久。[15]P10-13所謂利維斯主義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指一種方法論的取向:利維斯反對在文學批評界中理論先行,閱讀在后,給文學文本貼各種“主義”標簽的“哲學化”傾向[16]P50-51[17]P12,主張對文學文本進行近距離地細讀、分析和感悟[18]P10-11。這種細讀不是封閉式的,而是以文本為跳板,以道德為標準對社會進行批評。因此,文學批評家是帶著比一般人更高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關懷介入到社會共同體生活中的,他們需要遠離大眾以保持獨立,才能引導社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方法論取向的利維斯主義也必然導致了另一層意義上的利維斯主義,即理論取向的利維斯主義,這典型地體現在利維斯于1930年發表的小冊子《大眾文明與少數人文化》上。一般而言,“文明”(civilisation)與“文化”(culture)二詞在英、法、德三種語言那里基本是可以混用的。[19]P137-140不過,利維斯并沒有采用這樣的語義而是跟隨馬修•阿諾德[20]P12,賦予了“文明”與“文化”特殊的對立含義[21]P26:文明指工業化社會的總體形態,其基本特點是商業化和大眾消費主義,以美國社會為典型[22]P16;而文化則由精通文學、藝術、科學和哲學的少數人所掌握,它以擁有“偉大的傳統”的英國文學為典范,理應規范著文明的走向,不過在20、30年代,英國正在步美國的后塵,少數人已經被波濤洶涌的大眾文明圍在了墻角[21]P3-12,社會已經處在了墮落的邊緣。利維斯深知:“對抗機器的勝利終究是徒勞的”[21]P31,但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發動少數人奪回逝去的權力。由于這樣一種文化情結,利維斯否認了“大眾文化”[21]P20的合法性,展現了他的歐洲精英論的成見。這似乎給人以一種印象,即利維斯和霍克海默、阿多爾諾是殊途同歸的:一、當時他們已經認識到文化對于社會的關鍵作用,共同開創了大眾文化批判這個領域;二、他們有著共同的精英主義情結,因而后人將這兩個學派并稱為“文化精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沒錯,但共同點并不能掩蓋他們的差別。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的《啟蒙辯證法》寫于二戰期間,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動搖了他們以及很多德國知識分子所信奉的啟蒙觀念的合法性[23]P127-132;對理性、自由的向往和對人的主體性的堅信[24]P35-38,被一種對人類命運的絕望情緒所替代。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他們認為,不僅大眾沒有任何主體性可言,就是作為精英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自身難保。與此不同的是,英國并沒有像德國那樣受到法西斯主義的重創,知識分子也沒有受到如此大規模的清洗,加上利維斯本人不是左派人士,因此他所看到的社會前景并沒有那么的暗淡。盡管擔憂大眾文化的泛濫會使英國走向沒落,盡管以緬懷過去作為聊以自慰的方式,但利維斯還是相信教育能夠救國的信念,并利用他在英國教育界里兩門大學課程——英語和文學批評的影響力[15]P13,培養一幫能用筆桿子打擊大眾文化,推廣高雅文化的弟子。因此在悲觀情緒的背后,利維斯仍然為意志主義和人的主體能動性留下了地盤。如果說,《啟蒙辯證法》表達的是一種悲觀主義甚至絕望的文化精英主義,那么利維斯主義就是一種帶有樂觀主義悲劇意識[25]P9-15的文化精英主義。其次,從政治立場上看,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是激進人士,批判大眾文化意在超越資本主義,而利維斯屬于保守人士,批判大眾文化意在回到封建社會,因此同樣是文化精英主義,卻有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區分。從階級分析的角度看,兩種立場背后所指向的階級利益顯然是不同的。正因為有了這種差異,一個新的理論空間也隨之建起,這為后人的選擇和揚棄提供了契機。
四選擇與導向:大眾文化的觀念重構
與英國社會的民主化對于利維斯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上述我們所區分的兩種意義上的利維斯主義,因為兩者是統一的。問題在于,利維斯堅持了一種老派的西歐精英論的文化標準,這種標準容不得大眾生活方式作為“文化”而存在,因此,大眾文化也不應該用“細察”的方法加以研究;不過,大眾文化的強勢來襲以及背后所隱含的美國文化霸權,又迫使他不得不認真面對,在藐視與重視之間,在近距離細察和遠距離觀望之間,利維斯給后人留下了很大的辯證空間:既然大眾文化比少數人文化更強大,簡單粗暴的對待大眾文化顯然結局悲慘,要想抵抗之,還得“細察”之,因此,兩種意義上的利維斯主義需要分離。在這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盡管不愿意承認大眾文化的合理性,但默認了它在語義上的合法性。因此,隨著時代的發展,利維斯的文化標準逐漸變得過時而越來越私人化,這是對文化持總體性觀點的后人所反對的,威廉斯將之命名為粗糙的“標準理論”(theoryofstandard)[26]P310,即以一種家長制的方式規定什么是文化,什么不是,它的反面則是將標準放到共同體所有成員之中去協商,不斷地修改之,以適應時代的發展,發揮時代關鍵詞的語義力量。因此,盡管當時的美國大眾文化并不是完美的,但至少當時美國人的文化標準比西歐精英論的文化標準更具有民眾性,因而也更具有民主的潛能,這與戰后英國的社會階級分化進程[27]P179-187有著某種契合性。所以,大眾文化的命運,就跟戰后英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這使得文化研究的誕生變得非常重要。正是大眾文化這樣一個新事物的出現給當時的西歐精英界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對于威廉斯所描述的“文化與社會”傳統(包括利維斯主義者)①而言,這是工業主義對社會的新挑戰,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則是資本主義以另一種方式煥發生機后對社會主義的新威脅。不過對威廉斯等人而言,利維斯主義者和法蘭克福學派都太悲觀了[30]P63,這種悲觀不僅僅是由階級偏見和政治上的無助造成的,也有理論方面的困境,而根子就在于他們對大眾文化的矛盾態度上。因此,當時英國社會的“情感結構”②呼喚著一種能夠更好地克服這些矛盾,解釋這些新現象的總體性理論,這樣就有了“文化轉向”的社會期待。霍加特、威廉斯和湯普森在投身于戰后成人教育運動[31]P24-25,介入大眾文化批判領域后寫出的文化研究“四大經典”——《識字的用途》、《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32]P31-40,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這樣一種需求。不過,威廉斯等人并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全盤肯定美國式的大眾文化,而是把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嚴肅的政治思考對象,比如霍加特對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工人生活方式進行親知性地描述,意在為工人階級爭奪平等的話語權,捍衛工人階級自主生活的權利;威廉斯探討英國知識分子眼中的“大眾文化”,意在通過批判的方式肯定大眾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通過日常生活這個媒介而推動著社會進步;而湯普森探討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則意在揭示英國激進主義運動史背后的大眾文化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存在于歷史中,而且存在于當下,它使得人民能夠借助它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以擺脫家長制的束縛,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共同體。[34]P13盡管三人對大眾文化的切入點不同,但無疑指向同一個話題:英國的民主化進程。可以說,他們所探討的大眾文化已經不是指一種事物,一種生活方式,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即作為“整體生活方式”(awholewayoflife)的文化,③這種觀念還有另一個表達法,即威廉斯所說的“選擇性傳統”(aselectivetradition),選擇性傳統意味著傳統不是冷冰冰的鐵板一塊,而是可以拆解成不同要素并進行重新組合,因此,美國的大眾文化在經過英國化之后,就可以成為英國人的民主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利用日益發達的大眾傳媒技術為公眾創造更多的表達心聲的機會。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的一部分,思想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正是在對美國大眾文化、利維斯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解構和重新組合上,文化主義部分選擇了美國的人類學意義上的大眾文化,降低了它的娛樂性和審美性;選擇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總體性和利維斯主義的文化主體性觀念,否定了他們的文化精英主義,將之整合進作為“整體生活方式”的文化觀念里頭,確立了英國式的大眾文化話語。這使得英國開始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理論輸出國,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美國的文化霸權,同時文化主義也抵御了英國的中產階級文化霸權,實現了理論創新并在某種程度上付諸了實踐,贏得了世界范圍內左派人士包括中國學者的尊敬。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主義的理論創新得益于這樣一個時空契機: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象征美國霸權的大眾文化以不可阻擋的氣勢沖擊著西歐社會,加速了西歐社會的階級分化,造成了西歐精英階層既輕視又恐懼的不服氣心理,由于他們用的理論武器是西歐式的文化定義,因此對美國式文化的批判顯得軟弱無力;法蘭克福學派和利維斯主義的文化批判盡管增強了這種批判力,卻也因為沾染了西歐人的文化精英主義而走向悲觀主義。不過,正是這兩個學派共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理論空間、問題域,以及多種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使得文化研究得以可能,加上威廉斯等人“識時務”地選擇,使得大眾文化批判朝向新的方向——文化研究而發生裂變。時隔半個多世紀,對于世界左派學界和中國學界而言,文化主義至今仍是有生命力的,因為他們堅持了一種歷史選擇和思想史選擇的標準:在歷史傳統和思想史傳統的解構和重構過程中,將阻礙人民說話、獨立、自由的家長制因素去除,將民主的因素整合進傳統,這不僅是理論上的策略,也是他們身體力行的原則。因此,回顧文化研究的史前史,讓我們更深切地看到文化主義的魅力,也給予我們關于理論創新的方法論和標準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