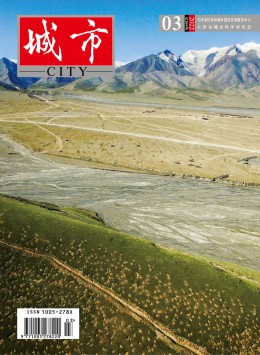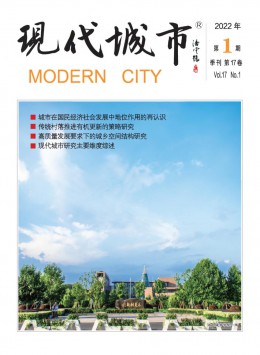城市建筑中的現代與后現代主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城市建筑中的現代與后現代主義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陳后亮 單位:山東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
自20世紀中期以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普遍發生在幾乎所有文化部門,比如人們熟知的美術界的馬歇爾•杜尚,音樂界的約翰•凱奇和小說界的塞爾曼•拉什迪等,都是這場斗爭中的關鍵人物。但這場爭端在城市建筑領域卻表現得尤為充分和典型,正如詹姆遜所觀察到的那樣:“毋庸諱言,建筑才是后現代主義斗爭最激烈的領域,因此最具戰略意義。正是在建筑領域,后現代主義概念備受爭議,被反復探究。只是在這里,我們才更趕趟似地擺出論爭所需的理論和實踐籌碼。”[1]247我們似乎并不難解釋城市建筑之所以會成為焦點的主要原因: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沖突雖然在其它領域同樣激烈,比如在文學和繪畫等方面,但這些文化部門畢竟距離大眾生活較遠,它們多少局限于專家小圈子,難以引發全社會關注。而城市建筑則不同,它可以非常直觀地矗立在人們視野之內,將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不同美學追求清晰地展現給大眾。由于后現代主義者素來有著強烈的大眾情結,他們自然不會忽略建筑這塊必須占領的陣地。這同樣可以解釋為什么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們雖然多數都是建筑學的外行,卻都對建筑及其文化內涵抱有持久而濃厚的興趣和言說欲望。加拿大的著名后現代主義理論家琳達•哈琴便以后現代建筑為理論模型構筑了其完整的后現代主義詩學體系[2],并認為“這種建筑的特點也是整個后現代主義的特點”[3]31。因此,仔細審視建筑領域內的這場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爭,將有助于深化我們對這兩種社會文化和藝術風格的整體理解。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主義建筑運動也是20世紀初期整個西方現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當時,現代主義在繪畫、戲劇和文學領域已過了巔峰期,游離于體制之外的現代主義藝術已開始進入拍賣行、博物館和大學課堂,淪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藝術經典。但現代主義卻在以格羅庇烏斯和柯比西耶為代表的新一代建筑師那里找到了傳授衣缽的信徒。當時歐洲社會普遍面臨的任務是盡快收拾一戰留下的殘局,同時更好解決過快發展的工業化進程所產生的眾多社會問題,比如城市人口膨脹,居住環境低劣,生活條件惡化,等等。在短時間內多快好省地建造現代化的車站、學校、醫院和居民區來改善城市環境是現代主義建筑師的首要命題。這就導致他們在建筑的總體風格上偏重功能主義、實用主義和理性主義,相反建筑的美學形式和內外裝飾等感官特征卻不被重視。這表現在他們提出的一系列口號上,比如“房屋是居住的機器”、“裝飾即罪惡”等。
由于工程量大、工期緊,處于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并講求效率至上的現代人,自然不愿再沿用傳統工匠式的建筑方式。另外工業化時代也為他們提供了更具現代感的建筑材料,鋼鐵、水泥和玻璃使他們有充分自由去挑戰傳統材料難以實現的建筑式樣。同時,他們的建筑對象也不再是教堂、宮殿和城堡等這些早已退出歷史前臺的傳統建筑類型,而是商場、車站和居民區這些更具世俗意味的現代場所。所有這些都使現代主義建筑師們像其他部門的現代主義同行一樣激烈地否定傳統。“裝潢、多色多彩、隱喻、幽默、象征主義以及通俗化都被引入禁錄,所有各種裝飾和歷史性參考資料都被宣布為禁忌”[4]。他們對洛可可或巴洛克等繁瑣的古典樣式嗤之以鼻,并把現代城市社會的臟亂狀況完全歸罪于傳統建筑的失敗。在現代主義建筑運動著名的宣言書《走向新建筑》中,他們如此宣稱道:“現代建筑的那些大問題必須以幾何圖形方式來解決,……沒有規劃,我們便會感到讓人難以容忍的混亂、貧窮、不雅和任性。”[5]這樣,用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和合理化邏輯為標桿,來改造城市、規范現代城市生活便成為現代主義建筑師們的夢想。美國后現代建筑理論家查爾斯•詹克斯將之比喻為建筑領域的一場新教改革,“他們似乎以為,一旦讓他們的信念統轄工業化進程,必將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讓世界變得更好”[6]。
格羅庇烏斯是現代主義建筑最主要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之一,他的風格最具代表性。他于1923年在德國魏瑪為包豪斯建筑學校建造的校舍成為現代主義建筑的典范。他在設計上始終堅持理性化和標準化,盡可能降低成本以適應大規模建造,在保證功能的前提下決不增加任何無實用價值的裝飾。詹克斯曾戲稱這種建筑看起來像是工廠里的廠房。這種樣式被他的學生和追隨者們迅速帶到世界各地,成為所謂的“國際風格”,其結果便是讓幾乎所有的城市建筑群都看上去千篇一律,單調乏味,尤其是那種最為流行的火柴盒和方格子幾何造型,顯得尤為機械呆板。于是,現代主義建筑僅僅經歷了二三十年的輝煌后便很快窮途末路。人們沒有看到現代建筑師們所構想的那種更加整潔有序的城市環境,反而隨處可見充斥著更多犯罪、丑惡和單調的城市混亂地帶。一位留美華人如此描述他在充滿現代摩天大樓的曼哈頓街區的感受:“這里是紐約的心臟,心率總是太快,整個城市的血壓居高不下,脾氣暴躁,永遠亢奮。不分晝夜,救護車、救火車、警車、各色車輛呼嘯甚囂塵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地鐵太老,站臺太臟,列車駛過,把臭氣頂出地道隔柵,彌漫在整個街上。”[7]
另外,由于功能主義的指導思想使他們自然地偏好統一、標準和模式化等工具理性的建筑元素,這給他們的建筑實踐帶來嚴重負面效應,尤其造成對建筑使用者的一種家長式統治,具體表現為:他們拒絕同建筑所處的周邊環境進行對話,壓制和排斥地方建筑語言,以及漠視建筑用戶們的實際感受,等等。哈琴曾對此提出過批判:“雖然格羅庇烏斯和柯比西耶都為工人設計房屋,但兩人似乎都覺得沒必要向將來的用戶征求意見;他們當時肯定想當然地認為知識欠發達的人們愿意讓建筑師安排他們的生活。”[3]38這種對建筑傳統、周邊環境和普通大眾均置若罔聞的精英主義姿態終究會激起人們的厭惡。難怪詹克斯會充滿嘲諷地宣布現代建筑的末日:“現代建筑,1972年7月15日下午3點32分于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城死去。”[8]
當時,人們用炸藥摧毀了讓他們非常不滿的帕魯伊特•伊戈居住區,這也成為現代建筑死亡的標志性事件。要知道,這片建筑最初還是按照現代主義最先進的理念設計建造的,并因此獲得了美國建筑師協會的褒獎。對現代建筑而言,這真是具有莫大的諷刺和象征意味。客觀地說,現代主義建筑并非一無是處,它至少在短期內卓有成效地解決了現代城市普遍面臨的居住和生活環境問題。不過讓人遺憾的是,它將理性主義和功能主義的標準貫徹得太過徹底,只把建筑看成是精打細算的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場所,卻漠視了他們也有審美的生活和“詩意的棲居”的愿望,由此使得現代主義建筑都成了工業意象———格羅庇烏斯的作品像工廠庫房,柯比西耶的作品則像糧食倉庫。因此,當時過境遷,西方社會從二戰的廢墟中走出來,迅速進入福利社會和消費社會之后,它便馬上遭到了厭煩,后現代主義的反叛也由此而起。
二、城市建筑中的后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建筑的英雄主義悲劇引發了后現代建筑師們的反思,他們力圖在各個層面上實現對先輩們的反叛和超越。美國建筑師羅伯特•文丘里率先表達了他對現代建筑的不滿,他說:“建筑師們再也不能被清教徒式的正統現代主義建筑的說教嚇唬住了。我喜歡基本要素混雜而不要純粹,扭曲而不要直率,含糊而不要分明,既反常又無個性,既惱人又有趣,寧要平凡也不要造作,寧可遷就也不要排斥,寧可過多也不要簡單,既要舊的也要創新,寧可不一致和不肯定也不要直接的和明確的。我主張雜亂而有活力勝過主張明顯的統一。”[9]16這預示著其后的后現代建筑師們將把模糊、混雜和多元主義這些新的建筑語匯引入建筑實踐,以反駁現代主義建筑對純粹、統一和簡約的偏好。
在詹克斯看來,現代建筑之所以會被人們最終拋棄,其原因“部分在于它沒有跟使用者進行有效溝通,部分在于它沒能跟城市和歷史建立有效聯系”[6]。有鑒于此,后現代建筑要想贏得大眾,就必須在這兩方面做出改進。一方面,建筑不應再是設計師曲高和寡的個人獨白,而應是期待與大眾溝通的公眾語言;它不應僅局限于建筑師的個人想象,而是必須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這也就是詹克斯所說的后現代建筑的“雙重編碼”。他認為后現代建筑就是這樣的:“它既是專業的又是大眾的,同時既基于新技術主義又不忘老形式。它雙重編碼以簡化那些既精英又通俗、既古老又新奇的方式。”[6]惟其如此,它才能成為大眾生活更積極的參與者和干預者,從而避免現代主義者總以大眾導師自居卻反被大眾冷落的命運。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者們對歷史和傳統也有了全新的理解,他們不再徒勞地試圖逃避歷史,而是對它重新煥發無窮的好奇心。現代建筑師們秉承了先鋒派們一切向前看的時間取向,視歷史為負擔和夢魘,他們最擅長的就是將歷史抹平,一切從零開始。比如他們在巴西和印度分別建造了全新的城市巴西利亞和昌迪加爾。柯比西耶甚至要把巴黎推倒重建,但幸好這一建議沒被采納,不然這座美妙浪漫的歷史文化名城很可能早已泯滅。與現代建筑相反,后現代主義者們把歷史看成是充滿象征和寓指的豐富資源并加以利用。當然,他們對歷史也并非尋常意義上的借鑒和引用,而是如文丘里所說的那樣,“非傳統地運用傳統,……利用傳統部件和適當引進新的部件組成獨特的總體”[9]42。
于是,恰如文丘里為自己的一本書的題名所標示的那樣,后現代主義建筑師們便開始熱情地“向拉斯維加斯學習”。賭城拉斯維加斯是娛樂業的天堂,這里處處五彩斑斕,燈紅酒綠。凡是去過那里的人們無不為大街兩旁五花八門的建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古典的還是現代的,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各種樣式應有盡有。所有建筑都拒絕遵循統一的模式,即便在同一座單體建筑上也可常見各種風格的混雜。這些都使得整座城市顯得自由奔放,無拘無束。文丘里用下面一段話很形象地描述了拉斯維加斯一條主干道兩旁的建筑景觀:“這一地帶的秩序是包容———各個層面上的包容,既有看上去不協調的土地使用,也有不一致的廣告宣傳,還有采用胡桃福米加材質的新有機主義或新懷特式的飯店裝飾圖案。這里的秩序不是由專家掌控并使之悅目的,……這個地帶顯示了象征和隱喻在建筑中的價值,……對那些過去的、現在的、偉大的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的喻指和評判,以及對不管是神圣的還是世俗的日常生活環境的包容———這些都是今天的現代主義建筑所缺失的。”[10]
在后現代主義的批評者看來,這種糟糕的風格完全就是變相的剽竊,是將傳統變成充滿純粹死亡符號的倉庫,從中盜用拆解各式各樣的風格零件來重新裝配成“七拼八湊的大雜燴”[11]291。不過,支持后現代主義的人們卻認為這是在以反諷和戲仿的方式向傳統表達敬意。通過賦予舊形式以全新的意義,后現代建筑顯示了其對歷史的批判性繼承。用哈琴的話來說:“整個后現代主義的建筑語言與‘過去經歷的全部歷史事件’建立起了有反諷意味的聯系,旨在創造一種‘自相矛盾、意義模糊但卻充滿生機’的藝術。”[3]40按照哈琴的理解,后現代藝術所慣用的戲仿手法既不是單純想要玩弄和解構對象的游戲,也不是靠抄襲和拼湊來以假亂真的簡單模仿,而是一種在保持批判距離的前提下完成的對對象的有限重復[12]。總而言之,后現代主義試圖通過將反諷、戲仿、矛盾和含混這些新的語匯引入城市建筑,以審視的目光重訪過去,和過去的藝術與社會展開一場有諷刺意味的對話,并以此來對抗英雄的現代
主義所追求的肅穆、簡約、標準化和紀念碑式的建筑效果。為此,他們要求建筑師應該多傾聽來自大眾的,過去的,地方的和邊緣人群的聲音,以一個生活的積極參與者的身份形象融入周邊環境,而不是像現代建筑那樣非要做城市生活的引導者和塑造者,像個龐然大物般與所處環境不相適應。
三、建筑之爭的文化政治之維
把后現代建筑得以出現的物質基礎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轉型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這是西方不少研究者的常見作法。比如后現代研究者道格拉斯•凱爾納就認為:“從現代向后現代建筑的轉換,并非僅是一種建筑風格的演變,它更是向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制度、新的社會秩序轉換的信號。”[13]詹姆遜亦持此論,他說:“我相信,后現代主義的出現和晚期的、消費的或跨國的資本主義這個新動向息息相關。”[11]41820世紀6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的商品經濟為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物質豐裕,人們似乎沒理由再去堅守簡約樸素的清教道德了,消費享樂主義開始向大眾發出誘惑。后現代建筑憑借鮮亮的裝飾、多變的造型和豐富的設計,很快滿足了人們追求視覺美感的愿望。這似乎已足以解釋城市建筑從現代向后現代風格的轉變。然而,詹姆遜卻提醒我們:“關于建筑的論爭有助于凸顯這些看似僅與美學有關的問題的政治內涵,使我們容易發現其它藝術領域中有時更專業或更隱晦的討論所包含的政治內容。”[1]248現代建筑與后現代建筑之爭表面看來僅是關于美學風格的,但深層之下卻有著其文化政治內涵。
嚴格來講,藝術上的現代主義運動其實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所謂的英雄現代主義,一般包括現代主義早期的大師們,比如畫家凡•高和畢加索、詩人喬治•艾略特和作家喬伊斯等人。他們大多以叛逆姿態追求高度的藝術自治,強調藝術與社會絕緣,但除此以外并沒有多少真正的政治愿望,甚至還常常因為自身與資本主義體制之間那條看不見的金錢紐帶而備受政治責難。二是所謂的現代主義先鋒派,通常包括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和情境主義國際等流派。他們痛恨英雄現代主義,認為后者只顧沉溺于美學形式的革命,卻對社會現實沉默寡言,從而也就忘記了更有意義的社會政治革命。因此現代主義先鋒派們都有著強烈的政治訴求,力圖運用藝術家獨特的藝術形式為武器來推進激進的社會政治變革。于是,他們毫不猶豫地摧毀了英雄現代主義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藝術對于社會的自治,將藝術大膽引向社會,以期成為“新感覺”的塑造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馬爾庫塞的解放美學可以被看作是其最完備的理論敘述,而1968年的法國左派學生運動則是其最激烈的現實行動表達。現代主義建筑在其改造社會的烏托邦愿望上來看,明顯屬于先鋒派。
然而,這場雄心勃勃的先鋒運動還是過快夭折了。無論是希特勒在德國的納粹統治還是日丹諾夫在前蘇聯的文化專制,都將其視為異己而加以驅逐。在美國,它沒有遭受冷遇,但其命運卻比孤獨更可怕:它很快便被強大的消費社會徹底吸納和收編,繼而淪為商品經濟的寵兒。在伊格爾頓和詹姆遜等新左派理論家看來,這就是后現代主義的起源。先鋒運動在消費社會的溫柔鄉里耗盡了它最后一絲政治沖動,卻唯獨保留了舊有的花哨藝術形式,并寄居于后現代主義的新軀殼里茍活下來。文丘里和詹克斯等人便是它的代言人,他們被詹姆遜譴責為資本主義的附庸,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再現或再生產———強化———消費資本主義邏輯的方式”[11]419。按照詹姆遜的見解,城市建筑之所以會成為后現代主義最充分表達的領域,恰在于它更密切地依賴于資本主義的資金支持。在后現代主義建筑師們營造的城市空間里,詹姆遜看到的是一種無端的輕狂和淺薄、一種無故的裝潢和修飾,它用最直觀的方式表明當今社會不再對任何公共政治實踐抱有興趣。詹姆遜以他在鴻運大飯店的親身體驗哀嘆道:“它使我們不再對烏托邦的允諾空存幻想,不再寄望于烏托邦世界所帶來的基要政治轉變;總之,對于這一切,后現代空間都讓我們終止期望,終止一切的欲求。”[11]492
不過,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或許便會擺脫詹姆遜的悲嘆情調。毋庸置疑,后現代主義的確派生于激進政治運動的失敗。絕大多數人們都會同意伊格爾頓的觀點:“后現代主義有許多源頭,……然而不管有多少源頭,后現代主義實乃政治失敗之子也。”[14]單就后現代主義建筑來說,它的確是緣于人們對現代主義建筑拯救社會的烏托邦方案的失望和不滿,但若說它因此便完全走向現代主義政治的反面,成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體制的附庸并徹底喪失了對社會現實的政治批判性,這未免言過其實。準確地說,后現代主義是從現代主義的失敗中汲取了教訓,它知道歷史和傳統雖不一定就是我們今天的財富,但也未必就是壓在我們頭上的夢魘。我們不可能像現代主義者設想的那樣可以輕易抹掉歷史。如何創造性地使用歷史,在引用和借鑒歷史的同時保持反諷和戲仿的張力,才是更好的對待歷史的策略。后現代主義者不再渴求能有什么獨立于資本主義體制的以及可以憑此實現對它的純粹批判的外在飛地。即使有這樣的飛地,也只會讓自己被社會徹底邊緣化,最終失去影響和干預社會的可能。它深刻意識到自身總是與其意欲批判的對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就像詹姆遜所說的:“我們浸浴在后現代社會的大染缸里,我們后現代的軀體也失去了空間的坐標,甚至于實際上喪失了維持距離的能力了。”[11]505于是,它學會了如何像費斯克所說的那種“權且利用”的藝術,“這種藝術會在他們的場所內部,憑借他們的場所,建構我們的空間,并且用他們的語言,言傳我們的意義”[15](黑體字部分為原文所加)。現代主義建筑崇尚簡約、標準、規范和統一,而后現代主義建筑則把這些視為集權主義的代名詞,是少數人以救世主的姿態對多數人的專政。于是,他們義無反顧地放棄了清晰選擇了含混,放棄了簡單選擇了復雜,放棄了越俎代庖選擇了平等協商。這正是民粹主義的文化政治訴求在建筑領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