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中法律適用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中法律適用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qǐng)閱讀。

在對(duì)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的審判中,由于行政協(xié)議可能會(huì)同時(shí)涉及行政方面的爭(zhēng)議和民事方面的爭(zhēng)議。欲實(shí)現(xiàn)以正確的審判程序及實(shí)體法律解決糾紛的目的,需對(duì)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行為進(jìn)行解構(gòu),區(qū)分行政協(xié)議過程當(dāng)中產(chǎn)生爭(zhēng)議的部分是民事還是行政性質(zhì),并在此基礎(chǔ)之上針對(duì)不同性質(zhì)的爭(zhēng)議選擇適用相應(yīng)的程序和實(shí)體法律。
一、問題的提出
行政協(xié)議是現(xiàn)代行政法中合意、協(xié)商、行政民主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行政協(xié)議具有簽訂主體在協(xié)商基礎(chǔ)上共同實(shí)現(xiàn)行政目的特點(diǎn),在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過程中,被征收人可以一定程度上對(duì)補(bǔ)償模式和標(biāo)準(zhǔn)實(shí)現(xiàn)意思自治,因而通過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能夠使被征收人更加自愿地交出土地。由于立法規(guī)范的缺位,實(shí)踐中征收主體對(duì)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適用方法與定位不盡相同,協(xié)議補(bǔ)償制度并沒有被建立并完善,許多地方仍由土地管理部門、地方政府向村委會(huì)發(fā)放補(bǔ)償款,再由村委會(huì)實(shí)施二次分配的方式予以補(bǔ)償。同時(shí),行政協(xié)議正式納入行政上訴受案范圍的時(shí)間并不算長(zhǎng),指導(dǎo)司法實(shí)踐化解行政協(xié)議糾紛的規(guī)范仍不完備。由于上述兩點(diǎn)原因,法院在審理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時(shí),在程序與實(shí)體方面的法律適用等方面都存有困惑,即在審理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時(shí),判斷哪些糾紛的化解需要適用行政訴訟上的程序,哪些需要適用民事上訴上的程序;在審理實(shí)體問題的法律適用上應(yīng)該適用民事類規(guī)范還是行政法律規(guī)范的問題。
二、爭(zhēng)議性質(zhì)的判斷
事實(shí)上,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效果的實(shí)現(xiàn)并非一蹴而就,其從磋商到締結(jié)再到履行,在多個(gè)行為的有機(jī)組合之下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才得以開花結(jié)果,而協(xié)議的糾紛恰恰來自于這些具體環(huán)節(jié)當(dāng)中的某個(gè)或某幾個(gè)。因此,審理模式的構(gòu)建需要先將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化整為零,分析其具體環(huán)節(jié)的性質(zhì),在司法實(shí)踐當(dāng)中根據(jù)糾紛的性質(zhì)來選擇適用法律。理論界對(duì)于行政協(xié)議問題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在圍繞其行政性與協(xié)議性,對(duì)協(xié)議的不同方面就行政性與協(xié)議性進(jìn)行區(qū)分研究,而作出這一判斷的決定性因素就是行政機(jī)關(guān)的高權(quán)行為是否介入。由于締約的民事主體不具備行使高權(quán)行為的可能性,同時(shí)行政訴訟的作用在于審查行政機(jī)關(guān)行為的合法性。從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締結(jié)到履行到過程到角度,在協(xié)議締結(jié)階段,征地協(xié)議并非像一般協(xié)議的締結(jié)那樣單獨(dú)同締約相對(duì)人進(jìn)行邀約和磋商,而是根據(jù)規(guī)劃或者擬征收的決定,在一定范圍內(nèi)向被征收人進(jìn)行公告或者通知,這一行為實(shí)質(zhì)上是實(shí)現(xiàn)征收補(bǔ)償目的的管理手段,具備高權(quán)屬性,應(yīng)認(rèn)定為行政性行為。在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履行階段產(chǎn)生的糾紛在于作為被征收人的原告方對(duì)作為征收主體的被告的履行行為,即對(duì)是否補(bǔ)償以及補(bǔ)償?shù)姆绞胶蛿?shù)額不服。而產(chǎn)生如上協(xié)議履行糾紛的原因既可能出自高權(quán)行為的介入,也有可能是其他客觀因素導(dǎo)致的履行不能。就協(xié)議變更而言,不能認(rèn)為協(xié)議變更都屬于民事行為,因?yàn)橥恋卣魇昭a(bǔ)償協(xié)議內(nèi)容的產(chǎn)生并不都是來自民事上的意思自治。對(duì)于協(xié)議雙方在達(dá)成合意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不損害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變更以及民法所規(guī)定的情勢(shì)變更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是民事性質(zhì)行為。只有當(dāng)高權(quán)行為介入,即征收主體出于行政效果當(dāng)變更而去變更行政協(xié)議,由于這一過程明顯有高權(quán)行為介入因而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其行政性質(zhì)。對(duì)于合同的撤銷與解除,民法典分別規(guī)定了對(du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欺詐、脅迫、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的情況下受損害的一方可以在一定時(shí)間內(nèi)單方撤銷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若被征收人及利害相關(guān)人因?yàn)樯鲜鍪掠芍鲝埥獬魇昭a(bǔ)償協(xié)議或征地主體基于上述事由而解除協(xié)議的,則屬于民事性質(zhì)行為。若行政機(jī)關(guān)出于上述事由之外的對(duì)征收補(bǔ)償所欲實(shí)現(xiàn)的效果進(jìn)行變化的事由而解除的,則屬于行政性質(zhì)行為。根據(jù)上述分析,司法實(shí)踐在處理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時(shí),如果涉及的糾紛性質(zhì)屬于單純的民事性質(zhì)的糾紛而不涉及高權(quán)行為,則只需要在程序上依據(jù)民事訴訟法,在實(shí)體上依據(jù)民法典合同編部分的規(guī)范進(jìn)行審判。而當(dāng)糾紛涉及高權(quán)行政性質(zhì)時(shí),則需要在程序上根據(jù)行政訴訟法、在實(shí)體上依據(jù)2019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以及地方的相關(guān)立法和其他規(guī)范。
三、法律的具體問題
(一)原告資格
由于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兼具行政性與民事性,在原告資格問題上,需要明確適用民事訴訟規(guī)范還是行政訴訟規(guī)范。民事訴訟規(guī)范和行政訴訟規(guī)范當(dāng)中對(duì)于原告資格的規(guī)定的差異在行政訴訟法中原告資格對(duì)協(xié)議相對(duì)性的突破。在民事規(guī)范當(dāng)中,合同關(guān)系的原告資格需要遵循合同相對(duì)性原理,即只有作為締約方以及合同當(dāng)中的明確規(guī)定了權(quán)利義務(wù)的第三方才能對(duì)合同提起訴訟,但就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內(nèi)容而言,一般規(guī)定了征地范圍和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的事項(xiàng),并不會(huì)對(duì)第三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作出明確規(guī)定。而根據(jù)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之規(guī)定,不僅作為行政行為相對(duì)人的一方(即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締約方),同行政行為具備利害關(guān)系的第三人同樣具備原告資格,這種利害關(guān)系則不局限于合同的明確規(guī)定,而在于行政行為所造成的事實(shí)影響。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可能存在如下幾個(gè)方面的爭(zhēng)議:其一是在協(xié)議締結(jié)方面產(chǎn)生的爭(zhēng)議,其二是因不滿補(bǔ)償方案的范圍與標(biāo)準(zhǔn)而產(chǎn)生的糾紛,其三是征收主體變更補(bǔ)償?shù)姆秶鷺?biāo)準(zhǔn)而產(chǎn)生的糾紛。根據(jù)上文之分析可知,以上三個(gè)方面的爭(zhēng)議,均具有高權(quán)行為介入而使?fàn)幾h成為行政爭(zhēng)議的可能性。因此宜采取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的“利害關(guān)系標(biāo)準(zhǔn)”作為原告資格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
(二)審查范圍
就審查范圍來說,如果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適用民事審查,根據(jù)當(dāng)事人主義的要求,其審查的范圍限于原告有關(guān)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訴訟請(qǐng)求。而對(duì)于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行政性質(zhì)的司法審查,其范圍則可能超出協(xié)議條款本身。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將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規(guī)定為征地審批的必要前置程序。即締結(jié)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是整個(gè)實(shí)現(xiàn)征地補(bǔ)償行政效果的一部分。整個(gè)實(shí)現(xiàn)補(bǔ)償?shù)倪^程,實(shí)際上包括了對(duì)土地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和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對(duì)于“征收范圍、土地現(xiàn)狀、征收目的、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安置方式和社會(huì)保障等”情況的公示、聽取被征收人的意見、組織召開聽證會(huì)以及最后的土地權(quán)利人登記的程序。而這些前期的程序最終以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中的條款的形式與被征收人形成行政法律關(guān)系,成為能夠?qū)Ξ?dāng)事人權(quán)利義務(wù)直接產(chǎn)生影響的行政行為。據(jù)此,對(duì)于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行政性司法審查范圍標(biāo)準(zhǔn)應(yīng)包括上述的形成征地范圍與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的全部過程而不限于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條款本身。在審查標(biāo)準(zhǔn)上,應(yīng)遵循合法性審查標(biāo)準(zhǔn),即審查從對(duì)土地情況調(diào)研到完成登記最終締結(jié)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是否符合新土地管理法的程序要求,是否符合法律及行政法規(guī)之要求。對(duì)于行政具體的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與征地范圍的合理性,一般不在司法審判裁量之限。
(三)協(xié)議效力
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效力實(shí)踐當(dāng)中一般都認(rèn)為其成立即生效,但隨著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將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的簽訂規(guī)定為征地審批的前置程序,司法實(shí)踐當(dāng)中需要重新審視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效力。因?yàn)樵谛碌囊?guī)范體系當(dāng)中,征地主體即使同被征收人簽訂了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由于該征地決定還沒有得到省級(jí)以上人民政府的批準(zhǔn),作為征地主體的縣級(jí)人民政府此時(shí)還不具備履行協(xié)議即征收土地并給予被征收人補(bǔ)償?shù)臈l件。此時(shí)由于協(xié)議不具備履行的可能性,所以在協(xié)議簽訂之時(shí)并不能直接認(rèn)定協(xié)議已經(jīng)生效。在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作為征地審批的前置程序的規(guī)范體系中,學(xué)界對(duì)于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的效力主要有“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不能生效說”“預(yù)約協(xié)議說”及“成立但未生效說”等觀點(diǎn)。其中“不能生效說”指為了控制土地的使用范圍,合同主體訂立的征地補(bǔ)償合同在未經(jīng)批準(zhǔn)的情況下不發(fā)生任何效力。這是基于對(duì)公共利益的考量,政府征地是為了滿足公共需求,因此未獲審批的合同即不應(yīng)當(dāng)發(fā)生效力。“預(yù)約協(xié)議”說認(rèn)為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等締結(jié)可以分為訂立預(yù)約階段和訂立本約兩個(gè)階段。“成立但未生效”說認(rèn)為在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成立時(shí)其并未取得效力,直到擬征收決定得到省級(jí)以上人民政府審批通過時(shí)才能生效。如果采用“不能生效”說會(huì)使被征收人在簽訂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后付出利益但失去法律保障依據(jù)。“預(yù)約協(xié)議”說雖然能解決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作為征地決定批準(zhǔn)的前置程序問題,但是實(shí)踐當(dāng)中征地主體與被征地人并沒有先簽訂預(yù)約再簽訂本約的習(xí)慣,一般都會(huì)一次性地完成征地補(bǔ)償內(nèi)容的全部締約,因此與實(shí)際情況不符。所以在新土地管理法所確定的征地補(bǔ)償程序下,宜采“成立但未生效說”,認(rèn)為其生效的標(biāo)志為省級(jí)以上人民政府批準(zhǔn)縣級(jí)以上人民政府之征地申請(qǐng)。同時(shí)行政協(xié)議司法解釋第十三條規(guī)定“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經(jīng)過其他機(jī)關(guān)批準(zhǔn)等程序后生效的行政協(xié)議,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jié)前未獲得批準(zhǔn)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確認(rèn)該協(xié)議未生效”,表明司法實(shí)踐中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生效判斷的最終節(jié)點(diǎn)在于一審法庭辯論結(jié)束之前。如果在簽訂征地補(bǔ)償協(xié)議后,征地申請(qǐng)未獲批準(zhǔn),擬征收土地的被征收人起訴縣級(jí)以上人民政府主張其付出信賴?yán)娴模嗣穹ㄔ簯?yīng)當(dāng)予以支持。
四、根據(jù)爭(zhēng)議選擇適用法律
在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爭(zhēng)議案件的受理方面,如果按照行政性與民事性的區(qū)分來構(gòu)建審理模式,那么案件的受理自然也應(yīng)當(dāng)按照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相區(qū)別。即對(duì)于單純民事糾紛的應(yīng)當(dāng)適用民事規(guī)則,對(duì)于行政性糾紛應(yīng)當(dāng)適用行政訴訟規(guī)則。但由于在對(duì)糾紛進(jìn)行審查之前難以預(yù)先判斷其性質(zhì),且可能存在一案件兼具兩種糾紛之情況,故實(shí)際上應(yīng)兼取二者之范圍,即選取“并集”作為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案件的受理規(guī)則。基于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兼具行政性與協(xié)議性,在一個(gè)案件的審判當(dāng)中,可能會(huì)遇到既要處理行政性爭(zhēng)議又要審理民事性爭(zhēng)議的情況。此時(shí)需要適用不同的審理規(guī)則。在審判實(shí)踐當(dāng)中,法官并非將當(dāng)事人雙方的主張與爭(zhēng)議進(jìn)行概括性審判的,而是在聽取雙方訴求與答辯的基礎(chǔ)上,首先根據(jù)爭(zhēng)議的法律事實(shí)與行為確定好爭(zhēng)議焦點(diǎn),再以舉證質(zhì)證和法庭辯論的方式逐一審理這些糾紛。在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當(dāng)中這些糾紛往往圍繞著協(xié)議過程當(dāng)中雙方當(dāng)事人的行為展開,因此本文對(duì)于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行政性與民事性的劃分效果在審判實(shí)踐當(dāng)中就表現(xiàn)為法官所總結(jié)的不同性質(zhì)的爭(zhēng)議焦點(diǎn)。依據(jù)爭(zhēng)議焦點(diǎn)所圍繞的行為或事實(shí)是否有高權(quán)性質(zhì)行為介入,可以將爭(zhēng)議點(diǎn)分為行政性爭(zhēng)議或民事性爭(zhēng)議,并以此來確定適用行政實(shí)體法律還是民法典相關(guān)規(guī)范。在案件判決方面,由于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以雙方互設(shè)權(quán)利義務(wù)的協(xié)議形式存在,其行政性質(zhì)的行為以協(xié)議條款的形式表現(xiàn)。因此被征收人在提起訴訟時(shí),一般會(huì)針對(duì)協(xié)議條款提起如確認(rèn)協(xié)議(部分)的有效或無效、要求征地主體履行協(xié)議、賠償被征收人因征地主體違約或締約過失等行為造成的損失等民事性質(zhì)的訴求。當(dāng)被征收人針對(duì)的條款或征地主體之行為涉及征地主體的高權(quán)行政行為時(shí),實(shí)際上會(huì)發(fā)生民事性訴求與行政性訴求的重合,即既具備行政性審查請(qǐng)求之性質(zhì)又具備民事性審查之性質(zhì)。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民事性請(qǐng)求與行政訴訟請(qǐng)求是等效的,如請(qǐng)求確認(rèn)協(xié)議的有效、無效與確認(rèn)行政行為的效力,請(qǐng)求履行協(xié)議與請(qǐng)求行政機(jī)關(guān)按照承諾做出行為,以及在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當(dāng)中請(qǐng)求賠償補(bǔ)償原告之損失等,這些訴訟請(qǐng)求在判決效果上實(shí)際上是等效的。而法院作出判決時(shí)需要注意的是,在審查有關(guān)行政性行為時(shí),基于全面審查之原則,需要對(duì)超過被征收人訴求范圍的行政行為的整體的合法性進(jìn)行審查,并在裁判當(dāng)中一并作出判決。
五、結(jié)語
法律規(guī)范是法官在司法過程當(dāng)中實(shí)現(xiàn)公平與公正的工具,只有選對(duì)了工具,才能實(shí)現(xiàn)維護(hù)正義的目的。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具備行政行為屬性較強(qiáng)而民事協(xié)議屬性較弱的特點(diǎn)。但這并不意味著司法實(shí)踐對(duì)于其產(chǎn)生的糾紛的審判過程當(dāng)中能夠忽略對(duì)民事實(shí)體法律和民事審判程序的適用。在程序選擇上,應(yīng)分析具體糾紛的性質(zhì),因地制宜地選用程序與實(shí)體法律,以此在集體土地征收補(bǔ)償協(xié)議糾紛的審判當(dāng)中統(tǒng)一裁判標(biāo)準(zhǔn)。
作者:肖海生 劉繼漢 單位:河南省高級(jí)人民法院 鄭州大學(xué)法學(xué)院
相關(guān)熱門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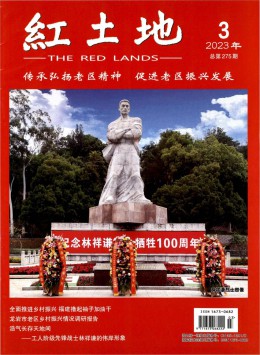
紅土地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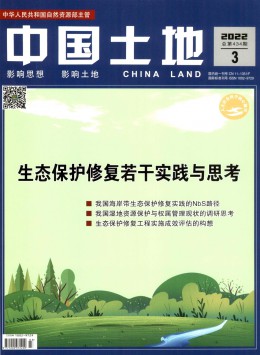
中國(guó)土地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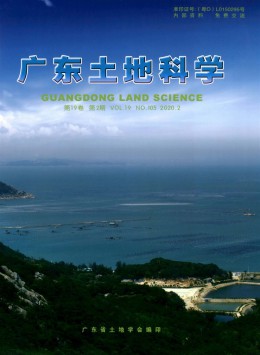
廣東土地科學(xué)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中國(guó)土地科學(xué)
級(jí)別:CSSCI南大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土地經(jīng)濟(jì)研究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