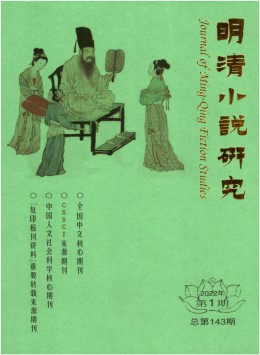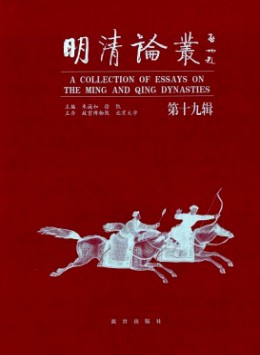明清傳奇無眠的審美積淀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明清傳奇無眠的審美積淀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黃雪敏 單位:華南師范大學南海學院
從文藝學的立場來看,物理境“主真”,心理境“重情”。鄭板橋在《題畫》中說:“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于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時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這句話從創作的角度,論析詩人創作時如何從對于“主真”的物理境的觀察轉入對于“重情”的心理場的關注。在明清傳奇“無眠”主題的唱段中,主人公正是從“無眠”的物理境轉入“無眠”的心理場,從對外在景物的觀察轉向對內心情感的關注與認知。具體而言,明清傳奇中“無眠”主題的物理境主要有以下三種:
其一,閑庭攬月,這是展示“無眠”主題最為經典的戲曲場景。明月意象是中國文學中最為常見的意象之一,而且由于“無眠”發生在夜晚,因而它與月光之間形成了最緊密的場景關系。月光下,夜色中,閑庭漫步,向來是中國文人夜深不能寐后的行為取向之一。閑庭、竹影、閑人,是文人們在夜色無眠中身心所處的物理環境,嫻靜而優雅。在傳奇的“無眠”場景中,主人公滿懷憂傷不能寐之時,多是選擇于庭中散步,空對春紅。《玉簪記》第十六出《弦里傳情》中潘必正出場時自言:“小生看此溶溶夜月,悄悄閑庭。背井離鄉,孤衾獨枕,好生煩悶,只得在此閑玩片刻。”后又對偶遇的道姑陳妙常解釋:“小生孤枕無眠,步月閑吟。”又如《牡丹亭》第十二出《尋夢》中杜麗娘所唱:“[月兒高]幾曲屏山展,殘眉黛深淺。為甚衾兒里不住的柔腸轉?這憔悴非愛月眠遲倦,可為惜花,朝起庭院?忽忽花間起夢情,女兒心性未分明。無眠一夜燈明滅,分煞梅香喚不醒。”明清為封建社會的末期,此間女子的生活為嚴酷的封建禮教氣氛所籠罩,終日與世隔絕,眼睜睜地看著青春逝去,卻又無能為力。因而,《牡丹亭》中杜麗娘來到園中不再是為賞花,而是在皎潔的月光下追尋那失去的美好:“[前腔]春香已去。天呵,只圖舊夢重來,其奈新愁一段。尋思輾轉,竟夜無眠。咱待乘此空閑,背卻春香,悄向花園尋看。”這段唱詞哀嘆自己將逝的青春和倫理奴役之身,語辭凄切婉轉,情思悠長,吟唱出一種無眠之中典雅、清麗的物理環境。
其二,孤燈淚枕,這是呈現“無眠”主題不可或缺的一種戲曲橋段。明清傳奇里,人物在無眠中傾聽更漏,殘燈撥盡,感受著時間的催逼和壓迫,卻又無法排遣,難以釋懷。如《桃花扇》中的詩句:“欲尋好夢難入夢”,再如《嬌紅記》中玉嬌紅在《期阻》里所唱:“[玉肚交]昏昏庭院,灑花枝聲聲慘然。冷清清獨對殘檠,悶騰騰輾轉無眠。潺潺小窗滴漏穿,瀟瀟變做心窩怨。恨悠悠燈前影前,淚斑斑腮邊枕邊。”在劇中人物的輾轉無眠中,孤燈、庭院、冷花、淚枕等意象構成了一種物理境,抒發內心的憂傷苦悶。這一段唱詞,將普通的日常場景營造為一種“別有幽愁暗恨生”的凄美境界。“無眠”主題的敘事行為,從庭外至房內,從聽覺到視覺,從客體到主體逐步拓展,展現的是一種內斂而豐富的物理境。無情的殘燈更漏,預示著時間的流逝;枕冷淚濕,展示著主體的孤獨。
其三,冷雨殘夢,這是“無眠”主題自我深化的一種戲曲安排。中國文人對于自然造化有一種本能的認同和契合,因而“無眠”場景中所展現的事物來自于日常所見。孔子就有“君子比德與玉”之說;鐘嶸在《詩品•序》中曾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陸機《文賦》也認為:“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這些都深刻揭示了外在物理景致對于詩人的審美啟發。可見,敏感的文人極易為自然界的草木、風雨、氣候所觸動并引發審美感悟。這種形式的“無眠”的物理境,是由于人物的情思憂懷所觸發的對于身邊日常之景的審美觀照,是一種情感的外在的投射與遷移。也可以說,傳奇中這一種由外及內的物理境敘事,也帶有一種“移情”的藝術功能。如《長生殿》第十九出《絮閣》中的一段唱詞:“[北黃鐘•醉花陰]一夜無眠亂愁攪,未拔白潛蹤來到。往常見紅日影弄花梢,軟咍咍春睡難消,猶自壓繡衾倒。”《桃花扇》中《寄扇》一出,也唱出了世亂時移之下,李香君在漫長的無眠黑夜中身單影只的心靈漂泊之旅。如“醉桃源”一段:“寒風料峭透冰綃,香爐懶去燒。血痕一縷在眉梢,胭脂紅讓嬌。孤影怯,弱魂飄,春絲命一條。滿樓霜月夜迢迢,天明恨不消”,讀之更加令人腸斷。料峭的寒風不僅是可感的自然事物,也為人物的無眠之夜營造了一種廣闊無邊的凄涼氛圍,更襯顯出人物所處的孤苦環境,以及人物精神家園的頹敗。
除了上述三種物理境外,傳奇中用以襯托“無眠”主題的物理境還包括女子深閨愁嘆、男子酒斷愁腸等類型,如《長生殿》第四十五出中唐明皇無眠之夜中酒后獨唱:“[越調引子][霜天曉角](生上)愁深夢杳,白發添多少。最苦佳人逝早,傷獨夜,恨閑宵。(生唱)不堪閑夜雨聲頻,一念重泉一愴神。挑盡燈花眠不得,凄涼南內更何人。”審美主體在“無眠”的物理境中,看到了人生的局限和青春的流逝,看到了人類自身的“百年孤獨”。物理境本身并不是“無眠”主題所要突出的重點,然而通過物理境中的若干意象,卻能夠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命運、情感和窘迫,傳遞著審美主體的沉重哲思。
在明清傳奇中,“無眠”主題的物理境對應和揭示的,是“無眠”的種種心理場。生命個體和個性的不同,心理和認知的向度不同,導致審美主體對同一物理境所期待和構建的心理場也不相同。反映到劇本或演出中,傳奇人物“無眠”的心理場主要包含以下幾種蘊含:
首先是抒情主體自我意識的蘇醒。在明清文化進步的、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文人的主體意識逐漸高漲,文人個性也不斷凸顯。具體而言,在明清傳奇中,不僅女性角色發出各種悲吟,許多男性角色包括作者自身,也一次次抒發自我的悲鳴,宣告個體的尊嚴和自由。《玉簪記》第十六出中的書生潘必正出場唱詞為:“[懶畫眉]月明云淡露華濃,欹枕愁聽四壁蛩。傷秋宋玉賦西風,落葉驚殘夢,閑步芳塵數落紅。”道姑陳妙常的出場唱詞為:“朱弦聲杳恨溶溶,長嘆空隨幾陣風。”二者都體現了作者通過劇中人物抒發的孤獨和感慨。孤獨情緒是自我意識的標志性符號之一,因為只有主體的自我意識蘇醒到一定程度,才能感受到人類自身的悲劇性存在,才會去尋找朋友和伴侶,也才開始構建一個安放性靈的精神家園。《玉簪記》的作者高濂主要活動于明代嘉靖、隆慶和萬歷年間,因而這一段“無眠”的唱段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暗含著明中葉以來男性和女性共有的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
其次是缺失性情感體驗的呈現。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看,人有七種不同層次的需要,需要未滿足之時,都意味著個體生命的缺失。而這種缺失性體驗常會引起情感上的變化。明清傳奇中“無眠”主題表現出來的情緒,即為一種缺失性的情感。《長生殿》第四十九出《得信》中,晚年的唐明皇,十分想念逝去的楊玉環,“因令方士楊通幽攝召芳魂,誰料無從尋覓”,在蕭索的孤燈殘照下發出了憂傷慨嘆:“[四時花]悠悠、欲眠不眠欹枕頭。非耶是耶睜望眸。問巫陽,渾未剖。活時難救,死時怎求?”愛情是生命中特別重要的一個構成,唐明皇的缺失性體驗此時尤為深刻。當然,不僅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吟嘆生命的悲劇性缺失,普通老百姓的體驗也許更多更復雜,只不過他們缺乏寫作能力和抒情技巧罷了,“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袁枚《馬嵬》其四)特別重要的是,在這一段時期的傳奇作品中,文人特別喜歡將自己的缺失性體驗,隱含在劇中女性旦角的唱詞中,顯現了細膩、委婉而精致的藝術構思。短命的南明王朝衰亡之后,歷史的風云變幻令敏感的文人愈加察覺生無所依,歸屬感的缺失,使得他們一次次發出“無眠”的悲嘆。文人以女性自喻,展示了“臣妾化”的心靈迷失和無奈。
此外是以國恨家仇為核心的憂患情懷的覺醒。明清易代,一方面是國家政權的更替,一方面是滿漢民族意識之爭,引發無數文人輾轉反側,憂思難遣。同時,這種憂患意識,還在作家的筆下,上升為一種對于時代更替、歲月流轉的普遍性認識和嘆息。《桃花扇》續四十出《余韻》中寫到“:[離亭宴帶歇指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過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傳奇的這種文辭,既是遣發作者自身的憂患情懷,也是在困境中探求個體性靈的詩性生存。明清時期,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狂儒”,嘯傲山林,不遵禮法,獨愛詩酒風流,在詩文傳奇創作上追求狂逸和野逸之美,在夜不成眠之際“寫胸中逸氣”,這是“不得志之逸”的時代性表現。
可見,明清傳奇中人物的“無眠”,常常寄托著生命之失的浩嘆。他們試圖追尋生命的自由和飄逸,卻在復雜的現實情境中遭遇挫折,超逸的愿望也往往落空。這一種欲望的表達與追求,正是明清商品經濟萌芽和啟蒙思潮影響下,人性的復蘇與個性的張揚的具體體現。
在中國文學史上,一種文體的興起和成熟,既是其所處的特定時代文化因子的整合,也是其內在的文化傳統的繼承。明清傳奇中“無眠”主題的頻繁出現,既是明清社會轉型之際社會啟蒙思潮的催生之果,又是文人作家對于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以及對于個體生命意志的持續求索。按照李澤厚的美學觀點,這是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文化積淀”。
明清兩朝處于中國封建統治歷史的末期,政治上高度專制獨裁,思想上則以程朱理學作為學術思想,并通過科舉制度和“八股取士”等政策限制、遏制和招攬知識分子。這一時期,封建禮教與儒家倫理的發展到了一種極端的地步,對于普通民眾和讀書人的壓制與摧殘也達到了一種嚴酷的程度,遭到許多文人的抗拒。李贄宣稱:“聲色之來,發乎情性,由乎自然。”因而,從程朱理學內部所派生出的王陽明學派,以及由此脫胎而出的“異端”即泰州學派、鼓山學派等,開啟了明代中葉具有一定現代價值的啟蒙思想,肯定人性即人的自然情欲、需求和欲望。同這樣一種“去天理,存人欲”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潮相呼應,明代中后期,一股“主情反禮”的文藝思潮席卷文壇,如袁宏道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湯顯祖對“至情”的謳歌、李贄對“童心”的高揚、洪昇對“純情”的贊美等等,都是對于“理”的否定,對于人性的高揚。而戲曲更是“情”的產物,特別是袁枚,對于“性情”和“性靈”極為鐘愛,“袁枚又認為性情不僅要真,而且要強烈,要激切,要滂沛充盈,要深郁沉摯。”又如王夫之極力提倡情景的審美合一,他在《姜齋詩話》中說:“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揭示了情景互生的審美發生論,駁斥極端的封建倫理情感論。明末,這種浪漫主義的“主情”思潮逐漸滲入傳奇之中,文人們開始用戲曲表演的方式批判傳統,重新審視人生和自我。由此,人性的復蘇與個性的張揚日益渴望得到實現,詩文傳奇等文體中的“無眠”主題也開始繁盛。
進一步說,“無眠”主題的頻繁出現,既源于明清社會思潮的催發,也基于古代文學傳統的變革和發揚,是古代詩歌“無眠”敘事母題的階段性展示。因為中國幾千年來的詩歌傳統,“強調的是‘代際’性的文類秩序、語言策略和象征體系的差異,而不是詩歌本質上的對立。”
關于“無眠”的主題,傳統的詩歌記載最早見之于《詩經•周南》開篇《關雎》,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除《關雎》篇外,還有《詩經•邶風•柏舟》篇“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等詩句,字淺意深,引發讀者無窮的審美遐思。
《詩經》作為中國的詩歌濫觴,它的詩句為“無眠”文學主題的形成樹立了典范。后人對“無眠”的描寫,也多肇始于此。《古詩十九首》繼承了這一傳統,多有這樣的詩句:“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緯。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這些詩句都是“無眠”的敘述來表達復雜的審美情懷。魏晉是政治昏暗動蕩不安的時代,也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創作開始轉向對于人自身處境的描寫,開始關注他者、自身和世界間的關系。魏晉的“無眠”,也正是自我之世界的開啟。此時,文人對于“無眠”的描寫,更專注于個體的行為及生活世界的“無眠”,呈現一種較為粗獷的風格,如曹植在《雜詩六首》其二云“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云”,阮籍《詠懷》其一詩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陸機《赴洛道中作》詩云“撫幾不能寐,振衣獨長想”,等等。
“無眠”的文學主題在南北朝的華麗詩風中得到了加強,尤其是在上層貴族的詩人群體中。南朝的《樂府詩集》中有不少這樣的篇目,如《子夜歌》其三:“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散喚聲,虛應空中諾。”此時“無眠”呈現的是一種沉醉頹靡的氣息。初唐詩人反對這種華麗而綺靡的詩風,盛唐詩人則為“無眠”主題開拓了新的氣象。白居易《長恨歌》詩中云“: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這首長篇歌行也成為傳奇《長生殿》的藝術源頭。《琵琶行》詩則描寫了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婦”的女子夜不成寐的故事:“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而以情致細膩、清幽動人為特色的宋詞,也不乏“無眠”、“難眠”的抒情主題,如范仲淹的《漁家傲》下闋云:“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又如姜夔《齊天樂》“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的詞句等。
元曲當中,“無眠”主題的使用更加頻繁,在“元曲四大家”的劇本中隨處可見。關漢卿《拜月亭》就有這樣的唱段:“[胡十八]我便渾身上都是口,待教我怎分辨?枉了我情脈脈、恨綿綿!我晝忘飲饌夜無眠。”這段詞把劇中人物那種急切分辨的情致刻畫得栩栩如生,從側面展示其內心孤獨彷徨的情感。“無眠”主題抒發的幽思之情細長而綿密,人物的形象也更為鮮活,充滿立體感。這為明清傳奇中人物的“無眠”主題的敘述,奠定了一種成熟的、可供模仿的范式。而這個“無眠”的敘述范式,又為其他文體如明清詩詞的創作提供了一種藝術參考。因而,明清傳奇中主人公的“無眠”,無論是其物理境的表現,還是其心理場的傳達,都受到了前朝“無眠”主題及其敘事藝術的深刻影響。
綜上所述,明清傳奇中“無眠”主題的吟唱,既顯現了傳奇作為中國古代戲曲形式之一所具有的清幽意蘊、典雅情趣和逸趣之美,也是對以《詩經》為范本的詩學傳統的一種繼承和發揚。同時,“無眠”主題也反映了明清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時代風潮影響下,對于自我意識和本我生命的深刻感知,對于生命缺失的體驗及情感變化,體現了人性復蘇、傳統批判、時代變遷等方面的文化認知價值。可見,明清傳奇中的“無眠”主題,一方面蘊含了傳奇這種時代文體內在的審美意蘊和民族風情,同時也彰顯了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文體價值和美學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