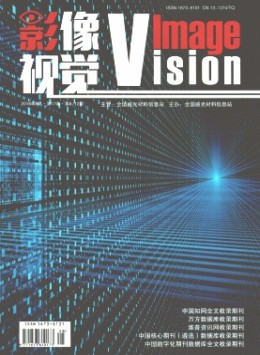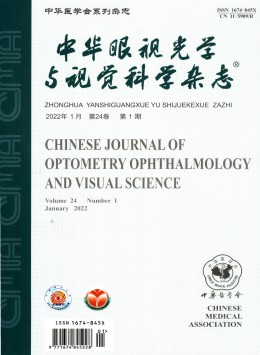視覺人類學視域下的扁擔舞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視覺人類學視域下的扁擔舞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廣西壯族扁擔舞因其以扁擔為道具而得名,古代稱為“打舂堂”,現在稱之為“扁擔舞”,壯語俗稱“谷榔”、“打榔”。扁擔舞主要是模擬人類生產勞動的場景,它流行于廣西紅水河畔的都安、馬山和桂西的百色、巴馬一帶,尤以馬山、都安最具代表性。扁擔舞的內容十分豐富,主要表現插秧、收割、打谷、舂米、織布和打布頭等,也展現了人們在勞動過程中的歡樂情緒。每逢年節,當地婦女們便手持扁擔,涌向街頭巷尾、曬谷場,跳起扁擔舞。他們兩人一對,圍在長凳或舂米木槽旁,邊擊、邊歌、邊舞,用扁擔兩端互相撞擊或敲擊長凳,發出咯嗒咯嗒的和諧音響。這種節奏強烈有力,聲響清脆高亢,舞姿變化多樣,富有濃郁的勞動生活氣息。
舞蹈視覺人類學作為舞蹈民族志研究的一種新方法,可以用來描述或解釋舞蹈的文化內涵和審美特征。
(一)壯族扁擔舞的視覺色彩藝術效應
根據托馬斯•楊和赫爾姆霍三原視覺理論,“將紅、綠、藍三顏色混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顏色。實際上,人類眼睛主要有三種感色細胞:第一種主要是對紅色作出反應;第二種主要是對綠色作出反應;第三種主要是對藍色作出反應”。[1]這些感色細胞體系活動的不同方式可以使人類感知到不同顏色。這一研究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最后科學家證明了人類視網膜中主要含有三種類型的視錐細胞,一種主要是對長波紅色的反應,其次是對中波綠色的反應,第三種是對短波藍色的反應。如果我們把“赤、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混合在一起,那么顯示出來的是白色。如果我們只選擇其中三原色紅、黃、藍的話,其結果也是白色”。[2]
如果我們只選擇三原色中的兩種顏色的話,那么我們就能見到我們所需要的各種不同的顏色。“三原色視覺理論解釋了視網膜上的視錐細胞所發生的變化”。[1]視覺與大腦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眼睛對各種光波和視覺圖像產生反應,并把它們復制成神經信號傳遞給大腦,大腦破譯神經信息,即通過感知舞蹈服裝顏色、道具形態,服裝與道具質地和舞蹈運動形式及動作技巧,形成視覺神經感色系統。壯族扁擔舞演出者的服飾道具均以紅、黃、藍三原色為主色調,分別再在服裝上鑲嵌以白色和黑色;道具底色是一種深板栗色調,目的是以三原色為主色調對觀眾能產生一種直觀的視覺反應,即視覺心理反應。扁擔舞的表演道具由舞蹈者手持一根扁擔,扁擔多用毛竹削制而成,長短各異,一般長約1.5米,兩端較窄,中間較寬。男女分別身著黃色和紅色服裝,手持黃色扁擔相向而立,圍著一條長一丈多、寬一尺的板栗色為底面的木槽或板凳(凳長250厘米,寬40厘米、高50厘米),在木槽和板凳上繪有一種原始狩獵巫術祭祀圖案,男女同聲呼喊,上下左右相互打擊,邊打、邊唱、邊舞,時而用扁擔兩端互擊,時而敲擊長凳或長方形木箱,時而敲擊地面,模擬農事活動中的耙田、插秧、戽水、收割、打谷、舂米等農耕勞作姿勢或動作。
在扁擔舞中,男性舞者以黃色調為主,女性舞者以紅色調為主。舞蹈者使用扁擔道具則以純黃色調為主,木槽和板凳的顏色以深板栗色作為底面,上面繪有原始狩獵巫術祭祀的動物圖案。在表演過程中,扁擔舞出場用鼓、鑼、镲、竹筒等打擊樂作為伴奏,節奏明快、氣氛熱烈。如舞蹈者一出場‖: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這種鏗鏘的打擊樂,無論是扁擔舞的單打節奏,還是男女雙打節奏,其舞蹈運動節奏感明顯,并配以紅黃兩色服裝相對應,說明顏色是運動的,它能把觀眾帶到不同時空場域。因此,色彩視覺效應成為自由視覺空間運動的流變形式。在舞蹈視覺色彩圖像中,是以“追求色彩振動”為視覺空間主題的,包含了不受特定視點約束的流變空間造型。但西方學者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并沒有把三原色視覺理論解釋清楚。“神經生理家和心理學家尤恩•海瑞從純色彩學理論方面進行考祭,并把三原色視覺效應理論作為色彩理論的基礎”。[1]觀眾在觀照舞蹈者服飾和道具三原色過程中,尤其是在自然光線下能產生不同舞蹈視覺效應。嚴格地說,它是處在舞蹈視覺色彩效應不斷變化的時空流變狀態之中,而不是一種恒常的舞蹈視覺現象。三原色“這種色彩的動感并不像康德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個人感覺,它們和現實之中顯示出色彩物體形態表情相吻合,并且各自都具有一種能被普遍理解的性質和一種普遍的適應性”。[3]210
“扁擔舞”的板凳和木槽極類似于后現代繪畫藝術,以紅、黃、藍三原色作色彩基調,結合繪畫平面藝術手法來表現舞蹈立體流變于運動空間所構成一種粗獷雄渾的舞姿,展示出一種繪畫色彩與舞蹈動作相結合的后現代審美藝術的心靈觀照。“關于色彩藝術,早在文藝復興時期歌德的色彩研究就已經超出了他的同時代學者。在色彩感受過程中,色彩對事物的美感能產生審美藝術判斷和審美價值取向”。[3]210盡管這種判斷是一種趣味性的,抑或是一種藝術性的,但是這種趣味性或藝術性是可傳遞的,并非是自我封閉的。我們強調趣味性或藝術性審美判斷與藝術審美價值取向表明了藝術主體性和創造性。如果色彩圖像不能在觀眾的主觀條件下設定視覺圖像的“同構性”,也就不能說明視覺圖像傳達可作為一種科學的理論依據。
(二)壯族扁擔舞的視覺時空藝術效應
扁擔舞在表演過程中,根據壯族農業生產活動一般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耙田插秧、戽水耘田、收割打場、舂米嘗新。就如農民“犁地打牛”節奏一樣,生動地表現了壯族勞動人民耙田農耕動作。“從美國學者格爾茲解釋人類學角度來理解舞蹈視覺空間構成的視覺藝術圖像,它具有實證性和多樣性”。[4]
舞蹈者把“耙田插秧”、“戽水耘田”、“收割打場”和“舂米嘗新”等不同勞動的自然場景作為視覺三維空間藝術的認識,通過不同舞蹈視覺空間主體動作的延續性和色彩的流變性,構成一個三維空間主體行為藝術———如果我們把時間軸交織在其中的話,就會構成一個四維時空流變,這才是藝術行為空間更為真實的性質。所謂藝術的時間性,即指藝術表演的歷時性和時間的不可逆性和在同一時間內的不可復制性。“在藝術中是一個強化的過程,它是由個別向普遍、由主觀向客觀、由事物向自我本質的轉化,這一事實的發現使我們意識到這一點”。[3]
壯族扁擔舞高度集中地表達了壯族農民四季勞動生產過程,也表達出人們歡慶豐收的喜悅心情。打扁擔是以扁擔和長凳為主,參加活動者是以婦女為主,甚至全部是女的。打法輕巧,花樣也較多而舞姿輕盈美觀,使人觀之有五彩繽紛之感。扁擔舞的基本動作是舞伴互擊扁擔,舞者以扁擔敲擊板凳或舂槽。起舞時,舞者成雙,兩兩相對。有4人擊打節奏,亦有6人、8人,10人、20人不等的“翻天覆地”的節奏等。
從壯族扁擔舞的視覺空間結構分析來看,這里包含有兩個時空層次的內涵:一是指扁擔舞的舞蹈者時空藝術的審美價值取向;二是指舞臺為舞蹈者提供靜態時空藝術審美觀照。前者是指舞蹈者運動所構成的一種流變的時空藝術。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是研究者假想中的一種不同形態的時空藝術說明舞蹈藝術價值的存在;后者作為舞臺靜態時空藝術為舞蹈者提供一個客觀實在的固定表演的藝術空間,或者說是一種靜態時空,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審美藝術觀照。當然,把扁擔舞作為時空藝術,可見這個靜態藝術時空與時空藝術運動相疊合所產生的強烈的藝術沖擊效應。扁擔舞在各種打奏法交叉進行時,發出的“咚咚、嗒嗒”、“得得”、“棒棒”的和諧音響;舞者時而雙人對打,時而四人交叉對打,時而多人連打產生錯落有致、此起彼伏的動作,使整個舞蹈節奏明快、舞姿矯健、優美清新,富于濃郁的民族生活氣息。表演者在高潮動作時發出“嗨!嗨!嗨!”的呼喊聲,伴隨著打擊樂器的強烈聲響,形成獨特的節奏,激發人們熱烈的情緒,充分地表現出一個民族的藝術震撼力,同時也說明壯族人民勤勞勇敢、性情豪放,體現出壯族人民樂觀奮進的民族精神。
二、舞蹈視覺人類學的研究意義
在我們的大腦中形成的物像并不是一個平面的二維圖像,而是一個三維的立體空間圖像。它具有高度、寬度和深度。值得人們注意的是,通過舞蹈藝術的“移情”作用,使這些具有高度、寬度和深度的立體藝術形象產生某種位移,這樣便于我們從不同角度來研究壯族扁擔舞的藝術移情機制而產生一種強烈的審美感受。當這些圖像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玫瑰形象時,或者說是一朵紅色玫瑰形象時,它能使你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藝術移情作用,它使你無法用一種語言來描述它的香味和色彩以及這朵玫瑰身上鋒利的錐刺。雖然作為玫瑰形象本身并不是一個完全清晰的概念,但“玫瑰”作為現實事物是絕對具有顯著特色的。舞蹈民族志田野觀察本身就是一個視覺藝術過程,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田野“視覺文化”或“視覺藝術”過程。在這里我們避開“田野觀察”一詞,改用“視覺人類學”或“視覺民族志”一詞,這樣避免了民族志田野觀察中所謂的“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某種不平等的關系,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是來自歐洲殖民主義時期不平等的權力格局的重要表現。吉首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蔣浩副教授首先提出:“舞蹈視覺人類學”和“舞蹈視覺民族志”并非是原有西方的“視覺主義”至上的歷史產物。[5]
我們所揭示的舞蹈視覺文化,是將民族傳統舞蹈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視覺藝術進行田野深度觀察,或者說我們運用舞蹈視覺人類學對民族舞蹈進行深度描述或者作為一種深層內在結構來解釋。自然界中的色彩同樣是一種最具有美感的分形,赤、橙、黃、綠、青、藍、紫,就表現出一種色彩分形。如果說我們把不同大小空間嵌塞進不同的顏色,就會產生不同的色彩空間分形,同時也就構成了視覺色彩分形。色彩分形和圖像分形是產生視覺美感的主要物質基礎。舞蹈作為視覺藝術,除了身體動作的視覺動態外,服裝、道具、化妝等都豐富了舞蹈的視覺美感和文化內涵。
換一種方式來說,我們把“舞蹈視覺藝術”或“舞蹈視覺文化”作為獲得知識理念的正確途徑來加以解釋,并著重強調舞蹈視覺民族志模仿客觀對象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舞蹈視覺藝術”或“舞蹈視覺文化”與“藝術模仿”使兩者拉近了文化“主位”與文化“客位”之間的平等關系,同時也避免了人類學者想象中的“田野觀察”。舞蹈視覺藝術消除了人們對田野觀察與“監視”的歧義,結束了田野觀察者與被觀察對象之間的不平等的對話。雖然“觀察”同樣包含了“視覺文化”或“視覺藝術”的意思,[6]但是觀察有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之分,有“局內”和“局外”之分,有觀察對象和被觀察對象之分,人類學家往往容易忽略“文化持有者內部眼界”的深度觀察,[7]尤其是對舞蹈、音樂和美術之類的視覺文化和視覺藝術內部結構的分析,總是容易使觀察者對被觀察者帶有某種歧視或歧義的理解。這就要求舞蹈家和人類學家之間要縮短原來田野觀察與田野被觀察對象之間的不平等的距離,要求我們提出“舞蹈視覺人類學”方法或者說“舞蹈視覺民族志”的概念與方法,并對當代人類學參與式觀察進行必要的反思。一方面我們不應該放棄對“文化持有者內部眼界”的觀察,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參與式觀察在舞蹈人類學中的局限性和歧義性。所謂局限性是我們對“扁擔舞”的動作節奏理解很難達到“文化持有者”的深層結構,即從“文化主位”到“文化客位”、從“局內”到“局外”的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講,舞蹈視覺人類學參與式田野調查對扁擔舞的文化內涵的理解仍然是有限的。舞蹈視覺人類學者在進行參與式田野調查時,對“扁擔舞”會生某種歧義性。這種歧義性是參與者或局外人對“文化持有者”所產生的某種文化距離,或者說是文化偏見,從而導致對異質文化的歧義。因此,局限性和歧義性是局外人對文化持有者的一種理解屏障并由此產生某種認知障礙。這種理解屏障和認知障礙將會直接影響“主位文化”與“客位文化”的融合,也就涉及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問題。
結語
壯族扁擔舞不是一個偶然的文化現象,而是壯族歷史文化發展的產物。扁擔舞同其它舞蹈一樣有著自身的演變軌跡、表演系統及其發展規律。它是壯族人民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受到保護和尊重,并健康地順應其發展規律向前演進,使廣西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得到更好傳承和全面發展,以至繁榮昌盛。
- 上一篇:商業攝影與藝術的關系范文
- 下一篇:讓穆克雕塑的視覺藝術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