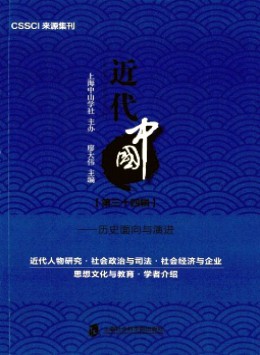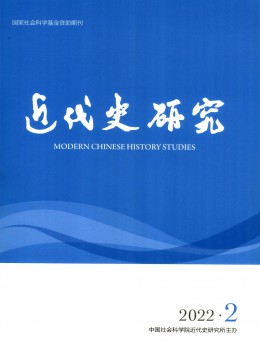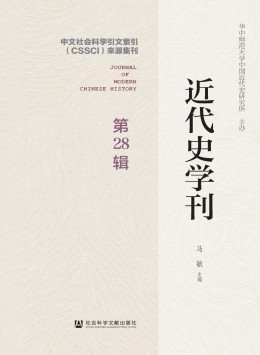近代漢譯法學書籍出版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近代漢譯法學書籍出版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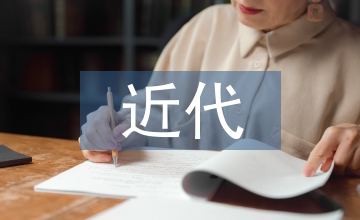
【摘要】晚清時期,來華傳教士等外國人和中國知識界人士,成為翻譯出版西方法學書籍的主要力量。這一時期,漢譯法學出版領域整體呈現書籍數量多且主題豐富、出版時間與地域分布不均衡、出版機構類型眾多、出版活動與時局走向緊密相連、出版質量參差不齊等特點;漢譯法學書籍大量出版,助推了近代中國出版業的發展。
晚清時期是近代西學東漸的早期階段,所翻譯出版的西學書籍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其中漢譯法學書籍格外引人注目。學界關于晚清漢譯法學書籍的研究成果,多以歷史學、法學和翻譯學等學科為側重點展開論述,鮮有從出版的角度進行探討。考察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概況和特點,客觀評析其歷史影響,有助于進一步深化近代中國出版史的研究。
一、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概況
鴉片戰爭前,從事翻譯出版西方法學書籍活動的多為個人,且缺乏系統性的譯介成果,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縱觀整個晚清時期,翻譯出版西方法學書籍的主體逐漸由來華傳教士等外國人變為中國知識分子。1862年,清政府設立同文館,揭開了官方吸納在華外國人翻譯出版西方法律和法學書籍的序幕[1]。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Fryer)和法國人畢利干(A.A.Billequin)等。1864年,在丁韙良的主持下,同文館翻譯出版了《萬國公法》,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本系統介紹國際法的中文譯著,“于泰西各約俱備志之”[2]。丁韙良于1869年擔任同文館總教習后,又先后翻譯出版了《星軺指掌》《公法會通》等西方法學書籍。傅蘭雅自1868年起被聘為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員,在近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主持翻譯并出版了多種法學書籍,主要有《法律醫學》《各國交涉公法》《公法總論》《邦交公法新論》等,其中包括我國第一本專門論述國際私法的譯著——《各國交涉便法論》。畢利干于1866年來華,在同文館任教期間,翻譯出版了《法國律例》,這是《拿破侖法典》的第一部中譯本。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翻譯出版西方法律和法學書籍的任務,基本上都由來華傳教士等外國人負責,中國人僅作為助手,一般采取“西人與華士同譯”的辦法,先是西人“逐句讀成華語”,“華士筆述之”并將初稿加以改正潤色,最后由西人核對后出版[3]。如在翻譯出版《星軺指掌》的過程中,由聯芳、慶常完成初稿,復經丁韙良審核。隨著各類新式學堂的增多,以及清政府陸續選派人員出國考察、游歷和留學,當時的中國積累了一批熟習西學的人才。19世紀90年代末以后,包括國內新式文人、留學生和上層統治精英在內的中國知識界,成為翻譯出版西方法學書籍的主力軍。1900年后,清政府實行“新政”,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翻譯出版西方法學書籍的熱情。除了官方機構——修訂法律館,留日學生團體、國內民間出版機構等是晚清最后十年間從事翻譯出版西方法學書籍的主要力量。1904—1909年,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修訂法律館翻譯出版了幾十部外國法律。商務印書館是晚清民間商業出版機構的代表,1907年編譯的《新譯日本法規大全》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幾乎國內每處官署都訂購一部,“銷數之多,僅亞于教科書”[4]。1900年,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了“譯書匯編社”,翻譯出版了大量近代西方和日本法律文本和法學書籍。1905—1906年,“湖北法政編輯社”翻譯出版了《法政叢編》,共24冊,其中涉及法學的書籍有18冊,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套大型法政叢書。
二、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特點
1.出版數量和主題豐富從具體的學科分類看,法學和政治學有一定的區別。田濤、李祝環在《清末翻譯外國法學書籍評述》一文中列舉了晚清引進的外國法學書目,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很多屬于政治學書籍,所以該目錄值得商榷。經筆者統計,晚清時期共出版漢譯法學書籍342種,這一數字遠高于同時期出版的其他社會科學類譯著;所涉及的類別十分豐富,既有法律文獻匯編和專業的法學著作,也有法學教科書、工具書等基礎類書籍;專業覆蓋面較廣,包括法學理論、法學史、憲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多個主題。其中關于國際法(包括國際法理論、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的譯著最多,達65種;關于國家法、憲法的譯著次之,有47種之多(見表1)。
2.時間與地域分布不均衡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在時間和地域上呈現一種集聚性特征,分布極其不均衡。首先,從時間分布上看,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數量雖不斷增加,但主要集中在1900—1912年,多達323種,占總量的94.4%。以甲午戰爭為界,中國譯介出版外國法學書籍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初興時期,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在各地設立了一批新式學堂和譯書機構,并延聘外國人為譯員,翻譯出版歐美國家的法學書籍;第二個階段是19世紀90年代末至1912年清朝覆亡的繁榮時期,得益于官方、民間各類出版機構的支持,中國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法學書籍的譯介出版事業迎來了繁榮發展,其中日本法學書籍所占比重最高。其次,從地域分布上看,國內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中東部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上海、北京和東京出版的書籍數量位居前三位,分別有123種、101種和67種。上海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批通商口岸,較早地受到西方的影響,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較其他城市而言較為開放、進步,吸引了大量知識分子,涌現出許多知名的翻譯出版機構,因而成為近代西方法學知識傳播的前沿地帶,所出版的漢譯法學書籍也最多。在北京出版的百余種法學譯著,主要依賴洋務運動期間同文館等新式機構及“新政”期間修訂法律館所進行的譯書工作。此外,甲午戰后國人留學日本成為熱潮,在東京的留日學生懷揣著“救亡求強”的愛國熱情,積極向國內譯介日文法學書籍,使得東京成為海外中國人出版法學譯著最多的城市。
3.出版機構類型眾多晚清時期開展翻譯外國法學書籍業務的出版機構有多種類型,其中以官方機構和民間機構為主,教會機構和國外(以日本為主)機構作為有效補充。官方機構主要包括兩類:一是中央政府部門,如修訂法律館、農工商部印刷所等;二是政府設立的譯書機構,如同文館、保定官書局等。出版數量最多者為修訂法律館,達69種(見表2)。民間機構則主要包括三類:一是新式知識分子設立的譯書社、學社(會),如譯書匯編社、丙午社等;二是國內的民營商業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等;三是國內的私人書坊,如浙江桐鄉汪氏求是齋等。此外,國內一些新式學堂也參與了譯書活動,主要為了滿足自身對于法學教科書的需求,如江西公立法政學堂于1911年出版了由曾有瀾、潘學海翻譯的《日本帝國憲法論》。
4.出版活動與時局走向緊密相連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活動,與清政府內外政策及政治局勢的走向密切相連。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面對外敵入侵,亟須了解國際的交往慣例。因此,在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開始后,翻譯出版的西方法學書籍大多涉及國際公法領域。1900年之后,清政府實行“新政”,進行官制改革,新設了民政部、商部、法部等中央政府機構,并由修訂法律館有計劃地譯介歐美、日本等國的法律文本和法學書籍,尤以民法、商法、刑法、憲法、國際私法類居多。1900—1912年是晚清出版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政治環境較為寬松,國內民間出版機構和留學生團體抓緊時機,與官方機構相呼應,翻譯出版了大量法學書籍。晚清時期外國法學書籍的翻譯出版,一直得到清政府的允許和支持,在官方和民間力量的雙重推動下,這一出版活動日益興盛。
5.出版質量參差不齊鴉片戰爭后,國內開始引進新式機器鉛印和石印技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手工雕刻和木活字印刷術,裝訂方式也由線裝轉變為平裝、精裝為主的近代圖書形制。然而,晚清漢譯法學書籍的質量仍參差不齊,主要體現在編輯過程和翻譯內容上。早期翻譯出版法學書籍的任務主要由外國人承擔,諸如丁韙良、傅蘭雅等深諳中國文化的傳教士在翻譯出版西方法學書籍時十分謹慎,采取以“意譯”為主的翻譯方式,力圖將西方法學術語與漢語詞匯相對應,對后者或進行引申闡述,或賦予新的含義;在編輯出版過程中與中國助手詳加校對,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譯著的質量。然而仍有很多外國人對中國文化和漢語詞匯并不十分了解,如中文水平不高的畢利干,所翻譯的《法國律例》內容極為難懂,該書雖由官方出版,但流傳范圍和影響力很小。直至19世90年代末隨著國內民間出版機構的興起,中國知識界尤其是留學生廣泛參與,充分理解這一跨文化交流中的“語言性語境和非語言性語境”[5],外國法學書籍的翻譯出版質量才得到了快速提升。此外,晚清時期翻譯出版的法學書籍在裝幀設計上比較單一,如在封面上只是用大號黑色字體突出書名、出版者和時間,未綜合運用“文字、圖形、顏色和材質四類視覺元素”[6]。
三、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出版的歷史影響
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的大量出版,不僅促進了中國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轉型和法學知識的普及,而且對近代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于這點,學界已有詳細探討。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時期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有力地助推了近代中國出版業的發展。第一,產生了一個持續升溫的圖書出版熱點。西方法律和法學著作對當時的國人而言是一個新鮮事物,是傳播法學知識和法律觀念的載體。晚清時期,一種外國法學書籍常有多種譯本,由國內多家出版機構競相刊印。如丁韙良翻譯的《公法會通》,有同文館本、益智書會本、北洋書局本、制造局本、美華書館本等多個版本;日本學者筧克彥所著的《國法學》有陳時夏譯本、熊范輿譯本,1907年分別由商務印書館和丙午社出版。晚清時期外國法學書籍一書多譯、一書多版的現象,使國內形成了新的出版熱點,繁榮了圖書出版市場。第二,加深了報社與圖書出版機構之間的共融共生。晚清時期報社與圖書出版機構之間存在合作關系,報社刊布廣告代售圖書,或兼辦譯介法學書籍的業務,而圖書出版機構在譯書的同時也發行一些報刊。如金粟齋出版的所有法學譯著,都在《中外日報》上刊載了廣告;南洋官報局除了主辦《南洋官報》,還翻譯出版了《國際中立法提綱》;譯書匯編社不僅翻譯出版日本法學書籍,而且經營發行《政法學報》。晚清時期報社與圖書出版機構之間共融共生,業務相互交叉,使得報刊出版市場和圖書出版市場呈現一種良好的互動關系。晚清時期,官方機構和民間機構共同參與翻譯出版外國法學書籍的活動。對于清政府而言,譯書只是為了發揮其“工具性”作用,為外交和內政提供參考;而中國知識界將翻譯出版西學書籍作為融入世界大潮、實現國家富強的一種途徑,契合了“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因而相較于官方,民間的出版活動更為活躍,產生的社會效用更大。許多知識分子在西學書籍的啟蒙下,或積極倡議變法,或走向革命,催化了晚清社會的激烈變革。考察晚清漢譯法學書籍的出版情形,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近代中國的出版活動及社會變動的深層次內涵。
|參考文獻|
[1]田濤,李祝環.清末翻譯外國法學書籍評述[J].中外法學,2000(3):355-371.
[2]張德彝.航海述奇[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7.
[4]吳永貴.民國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5]姜海英.跨文化傳播視域下中文圖書外譯芻議[J].出版廣角,2020(5):89-91.
[6]杜妍.書籍封面設計中視覺元素的運用與思考[J].出版廣角,2020(17):83-85.
作者:崔嘉欣 宋永林 單位:河北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