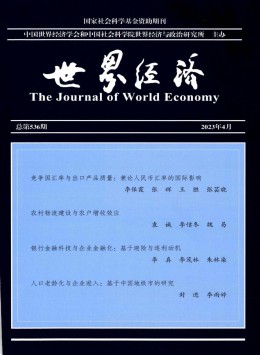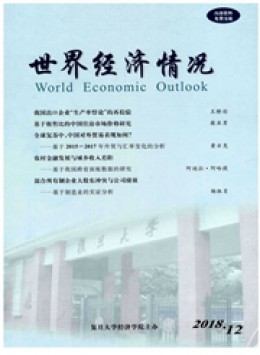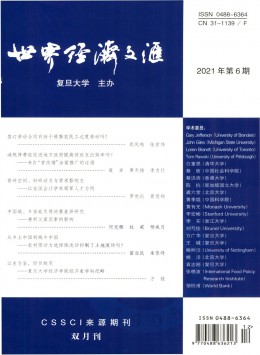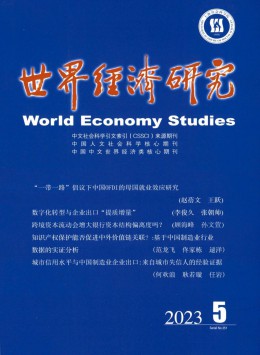世界經濟雙重經濟學分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世界經濟雙重經濟學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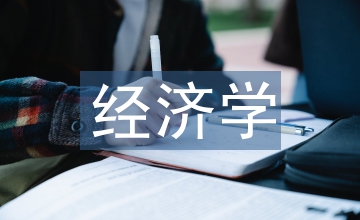
曼德爾指出:“《資本論》第一卷最初出版時,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在西歐少數國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歐大部分地區在內的整個世界上,它還是獨立農民和手工業者大海所包圍的孤島。”④因此不難理解,馬克思為什么選擇英國作為典型進行剖析。《資本論》所闡述的,主要是為了追求私人利潤并把這種利潤用于資本積累的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無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長趨勢。《資本論》問世以來,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工業已傳播到全世界,不僅物質財富以及把人類從無意義的機械重復勞動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會的兩極分化也擴大了,資本的所有者越來越少,被迫向他們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越來越多。財富和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工業巨頭和金融企業手中,這使得資本和勞動之間展開了越來越廣泛的斗爭。曼德爾指出,資產階級為挽救資本主義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盡管采取了凱恩斯的辦法,盡管實行了各種各樣企圖使工人階級與晚期資本主義一體化的措施,最近十幾年來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說發生了什么變化的話,那就是變得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更加危機四伏了”⑤。從越南戰爭到世界貨幣制度的混亂,從西歐1968年以來激進工人斗爭的高漲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對資產階級的價值和文化的拒絕,從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到周期性的經濟衰退,隨處都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曼德爾總結道,“《資本論》說明了為什么這個制度的日益尖銳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發展一樣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資本的內在否定性———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
曼德爾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由于像19世紀的英國那樣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越來越多,今天的世界遠比寫作《資本論》時的世界更接近《資本論》中的“純粹”模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一般公認的信念相反,馬克思與其說是19世紀的經濟學家,還不如說是20世紀的經濟學家。眾所周知,《資本論》研究的是生產關系,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⑦《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全部三卷所講的“資本”都是一個生產關系概念,而不是生產力概念。這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資本”,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所理解的“資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經濟學大多把資本當成了生產力概念,它講究的是投入、產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價值”和“剩余使用價值”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這里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都是通過交換實現的抽象勞動,因而表現的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它只適用于私人勞動與其他私人勞動在相互對立、相互統一中構成整體社會勞動的市場經濟。從生產力的角度看,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勞動,只涉及具體勞動。
具體勞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體勞動進行比較,不涉及與其他人的關系。在生產力經濟學中,資本創造的不是剩余價值,而是剩余使用價值。按照這種眼光,資本在一切時代都存在———只要使用價值通過一個生產循環,能夠生產出更多的使用價值,它就是資本。在馬克思看來,正是這種理解,把資本這種特定時代的生產關系當成了永恒的自然關系。馬克思真正主張的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中考察生產力的發展。盡管馬克思強調,資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價值即勞動產品,而是剩余價值即多余的貨幣;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價值的轉化形式。但是,在《資本論》第二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潤、利潤率的時候,馬克思恰恰是從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兩個方面來考察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的。實物補償實際上就是使用價值的補償。馬克思指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態的制約”⑧。因而,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方面來考察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題中之意。今天,我們無論是研究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現,還是研究當今的世界經濟,都應當著眼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種經濟學視角。
二、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現
羅莎•盧森堡在研究資本積累時發現一個問題,作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資本論》沒有顧及資本主義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環境:“我們在《資本論》全部三卷中看出,馬克思的分析的理論前提,是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著普遍而唯一的統治地位。”在她看來,“這個前提,乃是理論上的權宜之計。現實上,從來沒有過那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前提,如果只是作為論證純粹形態的問題之助,而不變更問題的條件,那么,它是一個完全可以允許的理論上的權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現實的世界經濟,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實際上,到羅莎•盧森堡的時代為止,資本主義經濟總是在一個非資本主義環境中,即在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聯系中得到發展的。盧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資本主義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前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價值循環和使用價值循環的情況下,資本積累的實現條件問題。盧森堡的研究可以視為對《資本論》的發展。它把《資本論》關于資本內在否定性的論述和《共產黨宣言》關于經濟全球化的論述溝通起來了。人們公認,《共產黨宣言》最早描繪了經濟全球化的圖景:“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變成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
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盧森堡所關注的正是《資本論》中資本的內在否定邏輯在世界市場中的現實表現。在《資本論》的最初計劃中,馬克思是把世界貿易、把生產和消費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賴排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也就是現行的《資本論》第三卷之后來考察的。如果這一計劃得以實現,我們就能夠看到,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是如何從抽象過渡到具體,表現在世界經濟的全景中的。遺憾的是,這個宏偉的計劃未能完成。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從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據馬克思遺稿編成的《剩余價值理論》可以視為《資本論》的第四卷,但從內容上看,盧森堡和列寧的世界體系論才是名副其實的《資本論》續篇。在馬克思看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并不是一種外部否定,而是資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產力的發展,都必須采取一定的生產關系形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所以能夠戰勝其他生產關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帶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而不是生產使用價值,但對利潤的追求迫使資產階級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旦這種發展不再能帶來利潤,資本就不再是資本,而還原為貨幣,資本的生產就還原為使用價值的生產。這也就超出了資本的限度。于是,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就轉化為它的外在否定性。馬克思對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種邏輯限度的分析。如果把盧森堡的研究和列寧的研究加進去,我們可以發現,資本內在否定性所表達的邏輯限度,實際上是在現實的時間限度和空間限度里表現出來的,即在資本積累的世界歷史中,資本的內在否定性必然會外化為具體的時空限度。盧森堡指出,“資本主義是第一個具有傳播力的經濟形態……但是,同時它也是第一個自己不能單獨存在的經濟形態,它需要其他經濟形態作為傳導體和滋生的場所。雖然它力求變為世界普遍的形態……然而它必然要崩潰,因為它由于內在原因不可能成為世界普遍的生產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資本主義本身是一個矛盾,它的積累運動帶來了沖突的解決,但同時,也加重了沖突。”⑩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擴張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贏得了世界市場,大大拓展了工業資本的發展空間,緩解了資本主義宗主國國內的經濟危機。
但是,這種空間的拓展相對于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而言是遠遠不夠的,遲早還是會出現宗主國國內的那種生產力與購買力之間的矛盾,只不過原先一國范圍內的矛盾升級到世界范圍內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場上,除了原有的勞資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不同宗主國之間的矛盾。而作為資本擴張的無限性與擴張空間的有限性之間矛盾的極端表現,就是世界范圍的革命的爆發。因而,以盧森堡和列寧為代表的國際共產主義認為,在資本積累的世界歷史中,“國內外資本積累的條件將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那就是它們變為資本沒落的條件”瑏瑡,到了那個時候,除了實現社會主義外,沒有其他的出路。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限度和空間限度。到《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主要是英國,因此,馬克思“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瑏瑢。但19世紀的英國同其殖民地特別是同印度的關系,無非是20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與前資本主義世界關系的縮影,或者說,前者向后者展示的,無非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然而,20世紀還是有兩大現象超出了《資本論》的范圍:一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和瓦解,二是虛擬經濟的出現和繁榮。這兩大現象同樣必須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視角加以理解。
三、雙重經濟學視角下的國際分工與中國發展道路
《資本論》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主要是生產關系的危機。但是,20世紀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遭遇的困難,特別是蘇東劇變,卻屬于另一種危機:生產力發展的危機。中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并且不斷發展,與堅定不移地奉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紀,資本主義沒有滅亡,原因在于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在美國,這是通過羅斯福“新政”、創立“宏觀經濟”實現的;在歐洲,則是通過社會黨創辦“福利國家”、建立“消費社會”實現的。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陣營的崛起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折,則與盧森堡分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聯系在一起。俄國十月革命,與其說是馬克思《資本論》的革命,不如說是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和列寧《帝國主義論》的革命。現在回過頭來看關于“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爭論,我們可以發現:這場爭論之所以沒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視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不僅應當在生產關系的層面上進行,還應當在生產力的層面上進行。斯大林混淆蘇聯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區別,誤把比資本主義還低的生產力水平上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混同于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這確實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二戰以后,斯大林甚至試圖建立平行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社會主義市場。實際上,蘇東劇變并沒有證明社會主義的失敗,它只是證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失敗。這種失敗的理論原因在于只是從生產關系經濟學的角度看待世界經濟,沒有從生產力經濟學的角度,特別是沒有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經濟。相反,中國采取改革開放政策,緊緊依靠世界市場,僅用了30多年時間,經濟總量就躍居世界第二,這一事實表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對于自身的經濟發展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經濟,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所導致的種種問題就不再僅僅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它也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尤其是面臨虛擬經濟的挑戰,中國必須拿出自己的對策。這同樣要從生產力經濟學和生產關系經濟學兩個角度著眼。在盧森堡看來,按照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關系,非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經濟國家,一類是商品經濟國家。對后者,資本主義需要購買其原料和向其傾銷產品,因此是一種“正常”的貿易關系;對前者,首先必須瓦解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體系,然后才能用市場交換的辦法進行剝削。因此,對自然經濟國家的經濟,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積累時期的暴力掠奪手段。但是,如果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強有力的民族國家政權,利用后發優勢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那么這種發展順序就可以被打破,這些國家就可以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爭取到相對有利的位置。至于這些民族國家政權采取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并不影響它們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中,德國和日本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則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些國家的成功,都與自覺進入世界歷史進程有關。意大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阿銳基(又譯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中追述了從文藝復興到當代的資本主義擴張和霸權大國的逐次循環。在他的論述中,資本的物質擴張階段最終在過度競爭壓力下逐漸消失,讓位于金融擴張階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國家間混亂的年代的出現。在新的社會集團的支持下,一個能夠恢復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啟物質擴張循環的新興霸權大國的出現,將消除國家間的混亂狀態。
熱那亞、荷蘭、英國和美國依次被稱為這種霸權國家。在《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中,阿銳基斷言,世界霸權從美國轉到中國的時代來臨了。由于中國是一個非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這一次權力轉移將給人類帶來曙光。從資本內在否定性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現來看,我們不得不說,阿銳基過于樂觀了。他忽略了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廉•I.羅賓遜在《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中所關注的全球資產階級的大聯合。這是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勢力。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不過是這種勢力擴張自身的理論反映而已。這種聯合不僅改變了《資本論》的語境,而且改變了《資本積累論》和《帝國主義論》的語境。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期待的是《共產黨宣言》中號召過的那種“全世界無產者”的國際聯合。這種聯合被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破壞掉了。在《資本積累論》和《帝國主義論》中,盧森堡和列寧期待的是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的聯合,這種聯合被第三國際的大國沙文主義者破壞掉了。在整個20世紀,對資本主義構成制約的,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外部壓力,二是受到社會黨影響的民族國家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治理的內部壓力。遺憾的是,蘇東社會主義的解體,使資本主義失去了外部壓力;經濟效率的降低迫使社會黨放松管制,使資本主義失去了內部壓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大量引進外資,客觀上使得發達國家降低稅收,以便把資本留在國內,從而使全球資本獲得了空前的主動權。在這種背景下,已經進入小康社會的中國顯然不能延續舊的發展思路。
從熱那亞到荷蘭,再到英國和美國,經濟霸權的轉移都與全球資源和生態的容納能力密切相關。中國既沒有盧森堡所說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水平國家作為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的目的地,也沒有發達的、足以吸納全球過剩資本的金融市場。唯一的出路是從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兩種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實體經濟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虛擬經濟的力量對比,力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全面超越傳統發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分工中占據主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經研究過虛擬資本。從生產關系經濟學角度看,虛擬資本僅僅是資本的虛擬化。由于整個國際貨幣體系仍然建立在金屬貨幣即抽象勞動的物化形態上,虛擬資本并未從根本上影響到資本主義的金融市場,反而對通常的所謂“物質資本”即從生產力經濟學角度看的資本的發展有一種促進作用。但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各國貨幣與美元脫鉤,貨幣也被虛擬化了。這就為虛擬資本成長為虛擬經濟,從而使金融市場空心化準備了前提條件。因此,中國目前面對的,一方面是國內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所積累的使用價值的堆積,另一方面是在國際金融戰爭中所處的劣勢地位。中國必須既通過經濟結構轉型、技術創新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又通過金融創新推進虛擬經濟的發展。只有在兩條戰線上都取得勝利,阿銳基所期待的人類曙光才會顯現。這就需要我們同時既在生產關系經濟學、又在生產力經濟學上實現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