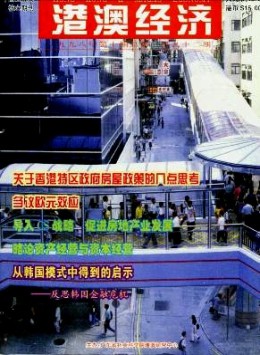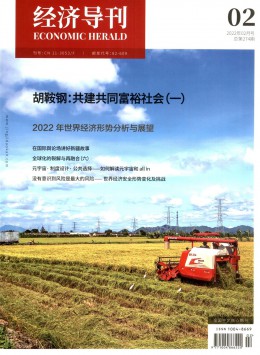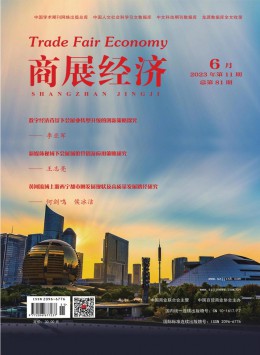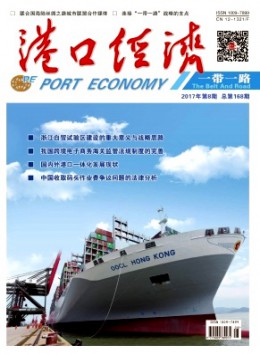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動力機制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動力機制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文章認為分工水平的提升是浙江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動力,轉型的關鍵在于利用分工促進機制。而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與信息化的推進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市場范圍、提高社會知識水平與降低協調成本,從而提高分工水平,使得浙江經濟從之前以部門分工為主的縣域經濟向以產業鏈分工為主的城市經濟過渡。最后,文章得出“縣域經濟轉型依靠內在的產業轉型與外在的都市圈經濟輻射”的啟示。
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新世紀以后,浙江“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空間布局分散”(低、小、散)的縣域經濟正在經歷“成長的煩惱”,面臨轉型升級路徑鎖定的困境,給浙江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滯緩、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務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縣域經濟亟須轉型升級。2014年,浙江人均GDP為72967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這一發展階段對浙江經濟形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經濟以集約集群集聚與高端高質高效的優勢無疑成為理想的經濟形態。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研究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的動力機制。
二、浙江縣域經濟轉型升級新趨勢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市場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推進,浙江縣域經濟轉型升級呈現新趨勢。主要體現在:一是城市經濟發展效率超越縣域經濟;二是縣域經濟融入都市區發展;三是發達縣(市)進入城市經濟快速發展期。這些表明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已成必然趨勢。
(一)城市經濟高效發展,成為驅動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主導性力量
隨著城市化重心從小城鎮向大中城市轉移,各類生產要素和產業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經濟快速、高效發展。2012年①,11個設區市GDP達16479.67億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僅占31.77%,而58個縣(市)②GDP達18038.49億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卻占了68.23%。11個設區市的經濟發展效率遠遠高于58個縣(市)。而且11個設區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財政總收入分別占全省的52.74%、56.34%,占據了半壁江山。隨著新型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以城市群和都市區為載體的城市經濟將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力量。2013年杭甬溫三大中心城市市區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卻創造了33.35%的地區生產總值。
(二)都市區和城市群逐漸形成,縣域經濟融入都市區發展成為新趨勢
都市區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強了縣(市)與中心城市的經濟聯系,促使縣域經濟從支撐城市經濟發展為主向接受城市經濟輻射為主轉變,促使區域空間結構網絡化發展。目前,環杭州灣、溫臺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四大都市區逐漸成形,將近50%的縣(市)已被納入網絡化城市體系中。杭州都市區吸納了臨安、富陽、德清、桐鄉、海寧和紹興等6個縣(市);寧波都市區吸納了余姚、慈溪、奉化、寧海和象山等5個縣(市);溫州都市區吸納了瑞安、永嘉、樂清、洞頭、文成、平陽和蒼南7等個縣(市);金華-義烏都市區吸納了東陽、浦江、蘭溪、武義和永康等5個縣(市)。這意味著這些縣(市)必將受到城市經濟的輻射,外圍縣(市)與中心城市融合發展將成為趨勢。城市經濟正在一步步“吞噬”縣域經濟。
(三)發達縣(市)進入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
“四換三名”①、“退二進三”等一系列產業轉型升級措施促使各種城市經濟業態不斷涌現,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或生產性服務業轉型,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縣(市)服務功能不斷提升。2013年,紹興縣、義烏市、慈溪市、嘉善縣等22個縣(市)人均生產總值跨越10000美元(見表1),迎來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商貿服務業、金融業、物流業、信息產業等產業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人數比重持續上升。以義烏市為例,從2000—2013年,義烏市第三產業占生產總值比重從43.5%持續增長至57.05%。發達的商貿服務業提高了義烏市服務其他縣(市)的能力。此外,部分縣(市)以“智慧城市”為抓手促進“生產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帶動了信息產業等相關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提高了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
三、分工視角下的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動力機制
浙江縣域經濟呈現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并非偶然。因此,我們很有必要研究其轉型的動力機制。如此,一來可以更好地推動浙江縣域經濟轉型;二來可以為全國其他縣域經濟提供發展的參考。
(一)概念界定
縣域經濟是農村市場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質上是農村工業化與以小城鎮(建制鎮)為重心的城鎮化在縣域空間上融合互動促使縣域產業分工所產生的特征鮮明的經濟形態。特征主要體現在:一是以傳統產業為主導產業,縣域功能以生產為主;二是縣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間集聚度低,產業布局分散,城鄉二元結構明顯;三是縣級行政區劃為經濟發展的空間依托,縣城與中心鎮往往是縣域經濟增長極;四是區域分工水平比較低,以部門間分工或區域產品分工為主,缺少產業鏈層面分工。城市經濟伴隨城市化進程而發展,本質上是集聚經濟,是分工與集聚在地理空間上互動所產生的具有較強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經濟形態。呈現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本推動力,農業現代化是重要的支撐力;二是在集聚與分工的互動中,生產性服務業從第三產業中脫穎而出成為主導產業,城市以服務功能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農人口為主,城市化水平比較高,中心城市集聚、輻射能力比較強;四是產業鏈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間分工明確、錯位發展,都市圈經濟是其演化發展的高級形態。由上可見,從分工角度來看,縣域經濟是一種以部門分工為主的經濟形態,而城市經濟是一種以產業鏈分工為主的經濟形態。因此,從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可以理解為分工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也就是說,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經濟形態的轉變,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經濟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而不是行政區劃的調整②,更不是縣域經濟的“消滅”。
(二)動力機制分工
從縣域與區域兩個層面作用于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縣域層面,分工深化提高個人或企業專業化水平,引起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推動人口集聚、產業集中,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促進服務業大發展,進而推動產業轉型,帶動縣域空間結構與功能的轉變。區域層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經濟能級提升,使得城際之間分工協作、經濟聯系密切,增強了縣域與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動,促進都市圈形成與發展,基于明確的城市等級體系與密切的城際經濟聯系,縣域經濟受城市經濟輻射而轉型。因此,轉型的關鍵是利用促進分工演進的機制。基于貝克爾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楊格(Young,1928)[2]與楊小凱(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場范圍、社會知識水平與協調成本的影響。因此,本文認為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與信息化是縣域經濟轉型的促進機制。市場化有助于明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消除市場壁壘,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建立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擴大資源配置范圍,促進區域分工。城鎮化推動人口、產業等資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間鄰近程度,加快知識、信息、技術等要素的傳播與分享,提高社會知識積累水平,降低生產活動的協調成本。工業化推動制造業發展,為服務業發展奠定物質基礎,為城市化提供基本動力。信息化釋放空間與時間對資源配置的約束,擴展了市場空間與容量。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與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縣域經濟呈現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
1.動力機制Ⅰ: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亞當?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觀點即“斯密定理”。阿林?楊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這一觀點,認為“分工一般的取決于分工本身”,即分工與市場規模之間是相互影響和決定的一種網絡關系。因此我們可以說:市場化深化縣域分工,推動分工網絡形成與擴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場化程度,擴大市場規模。市場化從廣度與深度兩個層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廣度層面,市場化促進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擴大了資源優化配置的空間范圍,直接推動市場規模擴大和區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層面,市場化明確政府與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消除市場準入限制、行業壟斷等各種市場壁壘,改善了經濟活動所需環境。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市場化深化的過程,是一個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網絡擴展互促互進的必然結果。20世紀80年代,浙江率先實施農村工業化,開始市場化取向改革。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市場化進程,推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農村工業化與市場化的互動開啟了縣域經濟支撐城市經濟發展之路。隨著市場化的推進,浙江經濟呈現出兩個發展特征。一是各類商品和要素市場規模迅速擴大,相應的商品與要素市場逐步建立,區域市場體系逐漸形成,區域貿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現為各類專業市場的快速崛起、擴張與國內外貿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引導下,縣域根據自身資源稟賦條件,依托區域市場體系,融入區域產業分工,建立自身的產業體系,這不僅推動了浙江區域產業結構的形成,也固化了區域產業分工體系。進入新世紀,信息化以其強大的滲透力、影響力融入經濟活動的每個環節,提升提速市場化進程。各類專業市場在信息化的作用下,無論是規模還是功能都得到極大地提升,分工網絡進一步擴展,縣域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目前,隨著義烏小商品城、余姚中國塑料城等專業市場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商貿服務業、信息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等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
2.動力機制Ⅱ:人口集聚、產業集中與縣域空間集聚度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縣域層面分工,推動產業轉型,進而帶動縣域空間結構與功能的轉變。錢學鋒、梁琦(2007)[4]認為分工與集聚之間的內在聯系乃是通過報酬遞增作為媒介而實現的。也就是企業為獲得遞增的報酬必然會集聚。貝克爾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勞動分工、協調成本和知識》一文中指出分工不僅受市場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協調分工的成本以及社會知識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協調成本或者協調成本相對較低而市場又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分工才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人口與產業的集聚或者說城市化的推進加速知識積累,縮短空間距離,方便經濟主體之間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產活動的協調成本。綜上所述,人口集聚、產業集中即縣域空間集聚度提高的過程就是縣域層面分工深化的過程,就是縣域產業轉型的過程。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以建制鎮為重心的城鎮化向以縣城與中心鎮為重心的城市化演進的過程,表現為人口、產業等資源從向建制鎮集聚到向縣城與中心鎮集聚。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物質基礎,推進城市化;城市化則為工業化提供空間依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中,人口、資金、技術、產業等各類經濟資源向縣(市)地理空間集聚,城鎮就業人數不斷增長,產業種類也不斷增加。縣域空間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樣化,引起中間產品需求擴張,進而深化了縣域層面分工,推動生產性服務業、消費性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使得縣域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不斷增強。20世紀80年代,浙江以小城鎮為重心的城市化與農村工業化的互動推進鄉鎮企業快速發展。鄉鎮企業與專業市場的融合互動導致產業集群發展,形成特色鮮明的“塊狀經濟”。在該城鎮化戰略的指引下,浙江經濟出現“弱市強縣”與“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時機地提出以中小城市為重心的城市化戰略。中心城市開始快速發展,城市經濟崛起。縣域經濟進入自身產業結構調整期,開始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但對城市經濟的支撐作用并沒有減弱。2006年開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縣域經濟與城市經濟的互動得到加強,使得縣域經濟受城市經濟輻射效應越來越強。
3.動力機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都市圈具備以下幾個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強、輻射能力強的中心城市為核心;二是具有發達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礎設施,周邊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交通通達性高、信息交流通暢;三是圈內城市之間產業分工明確、職能互補;四是圈內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與勞務自由貿易,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強。可見,都市圈的形成與發展是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與信息化在區域空間互動發展的結果。這是因為:市場化消除市場壁壘,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勞務自由貿易,是都市圈形成與發展的前提與保障;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高級要素與高端產業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強中心城市的集聚與輻射能力;信息化統籌提升工業化、市場化與城市化,促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縮短城市之間空間距離,擴大了市場規模,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而且加速了知識積累,進一步深化分工,最終推動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熟都市圈由強大的中心城市、緊密的城際聯系與清晰的城市等級體系的構成。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在空間上的融合互動,促使環杭州灣、溫臺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與杭州、寧波、溫州和金華-義烏都市區形成。隨著“七線兩樞紐”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進,城市化的集群化、網絡化發展趨勢日漸明顯。“十二五”時期,浙江四大都市區、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積極推動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級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之間的產業梯度,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縣(市)則主動承接中心城市產業轉移,因地制宜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現代物流、商務、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積極發展旅游、商貿等生活性、消費性服務業;中心城市與外圍縣(市)之間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礎設施為依托實現鏈接。這些規劃都將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的融合互動,最終實現中心城市拉動縣域經濟轉型。
四、啟示
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與市場化的影響下,區域分工水平不斷提高,縣(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經濟聯系不斷加強,一體化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未來,浙江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應堅持“強縣戰略”與“都市圈戰略”雙輪驅動轉型。在“強縣戰略”指導下,深化縣域內部分工,加快推動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轉型,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以產業轉換推動縣域經濟轉型;在“都市圈戰略”指導下,深化區域層面分工,城市化重心從中小城鎮向大城市傾向,促進高級要素、高端產業等資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與輻射能力,將縣(市)納入都市區發展。深化縣域內部分工關鍵在于以城市化與信息化優化工業化,重點在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主動力在于縣(市)城市化的推動作用;政府作用則在于營造良好發展環境,針對性地實施“招商選資”,延長產業鏈。具體表現為:一是加快推進縣(市)城市化,提高縣域空間集聚度,合理發展服務業,重點發展現代物流業與信息產業等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二是以“智慧城市”、“數字城市”建設為著力點,努力提高企業、產業發展平臺與社會領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實現企業產品、研發、生產過程與管理、營銷等環節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經濟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區域甚至全球分工,圍繞主導產業承接中心城市或國際轉移產業,采取“補鏈式”招商引資,提高生產迂回度,提高中間產品生產量,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深化區域分工關鍵在于深化市場化改革,推進新型城市化與信息化融合互動,重點在于明確縣(市)區域地位,主動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領作用;政府作用則在于擴大區域合作范圍,加深區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區域壁壘,實現地方政府共贏。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完善縣域經濟發展的“硬環境”與“軟環境”,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二是創新區域經濟管理體制,構建區域協調機構,消除行政區劃與體制機制對都市圈發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進新型城市化,構建“分工明確,功能互補”的城市等級體系,同時要重點提高中心城市經濟能級,發揮中心城市帶動作用,以城市經濟反哺縣域經濟。
【參考文獻】
[3]楊小凱.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4]錢學鋒,梁琦.分工與集聚的理論淵源[J].江蘇社會科學,2007(2):70-76.
作者:劉亞卓 劉鎧鋒 單位: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地鐵運營管理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