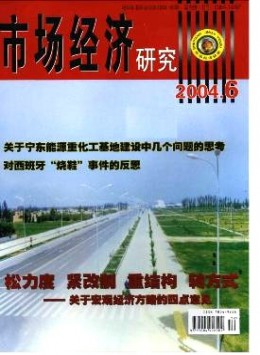市場經濟對鄉村典型的政治影響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市場經濟對鄉村典型的政治影響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鄉村典型作為政治櫥窗里的展品,為獲得推展鄉村典型政治的勢能,經常被以理想純化的宣傳推至很高的地位,以突出其政治追求的崇高性和超越性,卻難免經常出現人為拔高脫離實際的情況。而鄉村典型也善于迎合意識形態的需要,如南街村毫不諱言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宏圖大略,而華西村宣稱“看社會主義”則要到華西,這樣的說辭確有一定的經濟成績作支撐,但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條件下卻難掩其烏托邦色彩。鄉村典型作為市場主體要生存下去,當然得“做事時自有妙法”,高調的理想正可以被編織成遮掩實利追求的迷彩服,一方面自我圣化其社會主義政治倫理,一方面雇傭大量外村廉價勞動力,以純粹的市場邏輯悄悄置換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理想,風生水起地玩轉市場和意識形態。這當然也是因為在強調生產力發展的新時期,村莊如果沒有另辟蹊徑的經濟理性就不太可能創造出顯赫的經濟成績以晉升為鄉村典型,而缺乏光鮮經濟成績的鄉村典型也會失去立身之本,備受質疑。這就是為什么即使被認為超越一般鄉村社會的鄉村典型,也直言不諱對于利益的追求,如天津大邱莊原黨支部書記禹作敏上世紀80年代說出“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話,既含蓄又直白地道出了鄉村典型生存的潛規則和硬道理。所謂“向前看”就是要認真學習時政,熟知國家方針政策,把準政治脈動,走對政治路線,看似鄉村典型的政治追求,實是其對于中國經濟與政治關系的準確把握,是經濟理性的體現;而“向錢看”可看作對于經濟中心的粗陋解讀,是鄉村典型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理性的必然體現。在適者生存的市場法則下,市場理性必然主導鄉村典型的運行邏輯,只是過于直白的利益觀使得作為典型支點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崇高性蕩然無存。鄉村典型政治的理想僅是裝點鄉村典型的美麗花邊。因而,被寄予政治厚望的鄉村典型頗為吊詭,鄉村典型所實際展現出來的東西和人們意圖通過鄉村典型所表達出來的東西之間不可避免出現鴻溝。
市場經濟所培養的理性精神還會合乎邏輯地延伸到對于樹立鄉村典型工作方法的深刻反思。一直以來,由于鄉村典型政治能營造出一種浩大熱烈的浪漫主義的動員氛圍,被好大喜功者當作理想的工作方法。但鄉村典型政治對權力的依賴和對示范可能性的主觀認定,必然帶有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刻板的官僚主義的特征,形式重于內容,很難有實質性作用。而市場邏輯的優勢就是不拘一格的靈活性[3],會自動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摒棄任何形式主義,從而削弱對于鄉村典型政治的工作方法的理想化期待。在市場經濟下,鄉村典型不僅要看起來很美,而且不能造成東施效顰的惡果,否則,鄉村典型政治很難行得通,鄉村典型也免不了遭到最終被拋棄的命運。如小崗村經驗能幫助大多數農村解決溫飽而被普遍仿效,成為改革開放之初紅極一時的鄉村典型,卻也只是純粹的農業典型,因此大包干在大邱莊和華西村等具有工業基礎的明星村莊照樣行不通。這些村莊繼續原來的集體管理體制,以便把分散的稀缺資源集中起來辦企業,發展村莊經濟,為中國農村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這些村莊也成為更受推崇的典型,其發展經驗受到青睞并無不妥,只是在上世紀90年代被以“農業學大寨”的方式在中西部鄉村強制推行的時候,成功者鳳毛麟角,失敗者滿目瘡痍,不但沒給中西部鄉村帶來發展,留下的債務一度成為束縛這些地方發展的沉重包袱。所以,鄉村典型雖甚合某些人之理想,也能激起農民之向往,但在一個具有更多自主選擇權的時代,農民會以自己的經濟理性加以評判,如果鄉村典型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那么,鄉村典型政治只能徘徊在大多數村莊之外,不得其門而入。
市場經濟的法治導向對鄉村典型政治的人治導向的制約
理性經濟人對于利益的全力追求會打開“潘多拉魔盒”,放大人性中邪惡的一面,所謂“利之所存,行之所尚;利之所去,行之所息”。市場經濟是把雙刃劍,其健康運行不能以個人的好惡為標準,須以明確的規則約束人們的行動,保證競爭規則的公平性、嚴肅性和有效性,引導人們確立合理的行為預期,所以,市場經濟即規則經濟,它內在地要求規范有序。經濟活動作為人類一切其他活動的基礎,經濟規則具有統率作用,“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4]。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最成熟最權威的規則,不僅是經濟運行的依據,也是政治運行的依據。因此,法治是現代人類經濟、政治和其他一切活動的基礎。而鄉村典型政治可謂中國人治傳統的現代翻版,在市場經濟日益成熟的今天受到法治的制約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檢視當代中國鄉村典型政治的歷史,單以樹典型而言,就充滿了偶然性。樹典型雖是政治所需,卻沒有明確的規則可循,多取決于領導人的喜好,具有明顯的人治特征,成為運動式治理的手段。“改革開放第一村”小崗村的三十年典型史清楚地印證了這一點。小崗村在時期,實際上是缺少集體主義精神的落后典型,誰能想到它會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功臣,并成為三十年來最有影響的鄉村典型之一?小崗村人在按下血手印的時候可謂誠惶誠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人民日報》刊登“張浩來信”以及大包干在北京報“戶口”受挫時,都給安徽省委造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小崗村的大包干也被“冷處理”了,可干三到五年看看[5]。小崗村沒成為反面典型已屬幸運,豈敢妄想成為登堂入室的正面典型。鄧小平的一番話解了安徽省的圍[6],竟使得小崗村咸魚翻身,成為人們心向往之的典型。1998年和2008年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為了強調改革的意義和彰顯改革的成就,兩次造訪小崗村,也讓小崗村更加具有象征意義。實際上,小崗村不要說同沿海發達地區比較,即使和安徽省其他地方相比,本來自然條件較差的小崗村的先發優勢很快蕩然無存,除了一張“血手印”,鮮有引人矚目的創新成績稱得上典型的地位和榮耀,甚至一度成為“落后標本”,僅剩下憶苦思甜的功能,常令參觀者失望而歸。作為改革典型的小崗村歷史使命業已完成,“典型不再”亦是人之常情。可為了保住小崗村典型,只得以各種無償援助、凌空蹈虛的宣傳、政策優待(如很早免除農業稅和獲得各種援助)和四星級“政治”旅游景點來維護典型形象[7],就鄉村典型政治而言完全是邏輯悖論。由此可見,樹立和宣傳小崗村典型不是“制度”、“標準”等客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人”的主觀因素在起作用。小崗村是老典型了,在小崗村問題上須照顧一些老領導的感受,導致落后也能當典型的情況出現。在以規則統率一切的市場經濟時代,終究難以消除人們對其資格的拷問,因為人們對于典型還是有著類似于“標準”與“規則”的共識性要求。
鄉村典型政治由于不會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框架把身份平等和發展權平等作為經濟生活的基礎,在規則之下公平競爭,往往成為鄉村典型的經濟和權力的積累機器,實際在刻意對村莊進行身份切割,以政治庇護造就鄉村典型的不敗金身。這般形成的鄉村典型被拿來運動式治理鄉村,要求全國鄉村學典型,即是以兩類鄉村之“異”而求鄉村之“同”,清楚暴露出鄉村典型政治的非制度化和非專業化的運動式治理特征以及不穩定性的人治特點,難以推動鄉村善治。此外,在市場經濟下,鄉村典型領導人借著村民自治和企業管理的名義更有效掌控村莊經濟政治資源,容易成為集美德能力于一身的克里斯瑪權威,為村莊的人治提供了條件。某些村莊領導人甚至蛻化為“紅色堡主”,導致普通村民某種程度上的人身依附。禹作敏的說法頗具代表性,“各吹各的號,都聽我的號;不聽我的號,一個也不要”[8]。村莊政治病變為家族政治,異化為“圣人治村”,典型村莊似是村莊能人打造的“羊的門”。村民們都努力表現自己對他們和村莊的忠誠。恩寵與排斥相結合的德治模式有效實現了對于村民的規訓,實現了村莊治理的權力技術與村民抑制改造自我的自我技術的一種特殊結合[9]。這樣的鄉村典型稀缺民主和法治的基因,即使擁有漂亮的經濟成績單也不能使其獲得示范引領新時期鄉村治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市場經濟的開放性對鄉村典型保守性的挑戰
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市場經濟則代表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這意味著市場主體為了完成交換實現利益最大化,會隨著小農經濟的解體打破從村莊到國家的所有層次上的割裂封閉狀態。物的交換也必然帶來附著在物上的文化交流,使文化管理或主動或被動地放松,由此帶來的思想沖擊會呈現破窗效應,推動多元化的觀念市場以及自由、平等和競爭的開放社會逐漸形成,部分社會成員會選擇新觀念取代舊觀念,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的觀念形態發生變遷,打破傳統社會對教條和權威的盲目崇拜。這使得封閉保守的鄉村典型面臨新挑戰,進而沖擊鄉村典型政治。
鄉村典型保守性的表現之一是鄉村典型作為先進模范,也是既得利益者,盡力維護其所代表的生產經營管理模式。這是因為該模式幫助鄉村典型獲得特殊的政治地位,被視為存身立命的政治資本,卻也成為它的沉重包袱,使它不能正視社會的轉型和挑戰,不但容不得別人說三道四,怠于改革創新,相反卻更愿意極端化其模式,以為非如此則不足以彰顯特色、鞏固地位,對其他村莊的新模式則態度消極,抱有戒心,甚至加以壓制。且不說“”期間,“不學大寨就是反大寨”,因為不學大寨很顯然意味著另搞一套,不僅是對大寨至上權威的蔑視和挑戰,也會使大寨模式遭到質疑和動搖,所以,當萬里來到安徽決定不學大寨的時候,遭到了大寨的指責和“中央的阻力”[10]。這樣的典型情結在改革后亦復如是。以改革著稱的小崗村在以激烈的按血手印的方式分田到戶后,因創建出一套新的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成為名揚一時的典型。可這種體制只能解決溫飽,難以帶來富裕,所以村中有人希望重新集體化,像絕大多數明星村一樣,借助集體力量整合資源,發展非農經濟,改變落后面貌,做一個名實相副的典型。可這個想法出來以后,立即遭到反對,理由很簡單,小崗村是大包干典型,再回到集體經營,那小崗村還是小崗村了嗎?[11]此外,像南街村的“外圓內方”管理體制和華西村的家族式管理體制雖飽受詬病,但兩村皆以典型之名博取政治優待,以企業之實虛化村民自治,還不斷強調其社會主義“特色”,占據政治意識形態高地,擁有不俗經濟實績,呈現絢麗的紅色文化,豈能隨便革新?可當今中國社會發展一日千里,焉有不變之理?
鄉村典型保守性的另一表現是鄉村典型刻意隱瞞與粉飾村莊真相,意圖展示完美的典型形象,卻與時代格格不入,愈顯保守落后。筆者多次調查曲折發現,小崗村雖小,村內矛盾卻大。兩位大包干帶頭人沖突尖銳,連上級領導也擺不平,需要駐村干部來維持平衡。當然,為了典型和上級的顏面,在宣傳的時候這些都被“和諧”掉了,只是“擇其善者”而登之。《小崗村調查》的作者在小崗村調研時遭到了當地的種種阻撓和非難。筆者在華西村的調研雖未遇到麻煩,卻要不找不到村民,要不找到的村民總是說著千篇一律的話,和宣傳材料沒什么區別。這種封閉保守僅能讓人看到鄉村典型表面的浮華,難以了解真相,既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開放社會背道而馳,也讓真心學典型者不得要領,鄉村典型政治又如何發揮作用?實際上,在當前高度市場化和信息化的條件下,資訊極其發達,很難筑起完全屏蔽村莊真相的防火墻,透明、公開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時代趨勢,而典型村莊的政治卻似乎總有著難言的禁忌。事實上,人們對于鄉村典型總有這樣那樣的疑問,卻罕見公開及時的回應。鄉村典型缺少競爭更新機制,更看重典型的身份,與現代社會的精英式選擇標準格格不入,似乎一朝獲取即終身擁有,雖然有的典型實在不堪。不過,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在開放社會的氛圍下,仍受傳統慣性影響的管理體制對現實反應的遲鈍,以及意識形態也對保守的鄉村典型政治有點厭倦了呢?
經濟現代化對鄉村典型政治的弱化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能夠快速推動經濟發展,加快現代化進程。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其另一面則是農業小部門化,即“隨著經濟增長,農業在國家經濟結構中的經濟地位,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主要表現在農業增長對整個經濟系統增長的貢獻、農業產出占整個經濟系統總產出的份額以及農業獲取社會生產所需稀缺資源的能力都不斷下降[12],自然表現為鄉村社會邊緣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國內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1982年最高,為33.4%,到2010年降至10.1%[13],表明中國經濟結構正在迅速轉型。因此,鄉村典型的示范功能錯位,示范空間逼仄,示范對象衰落,自然會弱化鄉村典型政治的作用。
改革開放后,鄉村典型的非農化特征非常明顯,少數村莊抓住經濟轉型的契機,以工商業率先致富獲得典型稱號,卻是非農化的鄉村典型。除了小崗村因率先大包干成為農村改革典型外,其他村莊中只有率先致富,才具備成為鄉村典型的物質前提,而要率先致富就必須擺脫農業束縛,走工業化道路。從華西村網站的主頁被命名為“江蘇華西集團•中國第一村”可知,華西村實已不是鄉村,而是一個大型經貿集團,村域經濟以二三產業為主,農業占GDP的比重不到1%,農業比重低,務農人數少。江陰市2011年批準華西村正式更名為“華西新市村”,盡管稱謂改得比較晚,但其管理方式早已由村莊向城市轉變[14]。像南街村等也是如此,殘存的農業微不足道,僅剩下點綴功能,徒具農村之名,卻有城鎮之實。即使以農為主的小崗村,也在竭力追求工業化,發展旅游業,到處招商引資[15]。根據產業分工,農村是農產品生產地,城市是非農產業聚集地。可現實卻是,鄉村是農業的領地,本應樹立農業生產和組織創新的鄉村典型,可現實卻是非農化的鄉村典型大行其道,儼然構成了鄉村社會發展的悖論。大多數鄉村徒生羨慕之情,卻無從模仿,因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非農化門檻日高,動員中西部農村不顧條件學習工業化的鄉村典型辦鄉鎮企業,實有誤導之嫌,鄉村典型政治的效率越高,貽害反而越大。
農業小部門化的另一面則是鄉村社會邊緣化和空心化,這會使得即使真正切合農民需要的鄉村典型的影響力也會因此下降。市場要求農民作為自由勞動力從農戶和村落共同體中分離,從而瓦解農村社會特別是村落共同體,“而且,市場力量對共同體的敵意和瓦解,雖采取解放農村自由勞動力的激進姿態,并不能遮掩它是要求經濟從社會脫嵌并以市場自由規則支配社會的組成部分”,甚至“釜底抽薪,徹底摧毀共同體及其規則”[16]。由于城鄉發展不平衡,在收人差距的推拉作用下,城市猶如黑洞吸走了農村的資金和人才,到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城鎮人口已上升到49.68%,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13.46個百分點[17]。其結果是農村精英人物和青壯年大量出走,村莊蕭條無人氣,留守農村的多是老人、婦女及兒童,他們的政治參與能力有限,政治態度消極冷漠,連接農民的紐帶漸漸松垮,農民生存狀態原子化,村莊公共生活衰敗。沒有了最起碼的人力資源和村落共同體的凝聚力,何談學習鄉村典型?因此,城市化雖沒有完全消滅農村和農民,但導致了農村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的地位下降,鄉村典型自然難免被邊緣化。鄉村典型政治在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能夠呼風喚雨,其經濟社會基礎是中國直到改革開放后仍是一個農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占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但當農村的重要性相對下降的時候,鄉村典型政治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必然變輕,逐漸被邊緣化。也許某位學者對鄉村末世景象的描述看似夸張,卻恰成最佳注腳:“農民,這個被現代化工具宣判了死刑的階層……在最后的日子里,老農們顯得十分平靜。豬圈、牛欄拆除了。古老的農具變賣給收藏家了,鋤頭上的泥土已經清洗,高高地掛在了墻壁上。”[18]此時,誰還有多少興致來談論鄉村典型政治呢?
鄉村典型政治集中經濟政治資源推出亮麗的鄉村典型,引導鄉村發展,鼓舞鄉村精神,提升國家形象。但鄉村典型政治的邏輯在某些方面可能與市場邏輯耦合,但在另一些方面則存在巨大沖突,因為有的鄉村典型很多時候憑借特殊的經濟政治地位,左右逢源,予取予攜,經常能夠輕易獲取普通村莊難以奢求的稀缺資源,非常規實現經濟發展,其真實的經濟發展路徑與其所示范的經濟發展路徑大相徑庭。相比絕大多數普通鄉村腳踏實地依靠自身努力發展經濟,鄉村典型即使經濟“高效”也難以激發其他鄉村的模仿而繼續其“政治神話”。鄉村典型政治歷經市場經濟的反復淘洗,作為意識形態花邊已失去其原本該有的一抹亮色,似乎還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從而消解了鄉村典型政治的多種可能性,如此的鄉村典型政治又何以為“典”,怎能行“治”?看起來,鄉村典型政治收斂于市場邏輯大概是二者當下博弈的必然結果。(本文作者:董穎鑫 單位:巢湖學院鄉村治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