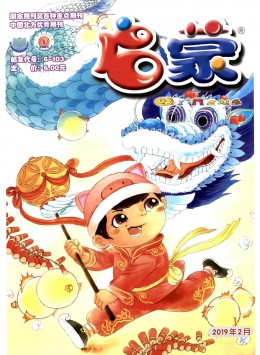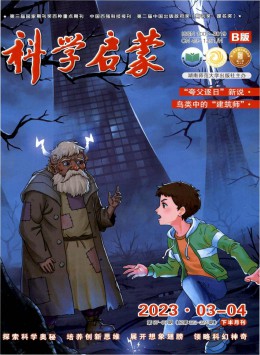胡風的啟蒙觀念研討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胡風的啟蒙觀念研討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在解放戰爭時期,胡風同樣把啟蒙置于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他在1948年2月20日和3月15日致阿垅的信中都提到:“今天,我們的工作要帶啟蒙的性質,每一論點都要考慮到反應。”“每一工作……甚至行文、用字,現在都得非為爭取大眾性而鄭重努力不可的。已經到了作文等于作戰的情形了。否則,辛苦追求到的東西容易讓人糟蹋掉。無論如何,要把啟蒙的效果放在心上。”④1954年1月,胡風在中央文學研究所講魯迅雜文時指出:“要有革命運動就要有一個思想斗爭,要有啟蒙把人民從舊思想中解放出來,產生了先鋒隊伍,這樣才能夠革命,革命也才會成功。”“他(指魯迅———引注)曾說,必須先有啟蒙,有思想斗爭,然后才有實際斗爭。”1978年12月尚在四川第三監獄的胡風在聽說中央正在逐步糾正“”中的一些錯誤以后,他“不斷地實感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定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再啟蒙,更普及,更深入,更和實踐有機地結合著向前發展,一定要出現一個思想上光華燦爛的新時期”。
《胡風全集》中有關啟蒙的論述很多,經過一番梳理,我們認為最主要有兩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類似于傳統意義上的“發蒙”。它是包括識字運動、狹義的宣傳劇本、墻頭詩、街頭劇等普及性、初步的啟蒙教育。在胡風看來這種大眾的啟蒙運動,即初步的文化運動或者說文化運動的基礎性的普及工作應該站在其他工作的前面。在文藝創作上,胡風對“啟蒙的文藝教育活動”和“分析的文藝創作活動”,“藝術力高的文藝”和“宣傳力廣的文藝”做了嚴格的區分,但他反對把二者割裂、對立起來,他認為二者是“同歸”的“殊途”,它們有著人民解放、社會進步、人類解放的共同目標。前者是基礎性、前提性的工作,相當于普及;后者是在前者基礎上的提高。胡風之所以強調“初步的啟蒙教育”的重要性和前提性,主要是從五四啟蒙運動的教訓中吸取了經驗。胡風認為:“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向著兩個中心問題集中了它的目標。怎樣使作品的內容(它所表現的生活真實)適合大眾的生活欲求,是一個;怎樣使表現那內容的形式能夠容易地被大眾所接受———能夠容易地走進大眾里面,是又一個。這是文學運動的基本內容,也是大眾化問題的基本內容。”應該說,胡風這一論斷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大多一開始就自覺地擔負起思想啟蒙的重任,希望通過大眾化、平民化的文學來喚醒勞苦大眾的自我意識,“人”的自覺意識。但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僅僅在知識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與廣大的勞苦大眾并無多少關系,以至有人攻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爾”的文學,是一種應該扔進歷史垃圾箱的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雖然遍及全國,但其主要活動范圍僅僅局限在一些所謂的“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先進的知識分子大多聚積在這些“文化中心”,也就是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們并沒有真正深入到大眾中去進行切實的啟蒙工作,這是造成五四新文化運動脫離大眾的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勞苦大眾受幾千年封建統治者愚民政策之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能識文斷句的不多。他們根本無法閱讀新文學作品,又怎么可能通過新文學獲得新思想、新觀念呢?正是基于這兩個原因,胡風強調初步啟蒙教育的重要意義。
胡風對啟蒙的第二層理解是在初步啟蒙教育的基礎上用先進的人生觀、世界觀去照亮、啟發大眾,幫助他們擺脫幾千年封建統治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也就是要“從民眾的生活、困苦、希望出發,誘發并且養成他們的自動性、創造力,使他們能夠解決問題、理解世界,由這參加戰斗,同時又會從戰斗里面涌出解決問題、理解世界的欲望,使他們的自動性、創造力繼續成長,‘從亞細亞的落后’(今天的狀態)脫出,接近而且獲得現代的思維生活。這樣地,我們的所謂‘宣傳’、‘動員’,就能夠成為改造‘今天的狀態’的‘經常的運動’……從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迎頭趕上’現代文化,‘使自己的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獲得更進一步,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時代’(潘梓年語)”⑤。這種對啟蒙的理解在當時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何干之在《中國啟蒙運動史》中開門見山地點明了啟蒙的含義:“啟蒙二字,從它的字義來說,是開明的意思;也即是‘打破欺蒙,掃除蒙蔽,廓清蒙昧。’更顯淺一點說,就是解放人們頭腦的束縛,教他們耳聰目明,教他們了解為什么,了解怎么做。”劉少奇指出:啟蒙就是要使廣大勞動人民“從黑暗、愚昧、盲從和迷信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具有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使他們對于現實,對于前途,對于國家民族,都有新的希望與新的理解,……使他們從長期受人奴役欺壓馴服的狀況中挺著胸膛站起來……成為各方面的活動的積極的因素!”⑥
在胡風那里,無論是啟蒙的第一層含義,還是第二層含義,啟蒙者扮演的都是先生、導師、先知的角色,對民眾采取的是一種從上而下的俯瞰姿態。事實上,并不僅僅是胡風一人在扮演先生的角色,幾乎所有抱著啟蒙觀念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在扮演先生這一角色。胡風這種啟蒙觀念一方面有傳統思想的淵源,另一方面又從斯大林關于作家應該做“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觀點中獲得了巨大的理論支持。他對自己手中的真理確信無疑,并用這一真理向大眾布道,希望通過自己的布道,能讓大眾接受自己宣傳的真理,從此改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態度和生活方式。
西方有關啟蒙的言說也是千差萬別,沒有一個統一的,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定義,但其中有一點是各種啟蒙思想所共同擁有的,那就是把啟蒙當作一種思維方式,說得更準確一點就是理性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卡西勒所說的“分析還原”和“理智重建”的思維方法。這是西方各種啟蒙思想的基本特征。所謂啟蒙就是要學會運用這一理性的思維方法去分析和判斷事物,而不是從啟蒙者那里獲得一整套既成的關于真理的觀念。這也就是意味著真理不再是預先設定好的,由真理的代言人(比如牧師)傳播給眾人的“福音”,而是個人獨自思考的結果,對真理的判斷成了純粹個人的事情。這一思想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萌芽。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人們認為,和別的東西一樣,教義也可能會出錯,這就打破了教會教義的絕對權威,摧毀了僵死呆板的經院哲學體系,把古代人豐富多彩的哲學思想重新納入了研究的范圍。“更重要的是,文藝復興運動鼓勵這種習慣:把知識活動看成是樂趣洋溢的社會性活動,而不是旨在保存某個前定的正統學說的遁世冥想”⑦,它鼓勵人們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去選擇自己的真理。
文藝復興運動養成的這種習慣,經過漫長的發展,終于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達到了它輝煌的巔峰———理性的確立與高揚。18世紀是“理性的世紀”,理性成為至高無上的審判者。一切事物存在的合法性都有待于理性的最后審判。理智的力量、理性成為各種啟蒙思想自身建構的內在核心概念。康德認為:“啟蒙是從自我招致的依賴監護的狀態中解脫出來。依賴監護是指人在沒有他人指導的情況下沒有能力運用自己的理解力。這種依賴監護的狀態是自我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是在于缺乏不要他人指導而運用自己的理解力的果斷和勇氣。要敢于運用你自己的理解力!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只有擺脫依賴監護狀態,敢于獨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力量,也就是說只有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才可能真正擺脫各種偏見的束縛。而“18世紀文化的基本目的,就是捍衛、強化和鞏固這種思維方式。18世紀認為,它的主要使命不只是獲取和擴展具體知識,而是確立這種思維方式。……狄德羅本人就說過,該書(《法國百科全書》———引注)的目的不僅是提供一定數量的知識,而且要改變一般的思維方式”⑧。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主要表現為對“理性這一概念認識的轉變”。18世紀把理性概念描述為“作用概念”,而不是“存在概念”,也就是說“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經驗,揭示了事物的絕對本質的‘天賦觀念’的總和……而是一種引導我們去發現真理、建立真理和確定真理的獨創性的理智力量。……整個18世紀就是在這種意義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識、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視為一種能力,一種力量”⑨。如前所述,這種力量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分析還原和理智重建。啟蒙運動拋棄了形而上學從既定原理出發的演繹法。在啟蒙理性面前沒有先驗的真理,啟蒙主義者把一切需要認識的對象分解、還原為最簡單的成分、最終極的因素,然后開始重建出一個真正的整體。總之,啟蒙哲學強烈反對從原理、原則、公理演繹出現象和事實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而主張從現象和事實上升到原理和原則的分析重建的思維方法。
胡風的思維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啟蒙哲學的思維方式有著相似性。由于對實踐論的堅持,胡風強調對問題的認識應該從實踐出發,從平凡的瑣事出發,而不是從原則出發。原則應該是從實踐中總結得出的結果,它從實踐中來,同時又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因此,胡風反對由政治概念、大原則出發演繹生活的主觀公式主義,同時,又反對自然主義(客觀主義)那種只注重瑣碎、零散的個別現象、經驗的真實,而不去發掘事實、經驗之間的秩序和規律的做生活的奴隸的態度。他要求透過生活現象去發掘出生活的本質真實。這與啟蒙哲學分析重建的思維方式有異曲同功之妙。另一方面,胡風認識到:“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實現只能依靠人民的‘自覺之聲’,因而要‘改變他們的精神’(也就是要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養成主動的精神,獨立負責的精神),使他們從封建意識的麻木里面覺醒,掙脫封建意識的偏見,起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堅決反對狄超白主張“政府應當以最良的方法消滅人民思想上的紛爭”以實現所謂“思想統一”的論調;反對對大眾進行所謂“訓政”,以實現一個“意志集中”了的政府。因為不管是用“最良的方法消滅人民思想上的紛爭”以實現“思想統一”,還是通過“訓政”以結成一個“意志集中”的政府,都帶有明顯的專制傾向,其實質是把一套既定的價值觀念灌輸給大眾,并讓大眾接受、服從這一價值觀念,而不是鼓勵大眾“敢于運用自己的理解力”,主動、獨立負責地起來決定自己的命運。胡風因此懷疑“政府里面有一部分人抱有統制思想的傾向”。
盡管胡風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啟蒙哲學所倡導的思維方式有著較大的相似性,但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那樣,在啟蒙過程中,胡風扮演的始終是“先生”的角色,他是高高在上的真理的掌握者,是上帝派來向大眾傳播福音的先知。因此,對胡風而言,無論是分析重建,還是反對“思想統一”,其背后都有一個終極真理存在,也就是說無論其思維過程多么復雜、曲折,其最終指向都是確定無疑的,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達到這一最高真理。因為胡風確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是各種思想經過互相批判,互相競爭,互相融合而得到的具有最大合理性的“最健康的力量”,是人們“在自己的生活實踐里面發生著燃燒作用,用熱情的傾注和意志堅強向實際問題搏戰的結果,而且也是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一切固有的外來‘觀念藝術品’里面感到了無法自慰的苦悶,因而‘摸索探討’出來的皈依”。因此,他對自己掌握的真理堅信不疑。一方面以胡風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自認為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理論,另一方面中國大眾的文化水平低下,還停留在“醉生夢死”、“雞鴨不分”的狀態。要讓這樣的大眾接受先進的科學真理,知識分子必須,也只能擔負起先生的責任,在先進思想與大眾之間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這樣,胡風對大眾的啟蒙就成了把一種既定的正確觀念灌輸給大眾,而不是去改變大眾的思維方式,使大眾擺脫依賴監護的狀態,主動、獨立負責地運用自己的理解力。這種體現了“最健康的力量”的先進科學理論對胡風而言可能是自己思考的結果,但當他把自己思考的結果灌輸給大眾時,他就是用自己的思考代替了大眾自己的思考,使大眾依然處于被動的,依賴監護的狀態之中,而且在胡風看來這一真理是絕對正確不能質疑的。正是在這一關鍵之處,胡風顯示出了與西方啟蒙哲學的根本差異。我們在上文說過,啟蒙在西方所指的主要是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所謂啟蒙就是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而不是讓人們去接受某種既定的主義、信條,或是具體的知識和觀念。因此,在西方啟蒙哲學家眼里是沒有絕對正確的真理和權威的,具有權威性的是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具體的科學結論。因為在科學理性看來:具體的科學論斷是按嘗試的方式提出來的,它隨時都要接受理性的質疑和修正。⑩西方啟蒙主義這種對科學理性的強調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形成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而胡風倡導的啟蒙觀念中則暗含著專制的傾向,這恐怕是反對用專制的方法實現“思想統一”、“意志集中”的他所沒有料到的。事實上,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最后成了這種啟蒙觀念的受害者,甚至是犧牲者,這恐怕更是胡風所始料不及的。
胡風一方面反對教條主義地照搬馬克思主義原理并企圖以此造成思想一致的庸俗社會學的做法,主張“用‘嚴肅的戰斗的科學態度’去理解對象,分析問題;對人對己任何事情‘都要經過自己的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要提倡奴隸主義’”。正是這種不盲從的非奴隸的主張,使胡風在“組織上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胡風“從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候起”,“從來沒有一次把黨的威信和真理在思想上甚至感覺上分成過兩個東西”輯訛輥。對胡風而言,對真理的追求就是對黨的威信的服從,因此,“對于一個真正的作家,自由主義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所以,他對胡適、朱光潛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義采取的是一律否定的態度。在文藝思想上,他獨尊現實主義,把現代主義統統斥為墮落的資產階級文藝,這顯示了他“左得可愛”的一面。令人奇怪的是,胡風對自己思想中這種自由與專制的矛盾似乎毫無察覺,可以說胡風是順著科學理性之梯爬上了信仰迷信之塔。在他看來,這二者是統一的。胡風之所以造成這種矛盾而不覺,主要是因為以下兩點:他一方面把馬列主義當作一種認識世界的思維方法,而不是教條。他認為原理、原則應該是從實踐中總結而來,并要回到實踐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不斷地為實踐豐富、修改、糾正,甚至推翻。這也就是他經常強調的主、客體之間要“相生相克”,才能達到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在這里沒有絕對正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一切都必須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一貫正確’這個盲目的自信,無論對作家,對理論批評家都是沒有好處的”。而另一方面,胡風又認為馬列主義是從客觀歷史運動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原則,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過去和未來的最正確的理論,把它當成一種既定的、絕對正確的原則、理論來信仰,而不是把它當成一種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這就造成了胡風啟蒙思想中自由與專制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本文作者:陳金琳、曾凡解 單位: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