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結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小議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結構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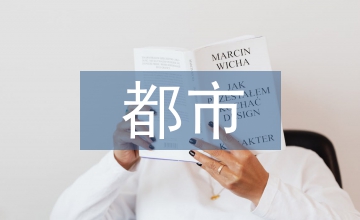
上海市的農業旅游在20世紀90年代初,方以1991年南匯“桃花節”與寶山“柑橘節”為序幕,進入其發展啟動期。然起步雖晚,發展迅速。到2009年,上海市已登記100多個農業旅游景點,其中17處為國家農業旅游示范點[4];農業旅游年收入達15億元,接待游客1100多萬人次(表1)。研究對上海市118個農業旅游點的旅游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并對其中近30個規模化發展的旅游點進行了現場調研。從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上看,上海市各個農業旅游點及旅游區的旅游收入差異非常大,2009年桃花村農業旅游收入高達2億元,占全市100多個農業旅游點總收入的13.3%,其中歷時僅23d的桃花節期間旅游收入達該景區全年收入的30%。相反,同樣位于南匯區的國家農業旅游示范點洋溢村2009年旅游收入僅310.9萬元,只有桃花村旅游年收入1.55%。上海市的農業旅游空間分布也不均衡,以17家國家農業旅游示范點為例(圖1),其空間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郊區的南部地區(南匯區及奉賢區)以及崇明島,并初步顯示出組團化的空間分布趨勢。下文將立足于都市農業旅游的產業特征,從市場供需特征、產業集群化與產業開發類型3個角度,探討上述上海市都市農業旅游空間形態特征的產業機制,并進而研究上海市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結構模式。
二、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的產業發展特征
1都市農業旅游的產業供需特征
在旅游產業的供需關系中,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對旅游產業的發展形成拉力,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資源與服務供給、以及當地經濟發展需求、政策扶持則形成發展推力,“推拉合力”引導著旅游產業的發展,產業的區位選擇則形成了其區域布局的空間結果。為了解上海市農業旅游的供需特征、游客現狀結構及滿意度,課題組分別于2011年10月在崇明島的農業旅游點,以及2012年7月在廊下鎮農業旅游點對游客進行問卷調查,2次共計發放問卷480份,回收問卷447份,其中有效問卷402份。調查發現,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的市場供需特征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與都市旅游、風景區旅游主要吸引外來旅游者相比,都市農業旅游的吸引力體現在以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風貌來吸引當地及周邊城市的城市居民[5],客源地與目的地之間的差異性主要為生活方式及環境,而歷史背景、語言、文化認同等差異性不大;2)旅游目的地是都市周邊的農業區,旅游客源地主要為中心都市及周邊臨近大中城市。根據游客問卷數據整理,崇明島游客中72.5%為上海市居民,廊下鎮游客中90%以上為上海市居民;3)旅游目的地位于都市周邊,因此居民的旅游消費總量相對較低。研究將旅游消費分為餐飲、住宿、景區門票、交通、農產品與旅游紀念品6類,發現上海市農業旅游中最大比例消費內容為餐飲(24%),交通與旅游紀念品則屬最小比例消費類型(11%與4%),而游客對旅游出行的交通成本考量主要體現在交通時間上;4)上海市的自然山水資源稀缺,而都市農業的產業規模化程度與科技化水平卻高于國內大多地區,因此都市農業旅游主要依附于農業產業本身;5)上海市2010年城鎮化率則已高達88.86%[6],是全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而都市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總是伴隨著周邊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因此都市地區農業旅游的設施及服務水平一般高于其他地區的農業旅游,以提高都市農業旅游的地區競爭力。
2都市農業旅游的集群化發展
識別產業集群通常根據兩大產業特征———產業規模和集群內產業聯系[7]。產業規模主要指在區域內聚集的企業數量與旅游人口數,產業聯系則包含了產業關系鏈與產業聚集程度[8]。雖然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分布不均衡,旅游點之間發展水平差異大,但組團聚集的空間布局已初具形態。研究收集了上海市118個農業旅游點的特征、規模與經濟數據,按照圖2的識別路徑分3步對這些農業旅游點的規模化程度、產業關聯度和集聚性進行分析判別,最后確認了上海市23個規模化的農業旅游點及其所形成的7大農業旅游產業集群。農業旅游的集群化發展可以節約產業成本、提高區域品牌價值、增強市場競爭力[9]。研究發現,在這7個農業旅游產業集群內部,規模化的農業旅游點從2個到5個不等,它們與周邊其他小型農業旅游點一起,不僅在地域空間上聚集,經濟上也緊密關聯,資源共享、相互合作,進而提高旅游目的地整體的農業旅游吸引力、承載力與生命力。關于農業旅游集群化發展的特點、優勢以及具體判別方法在此不作贅述,本課題的另一研究專題“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產業集群判定研究”已就這一問題專門作了探討。
3都市農業產業開發類型
目前國內農業旅游研究對于該產業的開發類型有3種分類方式,一是按照農業旅游資源類型分,如觀光果園、水產觀光園、種植觀光園、森林公園等[10];二是按照旅游活動進行分類,如農業體驗游、鄉村休閑游、自然生態觀光游、農家度假游、民俗文化游等[11];三是按照農業旅游的經營主體或者說是經營組織方式進行模式分類,據此上海農業旅游就可以分為公司+農戶開發模式、公司制模式、股份制模式、政府+公司模式以及政府+村委會(農戶集體)+企業模式等[12]。研究認為,旅游資源的特質對旅游活動的開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性,而旅游需求又引導著旅游資源的組織配置,因此結合旅游需求、依據旅游資源對農業旅游產業進行劃分更能體現產業不同類型的核心價值,據此研究將上海都市農業旅游分為以下5種開發類型(表2)。研究發現,上海市都市農業旅游集群內的規模化旅游點彼此之間大多類型不一,例如奉賢集群內包含5個規模化農業旅游點,分別代表了4種開發類型:村鎮類(潘墊村)、農業科技示范園(都市菜園)、農業公園(申隆生態園)、特色種植園(玉穗綠苑和百棗園)。正是集群內旅游點開發類型的差異,讓各個旅游點能夠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機會,形成了旅游點之間的差異性合作,進而能夠發展成為產業集群。另一方面,各個集群之間的開發模式則大同小異,大多是村鎮類旅游點為旅游接待點,并以其他類旅游點作為旅游吸引點。
三、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的區域空間結構
研究對前文分析的23個規模化農業旅游點繼續進行空間分布研究,發現都市農業旅游的產業特征直接影響了產業在都市空間的布局,這導致上海市農業旅游空間布局呈現出“Circle圈層”結構與“Cluster組團”結構兩大特征,其中“圈層”結構受到農業旅游業的供需關系、以及城市居民對農業旅游的區位選擇影響,而“組團”結構則是農業旅游產業集群化發展的空間體現。
1農業旅游空間的圈層結構
研究以上海市人民廣場作為市中心,結合Google地圖車行時間距離查詢結果與實際駕車情況繪制3個車行時間圈層:0.5h圈、1h圈與2h圈(圖4)。鑒于上海市的快速道路網布置結構,上海市的車行時間距離圈層并沒有呈現標準的同心圓,而上海市的農業旅游空間分布卻與這3個時間圈層基本吻合,呈現出環中心“圈層”分布的空間結構特征。
空間分布圈層化。都市農業旅游作為城市近距離游憩方式的一種,交通距離通過時間、經濟成本直接影響都市居民的出行率。保繼剛等認為都市周邊的游憩空間呈圈層分布,其旅游強度基本上滿足同心圓遞減規律[13],即在忽略自然資源稟賦的前提下,城市周邊的旅游地與城市的距離越遠,旅游強度越低。農業旅游是依托與都市生活空間相異的農村風貌、生活方式及農業生產來吸引都市居民,而根據上海的都市規模,0.5h圈附近的農業旅游點基本還處于城市建成區的邊界附近,只能形成“城市農莊”。鑒于該區域的城市用地限制與土地機會成本高,該圈層內農業旅游點數量少而規模小,旅游吸引力與承載力也相對低。因此上海市的農業旅游強度最高的圈層出現在1h交通圈附近,進而向外逐層遞減。其中上海西北角受到江蘇昆山地區密集的農業旅游區陰影影響,該區農業旅游點少且沒有集群化發展趨勢。
旅游形式圈層化。不同的農業旅游圈層所體現的農業旅游形式也不同。0.5h交通圈附近的農業旅游點規模小,兼具“城市公園”的景觀形態與游憩、生態功能,其旅游形式以居民短暫游憩為主;1h交通圈附近的農業旅游點分布密集,以休閑體驗游為主,其形式多樣,包括農村風貌觀光、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體驗等,旅游點之間相互影響,并可組織在一起成為1日游(含周末游)旅游區;上海2h交通圈附近分布的農業旅游點主要處于崇明島西部地區,其旅游形式以休閑度假游為主體,并涵蓋農業生產、農村生活體驗的旅游活動方式,形成多日游(含長假游)的旅游區域。其旅游地位等同于省級旅游點,旅游客源地既包括上海市,也涵蓋了外省市。
2農業旅游空間的組團結構
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的產業集群化發展導致了農業旅游的組團化空間布局形態,每個產業集群可對應一個旅游空間組團,另外還有具有集群化發展趨勢的崇東組團與青浦淀山湖組團。因此目前上海市形成了9大農業旅游空間組團(圖5)。其中崇明島作為上海的生態休閑島,且西部及中部兩個組團位于上海市2h出行圈(及2日游或長假游區域),游客往往將這2個組團的旅游點作為一組旅游對象,從而成為一個更大的旅游組團。組團內旅游點除了集群內的規模化農業旅游景點外,還包括小型農業旅游點及其他非農業旅游景點,如崇明島的西沙濕地、東灘候鳥保護區、奉賢的金色沙灘、森林公園、青浦的淀山湖等等。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組團的旅游類型構成與前文闡釋的集群構成特征一致,即組團內部旅游點彼此不同類,空間聯系便捷,能夠優勢互補、協作發展。每個農業旅游組團大多是以村鎮類旅游點為旅游接待點,以其他類旅游點作為旅游吸引點,同時根據農業資源開展了各類節慶活動,進而使整個組團形成了一個整體化的旅游目的地。且組團內的旅游景點及企業經濟聯系密切,并位于同一個行政區內,便于對整個組團統一規劃與管理,促使其協同發展,能夠發揮集群化的產業優勢。研究對旅游點游客的問卷調查還發現,鑒于每個組團的旅游點類型構成比較類同,都市居民每次旅游出行只會選擇一處組團作為旅游目的地,這形成了同一圈層上各個組團之間的旅游競爭關系。這一競爭結果會導致旅游組團的自我優化,包括更鮮明的旅游形象、更全面的旅游類型、產業的集群化發展、旅游點之間更密切的協作關系、更為合理的組織形式與信息平臺等等。
3上海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結構模式
根據前文分析,上海市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布局受到旅游者目的地選擇與產業集群化發展的雙重影響,呈現出“Circle圈層+Cluster組團”的空間結構模式(圖6)。上海市農業旅游空間布局的3大“圈層”既反映了旅游強度的同心圓遞減規律,也代表3種旅游形式———居民游憩、休閑體驗游(1日游)、休閑度假游(多日游)。“組團”則體現出上海農業旅游點的地區內合作、旅游產業集群化發展,并反映了組團內部農業旅游點的類型組成。該空間結構模式同時還將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研究劃分為3大層次。層次1為上海市域層面,即本文的研究范疇;層次2是農業旅游組團層面,農業旅游的產業集群研究則屬該空間層次;第3層次的研究則落在具體農業旅游點上,即對各類農業旅游點的空間要素構成及空間結構進行探討。
四、結語
都市農業旅游是都市農業與旅游業相結合的產業,其產業發展過程在空間上表現為都市農業旅游的空間結構及變遷,因此上海市都市農業旅游的“圈層”與“組團”空間結構就是都市農業旅游產業的區位選擇及產業集群化發展的空間結果,都市農業旅游規劃應該順應這一空間結構特征。另一方面,都市農業旅游點的開發,應該首先確定自身在都市農業旅游空間結構中的定位,即根據區位判斷所處的農業旅游圈層及組團,并依據組團現有農業旅游開發類型,選擇合適的農業旅游形式與旅游類型。這樣才能盡量拓展錯位優勢,避免組團內部競爭,從而借助農業旅游組團提高自身吸引力。(本文作者:王玲、柳瀟、車生泉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農業與生物學院、農業部都市農業(南方)重點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