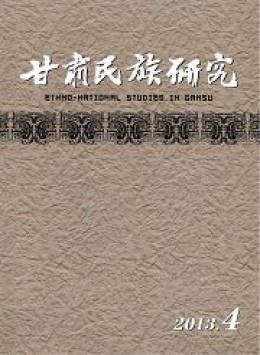民族管弦樂創作探討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民族管弦樂創作探討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內容摘要:近年來,民族管弦樂創作呈現多元并存的文化景觀,文章就“民族器樂劇”“主題性音樂創作”“新創作品的地域性特色”三種創作現象進行延展和探討。一方面,階段性記錄民族管弦樂發展軌跡、追蹤民族管弦樂發展態勢;另一方面,通過學理分析,理解當下,也指示出未來民族管弦樂創作可做可為的道路。
關鍵詞:民族管弦樂;創作;民族器樂劇;主題性;地域性
民族管弦樂從最初的探索、創建,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擴充、改進,再到形成結構相對穩定、音效相對豐厚的民族管弦樂隊,涉及到樂器形制、編制組合、藝術創新、價值建構、國家在場等一系列附加的文化表述,一直是學界值得深挖和探討的話題。學者張萌在近年發表的《新時代民族管弦樂創作述略》[1]一文,系統地梳理了民族管弦樂的發展歷程。該文指出,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民族管弦樂發展活躍,并呈現主題性創作繁榮、多元跨界、青年一代作曲家迅猛崛起等特征,展現出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多元并存的文化景觀。以面對這種多元并存的文化景觀,當然還應囊括更寬泛、更客觀和更理性層面的思考。為此,筆者結合自己在該領域的實踐,就近年來民族管弦樂創作領域的三種現象進行延展,以期階段性記錄民族管弦樂發展軌跡、追蹤民族管弦樂發展態勢。
一、民族器樂劇
說起民族管弦樂的既定印象,定會和“音樂會”聯系在一起,不論規模大小、編制繁簡,抑或樂器擺位各異,演奏者在臺上的固定席位演奏樂器,觀眾在臺下欣賞樂曲,無可非議、習以為常,我們慣常的說法稱作“聽音樂”,而非“看音樂”。但近年有不少新創作品打破這種延續了近一個世紀的固定模式,一種將劇情引入民樂的方式不約而同地進入了創作者的視野。近年來,以“劇”冠名的作品不在少數,諸如民族樂劇《印象國樂》(2013)(圖1)、民族樂劇《又見國樂》(2015)、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2017)(圖2)、民族器樂劇《笛韻天籟》(2017)、多媒體民樂劇《九歌》(2018)、大型情景器樂劇《揚帆大灣夢》(2018)、跨界多媒體舞臺劇《大禹治水》(2018)、音樂劇場《桃花扇》(2018)、大型器樂劇《韻魂弦夢》(2018),等等。這類新興作品通過更多的表現手段為民樂做了宣傳,許多劇目在更大范圍內拓展了民樂的觀眾群和影響力。民族器樂劇的涌現,的確引領著各民族樂團開拓市場,但這類劇目在追逐潮流的同時,也把對這一現象的探討推向了學術爭鳴的風口浪尖。有觀點認為,中央民族樂團邀請王潮歌導演創作的《印象國樂》是這一輪行業熱潮的發軔,演奏家、作曲家、指揮家在臺上直面觀眾,講述自己真實的故事,還音樂以人格特征,對民族管弦樂的提升大有裨益。該劇首演之后,音樂學家喬建中稱其為國樂的新語體[2],顯然,他對這一形式持“支持創新”和“鼓勵探索”的態度。此后,亦有多位學者對這一創新進行肯定,例如,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張振濤認為:“這些賦予器樂文化的立體感的現代氣息,有效提升了國樂形象。”[3]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薛藝兵認為,這些作品表明藝術的創新沒有定規,音樂的表演形式也需要不斷創新[4]。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傅謹認為,這一系列創新之作無論還存在什么瑕疵,都能明顯感受到其中無法遮蔽的閃光[5]。哈爾濱音樂學院院長楊燕迪在充分肯定這種“新語體模式”的同時,認為它還在成長中,相信會不斷完善,也會繼續發生變化[6]。創新必然會引起“保守派”與“改革派”的觀念交鋒,自然亦有許多業內人士持觀望甚至批評態度,認為民樂應該固守陣地,傳承幾千年的文明應該謹慎對待。例如,文藝評論學者倫兵指出:“民樂‘器樂劇’究竟是新形式、貨真價實還是玩概念、過度包裝?這是目前‘民樂劇’演出尚未解決的問題,無疑也關系到民樂‘器樂劇’究竟能夠走多遠。”[7]學者刁艷認為音樂表演的動人之處“無關所謂表現形式的創新、無關你為音樂付出的艱辛、也無關音樂家的身世和故事、更無關音樂會結束后空空舞臺的一地失落”[8]。另有學者在多個學術研討場合表現出像當年孔老夫子看到“八佾舞于庭”那樣“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義憤填膺,認為對待嚴肅音樂的態度就應該正襟危坐,甚至認為有些劇中情節與歷史和現實有所偏差、尚須考證。筆者認為,對待音樂的嚴謹態度固然值得尊敬,但持完全否定態度的觀念亦矯枉過正,其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仍值得商榷。首先,回歸“民樂是什么”的問題,我們都不可否認民樂是藝術。既然藝術不是類型,藝術的表現形式本來就可以多樣,可以表現為音樂會,亦可以表現為其他,那么如此說來民樂表現為一臺民族音樂會還是一臺民族器樂劇已然不是原則性問題,何況“嚴肅音樂會”(ConcertofClassicalMusic)本身就是西方舶來品,既然人們可以接受參照交響樂編制創作出來的民族音樂會,為什么不能接受類如歌劇和舞劇一樣用民族器樂表現戲劇的民族器樂劇呢?其次,關于藝術和學術的區分顯而易見,藝術不等同于學術。做學術需要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藝術創作雖然同樣須抱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但也需要“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創新精神。換言之,藝術和學術無所謂高下,但兩者實屬于兩套不同的評估體系,因此,把藝術作品完全等同于歷史真實和現實真實并加以評判顯然有失偏頗,在藝術創作中“現實”與“超現實”都只是手法,創作者有權選擇適合表現自己藝術的手法。因此,比較客觀的評價應該是,無論創新與否、何種形式,最重要的是“民族器樂”作為主體不應該淡化,作為支撐的依然應該是高質量的創作、高質量的演奏和高質量的表演,這一直是而且永遠是評判一臺民樂劇目優劣的根本標準,確切地說是評判一部舞臺劇目的準繩。
二、主題性音樂創作
除去上述民族器樂“劇”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其他常規音樂會的創作與編排也更具明確主題性,音樂會不再像十幾年前那樣草率地僅以“民族音樂會”“民族器樂音樂會”“民族管弦樂音樂會”印入節目單。誠如“標題性音樂”一般,音樂會名稱與劇目闡述更加講究,它賦予了聽眾一個大致的思想范圍。這類主題性音樂會在近年頻頻涌現,例如《絲路粵韻》(2015)、《尋找杜甫》(2016)、《永遠的山丹丹》(2017)、《高粱紅了》(2018)、《七彩之和》(2019)、《中軸》(2020)、《孫子兵法·回響》(2020),等等。再具體點說,每一場主題音樂會大多有其內在的邏輯結構和敘事結構,它更注重一場演出的文學統籌。以《絲路粵韻》為例,該音樂會以開海、祭海、遠航、異域、鄉愁、歸來、新夢為敘事線索,分別用七個樂章展現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畫卷;再以《高粱紅了》(圖3)為例,音樂會以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為敘事線索,揭示了人與自然、土地與生命相互依存的內涵。這種主題性表達的涌現當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如此說來,作為音樂會形式的民樂呈現,在整體表達上確實略遜于其他舞臺藝術。“民樂聽韻味”的傳統讓創作者更注重每首樂曲個體的表達而相對忽略整臺劇目的布局謀篇,策劃者和表演者鮮有考慮聚焦一個主題的問題。并非說,每臺音樂會都必須按戲劇作品那樣以起因、發展、高潮、結局來講述一個包含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矛盾沖突的故事,但是完整的音樂會,一定需要遵循某種邏輯關系,通過某種文化結構串聯起來。一臺優秀的音樂會一定由包含其中的優秀曲目構成,但音樂會與曲目之間的因果關系不可本末倒置,一組優秀的曲目,即便表達了相同的主題,如果邏輯結構不合理,也未必就能夠組合成一臺優秀的音樂會。說起來雖有些繞口,但道理很簡單——完整的劇目需要整體布局,速度的快慢緩急、情緒的跌宕起伏、結構的起承轉合等因素都應考慮其中。從目前創作推出的主題性音樂會觀之,完成一臺音樂會整體性布局,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受制因素也很多,尤其是現代音樂作品大多采納委約制的情況,受約作曲家大都在相對密閉的環境下獨立完成單曲寫作,待到作品視奏階段已基本“定局”,回過頭來考慮整體性問題確實十分受限。以《絲路粵韻》為例,該音樂會已是近些年民樂創作中比較注重整體表達的一臺劇目了,策劃者目標清晰,創作者方向明確,而且委約的數位作曲家均在業界有口皆碑。演奏該音樂會的廣州民族樂團在技術上、作品闡釋上也有目共睹,可以說是算得上良心之作了。但其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七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在發力,每一位作曲家都不甘示弱,整場下來,亢奮的點太多、高潮太密集、音響太滿便成為影響整體感觀的問題,因此,有時候“干貨”太多也未必都是好事。在這個問題上,由一位作曲家獨立完成的一整臺音樂會,例如《高粱紅了》,其樂曲風格和布局則更為統一。做此評價,并不是倡導作曲家今后都來創作整臺音樂會,委約者今后一臺音樂會只委約一位作曲家,而是應該從中看到統一性的關鍵所在。這一點,民樂一定要向戲劇、戲曲、歌劇、舞劇的藝術創作學習,主創團隊需要更多的研討、交流,也需要更多的協作意識和協作精神。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值得推廣,并亟待更多作曲家的認同。
三、地域性特色
立足本土、吸納優秀的民間文化,繼而創作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的作品,這并不是什么新鮮提法,此準則也早已達成共識。近年來,因為作曲家強烈的共識,以及各省級民族樂團的崛起,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反映本土文化特征的作品占絕大多數。因此,問題不在于是否要立足本土,而是如何更好地立足本土。我們一再呼吁作曲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底怎樣才叫“深”,如何才算“扎”?是不是應該像人類學者那樣,研究某一文化事項,至少在自己研究對象的所在地住上一年的時間?當然,如果作曲家和創作者也能夠做到自然是好事,但恐怕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大部分人拋開一切職務的、生活的、工作的瑣事,離群索居、心無旁騖地在創作對象所在地住上一年。那么,我們不妨從這些較為成功的作品中汲取些許經驗。“局內人”的創作立場,是一種絕對的優勢,這一現象自不待言。如廈門的《土樓回響》、廣東的《絲路粵韻》、吉林的《高粱紅了》、山東的《大道天籟》、北京的《中軸》,細數下來,這些創作主體都在做“局內”的事,或者直接點說,在做“家鄉”的事。人類學對于這一現象叫“家門口的田野”,移植到作曲家身上,暫且稱其為“家門口的創作”。這些“家門口”的作品確有深意,以《高粱紅了》為例,筆者認為,按照“四季”結構整場音樂會顯然是基于作曲者王丹紅對東北文化的深刻理解,因為那是她的家鄉,充分利用家鄉資源,而無須額外住上一年,這是作曲家寫作家鄉題材作品的最大優勢,許多本土作曲家對于地方民間素材的運用都較為自如,對于民間素材沒有貼標簽式的移植改編,而是恰到好處地融入作品,用真實的民族器樂語言表達這一地域的文化,而非抽離出來的旋律和曲調,不是拼貼,而是將所選擇的民間素材中的核心材料,打造成為具有邏輯意義的結構力的作品,讓人聽來既熟悉又新鮮,充滿了期待。如果說,諸如《高粱紅了》這樣的作品是因為創作者家鄉的“內力”,是局內人的立場,那么,《永遠的山丹丹》(圖4)則可以看作是借助了音樂學者的“外力”,是局外人融入其中的典范。曲作者王丹紅在談及創作過程時說:“在《永遠的山丹丹》這臺音樂會寫作之初,所有采風的路線包括看哪些東西、怎么看,都是喬(建中)老師親自安排的。”確實,作品無論是整體結構安排還是某些陜北素材的運用都非常精彩,其中的《祈雨調》《刮大風》《朝天歌》實非一個局外人對陜北音樂僅僅是信天游這樣的想象就可以得來的,這一感受在此后喬建中關于該音樂會的深度樂評中亦得以驗證[9]。因此,在筆者看來,這一“借力”的方法可以作為作曲者“采風”的一個重要路徑:一位作曲家在寫作一部作品的時候,最好能夠尋求到一位音樂學家或者對當地民俗和文化特別了解的學者作為向導,這樣的結合,一定會比蜻蜓點水式的采風能更迅速地進入角色和切入要害,繼而創作出高質量的作品。
四、結語
以上論述,僅從三個側面反映了近年來民族管弦樂創作領域的三種現象,也是民族管弦樂創作的三種趨勢,這三種趨勢為民族管弦樂的發展注入了不可低估的推動力,也引發了業界的多維思考。但從很多角度來看,民族管弦樂仍然是小眾,民族管弦樂的發展,仍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呵護,也需要創作、演奏、評論等多個領域、多個層面的共同努力。對待每一部新創的作品,創作者需要以開闊的胸襟來真正思考和取舍,應有海納百川、止于至善的精神;演奏者須融入其中,真正理解作品的創作意圖及其背后的文化,并在二度創作鏈上精彩轉譯;評論者更應肩負責任與擔當,既不輕率否定,亦不絕對肯定,理解當下,也指示出未來可做可為的道路。
作者:楊雯 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