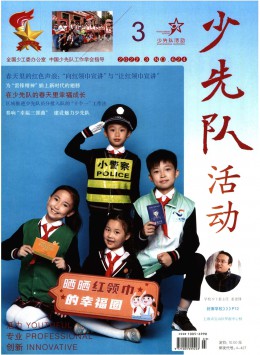活動雕塑的美感根源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活動雕塑的美感根源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地球上的物體無不受重力影響,重力的方向總是豎直向下。活動雕塑在風中輕盈舞動可以看作是雕塑與地心引力之間的對抗,但這不是一個互相征服的過程,而是一個互相依托存在的方式。活動雕塑與重力需要建立一個平衡,才能將彼此間的爭奪、糾葛翻譯成活動雕塑運動的美感。藝術(shù)家善用“杠桿原理”可以將作用在雕塑上的重力加以利用。為了使雕塑中杠桿平衡,作用在杠桿上的兩個力矩(力與力臂的乘積)大小必須相等[1],即:動力×動力臂=阻力×阻力臂。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Calder)的作品即基于此原理,使得只要一點細微的外力打破雕塑的平衡,雕塑就會產(chǎn)生相互牽連、變幻莫測的運動美感。活動雕塑中,杠桿被巧妙地替換為聯(lián)結(jié)單元金屬葉片的枝桿,以枝桿和金屬葉片為單元的組合可以被不斷地復(fù)制,只要符合杠桿實際運用的公理——一個重物的作用可以用幾個均勻分布的重物的作用來代替,只要重心的位置保持不變。相反,幾個均勻分布的重物可以用一個懸掛在它們的重心處的重物來代替。考爾德雕塑的絕妙之處在于杠桿原理的藝術(shù)化處理,使得藝術(shù)家對重力的利用顯得不鑿斧痕,只需靈活地改動葉片的造型和杠桿的曲線就可達到杠桿的平衡。通過對鐘擺的研究,同時代的雕塑家喬治•里基(GeorgeRickey)在利用重力制作活動雕塑的道路上找到一條切實可行而又特立獨行的路徑。想要利用重力與風力共同作用而形成雕塑的擺動,需要借助復(fù)擺的原理。復(fù)擺是一鋼體圍繞固定的水平軸在重力的作用下作微小擺動的動力運動體系,又稱物理擺。喬治•里基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利用了重量與距離的平衡配置而制作成簡單的鐘擺型雕塑。在他的早期創(chuàng)作中,對軸的改造使得擺動的方向更加多向而外力作用使得雕塑中活動的部分可以干涉雕塑的平衡,增加動態(tài)的多樣性。在喬治•里基早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一瞥其對鐘擺型雕塑擺動的多變追求,但因擺動的角度受到了限制,動態(tài)無法突破固定的程度,后期的作品在復(fù)擺的基礎(chǔ)上吸納了雙擺的原理,多個軸承被納入其動態(tài)雕塑中,動作的軌跡更趨向混沌。雙擺即軸互相平行,一個擺的支點裝在另一擺的下部所形成的組合物體。雙擺有兩個擺角,所以有兩個自由度。雙擺是多自由度振動系統(tǒng)的最簡單的力學模型之一。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喬治•里基的代表作品《破碎柱》來近一步理解藝術(shù)家如何借助雙擺原理實現(xiàn)活動雕塑“反重力”般的運動。《破碎柱》中的三個立方體分別被三個軸承聯(lián)結(jié),可以被看做是三個擺。因為藝術(shù)家的小把戲,我們并不能直觀地辨認出其中的雙擺原理。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其中的物理原理,我們將圖4旋轉(zhuǎn)180°,形成一個顛倒的圖像。原本雕塑頂端的兩個擺與原本雕塑底端的擺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擺的支點裝在另一擺的下部所形成的組合物體,也就是雙擺。原本雕塑底端的擺的重量需要略重并幾乎達到平衡頂端兩個擺的重量配置,原本雕塑頂端的兩個擺則是運用復(fù)擺原理達到平衡。如藝術(shù)家解釋的那樣,只要軸承兩邊距離與質(zhì)量的乘積相同,就可以達到旋轉(zhuǎn)的瞬間,如豎著的蹺蹺板一般。但實際上,喬治•里基的雕塑在精準的計算之余是可以容許部分“誤差”存在的,因為軸承接近地面的一邊質(zhì)量與距離的乘積需要略微大于另一頭質(zhì)量與距離的乘積,這也就使得喬治•里基的雕塑可以在表面打造手工的痕跡而無須絕對理性的工業(yè)化生產(chǎn)[2]。對藝術(shù)的感受確實來自藝術(shù)家天生的、與眾不同的天賦,但活動雕塑又與一般的雕塑稍顯不同,純粹利用美感的區(qū)別很難達到個人化的彰顯,因為活動雕塑的美感除了造型本身的美感,還介入了可以被肉眼觀察到的時空感受。一切寓于動態(tài)的變換之中。考爾德與喬治•里基同樣運用了平衡的原理,同樣借助了風與引力的動力來源,卻因運用了不相同的物理學原理,而造成了不一樣的作品面貌,產(chǎn)生了不同的藝術(shù)視覺魅力。
二、活動雕塑基于編排的次序美
當活動雕塑經(jīng)過一種嚴密邏輯的編排,它將會因數(shù)量、結(jié)構(gòu)等規(guī)律性的呈現(xiàn)而形成一種次序美感。從中,我們可以看作是通過嚴密的計算而使運動狀態(tài)次序化。通過抽象化和邏輯推理,由計數(shù)、計算、量度和對物體形狀及運動的觀察,將自己的靈感邏輯化和數(shù)據(jù)化,使得活動雕塑最終從具體形式達到抽象美感。藝術(shù)家伊凡•布萊克(Ivanblack)的作品結(jié)合了斐波那契數(shù)學原理的造型應(yīng)用以達到次序化的美感。在數(shù)學上,斐波那契數(shù)列以如下被以遞歸的方法定義:F0=0,F(xiàn)1=1,F(xiàn)n=Fn-1+Fn-2(n>=2,n∈N*),用文字來說,就是斐波那契數(shù)列由0和1開始,之后的斐波那契數(shù)列系數(shù)就由之前的兩數(shù)相加。通過斐波那契數(shù)列可以產(chǎn)生黃金比例、黃金矩形、黃金螺線等。藝術(shù)家伊凡•布萊克消化了這種遞增關(guān)系,作品呈現(xiàn)出經(jīng)過設(shè)計的極簡造型。通過這個設(shè)計,只需給予雕塑一個初始的作用力,雕塑中的一邊每一個單體獲得相同大小的速度,因此會以同樣的角度甩出而形成黃金螺線,螺線的臂距以幾何級數(shù)遞增。由于慣性作用,雕塑中反向力作用的運動形態(tài)也會反映在雕塑上,基于黃金螺線而形成的一系列運動變換被秩序的波動體現(xiàn)出來。同樣利用了斐波那契數(shù)列,藝術(shù)家約翰•艾德瑪克(Johnedmark)基于其數(shù)學原理進行次序的編排以展開藝術(shù)創(chuàng)作,他運用的這組數(shù)列其實就隱藏在許多自然形態(tài)之中,包括松果、鳳梨、羅馬花椰菜的排列,每片葉子中軸線連接至中心與前一片葉子中軸線連接至中心的間隔角度都幾乎是137.5°,稱為黃金角(基于黃金比例)。當黃金角度被自然界用作生長策略時,螺旋形圖案因此形成。螺旋的數(shù)量也總是斐波納契數(shù)。藝術(shù)家最經(jīng)典的作品《綻放》正是利用了斐波那契數(shù)列制作螺旋,仿照自然界中的某種植物形態(tài)提煉出一種具有生長趨勢可能的造型。基于數(shù)列設(shè)計的植物通過以550RPM的速度旋轉(zhuǎn),并以非常快的快門速度(1/4000秒),以每秒24幀的速度進行錄像。旋轉(zhuǎn)速度與攝像機的幀速率小心地同步,以便每當植物轉(zhuǎn)動至137.5°(黃金角度)時捕獲一幀視頻,最后通過視頻呈現(xiàn)出雕塑在旋轉(zhuǎn)中如自然中植物綻放的視覺效果。[3]還有一個探尋活動雕塑次序美的藝術(shù)家羅本•馬格林(ReubenMargolin),其活動雕塑的基礎(chǔ)是。“波”,實際上是利用了三角函數(shù)中的正弦曲線,通過對函數(shù)與圓周運動的研究,他找到了一種美的表現(xiàn)。羅本•馬格林活動雕塑的主體“波”與控制波動的圓盤,可以轉(zhuǎn)譯為三角函數(shù)線與三角函數(shù)圖像的關(guān)系。通過改變正弦曲線的函數(shù)y=Asin(ωx+φ)+k中的系數(shù)可以調(diào)整其直角坐標系上的圖象,以計算并調(diào)整影響雕塑波動的位移、周期、幅度。當藝術(shù)家計算出牽動“波”所需的線的長度后便可以將“波”的經(jīng)緯交錯聯(lián)結(jié),形成一個次序化波動的大網(wǎng)。藝術(shù)家可以根據(jù)函數(shù),在雕塑“波”中再加入不同幅度的“波”,形成更加復(fù)雜而迷人的次序美感。當活動雕塑被轉(zhuǎn)換為“數(shù)”,其美感則會從藝術(shù)家個人化的體驗轉(zhuǎn)換為一般化的操作,這是為了經(jīng)過“簡單化”和“一般化”將美轉(zhuǎn)換為規(guī)律和狀態(tài),而使自身的表達更加純粹、有力和直接。想要突顯藝術(shù)家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靈性,則次序是一種公理而將它編排是藝術(shù)家才華的施展之處,通過安排事物的序列、方式、方法,藝術(shù)家通過提煉和抽象,編排了作品的次序。次序美實際上就是自然中便普遍存在的精心設(shè)計的美。當藝術(shù)家真正深切體會并可以自由轉(zhuǎn)換數(shù)理所帶來的次序美感,則藝術(shù)家便可以真正展示被美襯托的真理。
三、活動雕塑基于視覺的錯覺美
人的視覺有時會因經(jīng)驗主義或者干擾的參照物而產(chǎn)生錯誤的判斷和感知,有一部分活動雕塑利用了視覺暫留現(xiàn)象,將錯覺美的體驗作為藝術(shù)家追求的動態(tài)呈現(xiàn)的結(jié)果。視覺暫留現(xiàn)象又稱“余暉效應(yīng)”,人眼在觀察景物時,光信號傳入大腦神經(jīng),需經(jīng)過一段短暫的時間,光的作用結(jié)束后,視覺形象并不立即消失,這種殘留的視覺稱“后像”,視覺的這一現(xiàn)象則被稱為“視覺暫留”。運用視覺暫留的原理,靜態(tài)畫面通過快速連續(xù)的翻頁更替可以產(chǎn)生運動的錯覺,費納奇鏡、西洋鏡由此而來。胡安•豐塔尼夫(JuanFontanive)的一系列作品利用了這種視覺原理,將時鐘部件加以改造,成為了驅(qū)動動畫播放的裝置,機械上配以收集來的鳥類插畫,當紙頁仿照鳥類翅膀拍打的速度翻動,畫面中按照飛行順序排放的插畫鳥也就撲閃著翅膀,鳥類動畫和運行的裝置因這簡單的動畫原理共同獲得了生命。空間中立體的作品也可以利用視覺暫留的原理,作品在連續(xù)的旋轉(zhuǎn)中可以達到流動、延續(xù)等等效果,田中武(TakeshiMurata)的作品正是這樣一個3D版的西洋鏡。作品在旋轉(zhuǎn)時,借由頻閃燈的輔助,通過特殊控制的照明創(chuàng)造了運動的幻覺,看起來好像在不斷融化自身,因此也有人稱之為動畫雕塑。另一位利用視覺暫留現(xiàn)象的藝術(shù)家后藤映則(AkinoriGoto)在作品《Toki》中將可以產(chǎn)生連貫、具體運動軌跡的每一幀人形圖像形成一個閉合的圈,當這個圈快速旋轉(zhuǎn)以播放畫面時,每一幀在固定的位置亮起LED燈,分解的圖像內(nèi)容就會在LED燈的“捕捉”下呈現(xiàn)出完整、連貫的動畫效果。活動雕塑與循環(huán)動作的影像之間有可以互相轉(zhuǎn)換的部分,即是通過連續(xù)的動態(tài)而形成一個狀態(tài)以達成轉(zhuǎn)譯的目的,以此作為活動雕塑的原理。藝術(shù)家掌握的是作品可以被欣賞的不一樣的角度——控制了呈現(xiàn)方式,這種控制為雕塑的運動提供了更多的想象與可能。活動雕塑的制作早已不再以令它動起來為唯一的追求,隨著活動雕塑的發(fā)展,雕塑與觀者有了更深、更多樣的互動。實際上,活動雕塑侵占了觀者更多的物理空間,而藝術(shù)家也在尋求可以令觀者與作品之間有更特殊聯(lián)系的可能。
四、活動雕塑在鄉(xiāng)村公共空間的運用延伸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推進公共藝術(shù)建設(shè)以來,公共藝術(shù)多在城市駐足,相關(guān)的研究和實踐基本上都是以城市為中心。但是,對于鄉(xiāng)村的介入幾乎沒有,更缺少一種很好地結(jié)合鄉(xiāng)村景觀和審美定位的公共藝術(shù)形式。針對此現(xiàn)狀本課題小組展開了對活動雕塑介入鄉(xiāng)村的研究。在活動雕塑領(lǐng)域,存在既考慮鄉(xiāng)村本源的記憶又照顧雕塑本身詩意的作品先例。通過對這類藝術(shù)案例的分析,結(jié)合對活動雕塑美學原理的研究,我們試圖將活動雕塑引入鄉(xiāng)村公共空間,以推進美麗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喚醒鄉(xiāng)村長期以來形成的、特有的人文生態(tài)和自然鄉(xiāng)土記憶。因此,既要對活動雕塑的造型原理進行提取,并找到制作活動雕塑的理性、科學的途徑,同時又要與鄉(xiāng)村的自然環(huán)境、公共空間及人文背景相得益彰。比如,在作品《清泉》中,我們試將基于斐波那契數(shù)列的黃金螺旋作為創(chuàng)作的初始要素。作品模擬植物生長規(guī)律以每137.5度“生長”一條曲線,將曲線緊貼在噴涌而出的泉水所形成的美妙曲面上,讓它的線條在旋轉(zhuǎn)時產(chǎn)生不斷涌出的視覺效果。此外,我們改變了曲線一端中一小截線段的扭曲程度,設(shè)計為兜風的葉片以帶動雕塑旋轉(zhuǎn)。通過對顏色的規(guī)劃可以加強運動時旋轉(zhuǎn)升騰的視覺感受,形態(tài)上無差別的曲線單元在風力作用下旋轉(zhuǎn),由不同顏色組成的曲線的區(qū)塊在不斷遮擋和涌現(xiàn),復(fù)制的單元組則有可能達成復(fù)合的動態(tài)的視覺呈現(xiàn),簡單的圓周運動也可以表現(xiàn)更加復(fù)雜的動感。另一件作品《風帆》是我們基于視錯覺對活動雕塑所做的嘗試,對行駛中船上的船槳的動態(tài)進行動作拆解,通過閉合的圓周排列,船槳因不同的傾斜度可以構(gòu)成正視呈波浪狀的空心圓環(huán)。圓環(huán)的中心設(shè)計了船帆以兜風力,在風力驅(qū)使下,圓環(huán)因規(guī)律的波動將產(chǎn)生美妙的韻律,同時拆解成不同幀的運動中的船槳,在自然動力下又會形成一個連續(xù)播放的動畫,像是童年的翻書動畫,只是風的無休無止使得小船的前行變得永無止境、循環(huán)往復(fù),理想中的小船得以在水面永遠航行。事實上,我國鄉(xiāng)村存在支持活動雕塑發(fā)展的、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及人文基礎(chǔ)。為了讓鄉(xiāng)村中公共藝術(shù)不再需要依托城市發(fā)展而獨立存在,在鄉(xiāng)村背景下的公共藝術(shù)應(yīng)結(jié)合鄉(xiāng)村景觀和審美品位。同時,應(yīng)試圖將活動雕塑的造型審美探索與特定的實用功能相結(jié)合,尤其是將活動雕塑裝置與鄉(xiāng)村水凈化系統(tǒng)進行結(jié)合。在作品《清泉》和《風帆》中,我們都設(shè)計了獨特的水凈化裝置。其原理是,將風力產(chǎn)生的后續(xù)效益隱藏在水下,以中軸連接水上活動雕塑與水下裝置,通過活動雕塑旋轉(zhuǎn)產(chǎn)生風力,風力發(fā)電為氣泵提供電力,再通過氣泵將空氣送入水下?lián)P水桶,使揚水桶中產(chǎn)生周期性的富含空氣的水對流,對活性炭中貯存的活性菌帶來氧氣以保持它們的活性,以活性菌生態(tài)凈水。如此,除了滿足最基礎(chǔ)的凈水功能,更進一步的是將鄉(xiāng)村公共藝術(shù)建設(shè)通過一種“直接美化”與“間接優(yōu)化”并行的方式,即是一種“美化環(huán)境”和“優(yōu)化水源”的方式,達成一種循序漸進的美的熏陶和美的完善。面對城市高度現(xiàn)代化的狀態(tài),如何讓人們停下腳步感受并喚醒那種來自鄉(xiāng)村“本源”的感動和記憶。活動雕塑無論在造型,還是動力系統(tǒng)上都與自然關(guān)系密切。因此,活動雕塑之美可以擁有更廣闊的土壤,通過公共藝術(shù)與鄉(xiāng)村地景結(jié)合,以推進美麗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蘊含遠古詩意的廣闊空間將會被重新尋得,作為一種根源的感動滋養(yǎng)城市和鄉(xiāng)村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
作者:陳漢 劉泠杉 單位:中國美術(sh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