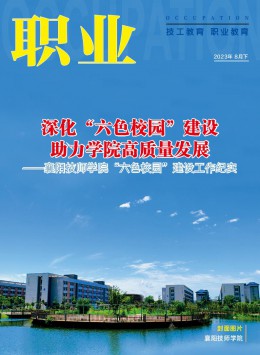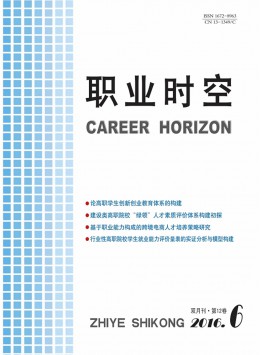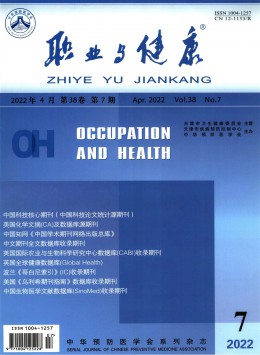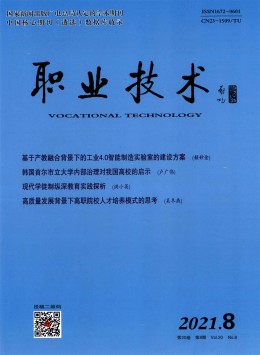職業會計教育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職業會計教育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培養全面人才、緊跟社會經濟發展
潘序倫先生以會計為終生職業,但他并不局限于狹義的“會計”。其在美國哈佛大學主修會計專業,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則攻讀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并學習一些會計課程,這一學習、研究經歷,不僅擴展、完善了潘序倫先生的知識結構,也進一步培養、提高了其學術研究素養。他認為,會計人員不僅要精通會計業務,而且還要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心理學等知識。他指出,在會計學研究時,不僅要有豐富的會計實務知識,“對于和會計學有關系的學問,如理論經濟學、經營經濟學、法律、金融、財政等等也應有深湛的修養。只有有了這些根基之后,才能明白會計學發展的原因和趨勢,才能對于一切大的或小的會計問題有解答的可能”。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全面發展的合格人才。同時潘序倫先生認為,會計學是“科學中的社會科學”,所以它必須與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保持步調一致,不僅會計實務要隨社會法律時時變遷,而且會計理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習會計者,應抱‘日日新又日新’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緊跟時代步伐,適應社會需要。如潘序倫先生所編著的《商業簿記教科書》、《公司會計》等教科書之多次改訂就是為了適應民國政府相關法令的變更。1980年代,潘序倫先生已經年屆87歲高齡,針對一些基層工廠、商店,尤其農村社隊和集體企業會計人員隊伍不穩定、專業性不強、水平不高的現狀,他指出必須提高業務技術,虛心學習“過去沒有過的……如利潤、成本目標管理、價值分析、電子計算技術等”。不僅如此,潘序倫先生對于新技術在會計學的應用、及會計的現代化也是非常關注。同樣在1980年代,潘序倫先生嚴肅地指出“會計是一門應用科學,沒有現代化的科學知識是不行的”,他敏銳地認識到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將可能對會計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因此“不應忽略通信新技術的學習”。當時“電子計算技術已應用到算賬記賬上來”,潘序倫先生認為“隨著電腦時代的到來,會計工作是否要來一個徹底的變革?……,以后是否可以用電腦代替人工”,現在許多會計業務都已經通過由電腦代替人工操作、盡管人工勞動不可完全被替代,但在三十年前就能提出“會計工作是否能完全用電腦來處理”這樣大膽的設想非常難能可貴的。
二、職業道德教育、誠信為本
潘序倫先生認為,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會計工作能不能做好,也是提高會計人員政治和技術素質、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之一。認為會計職業道德方面應有的修養,首當其沖的是“守信”。1927年1月,潘序倫先生開設“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次年取“民無信不立”之意更名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后來創辦的的以編輯發行會計圖書、會計賬冊為主要業務的會計圖書用品社也以“立信”命名,以“立信”冠名的各類學校更是培養出了大量會計人才,遍布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關于“信”在會計事業中的重要性,潘序倫先生曾于1940年進行過論述,“信為吾人立身之要件,尤為吾會計從業人員之要件,設稍于信字有虧,則不僅本人名裂,亦將貽害社會。故凡會計員必先養成其會計的人格,所謂會計的人格,即可以信之一字概括之。”“立信”不僅是潘序倫先生會計事業的“字號”或“商號”,更是終生堅守的教育理念。潘序倫先生在發展立信會計事業的過程中,更是形成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處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當必有成”的立信會計學校24字校訓,涵義豐富,沿用至今,成為立信辦學的最大特色。潘序倫先生不僅提倡從事財會工作者應當做老實人,辦老實事,講老實話,始終堅持真理, 實事求是的精神。對自己也是如此要求,他在1980年代回顧自己職業生涯時說,自己“過去是為個人的‘立信事業’而奮斗,現在則要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應該做到“忠誠老實,毋忘立信”。而這一原則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不僅沒有過時之感,反而顯得尤為珍貴。
三、人才培養,必須關注教育成本
潘序倫先生在會計教育領域的另一重要思想貢獻就是提出了學校培養人才的成本概念問題。早在1934年,潘序倫先生就提出了學校成本的觀點,他在浙江省教育廳附屬機關會計人員講習所進行演講時指出,學校雖然屬于非營業牟利機構,但也有必要計算成本,“學校里工作的效能,究竟怎樣?總也應該明白了解”。同時,他還認為,“學校對成本會計的需要,實在與營業機關對于成本會計的需要是差不多的。”在演講中,潘序倫先生不僅闡述了學校成本會計的意義和功用、討論了學校是否需要成本會計等問題,還以立信會計學校經驗詳細論述了學校成本會計的計算方法等實際操作問題,因此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演講稿雖然主要論述大學成本,但其中的做法稍加修改,即可用于中小學的成本核算,因此還具有很廣的適用性。演講稿除在期刊發表外,還以《學校成本會計》為名編入1935年5月出版的《各業會計制度》第二集。這些會計制度由各行業富有會計工作實踐經驗者編撰,以各行業中實行的制度為藍本,結合學理和撰寫人的個人體會而擬訂,雖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但在客觀上促進了同一行業間會計核算和成本計算的規范化,為工商各業采用新式會計制度創造條件;不僅可作為各大學商科各業會計制度課程的教材,對于相關行業的會計人員理解會計學原理及實施也具有參考價值。潘序倫先生關于學校成本會計的研究,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從會計學看,潘序倫先生以其辦學實踐經驗拓展了成本會計的應用領域、豐富了會計理論,其中的操作方法并不限于會計教育領域,而是適用于各級各類學校,甚至可以推廣至其它事業單位;二是從教育領域看,有了考核學校投入與產出的理論依據和操作辦法,有利于促進教育經費的合理、有效使用,加強成本核算、節約辦學成本、提高辦學功效。除了學校經營成本的考量外,潘序倫先生還較早地提出了“人才的培養成本計算和效益問題”。一些發達國家比較早地就開始重視人才價值研究,在美國,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開始就是“人才會計” 的思想,其他西方國家也有仿效應用的趨勢,根據國家、企業、事業的實際需要來培養人才。而我國從1949年建國直到1980年代初,對于人才的培養和使用還是粗放型的“大鍋飯”公費制,基本上是采取“包下來”的辦法,由國家負擔大學生就業期間的所有費用,不作經濟核算,對于學生畢業后是否能夠學以致用、學有所用、能為國家社會賺回多少利潤、做出多少貢獻,則少有考慮、研究,更沒有精密的成本計算。潘序倫先生認為,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模式難以為繼。盡管基礎理論科學的研究,很難用眼前的貨幣計算來衡量。但國家的長遠投資規劃,也必須估計到國家對于這些事業的投資。這種投資究竟對國家的長遠利潤有多少價值,總應當切實估計一下,以避免浪費,增加效果。因此,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秉著“洋為中用”的原則和方法,用貨幣形式來計算國家或某一企業、某項事業對于培訓各種所需要的人才所支出的費用(投資) 金額,并計算被培訓成材的人,是否能為國家、為某一企業、為某項事業獲得若干成果(或稱利益),假使所獲成果利益超過培訓他們的投資,就是國家、某一企業,某項事業的純收益;否則就是純損失。事實上,潘序倫先生關于人才成本的考慮并非紙上談兵,而是其畢生辦學經驗的總結。實踐表明,自費生的成績不見得比公費生差,有的在職青年由組織支出培訓經費, 其中自有少數學生認為讀書并無經濟上的損失,往往不甚注重學習,這實在是種浪費,對培養人才不利。他建議有關部門重視“人才會計”的研究,運用會計手段促進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以使人盡其才。這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時,潘序倫先生還提出了“人才會計”的試行處理辦法,以供我國關心教育培訓人才的人士參考。后來立信舉辦走讀、收費、不包分配的培訓模式,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意義非凡。現在不僅被各類成人教育、繼續教育、遠程教育所采用,收費、不包分配也已經成為全日制高等教育的普遍模式。潘序倫先生已經逝世20多年,距其初創立信會計事業已有80年之多,但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仍然并不過時,對于現在的會計教育、職業教育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值得教育從業者深思。
作者:李湖生 單位: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