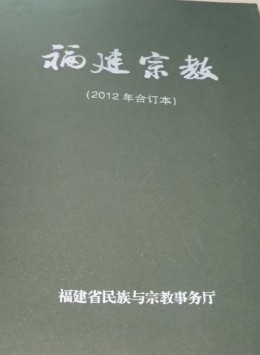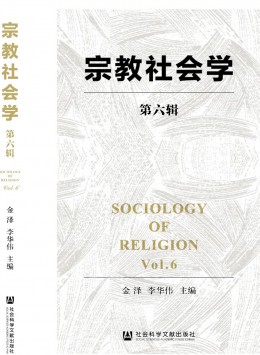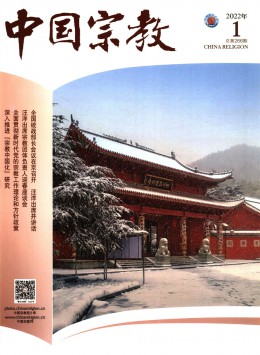宗教與教育的基本關系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宗教與教育的基本關系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宗教的論述
關于宗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一生當中有過諸多論述。主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宗教屬于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
在階級社會,被統治階級處于社會的最底層,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同時他們又對自己受剝削受壓迫的境遇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把自己的不幸歸結于上天和命運的安排,喜歡和習慣于在虛幻的宗教世界里尋求安慰和解脫,找尋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依托。正如列寧所說:“在各階級中必然有一些人,他們既然對物質上的解放感到絕望,就去追尋精神上的解放來代替,就去追尋思想上的安慰,以擺脫完全的絕望處境。”[2]正是由于被剝削階級沒有力量也沒有辦法同剝削階級對抗和斗爭,“必然會產生對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蠻人由于沒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產生對上帝、魔鬼、奇跡等的信仰一樣。”[3]
(二)宗教屬于上層建筑,它決定和服務于一定的經濟基礎
宗教是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和生產關系的狹隘性造成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宗教不是用“自我意識”等概念能解釋清楚的,“而是應該用一向存在的生產和交往的方式來解釋的。這種生產和交往的方式也是不以純粹概念為轉移的。”[4](P170)宗教作為上層建筑,它的現實基礎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發生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基礎。所以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5](P82)恩格斯在繼承馬克思上述思想論斷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明確指出:“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系和國家關系,一切宗教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伸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5](P117)這是因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便構成為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制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過去那樣做得相反”[4](P574)。
(三)宗教在階級社會里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
在階級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不但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掌握著國家的上層建筑,并且把上層建筑作為蒙蔽、愚弄、奴役和控制民眾的主要工具,因此,宗教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對此,馬克思曾經一針見血地說過:“基督教的社會原則曾為古奴隸制進行過辯護。也曾把中世紀的農奴制吹得天花亂墜,必要的時候,雖然裝出幾分憐憫的表情,也還可以為無產階級遭受壓迫進行辯解。基督教的社會原則宣揚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存在的必要性。他們對被壓迫階級只有一個虔誠的愿望,希望他們能得到統治階級的恩典。”[6]恩格斯也同樣批判了統治階級把宗教當作維護政權的愚民手段。他認為統治階級,特別是英國的資產階級,“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響群眾的精神手段中第一個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學校董事會中就讓牧師占優勢;于是,資產階級日益增加自我捐稅,以維持各種基督復活派,從崇禮派直到‘救世軍’。”[4](P393-394)
(四)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確有效處理與宗教有關問題的關鍵
由于宗教的產生根源、存在條件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宗教賴以生存的條件又不可能很快消除,所以使得宗教將長期存在。在此認識基礎上,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處理好宗教問題。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指出:“人權并沒有使人擺脫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的自由。”[7](P145)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也再次強調:“信仰自由!如果現在進行文化斗爭的時候,要想提醒自由主義者記住他們的口號,那么,只有采取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能做到這一點:每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一樣,不受警察干涉。”[8]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確有效處理好一切與宗教有關問題的關鍵。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教育的論述
恩格斯在描述早期中世紀歐洲的文化特征時曾說:“中世紀是由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它從沒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來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結果正如一切原始發展階段的情形一樣,僧侶們獲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的性質。”[9]從恩格斯這段精辟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紀的西歐,基督教對中世紀教育產生了全面的和決定性的影響,整個中世紀的教育發展是在基督教教會的控制下發展的。由于神學在中世紀歐洲的教育中占據統治地位,因而那個時代的教育基本上都被束縛在經院神學的范圍內。到了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新興資產階級已逐漸認識到教育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和政治斗爭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教育規律的認識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因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教育新理論。與此同時,這一時期教育活動的范圍、質量、實際效果等各方面也都大大超越了中世紀。但是,這時的教育還僅僅處于資產階級新教育的萌芽階段,封建的、教會的教育還有著相當大的實力與影響。中世紀以及早期資本主義歐洲的教育,始終與宗教和教會緊密相關,它充滿了神性,也脫離不了濃厚的宗教神學色彩,教育總是在為宗教、教會和統治階級服務。在綜合考察了中世紀以及早期資本主義歐洲的教育狀況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教育是人類社會特有的培育人的活動,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表明,一定社會的教育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并且服務于這個經濟基礎以及建立在該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
(一)教育伴隨著人類的出現而出現,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
原始社會,由于人類社會的整體生產力水平低下,教育并沒有成為獨立的體系,還融合和體現在人類的生產和生活之中。這個時期的教育略顯單純,其主要目的是傳授生產和生活經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維系族群的延續,教育對每個成員是公平的,人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獲取教育。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教育的功能也隨之變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在精神上奴役民眾的工具。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育和受教育的權利全部屬于統治階級,教育成為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在這一歷史時期,面向公眾的大眾教育很少,僅有的為數不多的大眾教育,也只是統治階級為了麻痹和蒙蔽民眾的需要而進行的功利化教育。
(二)教育服務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批判資產階級的教育時,指出:“……而你們的教育不也是由社會決定的嗎?不也是由社會通過學校等等進行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干涉決定的嗎?”[1](P268-269)原始社會時期,教育沒有階級性。階級社會里,教育總是服務于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在資本主義社會,教育被牢牢控制在資產階級手中,他們一方面在本階級內部強化意識形態教育,培養更多合格的、優秀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借助國家政權,通過控制和主導教會學校和世俗學校的教育,對被統治階級進行愚化教育,麻痹被統治階級,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思想,使被統治階級能夠安于現狀,寄托未來,缺乏反抗和斗志。資產階級認為:“工人受教育,對資產階級的好處少,但可怕的地方卻很多。”[7](P396)所以,被統治階級,特別是工人階級受教育的機會少,即使有,也接受的只是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他們無權選擇教育內容;同時,教師素質十分低下,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因為“資產階級所關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碼生活”[7](P395),而不是他們的教育、成長和發展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宗教與教育基本關系的論述
在考察和批判了當時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教育狀況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參與法國巴黎公社的社會革命實踐活動中提出:在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與國家相分離,宗教與世俗事務相分離的前提下,宗教與教育相分離。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宗教與教育基本關系的現實背景
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初等教育主要是為勞動人民的子女設立的,但是教育的領導權和主導權主要控制在教會手中。宗教改革后,英國國教教會在國內獨據一方,排斥異己。為了與國教教會相抗衡,愛爾蘭的農民創辦了籬笆學校,這些學校由于是農民自己創辦的,體現著農民自身的意志,反映著農民自身的訴求,因而世俗的教育內容比較多。為此,它也得到了恩格斯的贊賞。恩格斯說:“這些真正的學校并不符合英國人的目的,為了消滅它們就創辦了一些假國民學校,在這些學校里世俗的東西少到什么程度,從下面的事實中可看出:課本中所編選的都是從天主教和新教的圣經里摘出來的片段,而且經過都柏林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大主教認可,請那些直到今天仍然對義務上學叫嚷不已的英格蘭人同這些愛爾蘭的農民對照一下。”[10](P158-159)由此可見,當時教會對農村教育是控制得相當嚴的,嚴重地阻礙了教育的世俗化。和農村教育一樣,在十八世紀前半葉的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也同樣滲透著宗教神學的內容。1844-1845年前后,恩格斯深入研究了工業革命后英國工人階級及其子女的狀況。恩格斯寫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之間,1845年在萊比錫出版發行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記錄下了英國工人階級及其子女的悲慘處境,他們不但肉體受到摧殘,而且在教育上接受的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愚民教育。工業革命后,機器的推廣和使用,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使一部分勞動者從繁瑣的手工業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使工人淪為機器的附庸,失去自由,得不到教育的機會。雖然出于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資產階級也開辦了一些工廠學校、星期日學校等,但是諸如此類的學校數量還是很少,而且學校的設備簡陋、管理落后、師資水平差、教學水平低下。“教師都是些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合適的人,他們只是為了生活才來當教師,大多數連自己也沒有具備最必要的基本知識,缺乏教師所應當具備的道德品質,并且一點也受不到公眾的監督。”[7](P395)最為重要的是,教育仍然沒有擺脫宗教的束縛,尚未完全世俗化、科學化。資產階級和教會勢力一起控制了學校教育,對工人及其子女灌輸宗教神學思想,進行精神奴役。“在所有的英國學校里,道德教育總是和宗教教育聯系在一塊”[7](P399),結果“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無聊的一面(即對異教教義的辯駁)成了最主要的課程,孩子們的腦子里塞滿了不能理解的教條和各種神學上的奧妙的東西,從童年時期起就培養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熱的偏執,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發展卻被可恥地忽視了”[7](P396)。“國教教會成立了自己的國民學校,每一個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學校,而它們這樣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懷抱里,可能的話,還要從別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靈魂搶奪過來。”[7](P396)為了奴役勞動人民,資產階級不惜從小就給兒童進行神學教育,腐蝕他們的心靈,禁錮他們的頭腦。廣大工人階級對此極為不滿,并且不止一次要求議會廢除宗教對教育,尤其是對世俗教育的影響和控制,建立真正的世俗國民教育制度,但是英國議會沒有這樣做。教會也只有在保證工人及其子女接受了教義、忠于教派和資產階級時,才愿意和允許讓他們接受正常的世俗教育。因此,那些在學校里接受教育的工人階級的子女,會出現的結果是:“這些孩子們被人們用宗教教條硬灌了四五年,結果并沒有比原來多知道一點什么。”[7](P395)
(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宗教與教育基本關系
的初步提出由于資產階級和教會勾結在一起,狼狽為奸,對工人階級等勞苦大眾及其子女進行宗教愚民教育,使他們智力荒廢、精神麻木、愚昧無知。這種極端殘酷的教育制度,激發了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及教會的堅決反抗,激發了他們為實現國家與宗教、宗教與教育相分離而努力斗爭。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潮流,指導當時的社會革命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提出了宗教與教育關系問題上的基本原則:宗教與教育徹底分離。在1844年出版的《神圣家族》一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當國家擺脫了國教并且讓宗教在市民社會范圍內存在時,國家就從宗教下解放出來了,同樣,當單個的人已經不再把宗教當做自己的私事來對待時,他在政治上也就從宗教下解放出來了。”[7](P143)這段論述表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宗教與世俗事務關系上的基本觀點:第一,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應該只在特定的范圍內存在;第二,國家必須獨立于宗教,不干預宗教范圍內的事;第三,宗教與世俗事務,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相分離。這一時期,宗教與教育相分離的思想只是蘊含在宗教與世俗事務相分離的大前提下,尚未明確提出來。
(三)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宗教與教育基本關系
的具體提出和實踐運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宗教與教育相分離的觀點是在指導和參與法國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中具體提出并運用于革命實踐中的。席卷歐洲大陸的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后,作為歐洲意識形態中心的法國的教育世俗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學校由國家管理、為國家育人,教育與宗教開始分離,學校從愚昧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走上了科學化的道路,沉重打擊了教會。1789年法國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基本上完成了教會教育向國家教育的轉變,但是,波旁王朝復辟后,又把教育控制權交給了教會。反動政府的倒行逆施導致了法國各種矛盾的空前尖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法國出現了空前的政治、經濟、文化危機,導致了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革命,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
在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思想指導下,巴黎公社在奪取政權后,就立即摧毀了舊的教育制度,實行了一系列新的舉措,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贊賞。首先,公社頒布法令,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學校和教會分離,全部清除學校中的宗教教育。馬克思欣喜地說:“當然,公社沒有時間來改組國民學校(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權主義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開了一個端。”[11]其次,公社的首要任務是驅除僧侶勢力。中世紀是宗教的世紀,而法國恰好是當時歐洲大陸的意識形態中心,中世紀神學對國家、對教育的影響仍然很深刻,到巴黎公社革命時,天主教仍控制著教育。因此,公社必須徹底鏟除僧侶勢力。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記述了這個情景:“公社在廢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種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工具以后,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勢力,方法是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并剝奪一切教會所占有的財產。教士們應當重新過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們的前輩們那樣靠信徒的施舍過活。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干涉。這樣,不但學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成見和政府權利的桎梏。”[5](P375)實際上,公社的法令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直接參與下頒布的,其對待宗教與教育的關系的態度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一貫的主張。公社不僅廢除了舊的教育體制,而且要求在新的教育中,加強科學知識的教育,與宗教神學做斗爭,反對宗教愚昧,使無產階級及其子女免遭宗教的毒害。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放棄他們的排除宗教對教育影響的主張,而是多次強調了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如1875年,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馬克思再次指出:“應該把政府和教會對學校的任何影響都同樣排除掉。”[12](P277)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堅持和發展了他們共同提出的理論,一再強調:“教會和國家完全分離。……排除宗教團體對公立學校的一切影響。”[12](P277)宗教教會可以允許存在,也可以開辦自己的教會學校,宣傳自己的教義,但前提是不能影響國家開展的正常的世俗教育。
結語
總之,在階級社會里,宗教與教育是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奴役和控制被統治階級的兩種主要精神手段,宗教與教育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高度的政治性。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政權與宗教相互利用,關系密切。尤其是在中世紀和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歐洲,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當時歐洲社會的考察和研究,深刻認識到宗教與教育不分給社會尤其是給被統治階級及其子女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指明在新社會里,必須割斷宗教與教育之間的緊密聯系,徹底實行國家與宗教、宗教與教育相分離的政策。由于宗教仍將長期存在,因此,在它消亡之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必須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宗教成為個人思想上的事。實現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與國家、宗教與教育相分離,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宗教與教育關系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則。這一思想原則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有利于教育的獨立、良性、健康和科學發展,有利于國家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形成和完善。同時,也為當今世界宗教國家和多民族國家正確處理好國家與宗教、宗教與民族教育的關系提供了參考和借鑒。(本文作者:李小輝、羅春梅 單位:臨滄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