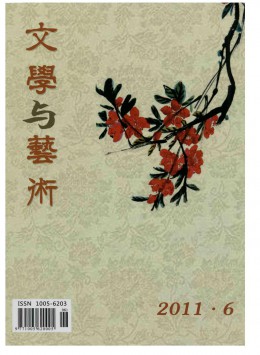文學(xué)信仰論文:沈從文小說的文化反思探討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文學(xué)信仰論文:沈從文小說的文化反思探討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蔡登秋 單位:三明學(xué)院中文系
當(dāng)大部分楚地的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被中原文化沖刷得蕩然無存的時候,湘西還是一塊相對純凈文化之地。所以,在這里楚文化存遺相對完整,并且一些原始文化元素一直延續(xù)到近現(xiàn)代。由于文化土壤的獨特性,作家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文化語境亦顯得自然獨特。歷史以來,這里孕育了許多卓有貢獻(xiàn)的作家,沈從文堪稱代表。沈從文在他的文學(xué)天地中開創(chuàng)性地拓開一個新的文學(xué)空間,即湘西世界的文學(xué)空間。五四啟蒙時期,在焦慮、危機、頹敗和失落等復(fù)雜的時代情緒沖突中,回歸和守望鄉(xiāng)土是沈從文那時的創(chuàng)作思想傾向。湘西是一塊孑遺著原始性狀巫楚文化的“圣土”,是沈從文離開此地后魂牽夢縈的情感寄托,這也正是他一再標(biāo)榜自己是“鄉(xiāng)下人”的原因之一。我們在閱讀沈從文作品的時候,不難發(fā)現(xiàn)文本所呈現(xiàn)出的湘西文化,大體有兩大內(nèi)容:其一是純潔中略帶著原始味的人情關(guān)系;其二是那種古樸略帶野性的地方習(xí)俗。這兩個方面的表達(dá)并行不悖,相互交織,共同構(gòu)成沈從文獨特的湘西文化世界。
沈從文文學(xué)作品中民間傳統(tǒng),主要是以湘西民間信仰中的鬼神信仰為主,而這些鬼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名目繁多,種類豐富。我們知道,巫楚文化有好善鬼神的特性,巫術(shù)的情結(jié)很重。《來鳳縣志•風(fēng)俗志》記載:“來鳳地僻山深,民雜夷獠,皆緣土司舊俗,習(xí)尚樸陋,史稱俗喜巫鬼,多淫祀,至今猶有存在。”來鳳縣今屬鄂西,與湘西交界,百姓與湘西相類,好鬼神民俗也是相同。古代長江以南的苗蠻之地,都有崇尚鬼神風(fēng)俗,就如宋代朱熹的《楚辭集注》卷二所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與湖湘地區(qū)同屬南方其他地區(qū),也有崇尚鬼神的習(xí)俗。如閩地也是多“尚巫信鬼,好淫祠”,唐代詩人劉禹錫所記載:“閩有負(fù)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與華語不通。”[2](P22)可見古代的南方的廣大地區(qū),人本文化出現(xiàn)相對較中原遲,鬼神信仰濃厚且延續(xù)時間長。當(dāng)中原已進(jìn)入較為自覺的人文時代,南方諸多地方還較處于神話時代。隨著中原文化的南漸,南方很多地方慢慢被中原文化所整合,而僻遠(yuǎn)的湘西地區(qū)保留了相對完好的巫楚文化,所以湘西的鬼神巫術(shù)信仰給人印象顯得神秘獨特,由此也顯示了湘西文化現(xiàn)象的獨特性。
沈從文青少年時期生活在湘西,湘西文化是他的文化經(jīng)驗根基,或者就是他的一種母語經(jīng)驗。在他潛意識中,作為文化內(nèi)核的民間信仰是他離開湘西后魂牽夢縈的情愫。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鬼神信仰的描述,究其原因,其實是文化母語經(jīng)驗不斷復(fù)現(xiàn)的結(jié)果,這也形成了沈從文文學(xué)世界獨特的文化景觀。
以豐富的民間信仰資源作為文學(xué)表現(xiàn)的重要對象
閱讀沈從文湘西題材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湘西文化有一種神秘感:這里民間信仰的豐富性和繁雜性,使湘西籠罩在濃厚鬼神氛圍中。湘西的土家族、苗族等民間信仰體系的復(fù)雜性和種類的多樣性,主要是源自于文化的原生性。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成長的沈從文,他文學(xué)中民間信仰譜系的多樣性和復(fù)雜性顯然在情理之中。
湘西民眾信仰大多處于一種自然的狀態(tài),有論者認(rèn)為這種信仰現(xiàn)象是一種自然拜物教,“由于苗族先民的自我,避讓和自主保存才換來了巫楚文化在一定范圍內(nèi)的長久流傳。巫楚文化作為自然拜物教文化的遺存,其特點在敬神、信巫、畏鬼。”[3](P178-179)其實他們信仰始終處于自然狀態(tài)之中,并非僅僅是一種拜物教。不僅如此,“在宗教儀式上,這個地方有很多特別處,宗教情緒(好鬼信巫的情緒)因社會環(huán)境特殊,熱烈專誠到不可想象。”[4](P397)苗族是一個多鬼神信仰的民族,祀奉鬼神的法事種類繁多,據(jù)了解這里的法事多達(dá)七十余種,主要功能就是用來“祭拜善鬼”、“驅(qū)除惡鬼”。這里的崇拜對象多得無法估量,與他們生活相關(guān)的事物,都有可能成為崇拜的神靈。如:天王神、土地神、山神、雷神、獵神、龍神、樹神、口舌神、飛山神、揭網(wǎng)神、簸箕茶神、樓公樓婆神等等。這些神靈大多是善神,與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社會習(xí)俗聯(lián)系緊密,往往是生產(chǎn)生活的護(hù)佑神;但也有所謂母豬鬼、吊死鬼、老虎鬼、東方鬼、西方鬼等鬼魅,這些信仰對象大多是兇神,它們被稱為惡鬼。這里“鬼神的種子,就放在沙壩兒孫們的遺傳著的血中了。”[5](P117)因此,這里的“廟宇的發(fā)達(dá)同巫師的富有,都能給外路人一個頗大的驚愕。”[5](P117)
由此可見湘西的民間信仰濃厚的程度。除鬼神崇拜以外,另外一大信仰譜系就是巫儺信仰。湘西一帶自古有“巫作儺戲酬神”的習(xí)俗,乾嘉年間,湘西、湘西南的苗族、土家族巫風(fēng)仍很繁盛。“冰雪官衙吟,千山響竹濤,苗風(fēng)尚巫卜,邊俗競弓刀。”這首名為《道署雪夜詠懷》的詩,描述了夜聞湘西鳳凰巫作法事的聯(lián)想。[6](P164)清代中葉容美(亦稱容陽)的土家族土司詩人田信夫?qū)Ρ镜匚變F(xiàn)象是這樣描寫的:“山鬼參差迭里歌,家家羅幫截身魔,夜深響徹鳴鳴號,爭說鄰家唱大儺。”[6]P164)這里巫風(fēng)興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lǐng)域。湘西的儺祭,晚清時名目繁多并與當(dāng)?shù)亓?xí)俗密切結(jié)合進(jìn)行:疾病延醫(yī)服藥之外,惟祈禱是務(wù)。父母病則延老者十人,用牲牢以為請命神,謂之打十保護(hù);童子病則延巫為之解熬,名曰揚關(guān);又或以處鬼作崇,于河邊井岸用犬羊祭之,謂之打波斯。[7]所以,湘西的巫儺祀神的現(xiàn)象就是常態(tài)化生活內(nèi)容:凡酬愿追魂,不論四季擇日延巫祭賽儺神。祭時必設(shè)儺王男女二像于庭中,旁列滿堂畫軸神秘像,愿大者反搭臺演儺神戲。[8]由此,湘西地區(qū)巫儺風(fēng)氣之甚可見一斑,顯然也是本地的一種文化特色。
由于湘西信仰豐富多樣,所以廟宇不少,“小小縣城里外大型建筑,不是廟宇就是祠堂”[4](P397),據(jù)統(tǒng)計這里有:風(fēng)神廟、火神廟、龍王廟、劉猛將軍廟、關(guān)帝廟、岳王廟、文昌廟、城隍廟、觀音堂、女媧宮、王公祠等五十多處。[9](P17)如此豐富的廟宇孕育了厚重的廟宇文化,為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也是沈從文寫作湘西風(fēng)俗歷史文化時,能夠駕輕就熟的一個主要根基。
湘西苗、土家等少數(shù)民族的信仰可以歸結(jié)為: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巫術(shù)崇拜等。湘西信仰的豐富和多樣化,給湘西文化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而這種神秘性實質(zhì)上是東方神秘文化的典型。在很多地方已不存在的信仰對象和儀式,湘西卻還有這樣的“活化石”。所以,在沈從文的文學(xué)作品中,以豐富的信仰對象作為文學(xué)主要表達(dá)對象,為他的作品籠罩了一層厚厚的神秘面紗。在沈從文的文學(xué)作品中,鬼神信仰是一大類,大致有以下幾種:在小說《哨兵》出現(xiàn)的觀音菩薩、巫術(shù)還愿、城隍廟、牛頭馬面、大小無常、天王廟、巫醫(yī)信仰、大手鬼、大眼睛鬼、死鬼等;在《落伍》中有“角母鬼”;在《神巫之愛》中有尉遲恭、張果老、鐵拐李;在《鳳凰》中有:狐、虎、蛇、龜?shù)取I驈奈牡淖髌分羞€有一類信仰是巫術(shù),如《鳳凰》中有“放蠱”、“落洞”等;在《神巫之愛》中有“巫儺崇拜”;在《病》中有“設(shè)壇捉鬼”;在《一個母親》中有“設(shè)壇打醮”求雨。這兩種類型的信仰體系大體能夠反映湘西信仰狀況,從自然社會神明、精靈鬼怪到巫儺崇拜,名目繁多。沈從文除了全方位地對湘西風(fēng)俗風(fēng)情進(jìn)行充分的闡述,也突出了湘西信仰的特異性和復(fù)雜性,呈現(xiàn)了湘西文化的神秘性,同時也凸顯了湘西民眾純凈的心靈與原始的生存狀態(tài)。
沈從文獨特的民間信仰敘事手法
在沈從文的湘西敘事中,民間信仰敘事往往是文本敘事的一種手段,而這種敘事是一種在場的敘事方式。“在這一民俗敘事建構(gòu)中,被聚焦的民俗事象成為敘述和描寫的基本內(nèi)容,其目的是詳細(xì)介紹某一民俗事象,其結(jié)果是民俗敘事呈現(xiàn)出描述民俗文化學(xué)的特征。”[10](P98)這是一種敘事者在場的方式,與敘事對象同時出現(xiàn),表現(xiàn)信仰儀式的真實性和現(xiàn)場感,那么這種敘事方式也就是人類學(xué)田野調(diào)查直錄的方法。如《神巫之愛》中神巫的祈福儀式活動過程與敘事者同時在場,神巫的表演就是敘事者觀察到的直接結(jié)果。神巫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敘事者的眼皮下進(jìn)行著的,都是一系列細(xì)致傳神的“現(xiàn)場直播”,而不加任何的渲染。這種敘事方式有利于民間信仰儀式過程記錄的真實性表達(dá)。
另外一種民間信仰敘事方式是信仰敘事作為故事發(fā)生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不充當(dāng)故事情節(jié)中的主要內(nèi)容,而只是起到了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作用,有的則是在故事情節(jié)的展開中起到了鋪墊的作用。如《哨兵》中以地方鬼神文化觀念作為鋪墊,用鬼神信仰來幫助結(jié)構(gòu)故事,作品從談?wù)摴淼挠袩o、鬼的真實性等入手,引出的沙壩是一個“鬼的種子,就放在沙壩人兒孫們遺傳著的血中了”和“廟宇的發(fā)達(dá)同巫師的富有”[5](P117)的地方,就連“普通一般人治病的方法,得賴靈鬼指示,醫(yī)生才敢下藥”[5](P117),如此地重視鬼神,所以他們的一切處事都與神靈掛上鉤了。軍人證明自己是否清白得去天王廟“明心”,甚至還有在神靈前“擲筊”判斷犯人的生死。由此作了充分的沙壩地方鬼神信仰現(xiàn)狀的敘述后,才引出了哨兵輪值夜班過程中對鬼魂一次完整的恐懼經(jīng)歷,鬼神信仰現(xiàn)象成為了發(fā)生在沙壩道尹衙門哨兵值夜班恐懼經(jīng)歷的必要條件,這種敘事方式與上述所說的“在場”敘事方式就大相徑庭了。
此外,還有一種敘事方式是直接把民間信仰對象和儀式活動作為敘事的內(nèi)容,也就是直接談?wù)撔叛觯轿坏亟榻B信仰的對象及其存在狀況。散文《鳳凰》純粹是以介紹地方巫術(shù)為主要內(nèi)容的作品,其中關(guān)涉了湘西的巫術(shù)中“巫蠱”和“落洞”兩種信仰。關(guān)于“巫蠱”,作者從典籍記載開始,介紹了湘西巫蠱中的名稱、蠱人、放蠱的方法、中蠱者的癥候、“草蠱婆”的習(xí)性、懲治蠱婆“曬草蠱”、蠱人的真相、行巫者的身份與過程等方面;介紹“落洞”(也是女巫的一種,專指在男權(quán)社會愛欲遭受壓抑,心理畸變行為反常,被世人貶斥的女性[11](P286))也是從落洞的緣起、身份、性質(zhì)、狀態(tài)、習(xí)性、最后死亡的情況及落洞的解決辦法等內(nèi)容。這種敘事方式是以講述事實的內(nèi)容為主,而不是一個故事的敘事;但在這種講述過程中,也穿插了一些相關(guān)的故事,如族長劉俊卿誤殺夫人的故事,為落洞習(xí)俗的敘述作了鋪墊。總之,以介紹信仰對象為內(nèi)容的文本敘事方式是闡釋湘西文化的一種主要方式,從沈從文湘西主題的文本整體上考察,這種敘事方式還大量存在于其他小說和散文中,也是他建構(gòu)湘西世界文化的主要手段,通過這種敘事方式,沈從文再現(xiàn)了湘西獨特的文化狀態(tài)。
民間信仰的詩化表達(dá)是沈從文文化反思的一種方式
沈從文的民間信仰呈現(xiàn)并非一味地表達(dá)一種宗教意義上的嚴(yán)肅性和本原性,更多的是以一種審美性意象表達(dá)來詩化民間信仰,這種表達(dá)無疑是對嚴(yán)肅的宗教情結(jié)和意義的消解,而走向一種詩性的文學(xué)訴求和本真自然狀態(tài)的人性追求。這也是湘西世界具有獨特“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主要原因,從而使之蒙上了溫柔敦厚的鄉(xiāng)土牧歌情調(diào),使他的作品充滿了詩化的情調(diào)。
神靈信仰與愛情結(jié)合的表達(dá)方式,使民間信仰的嚴(yán)肅性淡化,增加了人情味和朦朧感。如《神巫之愛》把神巫描寫成“驕傲如皇帝”的“神之子”,他的“風(fēng)儀是使所有女人傾倒”,全然是一位讓所有姑娘傾心的“情種”,這與現(xiàn)實中神巫莊重的身份有著明顯的反差。同時沈從文筆下的民間信仰敘事與民間信仰儀式的嚴(yán)肅性不盡相同,神巫的祈福祀神的過程卻變?yōu)榱耸緪酆颓髳鄣倪^程,這無疑是對民間信仰儀式過程的嚴(yán)肅性的一種詩化化。神巫被人認(rèn)為是一種“絕地通天”的社會角色,這種人能夠做到“人神相接”的特殊身份與普通人完全不同,“巫扮成‘神’后,便成具有神靈力量的超人”[6](P336),有詩唱道:“沙鑼鏜其嗚,銅鼓坎其鼓,雜沓如巫覡,繽紛飾貓虎。束腰垂紅巾,齊頭裹青組。里僚擲叉跳,洞瑤掉臂舞。……我聞教民俗,祭法必師古。容貌束衣冠,揖讓嚴(yán)步武。……非類必不歆,失禮非所取。……”[6](P164)詩行中主要內(nèi)容講述了苗族、土家族人跳儺祀神的狀況,神巫的裝束動作行為規(guī)范,氣氛凝重,體現(xiàn)了人與神之間溝通的嚴(yán)肅和莊重。而沈從文小說文本中的人神溝通詩意化和人性化,這種敘事的詩化化與現(xiàn)實的差異性完全在于作者的“小說在探索理想的人性形式、關(guān)于人的改造的理想時”,“所堅持的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性立場和文化精神”[12](P212)。有意識地把民間信仰儀式過程嚴(yán)肅性進(jìn)行淡化,追求一種人性和人情的詩意存在。
沈從文對民間信仰進(jìn)行詩意化的目的是他的文化思考,對于“鬼神”觀念的強調(diào),并不是把它置于“科學(xué)”的對立面來認(rèn)識,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加于闡釋;不是把它簡單地視為一種信仰,而是作為一種娛樂人的性情的文化來對待。小說《鳳子》從城市寫到鄉(xiāng)村,敘述了走進(jìn)湘西的城市人對鬼神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你前天和我說神在你們這里是不可少的,我不無懷疑,現(xiàn)在可明白了,我自以為是個新人,一個尊重理性反抗迷信的人,平時厭惡和尚,把這兩東西外加上一群到廟宇對偶像許愿的角色,總攏來以為簡直是一出惡劣不堪的戲文。”[5](P386-387)這里是總爺與城里來老師的對話,在看完儺戲后“老師”的觀念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來自于都市現(xiàn)狀是“虛偽的象征,保護(hù)人類的愚昧,遮飾人類的殘忍,更從而增加人類的丑惡”[5](P387)。然而對于湘西百姓來說,“神”是存在的,是“莊嚴(yán)和美麗”的,不過神存在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人生的素樸,觀念的單純,以及環(huán)境的牧歌性”[5](P387)。這種觀念就是作家在城市和湘西的對比中產(chǎn)生的。此外,作者還借“老師”之口談?wù)摿松裰凇翱茖W(xué)”和“政治”的關(guān)系,批判性地指出政治的自私、愚昧和屠殺的一面。沈從文對五四時期“科學(xué)”和“民主”的思考是獨特的,對民間信仰態(tài)度并沒有與五四時期的反抗迷信和“現(xiàn)實批判”的潮流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而是采取獨特的文化視角自覺反思民間信仰,從中發(fā)現(xiàn)人性的純潔和人情的素樸,發(fā)現(xiàn)貼近自然、皈依自然的重要性,從湘西文化的觀照中發(fā)現(xiàn)“善”和“美”,由此更加深入地對現(xiàn)代文明進(jìn)行了反思。這種反思與尋根文學(xué)中“湘軍”的民間信仰描寫是不同的,“湘軍”所反映的更多趨向于巫楚文化重新發(fā)現(xiàn)和傳統(tǒng)文化的尋根,而沈從文的立足點更多在于借湘西文化反思現(xiàn)代文明;沈從文的湘西文化呈現(xiàn)也并非是局限于地域情懷中,而是應(yīng)用對比的思維對未曾受過現(xiàn)代文明浸染的湘西文化進(jìn)行發(fā)掘,這種對比思維恰恰是當(dāng)時“京派小說”的審美追求和藝術(shù)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的現(xiàn)代反思是從湘西文化的反思出發(fā),對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化所存在不足與缺陷進(jìn)行了深入的反思,這一點恐怕是沈從文文學(xué)思考的獨到地方,也是其創(chuàng)作獨具魅力的一個原因。
湘西是沈從文魂牽夢縈的故鄉(xiāng),湘西古樸的文化傳統(tǒng)是他對現(xiàn)代文化反思的起點,湘西神秘的民間信仰現(xiàn)象是他文化反思的內(nèi)核。沈從文通過民間信仰敘事構(gòu)建了一個區(qū)別于現(xiàn)代文明的湘西文化圖景,呈現(xiàn)了一個朦朧的、詩意的、神秘的湘西人的精神世界,他也隨之成為一位難得的自然純樸文化的精神家園守望者。
相關(guān)熱門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 1古代文學(xué)文學(xué)感悟力思考
- 2瑤族文學(xué)植入比較文學(xué)教學(xué)思路
- 3文學(xué)教學(xué)現(xiàn)代文學(xué)論文
- 4談古代文學(xué)史料及古代文學(xué)研究
- 5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女性主義文學(xué)解讀
- 6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中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影響探析
- 7文學(xué)政策論文:前蘇聯(lián)文學(xué)政策的思考
- 8俄國文學(xué)對我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影響
- 9選本文學(xué)與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模式的演變
- 10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對傳統(tǒng)文學(xué)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