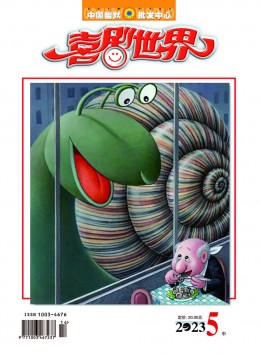李健吾對莫式喜劇的借鑒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李健吾對莫式喜劇的借鑒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徐歡顏 單位: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
1936年1月,李健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以身作則》這出三幕喜劇,屬于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1輯。他在書中標注了“后記”的寫作日期:1936年1月10日,由此推想這部喜劇的寫作時間應該在后記所署的時間之前。李健吾晚年在其自傳中,提到《以身作則》在重慶和上海的演出情況,卻沒有交代此劇的寫作背景。[4]1935年8月,李健吾離京赴滬,任上海暨南大學的法國文學教授,除去上課之外,李健吾平時深居簡出,伏案寫作。[5]很有可能《以身作則》創作于他定居上海之后。這個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并不復雜:地點發生在華北某縣城內,一位地方鄉紳徐守清有一子一女,他經常以道學教條和封建倫理來要求子女。一位前來縣城駐扎的年輕營長方義生愛上了徐守清的女兒玉貞小姐,在馬夫寶善的幫助下,假裝成醫生混入徐家。王婆介紹了一位年輕寡婦張媽給徐家做傭人,滿口仁義道德的徐守清對她垂涎三尺,但最終張媽寧愿選擇馬夫寶善,也不選擇這個虛偽的前清舉人。方義生的身份最后被徐守清的外甥揭穿,徐守清不得已答應了他和自己女兒的婚事,但要求方義生處罰馬夫寶善50軍棍。
1937年4月,李健吾繼續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三幕喜劇《新學究》,這一劇作屬于“文學叢刊”的第4輯。李健吾既沒有寫作前言后記,在此后的各種文章中也沒有提及過這部喜劇,甚至在1981年寫作的自傳中也諱莫如深。徐士瑚認為《新學究》的寫作時間是在1937年1月,[6]徐士瑚和李健吾是山西同鄉,又是清華時期的同學,兩人私交甚好,因此即使在徐士瑚并未給出理由的情況下,這一說法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王為民、祁忠寫作的李健吾評傳卻提出了另外一個說法:由于《新學究》引起了清華某位教授的猜忌,所以李健吾失去了回母校任教的機會,所以才舉家南遷上海。[7]如果此說成立的話,那《新學究》的創作時間當在1935年8月李健吾南遷之前,可能還早于《以身作則》的寫作。這位“清華某教授”,在唐振常看來,是吳宓(雨僧)先生。他說:此事(指毛彥文嫁給熊希齡一事)大傷先生之心,更感孤獨。先生的學生、劇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寫成話劇《新學究》,從而嘲諷之。先生確乎有新學究之氣,但我以為做此事有失忠厚之道,更非先生所應為。1946年,在上海我偶然對李健吾先生言及此意,李先生仍不無自得,說他很了解雨僧先生。嘲弄老師的痛苦,實在是并不了解老師。[8]
鑒于李健吾在公開場合一直對此劇保持緘默,所以唐振常的說法也有待考證。但不管《以身作則》和《新學究》孰先孰后,都被研究者當作“莫氏喜劇”來看待。作家師陀在回憶文章中記述了1937年9月,李健吾和他在李家書房的談話,談話是在莎士比亞和莫里哀、杜工部和元明戲曲等眾多書籍的包圍中進行的。[9]由此可見,1937年左右,莫里哀喜劇在李健吾書房是占據一席之地的。李健吾還在1935年就天津南開新劇團演出的《財狂》一劇發表了《L’Avare的第四幕第七場》的評論文章,而《財狂》恰恰就是戲劇家曹禺對莫里哀喜劇《吝嗇鬼》(L’Avare)的中國式編譯。由此證明在1935-1937年之間,李健吾對于莫里哀喜劇是非常熟諳的。
《新學究》是李健吾以高級知識分子為題材的一部喜劇。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某大學附近,主要人物是一個自作多情的迂闊的中年教授康如水。他當初拿錢送謝淑儀出國留學,為了等她回來結婚,竟和跟隨他15年的發妻離婚。但是謝淑儀并不愛康如水,她愛的是與她同船回國的馮顯利。馮顯利與康如水是老朋友,但他并不知道謝淑儀就是康如水朝思暮想的意中人。同事孟序功夫婦為馮顯利和謝淑儀接風,邀請康如水參加。康如水本來打算趁機機會向朋友們宣布他與謝淑儀結婚的消息,但最后才發現謝淑儀并不愛他,她最終選擇了與馮顯利結婚。這個以愛情為主題的喜劇出版后相當受歡迎,1937年4月初版,5月旋即再版。
在40年代孤島困守期間,李健吾又創作了《青春》,這是一個農村題材的愛情故事。觀眾反響并不很好,讀者徐光燦認為《青春》里面最后一幕的大團圓,顯然是一種生硬的湊合,這類悲劇,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故事。但李健吾在回復徐光燦的信中說,他原是把《青春》當作喜劇寫的。他還辯解說,喜劇,尤其是高級喜劇,往往和悲劇為鄰,它讓人在笑后感到悲哀,不由不墜入思考;這種笑,才有韻味;這種笑,不僅僅一笑了之,往往倒是真正的悲劇。人世或者由于制度的缺陷,或者由于性格的缺陷,往往形成一種錯誤,悲劇家把它們看成是悲劇,喜劇家把它們看成是喜劇。莫里哀偉大的地方就在這些特殊的造詣。[10]這出喜劇在當時的上海孤島淪陷區并未引起太多重視,但到了50年代宣傳新婚姻法的時候,卻機緣巧合被改編為評劇《小女婿》,接著政策的東風演遍大江南北,風靡一時。
從以上對于李健吾喜劇創作的簡要辨析中可以看出,李健吾在30-40年代創作的4部喜劇,均或多或少與莫里哀喜劇有些關聯。其中《新學究》與《以身作則》兩部劇作更是鮮明地體現出莫里哀喜劇的影響。
李健吾在《以身作則》和《新學究》中模仿莫里哀喜劇的痕跡是相當明顯的,從這兩部喜劇最基本的故事情節上就可以比較出來。實際上,這段法文出自《丈夫學堂》第1幕第4場,而非李健吾所標示的第1幕第6場。中譯文如下:一個女人受到了監視,就起了一半外心,丈夫或者父親愛發脾氣,永遠成全情人的好事。當然,這種表面的相似過于明顯,但李健吾這兩個喜劇的故事情節,都有一個或幾個略隱略現的摹本。《以身作則》與李健吾1929年出版的中篇小說《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的故事情節也有相似之處,都是一個大兵怎樣通過巧計來逼使父親同意女兒的婚事,這是李健吾創作中存在的相當有趣的喜劇作品與小說作品的互文性再現。《以身作則》中方義生扮作醫生去會玉貞小姐的情節還與莫里哀的喜劇《愛情是醫生》類似,都是戀人裝扮成醫生,借看病之機談情說愛,最終喜結良緣。而《以身作則》中馬夫寶善耍詭計、最后遭棒打的故事情節和《司卡班的詭計》又有雷同之處,都是給青年出巧計贏得愛情的忠心仆人最終都會受到頑固封建的老主人的棒打。《新學究》的故事情節則與莫里哀的風俗喜劇《憤世嫉俗》有類似的地方:都是偏執的不為社會習俗所容的男主角在愛情角逐中落敗,發表種種奇怪的人生哲學和奇談怪論。這些相似之處給閱讀者帶來非常奇妙的似曾相識之感,但并不抹殺李健吾喜劇在情節上的創造性,作家是將各種情節類型揉碎之后進行了重新組合和變形。況且莫里哀喜劇本身在故事情節上也是非常類似的,將莫里哀喜劇與李健吾喜劇區別開來的不是情節,而是人物的性格,因為只有典型的性格才是喜劇創造的關鍵。
《以身作則》中的徐守清是一個喪失了全部現實感的喜劇人物。盡管時生了巨變,但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以往的世界中。他蜷縮在道學之中,用儒家的經典話語代替本真的生活語言,前清舉人早已不復存在的優越感遮蔽了他看清現實的眼睛。對于脫離時代的虛偽的守舊者,時代帶給他重重的挫敗:他的女兒要離他而去,他的兒子也絕不會繼承他的衣缽,而那位張媽寧愿跟馬夫走也不選擇他這位堂堂的舉人。李健吾通過道學與人性之間的深刻矛盾,刻畫出“假道學”這一性格內在的虛弱和虛假,揭示了現代性因素戰勝不合理的傳統因素的必然性。《新學究》中康如水的性格是完全流動的,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樣,這種流動性突出表現在他對于女性人物的狂熱追求上。他剛剛還在向自己的夢中情人謝淑儀求愛,遭遇挫敗后一轉眼的功夫就跪倒在已婚女士孟太太的腳下;他剛剛責罵完自己的戀人忘恩負義,掉頭又會湊上去搖尾乞憐。但流動性只是其性格的表面狀態,在性格深層實際上還存在著傳統的穩定性:康如水主張婚姻與戀愛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只有他自己可以享有,女人只能“純潔、貞節,從一而終”;康教授盡管把女人奉為“高貴的詩神”、“清純透明的詩之材料”,但他本質上是一個專制褊狹的男性中心論者。因此康如水這個大學里的“新”派教授骨子里仍然是一個“老牌兒的學究”。
李健吾抓住“五四”以后社會風俗中現代因素與傳統因素的沖突,在沖突中塑造舊派或新派的人物,創造出20世紀30年代社會獨有的典型性格。但這種性格卻利用了中西極為相似的喜劇情節,在模仿中進行創造。
李健吾還借鑒了莫里哀的喜劇形式。莫里哀喜劇是古典主義喜劇,一般而言都是遵守“三一律”的。在《以身作則》和《新學究》中,也完全遵守了時間、地點、行動的“三個統一”。《以身作則》的時間:第一幕是某日早晨十時,第二幕是一小時以后,第三幕是再一小時以后。地點是:華北某縣城內。行動是馬夫寶善以種種詭計揭穿前清舉人的虛偽面目,使年輕男女終成眷屬。《新學究》的行動統一,即康如水等待多年要與謝淑儀結婚的迷夢破滅了;地點統一,即某大學附近的康家與趙家;時間統一,即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吃茶點時。兩個劇本在形式上都嚴格遵守了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的“三一律”原則。李健吾在《以身作則》的后記中說:“我夢想去抓住屬于中國的一切,完美無間地放進一個舶來的造型的形體。”[11]這個“舶來的造型”,可能是指話劇,也可能是指古典主義“三一律”,但無論如何,他的喜劇創作目標是很明確的,即借助西洋的外殼,使用中國的材料,創造屬于自己的東西。
李健吾對于莫里哀喜劇的模仿畢竟是表層的,他的喜劇創作成功之處更在于成功地吸取了莫里哀喜劇的精神。在他的《新學究》中,通過主人公馮顯利之口表達了作者本人對于人生喜劇和悲劇的看法:人生是一出喜戲,還是一出悲劇?是一出悲劇的話,什么東西做成它的悲劇呢?你得承認,一個人歡喜的時候總比悲哀的時候少,就在歡喜的時候,馬上接著的也許就是一個傷心的傷心。我們不敢凝定思想。一凝定,我們就明白自己多空虛了。真實的只有悲哀的永長的情緒。[12]67你知道,頂高的喜劇也就是悲劇。[12]69
莫里哀喜劇“內悲外喜”的特色,焦菊隱早在20年代就已經總結過了,李健吾也非常認同這一點,認為喜劇,尤其是高級喜劇,往往和悲劇相鄰。他在30年代曾經有過這樣的表述,“最高的喜劇不是環境的湊合,往往是人物的分析”。[13]而這種人物的分析,歸根到底就是人性的表現。20年代的焦菊隱轉引法國批評家圣駁夫評價莫里哀的話說:“他是一個有人性的人。”30年代,在對《吝嗇鬼》的分析中,李健吾認為中國文學最大的弊病在于“對于創造性格的淡漠,對于故事興趣的濃郁”。而中國傳統戲劇的主要問題也正在于此,單純“注重故事的離合,不用人物主宰進行”的結果,使它“缺少深刻的人性的波瀾”,因此即使偶爾成就“片段的美好”,但總體上卻往往難以達到藝術的勝境。[14]在李健吾30年代的表述中,“人性的共同精神”、“普遍的人性”、“深廣的人性”、“人性的普遍情緒”,這些都是反復在作家評論文章中出現的概念。在《以身作則》中,他也寫道:我愛廣大的自然和其中活動的各不相同的人性。在這些活動里面,因為是一個中國人,我最感興趣也最動衷腸的,便是深植于我四周的固有的品德。隔著現代五光十色的變動,我先想撈拾一把那最隱晦也最鮮明的傳統的特征。[11]1
李健吾對于莫里哀的“自然”是這樣解釋的,“尊重自然(不是風景,而是人性naturehumaine,而是社會生活)的客觀真實,是和莫里哀的唯物觀點分不開的。這也正是同樣尊重自然,然而他和古典主義理論家在領會問題上,根本分歧所在,自然對莫里哀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本來面目,屬于外在,屬于形象,‘照自然描畫’等于我們今天常常說起的‘表現現實’;藝術家必須正確觀察社會現象,在藝術上做出正確的表現。但是對于莫里哀,自然不止于是一種形象存在,所以,尊重自然的客觀存在,不僅由于他有形象的一面,而且也因為他有精神的一面。”(李健吾《戰斗的莫里哀》,見中央戲劇學院國書館館藏油印稿)這種對于“自然”(人性、社會生活)和人性精神的熱愛,使得李健吾在創作中希圖揭示30年代社會中人性與社會變動的矛盾與沖突。
他進一步解釋《以身作則》這部喜劇的創作意旨和塑造人物的原因:人性需要相當的限制,然而這相當的限制,卻不應擴展成為帝王式的規律。道德是人性向上的坦白的流露,一種無在而無不在的精神飽滿作用,卻不就是道學。道學將禮和人生分而為二,形成互相攘奪統治權的丑態。這美麗的丑態,又乃喜劇視同己出的天下。《以身作則》證明人性不可遏抑的潛伏的力量。有一種人把虛偽的存在當作力量,忘記他尚有一個真我,不知不覺,漸漸出賣自己。我同情他的失敗,因為他那樣牢不可拔,據有一個無以撼動的后天的生命。這就是我為什么創造徐守清那樣一個人物,代他道歉,同時幫他要求一個可能的原諒。[11]2-3這一大段表述,區分了道學和道德,認為道學的丑態正是喜劇表現的對象。這和莫里哀喜劇傾向于表現人性弱點、缺陷是一致的。而且他對于徐守清這個人物的塑造,也正符合莫里哀對于喜劇任務的界定:“喜劇只是精美的詩,通過意味雋永的教訓,指摘人的過失。”
此外,李健吾對于喜劇作品,還有這樣的期許,認為“作品應該建在一個深廣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傳達人類普遍的情緒”。[11]2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將現代中國的一切放在舶來的造型中,將莫里哀喜劇的形式和精神借用到自己的喜劇創作中,傳達中國社會現實中的人性和人類共通的情感。
總之,李健吾在自己的現代喜劇創作中,通過與莫里哀喜劇情節和形式的表層相似,尋求精神內質的溝通與契合。他的《以身作則》和《新學究》這兩部中國現代喜劇,不是單純的“莫氏喜劇”,而是地道的“李氏喜劇”:將莫里哀的美學影響化入到自己的創作中去,形成自己的獨有風格———沒有鬧劇的膚淺,又不及莫里哀喜劇的沉重,而是“內悲外喜”,深挖人性,是個性化的、民族化的喜劇藝術。
但令人遺憾的是,1949年之后,李健吾對于莫里哀喜劇的借鑒和超越并未能在他的喜劇創作中延續下來。50年代初期,李健吾創作了活報劇《美帝暴行圖》中的兩出:一為《戰爭販子》,一為《偽君子》。為了抗美援朝的政治背景而緊急趕制的《偽君子》與30年代的《以身作則》、《新學究》相比,藝術上顯得粗糙之極。在李健吾的《偽君子》劇作中,大而空的政治宣傳話語代替了細致入微的性格描繪,急就章的劇作忽略了對于人性的開掘,導致他的《偽君子》在形式和語言上都有明顯的模仿莫里哀《偽君子》的痕跡,卻缺乏莫里哀喜劇深刻的人性力量。李健吾的《偽君子》創作,是抽離了莫里哀喜劇精神之后的膚淺模仿,形在神失,是其后期喜劇創作中的敗筆。而形肖神聚的“莫氏喜劇”,正好是李健吾20世紀30-40年代現代喜劇的點睛妙筆,使得中國現代喜劇擺脫了初創期的草率和粗略,開始逐漸過渡為相對成熟的中國現代喜劇。
通過對李健吾現代喜劇創作的考察,可以看出莫里哀與李健吾喜劇創作錯綜復雜的影響關系:莫里哀喜劇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著李健吾的喜劇創作,莫里哀慣用的情節和形式為李健吾的奇思妙想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舶來的造型”,但李健吾被稱為“莫氏喜劇”的那些現代喜劇作品,其中凸顯出來的精神氣質和包蘊著的美學內涵,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