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學的賦形結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京派文學的賦形結構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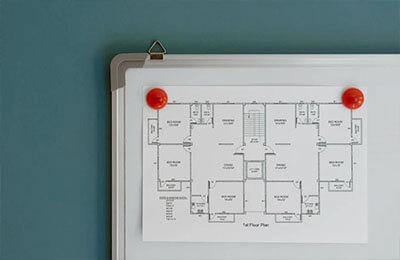
本文作者:陳嘯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京派散文是自然生長而成的少匠氣、重天然的整體存在形態,是一種超越常規形式之上之無型的有型、有型之無型的結構,它所遵循的是內在的結構以及各種賦形結構的內在原理。京派散文的結構有一種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開放自由美。
無型之有型
京派散文追求結構的開放和境界的瀟灑大美,充溢著一股流動性的活潑新姿。但這并不等于說京派散文散漫無章,放蕩無羈。京派文人在寫人寄思、敘事言情、借景抒情等的具體表現過程中,在遵循散文開放自由的審美約束中,同樣追求著無型的有型,追求著“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瀟灑中的形式常態。主要表現為:
京派文人為文,非常重視自己的情緒和心態。沈從文曾說:“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3](P74)“我看到一些符號,一片形,一把線,一種無聲的音樂,無文字的詩歌。我看到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實前反而消失。”[4](P295)何其芳也說:“對于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5](P1)“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在我心靈里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些圖案……有些作者常常略去那些從意象到意象的鎖鏈,有如他越過了河流并不指點給我們一座橋,假如我們沒有心靈的翅膀,便無從追蹤。”[5](P60)其實散文本身就是一種情感的文體。如此,京派文人在散文創作時,常常將強烈的情緒投射到外在的人事景物上,讓感情回旋、跳躍,呈現一種散點透視、凌亂無序的扇面結構。如蕭乾的《雁蕩山》,以情感的邏輯貫穿其中,并運用聯想和想象進行描繪,因而收到神韻融合、天然入妙的功效。整篇散文采用連綴式及散點透視。文本先寫臨雁蕩山的驚險、美艷、刺激、山的偉大;由山路的艱險欽佩那堅毅勇敢始終警醒著的司機以及當日筑路的民夫等等,置身于那幽奇渾龐的境界,古怪,怕人!“平時見了山,你還忘不了民生大計。……到這里,山卻成了你的主人了。”接著以“永遠滾動著”、“靈峰道上”、“銀白色的狂巔”、“那只纖細而剛硬的大手”等幾個小標題分別寫到了于險峻、雅麗無數怪狀的峰巒之背景中永遠滾動著生命浩蕩的小龍湫瀑布以及那也同樣永遠滾動著的以“二十塊錢,賣一條活命”代代相沿的山民的縋繩表演;靈峰道上的怪峰森峭,清流激湍的驚險、神秘、刺激、怪異;乍乘山轎所引起的良心上的傷感性的鞭笞以及羅帶瀑以一個震怒的絕代美人的氣派所顯現出的萬斛晶瑩、一道銀白色的狂巔等等。而貫穿其中的情感邏輯也是一波三折,散而歸一:即隨著外在景物之不同而感嘆生命的浩蕩、悲憫山民的生計、驚嘆自然的奇觀……這一切都讓作者感到一種胸中的悶壓、人間的悲戚。文本就在這情感的起伏漲落中散珠成串。情緒結構的基本特征即為重情緒,重生命體驗的知性化,在“我”與“物”,感性和理性之間融貫著飽滿的情感和體驗。情緒結構在外在表現形態上,常常表現為圍繞著某種或幾種情緒,組合與升華外在生活的細節或意象,情緒與外物之間有一種說明與被說明、解釋與被解釋的關系,同時這種解釋和說明是主體內在的、直覺的、渾圓的。情緒是散發、感知、體驗、生成的原點,外在的人事景物是情緒回旋、跳蕩的場地,整體格局上呈現發散型的扇面結構。
京派散文的意象結構是指以凝聚著作者生命體驗的某一意象為結構核心,文本由此意象做層層意義生發,或以這一意象為中心衍生出多種意義。如何其芳的《秋海棠》(1934年),文本的顯層主要寫靜靜庭院,寂寞思婦。作者以比喻、象征、通感、幻覺等多種藝術手法極寫夜的靜謐,幽暗,陰濕,思婦的孤獨、凄涼、彷徨和哀愁,而文本的末尾才歸結到對秋海棠的描寫:“就在這鋪滿了綠苔,不見砌痕的階下,秋海棠茁長起來了。兩瓣圓圓的鼓著如玫瑰頰間的酒渦,兩瓣長長的伸張著如羨慕昆蟲們飛游的翅,葉面是綠色的,葉背是紅的,附生著茸茸的淺毛,朱色莖斜斜的從石闌干的礎下擎出,如同擎出一個古代的甜美的故事。”顯然,秋海棠的意象是一種潛在象征意象,它象征著一種哀怨、憂愁,而文本中顯在描寫的思婦所包孕的主體情思與秋海棠在內涵上是等一的。秋海棠所代表的哀怨、憂愁、怨懟等內涵即為文本構思的潛在基點。總體上看,京派散文意象結構之表現形態常常是圍繞某個中心意象展開思緒,或生發或引申或聯想,思維呈發散輻射式特征,使文本詩情濃郁。另外,京派散文意象結構中所用之意象多是個人化和多層性的象征意象,象征符號自身的能指與所指意義具有著不固定的隨意性、模糊性、多層面的陌生意味,使京派散文充滿了現代性的蘊涵。
情節結構的散文側重探討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動與結構的關系。由于京派文人很多就是小說家,小說手法有意無意地都影響了其散文的結構形式,而在此方面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京派散文吸收了小說有中心人物,以人物行動為主,使其散文具有了小說描寫的客觀性。所不同的是,京派散文對人物的描寫當然不可能像小說那樣做全面的描寫,而以散文特有的抽象的言論統貫其中,以主觀的態度統攝全篇。在此方面,李廣田為最,以他的《柳葉桃》(1936年1月)為例。文本寫了一個女戲子的故事,主觀色彩濃郁。文本開篇即說,“提起筆,心中有說不出的感覺。既高興又煩憂。高興者,是自己解答了多年前未能解答且已忘懷了的一個問題。煩憂者,是因為事情本身令人不快。”接著敘述了十幾年前的往事,“我們”其時為一些五顏六色的夢所吸引,過著浪漫的日子,在“我們”租賃的院子對面,住著一衰落富戶,富戶中一美麗女人,即女戲子。想兒子想瘋,常把“我們”所租賃院子里哥兒當成自己的兒子,十幾年后打開了這葫蘆。原來,女子幼貧學戲,二十歲左右小有名氣,故得以與秦姓少年相好,并接回家中。在秦家是三姨太的身份,受著二姨太壓制,過著奴隸不如的日子,于是希望為秦家養出一個繼香火的小人兒,后來希望破滅,被迫回家,艱難度日。接著作者跳出來說道:“說到這里,幾乎忘記是在對你說話,先檢些重要的題外話在這先說,免得回頭忘掉。假如你想把這件事編成小說,尚須設法把許多空白填補起來,我所寫的僅是個報告。”后來,種種原因的湊合,秦家又接女戲子回去,去后更是虐待的厲害,女戲子更想著孩子的夢,終至發瘋,以至死去。“我”煩擾著,仿佛這件事和“我”發生了關系,“我”不禁向你問一句:“我們當年那些五顏六色的奇夢,現在究竟變到了什么顏色?”顯然,文本主要是講故事,在故事的回憶中,包蘊和充斥著作者本人的理解、憤懣、惆悵、惋惜……情節結構的散文有人物有故事,有時還采用第三人稱敘述的手法,具有了小說的客觀性,但也更有著散文的主觀色彩。
京派散文的象征結構是指用具體物象對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進行寓示和概括。象征結構的散文常采用象征手法,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來表明與之相近的某一抽象概念、思想、感情。如蕭乾的《破車上》,作者開篇即用了象征意味的筆法點出題目的意旨:凡是殘舊了的時髦物件都曾有過昔日的光輝,“像紅過一陣的老藝人,銀白的鬢發,疲憊的眼睛下面,隱隱地卻在訴說著一個煊赫的往日。”接著便敘述了“我們”鉆進一輛破汽車,去看一位垂暮的老人。路途中,極寫了路的艱難,車的嘶喘和屢次斷氣,并借用途中人物對話的形式寫出破車的象征意味:中國就是輛破車,但車破,可也走得動艱難的路,“出了毛病,等會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癱倒,這才是中國。”顯然,表面寫的是破車,其實寫的是中國,破車的形象就是中國的形象,是公共化的中國象征形象,也是文本結構的凝聚點和發散點。李廣田的《老渡船》,題目為老渡船,但文本顯然寫的不是船,而是用渡船的堅實,穩固,最能適應水面上的一切顛顛簸簸,風風雨雨的顯在象征意義來寫一個老渡船式的人。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中所說的窗子,顯然不是現實中實在的窗子,而是一種潛在象征符號,代表著一種“隔”,一種自我世界與外面世界的隔離。京派散文的象征結構,具有著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的分子,包蘊著中國古典詩詞與西方現代派的藝術神韻,呈示出含蓄蘊藉、欲綻還休的幽幽風姿。
有型之無型
京派散文的有型其實質又體現著自由的無型之美,它比詩歌、小說等文體更自由、更靈活、更多變、更開放,有一種自洽生長的無規范的自在之態。也就是說,京派散文在上述所列的種種型式中,又表現出一種流動的和不安分的自由,表現出有型的無型:
其一,結構的宏闊性和開放性;前文所論的情緒結構、意象結構、象征結構、情節結構等,盡管也表現著結構中的常態,比如文本中的情緒、意象、情節等是文本結構的內在凝聚點、發散中心及結構核心,但在文本具體展開的發散形態上,又表現出無定局、無定法、甚至無定體的特征,追求行文的瀟灑自由。情緒結構的散文一任感情的回旋、跳躍;意象結構的散文又常常表現出意象的發散性、思維的輻射性;情節結構的散文則表現出斷片性、主觀性;象征結構的散文表現出個人化、潛在化、浪漫化的神韻……這些特性都散發著自由瀟灑的因子,也規約了文體的自由、宏闊、開放。誠然,概觀整個京派散文,我們大可感覺出,它們盡管寫的都很精美,但并沒有模式化、定型化、程式化等的傾向,是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大美。
其二,流動性。不拘泥于成法,隨物賦形,依如蘇軾在《自評文》中所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京派散文于整體的結構風格上有如上文所論的情緒結構、意象結構、象征結構、情節結構等不同的多元流動的表現形態,即便具體到各種具體結構形態的內部,也同樣表現出復雜多樣流動性的風格特性。比如同樣寫情緒,沈從文的《桃源與沅州》,何其芳的《獨語》寫得較為空靈、變幻、虛玄,因為它寫的是內在心靈的思辯和孤獨。而蕭乾的《雁蕩山》則寫得繁復、附實,因為它所寫得則為現實的引發、觀感、思考,是隨著現實的蹤跡而依次凸顯自我的情緒;同樣寫意象,何其芳《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潛在象征著一種哀怨、憂愁、怨懟,內涵和神韻豐富、深沉、朦朧,而李廣田《井》中的意象,梁遇春《墳》中“墳”的意象,等則為心造的幻影,是一種心理意象,是作者自己的那種難明、晦澀、朦朧之幻想、想象的詩意表達。
其三,適然的思維支撐。思維是無形的,它既是邏輯的、理性的因素,又有非邏輯、非理性的因素。其中,非理性的因素對于思維的創造力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比如直覺就是思維中一種非理性的因素,它看似無明顯根據,實則乃以思維主體長期之經驗積淀為基礎的。直覺的本質是領悟,指主體不經過嚴密的邏輯推理而直接洞悉事物的本質。從心理學角度看,直覺是一個熟悉的過程,是個體在先前知識經驗基礎上再認識某事物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概念邏輯被懸置,個體感覺、經驗被突出。京派散文的上述結構其內在的支撐力量是各種適然的思維,是在各種思維引導下的思維結構。思維的無形決定了散文結構的理性與非邏輯,即常態中的自由形態。比如:情緒結構的散文,受制于意識流思維,作者通過心理意識的自由聯想延伸、生發成文,是一種個人的冥想。冥想中,作者打破現實與想象、現實與夢境的界限,自由表達其對生命的質詢與追問。表現出強烈的內傾性、自在性、自為性。
另外,所有上述京派散文的結構形態還都往往多遵循著中國傳統的和最重要的順應自然思維形式。中國古代的儒、釋、道都強調順應自然但各有側重,而又相互補充,使此一思維更為深刻。儒家講順應自然,強調合乎時宜,順應人心。如《易•革•彖》:“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強調符合自然和社會規律,如《易•賁卦•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于文學批評,則是主張詩文符合時代和政治道德的需要,強調其“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講順應自然,強調“道法自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則強調“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佛教哲學特別是禪宗哲學,歌頌如同“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云淡演,出沒太虛之中”(慧中語錄)的心靈自由自在的自然狀態,歌頌順其自然,便會有心靈澄澈之福的境界。三者的合流,便成了向內宇宙和外宇宙掘進的時空意識。這種開闊深邃的時空意識又是辨證的。它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為其特征,以“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思想為指導,是既包含著量變,也包含著質變的辨證的時空意識。京派散文吸取了傳統中國順應自然思維的內在哲學神韻,于散文的結構形態上追求自我與自然的融合,“真我”心靈的自由自在,敘述抒情的自適、自然等,追求文本結構的順勢行文、自然天成。質言之,京派散文的結構是“賦形”的結構,生長的結構,京派散文不是寫成的,是生成的。
賦形結構的內在原理
李廣田說:“我以為詩與小說來和散文相比,也許更容易見出散文的特點。假如各用一個字來說明,那就是:詩必須圓,小說必須嚴,而散文則必散。若用比喻來說,那就是:詩必須像一顆珍珠那么圓滿,那么完整……小說就像一座建筑,無論大小,它必須結構嚴密,配合緊湊……至于散文,我以為它很像一條河流,它順了溝壑,避了丘陵,凡是可以注處它都流到,而流來流去卻還是歸入大海,就像一個人隨意散步一樣,散步完了,于是回到家里去。這就是散文和詩與小說在體制上的不同之點,也就是以見出散文之為‘散’的特點來了。”[6](P97)誠然,京派散文之“散”就表現在它的生成性,即隨著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或物的需要,賦予其恰當的結構形態。深究之,京派散文賦形結構的內在原理本質表現為圍繞一個基本生長點,合宜地運用渲染與反襯,并通過各種因果與相似立意思維及分析與綜合的徑路思維以達成文本的復制生長和最終形態。所謂渲染,即一種信息的重復思維操作,所謂反襯,即是一種功能性重復的思維操作。是對所指(意思、主題、立意、情調、色彩)的復制,也是對能指(形式、形象、載體)的創新。主題的自我復制過程就似“滾雪球”,即自相似的分形生長過程。而在文本最終生成的過程中,立意思維和徑路思維特別是徑路思維起著重要的作用。徑路思維是寫作行為的(實體)結構性思維,其基本原理就是因果(邏輯)、共時(空間)、歷時(時間)、程度等不同形式不同形態的分析與綜合,最終達成功能性賦形的完成和定型。
當然,不同類型的散文其賦形生長的結果又各具其美學形態。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京派文人敘事的散文,常常表現出因果式的線脈美與遞進式的層次美。不管是先因后果,先果后因,或是果中有因,因中有果,都講究脈絡的清晰呈現。以李廣田的《柳葉桃》(1936年1月)為例。文本敘述一個女戲子的故事。開篇即說自己解答了一個既高興又煩憂的問題。成為文本的引子。接著敘述十幾年前的往事,敘事的過程與文本的引子形成了整體上的因果(邏輯)分析與綜合,解答既高興又煩憂的原因。具體敘述的過程中,先果后因,我們當年遇一富戶美麗女人,想兒子想瘋了,常把我們所租賃院子里的哥兒當成自己的兒子,這是果,接著敘述十幾年后打開了這葫蘆,并運用了原因分析與綜合。女子幼貧學戲,二十歲左右小有名氣,所以得以與秦姓少年相好,并接回家中。在秦家是三姨太的身份,受著二姨太壓制,過著奴隸不如的日子,這是背景分析。于是希望為秦家養出一個繼香火的小人兒,這既是因受壓制而借以自慰的果,也是秦家買她過來的因。后來希望破滅,被迫回家,艱難度日。這又是因中有果。后來,種種原因的湊合,秦家又接女戲子回去,也是因中有果。去后更是虐待的厲害,女戲子更想著孩子的夢,這是她堅強承受虐待的原因和心理支撐,也是導致她后來想孩子想的發瘋的原因。敘述的過程,表現出因果式的線脈美與遞進式的層次美。文本至此,還沒有交代清楚為何取名“柳葉桃”的原因。于是接著敘述:柳葉開花之際,秦家滿院桃花,女戲子愛花,并于花下嘆息、哭笑、自語:“柳葉桃,開得一身好花兒,為什么卻永不結一個果子呢?……”整日瘋狀,終至死去。死時滿面脂粉,一頭柳葉桃的紅花。文本的解題運用了人與物的異類相似思維的分析與綜合。桃花的美麗與不果恰與女戲子的美麗不生子相似,都有美麗而讓人憂愁的他相似品性,這也正是文本生長的基點。文本正是通過因果(邏輯)思維、相似(形象)思維進行立意,并在女戲子的不同和反復的遭際的渲染性和反襯性的信息重復中,運用一系列的原因分析與綜合,以剝筍式分析法,層層遞進,脈絡清晰,生成文本。
第二,京派文人寫人的散文,常常呈現輻射式的廣度。以李廣田的《老渡船》為例。文本以渡船堅實,穩固,最適應水面顛簸的象征意義來寫一個老渡船式的人。題目與正文運用了人與物的他相似思維進行立意。而在文本的生成過程中,則運用了多角度分析法的思維操作。文本的前段先總說“他”麻木地安于遇到的一切,整天背負別人的重載,耐勞,耐苦,耐一切屈辱,并無一點怨尤的永被命運渡來渡去。接著,分別通過“職業”、兒子的父親,妻子的丈夫,妻子“朋友”的對手等不同方面展開對“老渡船”的描寫。于職業,一個鐵匠的打“下錘”的伙伴,但更多地又在田里,然二畝薄田,難以維家;兒子“高傲”,看不起他且任意吩咐他;妻子的“朋友”是個強悍,狡黠跑大河的水手,他不勝對手。……他的家庭似一個不斷有閑人來陪那水手和女人閑談的“閑人館”,經常由妻子任意驅使,他永遠忙著,終日勞碌,……如今人老,仍像一只老渡船,負了一身的重載艱難的度日。整個文本的敘述與題目形成了整體上的物與人的異類相似思維的分析與綜合,而文本的內部,為了說明“老渡船”的渡船性,作者以渲染性的信息重復思維操作分別從“職業”、兒子的父親、妻子的丈夫、妻子“朋友”的對手等方面輻射展開論證,此又為事與事的他相似同類相似思維的分析與綜合。這樣,文本基本循著他相似思維立意與他相似思維的分析與綜合,圍繞著“渡船性”,多方面多角度地生成文本。
第三,京派文人托物抒懷的散文,具有著情化式的輔助美:所借之物之描寫,只是起著輔助性、背景性的前提作用,同時多有著象征性的結構形態。如蕭乾的《破車上》,開頭作者即用了象征意味的筆法點出題目的意旨:凡是殘舊了的時髦物件都曾有過昔日的光輝。顯然,文本的立意運用了他相似思維立意,是一種隱喻、象征的思維。接著便敘述了“我們”鉆進一輛破汽車,去看一位垂暮的老人,路途中,極寫了路的艱難,車的嘶喘,且屢次斷氣,并借用途中人物對話的形式寫出破車的象征意味:中國就是輛破車,但車破,可也走得動艱難的路,“出了毛病,等會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癱倒,這才是中國。”顯然,表面寫的是破車,其實寫的是中國,破車的形象就是中國的形象,作者借“破車”來抒發對中國的感情。這顯然又是運用了聯想性的異類相似思維的分析與綜合的思維操作,把中國與破車聯系起來,而文本的生成過程即是通過圍繞破車的“破”和路的“難”不斷地進行渲染性和反襯性的信息重復。
第四,京派文人純抒情性的散文,常常表現為緣情布線,在描繪喜、怒、哀、樂、悲、恐、驚等情感的走向時,如何先鋪設若干情感層次,爾后推出一個情感高潮的頂點層次,便形成起伏式或遞進式的結構形態。如何明顯運用抑揚、褒貶、直曲、疑解等方法,便形成“交互式”或“并列式”的結構體式。如何其芳的《街》,記錄自己一次凄涼回鄉的孤獨感受:回到故土,由家鄉縣城的冷淡陌生,回憶幼年的陰暗與荒涼;艱難地從由讀著經史到縣城初中,學生年齡差異大,自己年小的孤獨;初次看到學生攻擊校長以及自己黑夜被禁,被嚇,被一旅長訓誡等等,第一次學校生活留下的記憶,產生沉默、孤獨、對成人的不信任感;接著,見昨日學校已拆,懷念老校,而眼前的人也盡是垂頭喪氣,失去希望,擔著勞苦的人。至此,作者孤獨的情緒并列式的形成了若干層次,由不同方面把孤獨的情緒遞次強化,這是孤獨產生的原因,整體上運用了原因分析與綜合思維操作,而在這若干層次的內部,則運用了同類相似思維分析與綜合的思維操作,多角度的闡述。接著,作者筆鋒一轉:自己已不再責備昔日同學的發泄,而要重新發現他們的美德。…與其責備他們,毋寧責備那些病菌似的寄生在縣的小教育家們(即校長們)”,“與其責備他們(校長們),毋寧責備社會。“這由人類組成的社會實在是一個陰暗的,污穢的,悲慘的地域。”“當我是個孩子時,已習慣了此陰暗,冷酷,卑微。于是,在書籍里尋找理想、愛、品德與幸福,”“我生活在書的故事里。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夢里。我沉醉,留連于一個不存在的世界。”“對人,愛更是一種學習,一種極艱難的極易失敗的學習。”至此,情感進一步提升,形成了高潮,運用的仍是與前文并列式的同類相似思維操作。文本整體上運用了因果思維立意,而在行文的操作中又運用了同類相似思維,并列式的、層進式的完成對“荒涼與孤獨”主題的渲染生成。
總之,京派散文的賦形結構,所內在遵循的是自洽的凝聚。它常常將一種情緒或一種理念作為賦形的凝聚點,將情感的流動作為散文的中心軸線,去縱橫交錯地吸附和粘連一切使情感得以產生和表現的自然之物,整體呈現出開放自由美和有序凝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