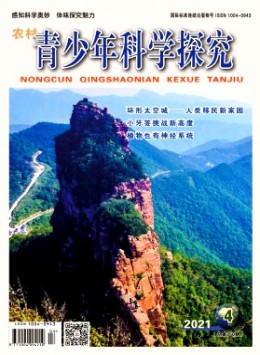探究詞的音樂性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探究詞的音樂性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詞的發展遵循著從民間到知識階層的發展脈絡。最初俚俗的曲子詞,逐漸被文人士大夫所重視。李白的《菩薩蠻》目前還有爭議,但是白居易、劉禹錫的“依《憶江南》曲拍為句”則是標志著詞體的開端,也是曲子詞從民間走向文人創作的開始。可是這些《憶江南》依舊是“以曲拍為句”,具有很豐富的音樂性,這一點是不同于詩的重要特性。晚唐、五代,文人詞有了很大的發展,致力于詞的文人逐漸增多,但是詞還是主要用于茶余酒后,歌筵舞榭的消遣,即便到了北宋初期還是繼承了五代的風格,延續的還是詞的早期用途。當時達官貴人的詞一般也都用來娛賓遣興,如晏殊在宴飲歌樂之余的“呈藝”,歐陽修“聊陳薄技,用佐清歡”的新聲,可見金樽檀板與詞作簡直是息息相關的,可見音樂性依舊占據主導地位。詞的藝術形式還是在傳統與慣性中延續。
到了柳永,詞的藝術形式有了一個小的突破。精通音律的柳永,突破了令詞的羈絆,寫出了長調慢曲,用俚俗的語言來寫作內容。通過柳永的創作可見,詞的藝術形式的豐富還是建立在音樂性基礎上的,因為這些慢曲長調還是要在秦樓楚館里歌唱,既然要歌唱,就離不開音律的限制。但是無論如何,晏殊、歐陽修,甚至是柳永,他們都沒有打破“香艷”的藩籬,詞的藝術解放還是始于針對文學性的變革,代表人物就是蘇東坡。他把詞的藝術形式主要建立在文學上,也就是“以詩為詞”———不僅用詩的某些表現手法作詞,而且讓詞和詩具有同樣的言志詠懷的作用。這樣就改變了詞在音樂性與文學性上的傳統限制。在音樂上,蘇東坡打破了協律的束縛,也就是不再對協律問題亦步亦趨;在文學上,他打破了題材的束縛,使傳統的離愁別苦不再是詞的唯一題材,引入了雄強的詞風,是詞的藝術形式的重大變革。宋人王灼《碧雞漫志》說:“東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但是,這種革新沒有被繼續發展下去,原因是固有的詞寫作觀念還是占據主流思想。及至周邦彥,繼承了柳永的路數,只不過周邦彥的詞去除了柳詞的俚俗之語,在寫作方法上又進一步提高,把柳永的直敘改為曲折回環,變化很多。由于他精通音律,在詞律方面起到了規范的作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所制諸調,非獨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可見,詞的音樂性還是占非常大的比重。(據《宋人軼事匯編》上說:周邦彥得罪了徽宗,被遣出城,李師師送別,周寫了《蘭陵王柳》,徽宗讓李師師唱來聽聽。)直到辛棄疾的出現。辛棄疾是蘇東坡革新的傳承者,他繼承了蘇軾“以詩為詞”的文學主張,突破詞法和音律的限制,甚至到了“以文為詞”的境地。散文化的語言,發而為詞,所描寫的對象題材也寬大了許多,從“閑愁”中擺脫出來,明確了“豪放派”詞風。詞在辛棄疾、韓元吉、楊炎正、陳亮、劉過等人身上再一次實現了從音樂性為主到文學性為主的轉變。南宋后期詞人岳珂、黃機、戴復古、劉克莊、陳經國、方岳、李昂英、文及翁、文天祥、劉辰翁、蔣捷、鄧剡、汪元量等,都延續這一風格,使詞的文學性之提升,成為一種發展必然。
與此同時,不能不提的是,在南宋還有另一派,仍然是以音樂性為主張的詞人,他們繼承了周邦彥的風格,強調以音律為主,姜夔、史達祖、吳文英,以及高觀國、張輯、盧祖皋、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等。這一派別的主張就是“詞以協律為先”,一切創作都要服從協律,他們還強調“雅”的用詞,因此創作所受的限制要多很多。到了元、明代,詞衰頹了,甚至可以說一蹶不振。元代崇尚北曲,明代崇尚南戲,詞徹底衰落了。吳梅《詞學通論》里說元代詞:“而詞之譜法,存者無多,且有詞名仍舊,而歌法全非者,是以作家不多。即作亦如長短句之詩,未必如兩宋之可按管弦矣。”可見,由于詞譜的遺失,詞的衰落首先表現為音樂性的衰落。明代人的主要精神用在了科舉八股上(龍榆生語),所以明代的詞如同元代一樣,也是衰落的,吳梅先生還把明代詞的衰落時期稱為中衰期。清代雖是詞學的復興時期,但無論清代如何復興了詞學,還是不能阻擋詞的音樂性的徹底衰落,詞不再用于歌唱了。即便如此,我們卻不能忽視,詞的音樂性其實是一個泛指,不單指歌唱,后來的詞學因之清代音韻學的發展而對于聲律學的研究又很精細了,加之漢語言本身在韻文上就有音樂美,所以后來的聲律性亦可以算作是詞的音樂性范疇。龍榆生先生在《唐宋詞格律》出版說明里的“由于詞和音樂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從而產生了嚴格的聲律和種種形式上的特點”的說法也可作為輔證。由此可見,音律性和聲律性都是詞的音樂性的體現,是與文學性不同范疇的。現代人賞詞,往往忽略詞的音樂美,只單純的在詞的文學性上下功夫,即使覺得詞讀起來上口,也不屑在詞的音樂美上多加斟酌,這樣賞詞又怎能算得淋漓盡致?這也是本文話題討論的出發點。
(一)詞與音律
詞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上不似詩,下不類曲”(吳梅語),卻與音樂有極其緊密的關系,所以有的學者稱詞是音樂文學。宋人沈伯時《樂府指迷》云:“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可見,詞的寫作如果不考慮音律的話,就是“長短不葺之詩”(李清照語),宋人張炎在《詞源》里也說:“詞以協音為先。”清人戈載《詞林正韻》云:“律不協則聲音之道乖。”可見詞在南宋以前與音律是緊密相關的。什么是音?按照目前普遍流行的西方樂理理論來說就是音名,也就是C、D、E、#F、G、A、B,相對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就是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音。什么是律?按照西方音樂理論,每一個八度都被劃分為十二份,代表十二個不同的音高,即中國傳統十二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七音、十二律可得到八十四宮調,詞的音律就在這八十四宮調里,實際上也不是全部都能用到。那到底如何是詞作不協律呢?這個問題有很多學者都以詞譜已失,避而不談,筆者經過研究,得出主張:漢語言的字在曲譜歌唱中不能發本身音的現象就是古人所謂的不協律。宋代張炎曾在《詞源》里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張炎的父親張樞“每一作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有一次張樞發現自己的詞里“鎖深窗”的“深”字不協,改為“幽”字又不協,最后改為“明”字歌之始協。清代戈載的《詞林正韻》里談及此事云:“‘明’字為陽,‘深’‘幽’為陰,故歌時不同耳。”也就是說“明”字是陽平調,“深”、“幽”為陰平調,所以唱出來是不同的。在京劇藝術里,有一標準是“字不能唱倒”,也就是唱腔中的每一個字都要發字的本身音才行。何為“唱倒”?用歌曲的例子也能說明問題,如歌曲《東方紅》開頭“東方紅”三個字中的“紅”字,在演唱的時候并不是發它本身的陽平調hóng,而是近似于陰平調,如果強行唱陽平,將不得不改變曲譜了。這就是古人所謂的詞不協律的現象。戲曲唱腔中能做到每個字都發本身音就是戲曲界非常重視的“字正腔圓”的標準。清代人黃周星在他的《制曲枝語》里的說法則更為概括:“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
(二)詞與聲律
利用四聲的調節使得文學作品具有了音樂性,是沈約等人最早研究和發現的,這對于中國韻文影響頗深。聲律問題的被關注,并不是在曲譜已失之后才興起的,寫詩只需要分辨平仄就可以了,但是倚聲填詞就不能如此簡單了。在音律關系里我們舉證了“兩平還要辨陰陽”,這里再來說說“三仄更須分上去”。寫詩的時候上去二音都屬于仄音,不需要分辨,填詞的時候就需要分辨了。因為詞由長短句組成,就是要靠四聲的調節來凸顯其音樂性,這里所說的“音樂性”不僅是指詞的音律美,更是漢語言聲律和諧的美。上去二音在古人認為是有區別的,不能完全歸結為仄音。清代萬樹說:“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大抵兩上兩去在所當避。”這個道理不難理解。說去聲“激厲勁遠”,有如《沁園春雪》中的“望長城內外”句,“望”字是去聲,張顯領字的氣勢,可謂“激厲勁遠”,如果換作上聲就沒有了氣勢(但是在目前存在的詞譜上,這個位置只是標明了是仄音),可見詞人們在“一字逗”處總是用去聲標注。宋人沈義父《樂府指迷去聲字》亦云:“但看句中用去聲字,最為緊要。”晏殊在詞作中已經有意識地使用去聲字了,所以說詞至晏殊而始正。說到上聲,可以蘇軾的《蝶戀花》為證,韻腳基本都是用的上聲,讀來回繞纏綿,感情委婉細膩,可見上聲“舒徐和軟”。
再說說入聲。一般認為入派三聲發生在元代,其實不然,在宋詞中早有入派三聲的現象出現,如晏幾道《梁州令》“莫唱陽關曲”,“曲”做丘雨切,葉魚虞韻;柳永《女冠子》“樓臺悄似玉”,“玉”做于句切;又《黃鶯兒》“暖律潛催幽谷”,“谷”做公五切……說明入聲可以做三聲,在宋代已經開始了,但是這種現象正和用方言入韻一樣,是被正統詞派所反對的。在詞的創作中,四聲陰陽的使用是非常講究的,尤其是周邦彥,他在處理三仄的時候,從不是草草了事,讀起來自有一番情趣。因此龍榆生《詞學十講》里評價周邦彥時說:“他對四聲字調的安排,確是能夠符合‘高下抑揚,參差相錯’的基本法則,而掌握得非常熟練的。”說到詞的音樂美,詞韻和雙聲疊韻也是不能不提的。詞韻不同于詩韻,詩韻使用起來很嚴,詞韻則不是,仄聲上去通押,入聲獨立,而且詞還有句中韻,這是詩所沒有的。清代戈載在《詞林正韻》里云:“韻有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呼分開合,音辨宮商,等敘清濁,而其要則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唇,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戈載又把各個韻部分別歸于這六種分類。這樣的分類,正滿足了詞的音樂性的需要。詞的音樂性體現在每一個音節上,所以說詞是音樂的文學。再說雙聲疊韻。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引用清人周松靄之《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說:“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也即是兩字同聲母的謂之雙聲,同韻母的謂之疊韻,這是一種運用聲律來達到詞作讀起來或唱起來音節優美的方法。如李清照的“東籬把酒黃昏后”,如果你多讀多念,會發覺這里面似乎有一種“押韻”的感覺,念起來順口好聽,因為這里面就有雙聲疊韻,“黃昏”就是雙聲,“酒”“后”又是疊韻。可見在美妙動聽的詞作背后,有很多音樂性的規則、理論和創作方法在為詞本身增加藝術性,豈止是文學性的功勞呢?我們今天不說創作填詞,只說鑒賞詞,難道只單單看那些文字嗎?音樂美是文字華麗的外衣上點綴的珠寶,更是文字由內而外氣質的流露,是和詞作文學美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的另一種詞魂。
音樂性與文學性的爭論
宋代,是詞創作的顛峰時期,也是兩大屬性相爭的敏感期。婉約派和豪放派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詞的創作是服務于形式(音樂性),還是服務于內容(文學性)。自詞興起以來,主要是用于歌唱的,士大夫家里的歌妓或者是秦樓楚館的藝妓都在歌唱這些詞作,所以對詞的音樂性是重視的。但是不是說就沒有了文學性的考量,之所以說那時詞的音樂性要重于文學性,原因有二:一是詞是為歌唱服務的,二是題材范圍太窄。詞的樂譜很多,但是題材卻只限閑愁,男歡女愛之情、思念之苦之類。雖然柳永使得詞在音樂上取得了很大發展,但是題材內容依舊跳不出晚唐五代的桎梏,甚至俚俗之詞,香艷之體充斥著詞壇。只有蘇東坡采用了新的填詞方式,看重詞的文學性和思想性,不再考慮是否每一個字都協律,詞不再僅為歌唱服務了,獨立成自有的文學形式,這自然就引起了爭論。李清照《詞論》里說,蘇東坡的詞是“句讀不葺之詩”、“又往往不協音律”。雖是蘇門四學士,陳師道說蘇東坡的詞:“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晁補之和張耒也是不贊同蘇東坡的詞風,晁補之說:“居士詞,人多謂不協音律。”
贊成支持蘇軾風格的也很多,如陸游,他說:“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宋人王灼《碧雞漫志》說:“東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蘇東坡本人也是在意自己的詞作和柳永的比較,宋人俞文豹《吹劍錄》記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為之絕倒。”這段記載看似是個小笑話,其實細細品味就知道,蘇東坡的詞風與當時主流認可的詞風有多么大的區別。試想在秦樓楚館,士大夫的宴席上,誰會讓關西大漢唱歌,還打著鐵板,彈銅琵琶來佐酒呢,這位善歌的幕士也是暗暗地諷刺蘇東坡。蘇軾也很不喜歡柳永的風格,他曾對他的得意門生秦觀說:“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所以龍榆生在《宋詞的幾個發展階段》里干脆就稱“柳永、蘇軾間的矛盾”,甚至說“這都表現了柳、蘇間的重大矛盾和兩派的劇烈斗爭”,由此可見一斑。
南渡之后,由于歌舞升平的生活沒有了,舞榭歌臺,總被雨打風吹去,凸顯的就是民族矛盾。愛國主義情感強大了,于是過去那種男歡女愛的詞風不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蘇軾的詞風隨之引起更多人的共鳴,辛棄疾便是其中一個。但是注重傳統詞風的人還是有的,而且也是大家頻出,比如李清照,她與辛棄疾同是濟南人,但是詞的創作主張卻截然不同,李清照在詞的創作中非常挑剔精致,注重音樂美,后來的姜夔、吳文英、張炎等人,也是音樂性的推崇者,尤其是姜夔,還能自度曲,把工尺譜標注在文字邊上,使之成為留給后人的研究宋詞音樂性的非常重要的資料。倡導音樂第一性,只考慮協律與否,就像張樞那樣,為了協律,把“深”窗、“幽”窗改為“明”窗,為了協律竟與創作初衷背道而馳,這豈不偏頗?直接影響了詞作的文學性和立意。推崇文學第一性,若如同宋代劉過的一首《沁園春》,也如入絕境: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鏡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銜杯。白云天笠去來,圖畫里、崢嶸樓觀開。愛東西雙澗,縱橫水繞;兩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爭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這首詞被宋代人岳珂譏諷為“白日見鬼”,雖然批評得狠,但也是有道理的。它不僅以詩為詞,甚至是以散文為詞了,豪放固然豪放,但是豪放不能粗鄙,詞總歸是一種特有的音樂文學形式,把它弄成散文化,有何意義呢,那就失去了詞的本質和韻味,這也是一種偏頗。
無論是詞,還是別的文學藝術形式,總會有人開天辟地地改革一番,這類改革開始總能被注入新鮮空氣,甚至促成一個派別,創始人總是才華橫溢,集大成者亦總是能夠更準確把握本流派風格的尺度。但總有追隨者刻意模仿,把本來是靈魂的東西方法化,化天賦為技巧,當技巧不能完全替代天賦時,就催生出故意擴大形式的弊病,長此以往,此派的創作之路越走越窄,直至衰落。比如唐代任華,崇尚李白詩風,效仿李白的自由奔放,但他的創作氣勢微弱,沒有張力,只故意夸大李白長短句的形式,將詩寫得很碎,最終未能有所建樹。詞也一樣,豪放派是看重文學性的,但是蘇辛并不是粗野和完全不顧音律。詞發展到今天,即使不歌唱還可吟誦,如果詞讀起來像散文像駢文,那還有什么存在的價值?后來者模仿蘇辛,只強調不講協律,就連文學性也給形式化了,那和只強調樂譜,不敢越雷池半步的音樂派又有何區別呢?同樣為了音樂性而不顧文學性的,也是音樂派的流弊結果。
任何藝術形式,詩詞曲也好,散文駢文漢賦也罷,能觸動人心靈甚至是靈魂的作品,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情”字。我們之所以被藝術作品打動,不是因為它的高難度的藝術技巧,而是被蘊含在藝術作品里的情所打動。清代詩人袁枚說過要“師心”,就是以自己的感情為中心,言為心聲,輔以技巧,才能成就傳世之作。《詩經》單純的語言,樸素的心靈,難道不打動人嗎?所以,當代的詞作者與其在詞的音樂性與文學性的桎梏中掙扎,不如真心捕捉自己的情愫,先嚴格按照譜調來填,真的有心聲召喚,就是違反一些規則也是未嘗不可的,關鍵是真我性情,打動人心。(本文作者:張曉蓉 單位:天津市電子計算機職業中等專業學校)
- 上一篇:論自然主義小說的革命性范文
- 下一篇:語料庫語言學對于英語教學的意義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