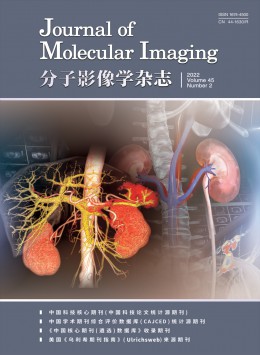影像繪畫的實踐探討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影像繪畫的實踐探討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邊曉剛 單位:宜春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
里希特喜歡那些偶然搶拍或抓拍到的攝影作品,它們大多數是由業余攝影愛好者拍攝的。他曾說:“對我來說,快照都比塞尚最優秀的作品強。”[2]里希特關注的是“平庸”快照這種“洋溢著的生命力”的品質。后來,他還在一次采訪中說:“我用那些所謂的‘平庸’來顯示,‘平庸’的是重要的,是充滿人性的。”[3]照這樣看來,里希特要表達的內容,就是那些看起來表面上不加選擇和無動于衷之后顯示的圖片內容。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平庸”也是他要描繪的“內容”。一些被攝影“復制”的社會現實在里希特的筆下蒙上了一層薄霧,畫面朦朧得就像拍照時因失焦導致的效果,他的作品中不論人物還是風景都沒有太多的表情手勢或故事性,沒有主題,沒有內容,看上去只有那種粗顆粒的油畫質感所呈現出來的美感。當別人問他為何要模糊觀眾的視線時,他說:“我就是想要用一種簡陋的手法來回避這一切。我想讓人明白,這雖然畫的是照片,但并不是辛辛苦苦照著照片畫下來的復制品。當時我的這個意圖是成功的,這樣的繪畫作品保持了與照片的一種本質上的類似性,但又不覺得只是照片的復寫。”[4]
里希特通過照相與繪畫的挪移,以油畫重新詮釋攝影的觀點,以攝影觀念來解讀繪畫。他甚至使用文藝復興的打格放大的繪畫技巧和投影儀,來完善他的影像繪畫,但里希特并不是按照傳統美學標準和觀點來畫客觀對象,而是以客觀的攝影技術來彌補肉眼的偏見,即通過照片的記錄消除主觀的意愿,讓作品顯得寬容和含蓄。里希特用一種近乎機械式的動作與破壞來挑戰根深蒂固的主觀殘渣,他需要的是一種純粹的美感與思想,而不是被教條所約束的規范。里希特還創作了許多抽象畫,用來證明自己的繪畫是在創造照片而不是在模仿照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這些抽象作品是表現主義的,然而它們完全是按照非表現主義的、機械的、客觀的方式制造出來的。那些顏料噴濺、涂抹的痕跡是他用寫實的筆法描繪出來的。表現主義不過是里希特抽象畫的主題,他以客觀的方式為充滿激情的表現主義冷靜地進行了一次造型模仿,就像他模仿一幅照片一樣。
“……如果我輕視認為照片是暴露在陽光下的一張紙這樣的遐想,那么我正在運用其它方法來實踐攝影:我不是在創作使你想起照片的繪畫作品,而是在創造照片。用這種方式來看,我的那些沒有照片來源的作品(抽象畫等等)也是照片”——里希特對此宣稱道。[5]從寫實到抽象,從極簡到極為繁復,從平面到幾何圖象,他不斷地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其創作元素及語匯幾乎融合了所有繪畫基本語法的同時,也將傳統繪畫中諸多因素一一消解了,比如色彩、空間、筆觸、形象、作者的情感等。他從未徹底放棄形象,但又與時尚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一段距離,拒絕被俘虜定位,拒絕理想完美、真實主觀、構造色彩關系等任何想總結他表達模式的定義。在圖像時代,里希特不但沒有放棄繪畫,反而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為繪畫開創了一個可能會生機勃勃的未來,并為世界開啟了一種新的繪畫大潮。
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一書宣告了影像時代的來臨,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也處在了這樣一個時代。近至泛濫式的影像應用已經無所不在,并浸入到物質和精神的各個層面,凸顯出其作為當代文化代表的深刻意義。人們的認知來源從真實的客觀世界轉移到虛擬的影像世界,形成了人們新的視覺經驗,從而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在畫家這里,影像世界已成了他們尋找新創作的資源地,而西方的里希特也已為他們提供了大量優秀的范本。陳丹青說:“當它(繪畫)接納了媒體的影像之后,便不再有理由被認為是失效的視覺文本,它因此確證了自身的價值,這價值,就是繪畫依然能夠調節或校正我們的觀看本能,使之不至于在媒體時代過度迷失”。[6]攝影被認為是復制的藝術,而當代很多畫家對攝影這種復制品進行了繪畫上的“復制”。陳丹青又說:“復制并不是模仿語言。就像演奏樂曲一樣,復制本身就是一種語言。”[7]在繪畫上能否有一種新的超越方式是這些畫家們要面臨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他們借用影像的語言,通過各自的體驗方式不斷地對繪畫進行新的探索。
張曉剛是一位較早受到里希特影響并付諸影像繪畫實踐的當代藝術家。他創作的《大家庭•系列》是其利用照片繪畫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中傳達出中國人具有時代意義的集體心理記憶與情緒,是對特定時代意識形態壓制人個性的批判,是對中國社會、集體以及家庭、血緣的一種再演繹,他挖掘了中國人的生存記憶,給中國人曾經失落的文化形象提供了回眸與反思的圖畫標本。《大家庭•系列》就繪畫資源而言,有照片修版、炭精素描、月份牌、版畫印刷品,以及德國畫家里希特的“照片繪畫”風格也在他的技法資源范圍內,是多種技法的借鑒和混用。在談到繪畫語言和技法問題時,張曉剛說:“我在這張畫上把自己熟悉和習慣的東西一點一點去掉,寫實的技法、表現主義的技法,能去掉的全都去掉。學院派所要求的,要有深度、有色彩、有筆觸,我把它們全都去掉了。剩下的才是我真正想要的。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過程,最后總算找到了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8]張曉剛作品的畫面放棄了筆觸,如同里希特的影像繪畫作品追求一種攝影“復制”效果,他從精心修飾過的具有模式化的舊家庭照片當中,轉換出新的語言,使自己的創作走向成熟。
謝南星是另一位用影像語言進行創作的藝術家。評論家朱其在《迷失在恍惚的視覺不安中》一文描寫道:“謝南星的圖像準確地說是在再現一種物象自身的絕對真實,它的視覺真實體現在細部上,幾乎是在挑戰一種“真實”在技術層次上的視覺極限,由此幾乎使對于“真實”的觀看達到一種眩暈感。在這個層次上,圖像似乎正好處在物象和意象之間。”[9]謝南星的作品描繪了年輕一代人在九十年代內心受傷害的精神記憶,讓人感到有些驚恐的寓言式畫面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謝南星在創作中關注的是對影像本身的制造,他一直在探討影像和繪畫之間的關系,吸收了攝影與繪畫圖像相近性的語言部分,盡量減低人物等敘事元素在寫實繪畫中的作用。他并不使用現成的影像素材,作品內容和人物情緒幾乎全是虛構的,畫面最后處理成像是一張虛焦的照片效果。謝南星在視覺表現力和影像概念上的語言實驗,凸現出他這一代人的藝術在美學和繪畫性上有別于上一代的特征,體現了新一代藝術家對繪畫概念新的理解和追求。但就畫面視覺效果而言,他比張曉剛更接近里希特。當代中國利用影像的方式對繪畫進行新探索的畫家還有很多,如李路明和他的《云上的日子》系列影像繪畫作品,他把從自己經驗中的歷史照片里的人物背景抽離,用白云取而代之,技巧上采用了平涂和虛化。另有畫家李大方的影像試驗,他的許多作品則是搬用影視劇的某個畫面,甚至把字幕也保留下來,使作品帶有敘事性,但畫中戲劇性的場景已失去了上下文的關系,影像原本的意義就得以轉化。
這些影像畫家無一不是從里希特的影像繪畫實踐中獲得啟示。他們從影像中目睹大千世界,把承載視覺真相的影像變得主觀化,在影像繪畫作品中,普遍反映出了對傳統寫實繪畫造型的背離現象,以往學院派要求的體積、空間等繪畫造型和色彩在這里基本失效了,造型問題在選擇影像圖片素材的時候,就已經由選擇的影像形象決定了。影像繪畫彌合了對傳統的寫實與寫意、具體與抽象等這種二分法對理解繪畫造成的分裂,與此同時,傳統繪畫造型的嚴謹性、主題的確定性與意義的深刻性等價值判斷開始變得模糊起來。新媒介和新技術對繪畫的滲透,使得影像繪畫擺脫了以往那種傳統的、單一性的繪畫概念而與大眾文化有著關聯,繪畫本體和繪畫語言能得以擴張,這對繪畫概念既是一種否定也是延伸。影像繪畫已經顯示出它強勁的繪畫生命力,并將有更多機會去體現其文化價值。繪畫從內容到形式上要表達的東西也將更加廣泛,里面依然有著很大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自由地挪用和我們的歷史、日常生活以及與社會問題緊密相關的現成的照片風格來創作,已經成為畫家們的一種選擇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