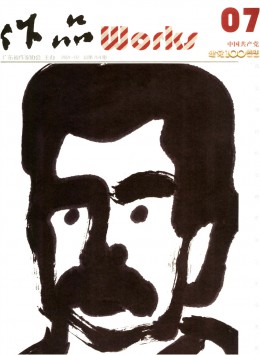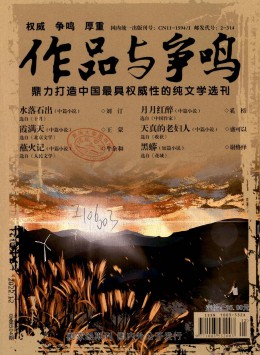里希特作品語言及當代油畫的影響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里希特作品語言及當代油畫的影響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德國表現性畫家格哈德•里希特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語言表現力,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擺脫了傳統繪畫觀念,里希特的作品風格中“照片繪畫”“模糊美學”及“灰色調”等表現性語言深深影響了中國當代油畫創作,構成了“里希特現象”。
關鍵詞:照片繪畫;里希特;中國當代油畫創作;模糊美學
格哈德•里希特,1932年出生于德國德里斯頓,被稱為尚健在的最受敬重的藝術家。他在創作中的勇氣與成功,是世紀之交藝術領域的一個奇跡。作品樣式變了又變,每一次變革都能給世界藝術帶來不小的震動,從浪漫主義、照相寫實主義、抽象主義、構成主義、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之間來回穿梭,從不把自己固定在某個風格領域。里希特對任何流派保持距離,是藝術探索孤傲的勇敢者。早在20世紀60年代,里希特對攝影照片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對照片進行二次創作,但他與美國流行的波普藝術不同,與安迪•沃霍爾選取圖片的取向完全不同,不關心大眾傳媒已有熱度的圖像,而只偏愛日常生活中的私人照片,一些不知名的普通人的生活照。到了20世紀70年代,里希特首次創作一批單純灰色調作品,而在20世紀80年代,他又開始在“抽象構成”摸索了,把一些具象形塊與隨意涂抹的抽象色塊相結合,形成奇異的協調平衡,而之后他的畫面完全拋棄了具體形象的抽象繪畫。里希特如此多變,以至于難以給他歸納哪一類流派,甚至其風格發展脈絡也無法明晰判斷。中國藝術從85美術思潮開始,就有油畫家受到里希特風格元素“照片繪畫”“模糊美學”等觀念影響,如張曉剛、毛焰、李路明、祁志龍等油畫家。這些油畫家從里希特作品中吸取了題材關注、形式語言、畫面特殊處理等元素進入自己的作品中,給當代中國油畫創作注入新活力。里希特旺盛的創造性品格至今還在影響中國當代“80后”“90后”青年藝術家們,這是一種值得思考的現象。
一、里希特作品的表現性繪畫語言
(一)“照片繪畫”觀念。20世紀60年代,里希特廣泛借助攝影藝術作品進行二次創作,被稱為“里希特照片繪畫”(photo-painting)。不過在選用原有照片圖像時,他有自己特有的眼光態度,往往是人們忽視的家庭影集、周刊、板報圖片等,盡量避免大眾傳媒熟知的經典圖片。按他的話說:“1962年,我建造了我的第一個安全窗口:根據照片繪畫創作,使我對從對主題的選擇中解放出來,當然,我不得不選擇照片,盡管如此,在某些程度上我的確可以通過采用具有時代錯誤的圖形來免除對主題的許諾。我對照片的挪用沒有更改,沒有像安迪•沃霍爾和其他藝術家那樣把他們轉化為現代形式拷貝策略。”[1]842里希特以油畫創作詮釋攝影與繪畫的聯系,努力證明架上繪畫不會隨著影像圖片全方位覆蓋而消亡。攝影記錄生活是快捷、準確的,但它永遠有其不足之處,攝影并不能揭示世界本質面目,它只是對這個世界一瞬間的客觀記錄,并不能記錄這個世界每分每秒發生的事,因而相片背后的故事的真實性值得懷疑深思。里希特早期代表作《下樓梯的女人》顯然借用了圖片創作,一個走下樓梯飄逸優雅的女子與硬朗的臺階形成對比,畫面強調了黑白灰的關系,放棄了色彩干擾,單純的圖像給觀眾自由想象的空間。1968年,里希特創作的《48幅肖像》群像作品標志著畫家作品風格成型,他走向德國藝術的前沿。《48幅肖像》,這是他從百科全書中挑選出48位非常有才華的人物肖像組畫,尺幅相等、黑白灰色調相同、構圖相似等重復的因素把這些不曾謀面的人物距離拉近,讓他們定型在同一尺度的描繪中,這是肖像畫嶄新的嘗試。里希特作品游離于繪畫與攝影照片之間,開辟了架上繪畫的另一種可能。因而畫家偏愛那些留下技術缺憾的照片,如過度曝光、虛晃、曝光不足和缺乏焦距的照片,為的是擺脫照片的紀實性以獲取作品繪畫性因素。(二)“模糊美學”與“黑白灰色調”。里希特繪畫表現性語言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模糊技法”和“黑白灰色調”,評論家把畫家特有的模糊性語言效果稱之為“模糊美學”。里希特創作過程中一直保持著“模糊”手法,并且以不同的工具手段試驗著各種“模糊”視覺效果。常用的方式,他將篩選出來的照片反射投影到畫布上進行放大,沿著邊線勾勒出圖形,著色之后,用軟筆刷或橡皮刮水刷趁顏料未干進行平刷,使整個畫面變得模糊不清。《下樓梯的女人》《米蘭的教堂廣場》《舅舅魯迪》《海德先生》等作品都是畫家“模糊美學”典型代表作品。這種特殊的體驗,給觀眾產生不同的心理暗示。里希特說:“我把事物畫得含糊不清,很難判斷其他事情是否重要,使物體看起來不像一種藝術,而是一種使其光滑和完美的技術。這項技術我可以使它忽略掉很多信息。”[2]這樣,將畫面原有的歷史感與現代感完美結合,照片作為主體并模糊處理,近似于真實卻與真實有一定差距,讓觀眾所看到的仿佛是記憶中的場景。里希特不斷嘗試,不斷改進制作工具。近些年,他特制了一種巨型金屬刮水刷,在未干的畫面中整體從一側推刮到另一側,讓色層混合滲透,出現奇異而模糊的色彩肌理。有時會反復推刮,在模糊中尋找新的可能。他曾說:“我在創作作品時,事先不知道它會變成什么樣子,也不知道我會將它變成什么樣子。”[3]無彩的“黑白灰色調”是里希特繪畫語言的另一特點,朦朧的黑白灰基調在創作中不斷演示。里希特在創作中盡力回避作品形成的個人化的情感色彩,把主題、觀念、情緒、風格等自覺意識降到最低限度,變得冷漠無情。最能體現這種狀態的就是黑白灰的灰調。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里希特用灰色和黑白的圖片表達身邊的事件,強調不夾帶情感的真實。他在作品中保持自我情緒中立,他認為,紛繁的色彩會將畫面引向某種感情宣泄,干擾作品內在真實。里希特在筆記中記錄了灰色的統治地位及其描繪出來的事件本質優先地位:“我只是對灰色的平面、層次過渡、色性、布局、轉換、重疊等感興趣。如果我可以不利用物體作為這種構造的支架,我會馬上去畫抽象畫。”[4]盡管如此,里希特作品仍然品讀到某種情感,如作品《魯迪叔叔》描繪了一位身穿戎裝的軍官站在照相機前,表情是喜悅的,但卻不知道生命定格在1944年七月戰斗中。還有《瑪麗安娜阿姨》描繪的是1932年6月瑪麗安娜和她尚在襁褓中的外甥在花園親昵的姿態,但瑪麗安娜卻不知道她外甥日后將死于1944年內納粹黨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中。這類作品看似平淡,卻在灰色布局中營造了陰郁的氣氛以及發出了“死亡”無常警示。
二、里希特繪畫藝術對中國當代油畫創作的影響
中國當代油畫創作有相當一部分畫家運用到里希特繪畫語言,采用照片繪畫、灰色調、平涂及模糊技法進行創作,可以說背后都有里希特的影子,被稱為“里希特現象”。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油畫創作以照片為媒介的模糊化表現及黑白灰色調技法得到部分畫家借鑒。畫家張曉剛采用老照片創作的方式直接來自里希特的語言影響,并獲得成功。張曉剛采用了里希特“黑白灰色調”及“模糊美學”語言方式,但他把目光投放到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通過那個年代的家庭合照來窺視“”時代的特質及人的生存狀態。如《血緣•大家庭》系列作品,畫中人物,具有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人所特有的表征:全家福合照、中山裝、瓜子臉、單眼皮以及那個年代特有的呆滯表情。畫中人物仿佛是父母面孔隱約浮現,緊扣觀者心理。張曉剛抓住了一個逝去時代的脈絡,那種特有的呆滯表情及驚覺的目光仿佛凝結了中國人特有的心路歷程。《記憶與失憶》《同志》《血緣•大家庭》系列作品深刻折射出張曉剛對人性及社會倫理的關懷。他曾說:“血緣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擊。”血緣與家庭的關系構成了張曉剛作品的主線。畫家李路明《云上的日子》系列作品,也采用模糊手法及黑白灰基調,虛化的背景似乎是歷史的一個片段。李路明的繪畫同張曉剛一樣帶著對“”時期的審視,再現了自己的經歷、思考和回憶,以表對逝去青春的留念。油畫家毛焰作品主調離不開黑白灰冷色調,人物塑造追求的是模糊朦朧的擴張顯現。但他與張曉剛和李路明不同,沒有把作品當作對過去時代的記憶及追思。他極力隱藏了作品中人物年代、身份及性格。其作品人物獨特之處在于那系列神經質般的人物肖像,呈現出怪異的角度、失神的表情,再加上空洞的、無物的背景,仿佛觸及生存狀態的幻滅、墮落。可見毛焰只從自己的心靈深處尋找生命的答案:一個孤立存在的生命最終呈現的方式是幻滅,是悲劇性。被稱為“鬼才”的毛焰本人氣質是孤寂憂郁的,他借助一個沒有本土身份及特征的西方人———托馬斯,來表達看待世界的態度。毛焰幾十年如一日地畫著朋友托馬斯的肖像,奇異的視角、虛朦的五官、冷漠的灰調等畫面元素,卻在提示作品最深處的指向。
三、對于借鑒里希特繪畫藝術的思考
前文綜述了中國當代畫家張曉剛、李路明、毛焰等幾個重要畫家創作情況,他們都能充分詮釋自己的創作觀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們都成功汲取了里希特作品某些元素融入自己的創作中。他們在借鑒中沒有停留在里希特技法表面,而是從本土文化及內心觀念意識挖掘創作源泉。總之,里希特對當代中國油畫創作產生不小的影響,至今仍然不斷掀起追捧熱潮。這里要強調的是,有很多畫家只是從里希特的技法材料上單純模仿,沒有深層理解里希特創作思想動態,不從內心出發看待自己的創作,顯然這是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弊病。當下是信息量發達、圖像化盛行的時代,創作者更容易迷失創作的思路,形式濫用、簡單拼湊、過度模仿、缺乏創新意識等像一股濁流充斥到中國當代藝術創作隊伍中。因而,正確領悟、正當利用才是借鑒學習的健康之路。對于任何一位大師的模仿,不僅只是學習外在形式,更應當運用本土文化元素、更豐富的技法、融會自己的個性特點,挖掘自己的內心訴求,創作出彰顯時代精神風貌的作品。目前對里希特繪畫的借鑒,很多創作者都沒有創新,僅僅停留在“模仿”“復制”的表面,如里希特模糊技法、灰調、照片挪用等,很多只是簡易、機械地模擬,缺乏自我深刻的認識。這種缺乏探索精神的拿來主義會影響創作活力,制約創造想象空間。里希特本人就是勇于突破傳統,不重復前人也不重復自己的藝術家,拿他的話來說:“我的藝術是對破壞的總結。”[5]這就告誡了人們藝術創作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也告誡人們對前人的借鑒必須尊重自己的內心,切勿簡單模仿。
參考文獻
[1]朱其.1986年筆記•形象的模糊———里希特藝術筆記和訪談[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52.
[2]朱其.1964—1965年筆記•形象的模糊———里希特藝術筆記和訪談[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7.18.32.
[3]潘羅斯.畢加索生平與創作[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54.
作者:齊增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