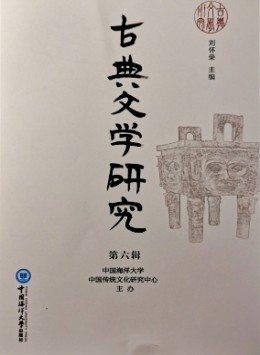古典文學詞學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古典文學詞學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詞,一代之盛,是一種與音樂相結合、可以歌唱的新興抒情詩體。研究唐宋合樂歌詞,不能忽視詞與音樂間的關系。在古典文學領域,施議對的《詞與音樂關系研究》是具有開拓性意義的詞學研究成果。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唐宋合樂歌詞概論”,作者站在“史”的高度,考察詞體的發展演變過程及其依賴的社會環境,論證詞的發展離不開音樂的制約和影響。中卷“詞與樂的關系”,主要論述詞與音樂既相互統一又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強調詞的性質、聲律特征源于音樂的賦予,而詞與音樂的關系變化對詞體的演變和特性有重要影響。下卷“唐宋詞和樂的評價問題”,總結唐宋詞和樂的歷史經驗,從藝術發展規律入手,分析詞與音樂兩種藝術形式的異同及分合的利弊。本文以施議對的《詞與音樂關系研究》一書為藍本,探討該書的核心理論、獨特研究視角及其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啟發。
一、微觀中現宏觀的演繹法
《詞與音樂關系研究》擅于將宏觀研究和微觀透視相結合。宏觀研究和微觀透視,即把研究對象置于廣闊的社會文化大歷史背景下進行透視分析,深入挖掘各個小問題,最后進行整體性的宏觀把握。施議對以翔實的材料為基礎,對詞和樂的關系作了較深入分析,從中尋繹出某些規律性。關于詞體的產生、發展、演化、蛻變正是這種方法的有力嘗試。詞體的產生存在多種說法,無論“詩余說”“樂府演繹說”,還是“和聲說”“泛聲說”,都說明詞體的產生與音樂相關。施議對認同這一觀點,但對詞體的產生時期存有異議。關于詞體的成立時期,以往學者只注重詞的形式、格律標志,忽視合樂應歌標志。通常,人們以朱熹“逐一添個實字,逐成長短句”及《詞譜》“字之多寡有定數,句之長短有定式,韻之平仄有定聲”等格式規定,作為辨別詞體的依據,判斷詞體產生的時代,這是片面的。施議對從詞體成立的兩個標志推測成立的時期。這兩個標志,一個是長短句歌詞的出現,另一個是由歌詩向歌詞的轉變。梁啟超以梁武帝《江南弄》為例,證實詞起源于六朝;劉大杰認為,梁武帝所作“還不能算嚴格的詞,可看作是由詩入詞的過渡形式”,提出詞體正式成立及其迅速成長是在中晚唐時期。唐奎璋經過確證《泛龍舟》七曲為隋曲,斷定“有樂曲就有歌辭,這是詞起源于隋的具體依據”。施議對認為,上述觀點雖然有一定依據,但缺乏科學判斷。他指出,考察詞體產生的時代,不可離開歌詞合樂的具體背景。梁武帝《江南弄》七曲,其一曰:“眾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從格式上看,《江南弄》已成固定句式、韻位,但依然是詩歌形式,沒有合樂,且與合樂長短句歌詞有區別。《泛龍舟》《穆護子》等七調,皆為隋曲,也可能都帶歌詞,但僅僅是偶然嘗試,由歌詞之法代替歌詩之法,隋朝樂壇尚不具備。從清光緒二十六年發現的敦煌遺書記載看,許多民間歌詞已經是比較定型的長短句歌詞格式。如《云謠集雜曲子》里《破陣子》四首,無論格律形式還是內容,都為中晚唐文人的創作提供重要來源。李白的《菩薩蠻》《憶秦娥》,被認為是文人詞的開山之作。張志和的《漁父》、劉禹錫的《竹枝歌》等都是模仿民間歌詞的典型。晚唐時期,溫庭筠大力填詞,成為第一個專業填詞的文人。隨后出現歐陽炯、韋莊等一大批花間詞人。到南唐,“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施議對通過分析歷史材料,結合長短句歌詞產生的兩個標志進行綜合考察,得出“詞體興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時期進一步發展成熟”的結論,并從歷史實際出發,既充分肯定民間創作對詞體產生的開創之功,又充分估價文人才士創作確定詞的歷史地位作用,避免了詞論的片面性。正是基于對詞體形成演變的宏觀研究,施議對對詞體蛻變這一問題采取了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論,對學術界流行的一種說法,即認為至南宋時,詞樂失傳,詞與音樂關系脫離,詞已逐漸衰亡,施議對“大膽假設”這一說法的錯誤,并列舉大量事例,證明詞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蛻變”。而且,在廣大民間的娛樂場所,唱詞形式更加豐富多彩。鼓子詞、諸宮調、唱賺的大量出現,加速了南宋合樂歌詞的蛻變。所謂“變”,即一部分逐漸擺脫其對外在音樂的依賴,進一步蛻變為獨立的抒情詩體。南宋作家和作品數量遠遠超過北宋,內容和藝術領域也有新開拓;或繼續與音樂相結合,“變”而與民間“小唱”合流,成為元曲之先聲。施議對“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論證詞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蛻變”,有力回擊了“宋衰即詞衰,宋亡即詞亡”不符合歷史史實的謬論。
二、歷時與共時的辯證法
在論述“詞與樂的關系”時,施議對始終堅持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指出處于一定關系中的事物是普遍聯系,相互作用的。他不像近代某些論者,只看詞受制約的一面。劉堯民在《詞與音樂》中說:“音樂是詩歌的靈魂,所以詩歌自然是要追隨著音樂,以音樂為標準。”突出詞對音樂的依賴;胡適在《詞選》序里指出,“重音律,不重內容,詞的末運已不可挽救”,過分重視詞的獨立性,廢棄音樂。然而,施議對力排這兩種意見,辯證看待詞和音樂的關系。施議對從大處著眼,整體把握,把我國詩歌與音樂關系的演進變化歸納為“以樂從詩”“采詩入樂”“倚聲填詞”三個階段。特別指出,“倚聲填詞,言出于聲”是詩和樂重新進行更高形式的結合,無論“質”還是“形”都體現燕樂的情調,音律特征。施議對認為,詞作為音樂文學,受燕樂的制約,但同時燕樂的格律、音韻又賦予詞的特性。只有兩者結合,音樂性才能成為詞最重要的藝術特性。同時,施議對運用“歷時和共時”的研究方法,從“史”的高度對詞與音樂關系的發展流變進行全面考察,幫助讀者探尋詞的內部規律。從共時角度看,注重同時期作家在一個橫斷面上對其歌詞創作進行平面考察;從歷時角度,注重作家對詞體的發展演變歷史所作的貢獻和成就。“歷時和共時”研究方法的運用,既擴大了本書理論的覆蓋面,又給讀者一些新的啟示。在《詞與音樂關系研究》里,施議對論述詞與音樂的關系經歷了由民間到“尊前”“花間”,再到“閨閣”,最后走向多極化的過程。同時,以這一變化關系為主線,對詞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作用的作家進行分析,從而給予中肯評價。
三、跨學科視角的創新性
黑格爾指出:“藝術家之所以成為藝術家,全在于他認識到真實,而且把真實放到正確的形式里。”長短句歌詞便是宋代藝術家體現“真實的正確的形式”。詞表現音樂的情感內容,音樂賦予詞藝術形式。施議對從藝術發展規律入手,運用美學思想挖掘文學與藝術的美,總結唐宋詞合樂的歷史經驗,分析詞與音樂兩種藝術形式的同異及其分合的利弊問題。唐宋詞合樂,詞借助于音樂,增加其藝術表現力及其審美價值;音樂又借助詞,使情感表現更明確、具體。但詞與音樂畢竟屬于不同的藝術形式,二者有各自的發展規律和獨特性。如,以是否入律可歌定優劣,只顧音律,不管言詞,使歌壇上出現了許多“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的作品,大大削弱了詞的藝術感染力;而有的雖是好文詞,卻“不協律腔”,把詞引向雅化、凝固化的道路,阻礙詞的健康發展。從藝術和文學觀點看,這些都不利于歌詞和樂曲發展。這個認知,對今天的新詩、歌曲創作仍有借鑒價值。施議對對建國以來普遍流行的“音樂束縛論”和“聲律無用論”兩種觀點進行批判辯駁,從而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例如,蘇軾革新詞體,轉變詞風,詞史上稱為“以詩為詞”,論者多認為是“打破詩詞界限,沖破音律的束縛”。然而,施議對認為,這是詞與音樂的一次調整。蘇軾處理詞與音樂的關系態度嚴謹,其作品大部分入律可歌,且對聲律及唱法尤為講究,是“以詞為詞”的當行作家。辛棄疾全力為詞,諸多論者多以“愛國主義”和“豪放”概括辛詞成就,以宣揚音樂束縛論,這是有失偏頗的。辛棄疾以詞為武器,多抒發愛國情感和戰斗精神,富有現實意義和英雄氣概。而藝術風格多樣化,仍十分注重歌詞合樂的效果,“以用字奇橫而不翻音律”和“以尋常語度入音律”,是“聲學”行家。另外,對南宋詞人姜夔、吳文英、張炎,建國以來論者多貶大于褒,而《詞與音樂關系研究》實事求是地評價他們對詞作的貢獻和功績,指出他們“為詞在形式特點上體現其音樂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對于維護詞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這些都是反駁“音樂束縛論”的例證。對“聲律無用論”,施議對從詩歌與聲音的歷史發展演變中,肯定聲律的重要性,指出長短句歌詞中,決定詞性特征和價值的首先是文詞,其次是格律聲調。著重強調聲律不是無關緊要,而是體現詞的最重要的藝術形式。
四、結語
施議對《詞與音樂關系研究》探討詞的文學形態與其它藝術形態的關系。這一方法的運用拓展了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空間,有一定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施議對的詞學研究并不僅局限于歷史考察,而是與時俱進。同時,施議對還提出“李清照的‘詞別是一家說’、王國維的‘境界說’、吳世昌的‘詞體結構論’為中國詞學史上的三座里程碑”的論題。這三種批評理論模式的提出是當今詞學研究的新突破,在學術界引起極大反響,對未來詞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作者:王艷梅 單位:重慶人文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