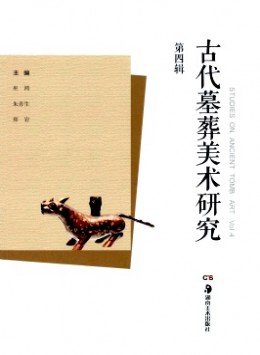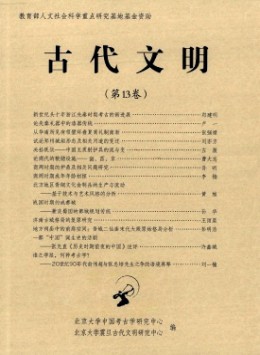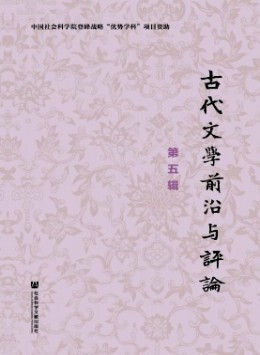古代文論的研究思路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古代文論的研究思路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儒道釋相結合。儒、道、釋三家思想形態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主體,是中國古代文論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古代文論中的范疇、命題以及演變規律等均需溯源于此,是古代文論具有獨特民族性格的傳統淵源。因此,對儒、道、釋思想沒有深刻了解之人,是無法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著者有著深厚的國學修養,對儒、道、釋思想皆有深究,這使得其研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開闊的視野。如對中國古代文論中藝術直覺和審美意象生成的研究,就是在考察儒、道、釋諸家思想的基礎之上,拈取相關文論進行析論的。著者指出,作為藝術直覺的動態心理形式,“虛靜實質上就是藝術直覺在進行創作活動時,主體心靈靜極而動、動極歸靜的辯證運動的心理歷程。”[2]1然后就其結構及動力因素展開論究,得出“藝術直覺,是中國古代形而上的藝術論的建構核心,它以老莊的直覺思維方式為導源,以虛靜為其動態心理形式,強調心靈的空明寧靜,而不流于幽昧的平板死寂……”[2]12對藝術直覺的形成及其運行過程作了充分的揭示。這一研究主要是以老莊哲學為背景,且建立在對中國古代文論形而上精神的準確把握之上的。
中國古代文論具有形而上之品格,是儒、道、釋思想深入滲透的結果。著者認為,“中國形而上之藝術理論,氤氳著道家、禪宗的玄遠靈動的精神;重‘體悟’的藝術精神與莊禪之道,可謂脈脈相通,息息相應。”[2]13因此,對中國古代文論中藝術直覺的研究,只有從道、禪思維方式切入,才有可能接觸其本真。著者在嚴羽《滄浪詩話》中拈出兩組看似矛盾的命題,以此入手仔細甄別道禪致思方式的特點及其在詩論中的運用,對藝術直覺的整體性、直入性、非理性、模糊性等諸多特征作了透徹的分析,形成最終的結論,“所謂藝術直覺就是指審美主體高度濃縮推理過程,超越理性思辨,對審美客體所作的模糊整體性的直入本質的審美觀照”[2]26。這一結論無疑凝聚了著者對莊禪智慧精神的深切體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儒、道、釋不是截然相分,而是相互融合的。如魏晉玄學就融合了儒道思想,禪宗也是印度禪學和道家思想結合的產物,宋明理學雖號稱“新儒學”卻也整合了道釋之觀念。它們對不同時代的審美理想、藝術風尚的形成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并通過對主體心靈的作用滲透在中國古代文論的各個命題、范疇以及審美趣味中,左右其流變。如著者在《從山水到美人的藝術變奏》一文中深入探討了玄學、佛學與南朝詩風的演進關系,揭示了南朝詩風流變的深層原因,即玄學、佛學對詩人審美心理的深刻影響所致。儒、道、釋之間相互融合使得中國古代文論意蘊極為深厚。同一命題、范疇在深受三者影響的文論家或著作里其內涵各個不同,面目各異,故在研究時既要別異,又要合同,更要深溯它們之間的歷史聯系。著者在研究《樂記》中“遺音遺味”說時就是循此思路,溯其源流,考各家同異,認為本于儒家禮樂文化而產生的“遺音遺味”說,其影響在于東晉以后形成“以味論藝”之風氣,而其淵源則是受到古代飲食文化和儒道釋思想的共同作用[2]177。這一研究,對揭示中國古代文藝審美觀念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詩書畫樂相結合。中國文學草創之初就是詩樂舞一體,中國古代文論的發端也是以詩論樂論相通。漢魏六朝之際,詩書畫樂在表現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為人們所重視,入宋之后,在理學“理一分殊”思想影響之下,人們更是自覺注重詩書畫樂等各門藝術的相互貫通,以畫論詩、以書論詩等現象紛紛出現,至清代,桐成派后學中堅方東樹在遍閱諸家詩話的基礎上予以總結:“詩書畫樂理一”①。可以說,注重各門藝術相互影響是中國古代文論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為注重中國古代文論中詩書畫樂之間的貫通研究。前文論及《樂記》中的“遺音遺味”說,即是從樂論的角度來研究古代文藝理論批評中的“以味論詩”的現象。著者認為,“中國古典詩歌最主要的兩大特征就是畫意與樂感”[2]51,并分別從“畫意”和“樂感”來探討中國古代文論中關于視覺審美意象和聽覺審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現,對詩與畫,詩與樂之間的關系等作了系統的研究。著者從視覺、聽覺等審美感官來研究古代文論并提出“感官詩學”這一課題,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它對揭示中國古代文論的藝術精神及古代文學所具有的藝術美無疑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畫意:視覺審美意象生成表現論》一文中,對中國詩歌的畫意問題從視覺這個感官角度進行了討論,提出“直視”、“懸視”、“內視”三個視覺審美范疇并以之作為切入點,對中國古代詩學審美意象的營構方式及其過程進行論究。“直視”是“物沿耳目,臨景結構”,“懸視”是“登高遠眺,籠罩全景”,“內視”是“視境于心,物在靈府”,詩歌創作是詩人借助“直視”,“懸視”或“內視”來觀物取象(境)而創作出來的,由此得出“中國古代詩歌的鮮明“畫意”性與詩人的視覺審美經驗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2]49的結論。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古代藝術追求“遠”的創作精神及中國古代詩歌的“畫意”性特點的根源。著者認為,“書畫藝術創作的不同,與文學創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響、相互貫通、并生激蕩的。”[2]136據此,著者常將古代文論置于哲學、宗教、繪畫、書等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進行綜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學地理學時,就充分注意到禪宗的南頓北漸之別對中國畫論、書論的影響,認為:“以南北宗派來區別畫學的南北流別,這種思想又深刻地影響了文學創作及其理論批評。”[2]132六朝文論向來是著者治學的重點,與之相關的研究最能體現這一研究特點,尤其在關于《文心雕龍》的研究上,著者認為,“從《文心雕龍》創作論方面,我們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時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對書、畫、樂等藝術理論觀點吸取和包容的特點。”[2]209故對其進行研究,也是本著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龍》與《六朝審美心物觀》一文中,著者將樂論、畫論和文論結合在一起,以《樂記》、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宗炳的《畫山水序》及陸機的《文賦》為主,對六朝審美心物觀演變過程及其對劉勰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該文將詩書畫樂與儒道玄釋融為一體,堪為著者治學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論、考相結合。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學的發展面臨轉型的問題。人們提出諸如語言學轉向、主體性轉向、文化學轉向等諸多觀念,體現了當代文藝學研究在困境中尋求突破的努力姿態。其實,無論怎么轉向,都離不開對歷史文本正確解讀。因此,對中國古代文論來說,應該向文獻學轉向可能更為合適。中國古代文論雖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卻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是對文學創作活動進行總結而形成理論體系。中國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滅物我的審美心態,以及觀物取象、立象盡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國古代文論上就是詩性話語這一特征。隨意性的、體悟式的意象批評到處可見,這使得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不像西方文論那樣思辨嚴密、概念明確,往往難以確解。因此對古代文學作品和理論文本進行歷史還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論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側重于“史”,或立足于“論”,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論、考相結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說必考之有據,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論自身的邏輯性,自足性。這使得本書立論尤為平實,公允。如在《司空圖“味外之旨”說新論》一文中,著者對古典詩學中的“味”、“韻”、“境”等范疇,既從“史”的角度進行梳理,探其流變,又作“論”的剖析,尋其真義,并對“味外之旨”說與禪學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大致說來,著者精于考證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證為主的研究,如《司空圖家世、信仰及著述問題綜考》、《司空表圣詩集輯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論,考論結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證。后者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論中帶考,析論之中,凡所征引,務求真解。如《〈樂記〉“遺音遺味”說及其審美觀念之發展》一文,先就《樂記》編撰問題進行一番考證,既為論題“遺音遺味”說奠定可靠的文獻基礎,又解決了其淵源問題。在探討《文心雕龍》中的儒學思想時,對其古文學派的立場及其對今文學派的統攝與汲取,既對《文心雕龍》本身之觀點進行辨析,又考征他說予以支撐。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證釋。注釋是對論證進行進一步的補充和說明,其本身就是論證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著者極其注重注釋的嚴謹和規范,并常加按語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詩的首要意義就在于,它是后代詩人妙悟自然,尋覓本體意義的山水詩的先聲”后,所加注釋就引《世說新語》之《文學》第85則劉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評孫綽、許詢詩,以及評價東晉玄言詩之說對此作進一步說明,并結合《文心雕龍》相關篇目加以辨析,認為:“檀道鸞只是說玄言詩風,‘謝混始改’,但開始逐步向山水詩寫作過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轉而說是玄言詩孕育了山水、田園詩。”[2]95這種注中考的方式,既強化了論證的力度,也強化了研究的深度。
在對中國古代文論進行宏觀研究時,需正確處理古與今、中與西的關系,使自己的研究避免流于庸俗類比、庸俗闡釋,當為研究者所重視。著者曾從文化傳承和學科建設的高度給予思考,“當我們在反思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承和建設當代文化時,我們應該更多地深入思考中西古今之通的問題,并將之切實貫注到我們文藝學研究和建設之中。我國當代文藝學的建設,不僅要注意古今之異、中西之別,更要考察古今之同、中西之通”[3]。其研究途徑是,“我們應該立足于‘古’與‘中’,究明其本來意;而又要放眼于‘今’與‘西’,闡釋其現代性,區別其差異,也注重其會通”[3]。那種過分地強調古為今用,西為中用,難免會產生強加古人的流弊,最終會導致傳統文論“個性”的丟失。鑒于此,著者在研究時,立足于古代文論本身,博考諸文,以究其實。又貫通古今,察其流變,在中西對話中彰顯其民族性、發掘其文化精神、闡釋其現代意義。如對中國古代文論中有關藝術直覺理論的研究,著者從嚴羽提出的詩要“妙悟”而又“不假于悟”以及“別材”、“別趣”與“書”、“理”相關而又不得不相關這兩組“悖論”入手,認為其“既指出了‘妙悟’非理性的特征,但也不排斥其理性的作用,就較為接近現代文藝哲學中的‘直覺’范疇內涵”,因而“比司空圖更具有現代意義,他的兩大命題已點到了藝術直覺最主要的特征”[2]14。這一見解顯然是以現代藝術哲學中有關藝術直覺理論為參照,旨在分析以該命題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直覺理論的現代意義,從而把古代文論與現代藝術理論貫通起來,使得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藝術直覺理論的現代性及其特征得到充分揭示。
“區別其差異,也注重其會通”即是將中西文論視為同等的主體,進行比較,以示其同異,并沿著既定目標進行相互闡釋,使之相互融通。這樣既保證了中西文論各自的文化性格,又避免了簡單的比附,隨意的肢解。著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文論關于“藝術直覺”理論時,曾引美國文論家阿恩海姆、柏格森以及蘇珊•朗格等現代西方思想家、文論家的直覺理論進行剖析,但并不只停留在中西文論的異同層面,而是注重它們之間的會通之處。這種會通研究就有這樣的研究意圖,即對藝術直覺的“直入性”等諸多特征的認識,雖屬于現代西方藝術哲學之發現,中國古代文論卻早已有之,這一發掘,使得中國古代文論在世界藝術理論史上的創造性價值得以凸顯。注重中西文論會通在研究效果上主要有三點,一是在古今貫通中彰顯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二是揭示古代文論在思想史上、文化史上的存在價值;三是揭示中西文論作為人類精神成果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影響。這三點往往是同時并存的。如在研究中國文學地理學時,著者就注意到“西方文學地理學的提出和研究就間接受到中國古代有關這一方面的學說和理論文獻的影響”[2]146,從而把現代西方文學地理學的創立與中國古代文論聯系起來,既有揭示中西文論之間的相互聯系,又有借此顯示中國古代文論對現代中西方文論的創造性價值之目的。著者認為,“因為中西文化交融創生,如果完全泯滅差異的‘同’就不是真正的‘和’的理想境界;只有堅持‘和’而不‘同’才能真正邁上全球化的理想發展之途。對無比豐富的中國傳統文論進行現代闡釋,必須遵循‘和’而不‘同’的思想方法。”[2]276(《王國維‘境界’說的傳統曲論資源》)這種‘和’而不‘同’的研究方式,應該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者必須遵循的一項原則。
荀子《正名》篇云:“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著者正是懷此三“心”來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工作的,故其所論多有真知灼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叢稿》雖只是著者部分研究成果之結集,但著者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上的創新據此可略見一斑。如在感官詩學、文學地理學等方面,著者身居前沿,有拓荒之功,非本文之所盡論。著者學有正脈,相繼稟受著名文論家梅運生、祖保泉、張少康諸先生之真傳,又親聆王元化等學界前輩之教誨,故其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多有建樹,實是有其淵源所自。上文所論是著者經多年學術歷練而形成的系統的治學方法,其中自然凝聚了學界前輩的治學智慧。因此,該書的問世,其意義不僅是推動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走向深入,亦為治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治學范式。(本文作者:郭青林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