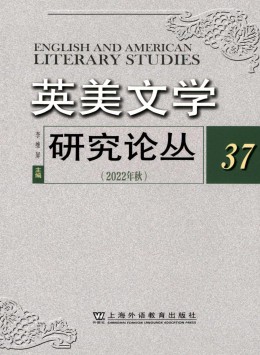英美詩歌論文:英美詩歌中存在主義解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英美詩歌論文:英美詩歌中存在主義解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逯陽 單位:大連外國語學院
宗教與自由的艱難選擇
羅塞蒂的詩歌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描寫信仰、受難與禁欲等宗教主題的。對宗教的眷戀,使她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宗教情懷。比如她在《圣灰星期三》中寫道:“耶穌,我愛你嗎?你的愛太遙遠,我夠不著,她躲在天堂的光里。”[4]在這首詩中羅塞蒂反復地吟唱“天堂”,希望身后能升入天堂,但又擔心自己得不到上帝的眷顧。羅塞蒂的這種復雜、矛盾的心態其實是對現實存在不滿的反映,一種寄希望于來世的表現。通過詩歌,她在反復質問耶穌的愛為何離人如此遙遠。可見,羅塞蒂對耶穌已經產生了懷疑,這不是一個普通教徒所能做到的。站在耶穌面前的羅塞蒂,儼然已具有了存在主義覺醒意識。在另一首名為《修道院門檻》的詩歌中,羅塞蒂借用“修道院門檻”這一意象,象征性地表達了自己面對宗教和自由之間的矛盾心理。這也說明了羅塞蒂并非是一個“潔白無暇”的修女,她也有強烈的個人理想和對自由的渴望。“自由哲學”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中心思想。“我命定是自由的,這意味著,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們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別的限制,或者可以說,我們沒有停止我們自由的自由。”[5]羅塞蒂在詩歌中對自由的吶喊是她萌發存在主義意識的表現。
存在主義哲學認為上帝是不存在的。人對自己行為的自由選擇是人的本性。人有選擇自己信仰的自由。狄金森眼中的存在也有類似的特點,在她看來存在應該是擺脫依附、自由選擇的存在。可是,狄金森對宗教的態度并不是簡單的否定或排斥,而是同樣充滿了矛盾與困惑。她生活在有著濃郁宗教氛圍的新英格蘭。在其家鄉阿默斯特小鎮,加爾文教統治著人們生活的各個層面。所有人都被要求將靈魂奉獻給耶穌。狄金森質疑宗教觀點和神學的價值觀。這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和羅塞蒂相似,狄金森也要面對宗教與自由的艱難選擇。一方面,她頂住了宗教壓力,終生沒有成為教徒;而另一方面,在她的內心深處又為自己冒犯上帝而具有了一種負罪感。她在詩中寫道:“我不放你走,除非你為我祝福”。這正是她與上帝關系的真實寫照。詩人的自我永遠處于抗爭、搏擊的狀態,而這抗爭不僅是為了遠離信仰,同時也是為了接近上帝。在《我死時聽到一只蒼蠅的嗡嗡聲》一詩中,詩人通過模仿死者彌留之際意識逐漸渙散的過程,以考證來世的確定性及上帝存在的真實性,也反映了她對宗教的矛盾心理。
愛情詩里的入世哲學
盡管羅塞蒂已經是一位具有了存在主義覺醒意識的教徒。但她的日常生活、詩歌創作,乃至談婚論嫁,還是要受到上帝存在的約束和影響。年輕時的羅塞蒂長相甜美,常為其兄拉斐爾前派詩人、畫家但丁•羅塞蒂做模特。18歲時,她愛上了畫家詹姆士•科林遜并與他訂婚,但因為科林遜信奉的是天主教,與英國國教的教義相互沖突,所以兩年后羅塞蒂解除了婚約。1862年,她又如癡如醉地愛上了學者查爾斯•凱利,后又因凱利是無神論者終使兩人勞燕分飛。此后,她還一度愛上了有婦之夫威廉姆•司各特,但結果也是有緣無分。
羅塞蒂通過詩歌述說著自己失敗的愛情,在表達了對愛情失望的同時也反映出自己缺乏行動力的入世表現。存在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要由人自己的行動來決定和體現的,而不是由上帝掌握和安排的。情感的創傷讓羅塞蒂的詩歌帶上了濃重的憂郁和悲哀的情調。《第一日》是羅塞蒂的一首哀婉感人的十四行詩“:我多么希望自己還記得你我邂逅的第一日,第一時,第一刻,它或是燦爛如夏或是暗淡如冬,我只能如此說。”[6]在該詩中,詩人抒發了自己急切地想找回與愛人第一次相會的那份記憶。卻又不能不為自己年少無知不懂得珍惜而懊悔不已。在面對宗教與愛情的艱難抉擇中,成年后的她依舊是無可奈何。她在《想念》中寫道“:請想念我吧,當我已經不在———不在這里,在遠方,寂靜的田園;當你已不能握住我的手腕,握住了我的手,我欲去又徘徊。”[7]可以看出,羅塞蒂對于愛情始終保持了一種被動的姿態。她渴望被記住,被懷念,甚至希望被再一次握住雙手。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行動哲學”,即“入世哲學”。“存在主義哲學思想鼓勵人行動,尤其是把人置于一種孤立無援的存在狀態下,并以絕對自由的事實性來強加于人,使其處于孤立無援又不得不行動的人生懸崖之巔,人必須要行動。”[8]站在愛情的世界里,羅塞蒂雖然孤立無援,卻用另外一種方式采取了行動。她在詩歌創作中直白地道出了自己愛的心聲,邁出了“入世”的步子,突破了宗教的禁錮。
與羅塞蒂相似,狄金森也曾經歷過幾次失敗的愛情,這也是導致她隱居及終生未嫁的主要原因。雖然狄金森思考的是入世的問題,但采取的態度則是出世的回避。學者們認為,狄金森先后與沃茲沃斯、希金森、羅德等人有過感情糾葛。1854年,狄金森在費城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英俊瀟灑的已婚牧師沃茲沃斯并深深地愛上了他。迪金森的一些詩歌和書信都是見證這份愛情的有力證據。甚至可以說沃茲沃斯是觸發狄金森詩歌靈感的繆斯,因為她們交往的這幾年恰好是狄金森寫詩最多的年份。然而,沃茲沃斯已有妻兒,并且身為牧師。在愛情和宗教法度的抉擇面前,狄金森選擇了后者。1860年,狄金森在愛情詩《但愿我是,你的夏季》中寫到對沃茲沃斯的思念:“但愿我是,你的夏季,/當夏季的日子播翅飛去!/我依舊是你耳邊的音樂,當夜鶯和黃鸝精疲力竭。/為你開花,逃出墓地,/讓我的花開得成行成列!/請采擷我吧———秋牡丹———/你的花———永遠是你的!”這首詩比喻貼切,正是狄金森內心的真實寫照。
與羅塞蒂一樣,狄金森愛的行動也同樣只是通過詩歌創作來展示的。相比之下,狄金森的愛情詩更加充滿激情。比如《暴風雨夜》:“暴風雨夜!暴風雨夜!/我若和你同在一起,/暴風雨夜就是/豪奢的喜悅!/風,無能為力———/心,已在港內———/羅盤,不必!/海圖,不必!/泛舟在伊甸園———/啊,海!/但愿我能,今夜,/泊在你的水域!”這首詩描寫了暴風雨夜,一對戀人心中卻是豪奢的喜悅。在拉丁文中“luxury”有“lust”(強烈的性欲)的意思,所以,這首詩就是表達詩人對其愛人狂野的愛。對愛和幸福的強烈渴望讓詩歌中的她穿越了層層風雨,到達了幸福的港灣。這種對愛情大膽、露骨的描寫更體現了詩人對宗教的蔑視和對真我存在的追求。
向死而生的存在主義意識
死亡對存在主義來說是一個核心問題。海德格爾說過,“畏”,是對死的體驗。而死作為此在之本質,并不是停止呼吸或停止思維的那一刻,而是伴隨著人的一生,無時不在的心理體驗[9]。因此,存在是向死而生的存在。只有當人讀懂了死,才能真正領悟生的意義。存在主義哲學將死亡看作是自在存在,一種不需要理論觀念陳述自然存在的事實。也就是說存在主義對待死亡的總體原則是直面死亡。
羅塞蒂一生身體羸弱,健康欠佳,感情生活又多挫折,晚年更是孤單寂寞,疾病纏身。因此,她鐘愛離群索居的生活,在誦經祈禱中獨自陷入冥思玄想。對“死亡”的關注幾乎貫穿了她所有的作品。她的一系列與死亡相關的詩都表現了詩人對死亡的深刻感悟:死亡是獨立存在,不依賴他物,沒有任何目的性的。比如在《歌》中,羅塞蒂指出“當生命逝去時,不需要愛人用悲歌來哀悼,不需要愛人用玫瑰和翠柏來紀念。只要綠草相伴,只要有雨水和露珠兒的滋潤”。這首詩是詩人心境的真實寫照。在詩人的眼里,生命如同綠草,柔弱卻頑強,死亡也不過是綠草的枯黃,是大自然的必然輪回。有一生就必有一死。在詩人看來死更是新生的黎明,它是生的一部分。對死亡的深刻感悟使詩人能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悲哀,克服恐懼、坦然面對死亡、超越死亡。詩人向死而生的存在主義意識在這首詩里表述得淋漓盡致。
與羅塞蒂相比,狄金森對死亡的感悟也毫不遜色。狄金森對死亡的觀察和體驗甚至可以說達到了癡迷的程度。在她一生創作的1775首詩歌中,有600多首是以死亡為題材的。她從生者和死者兩個角度來描寫死亡。有時,她還把死亡擬人化,讓死亡變成了一個復雜的人物形象。說來也怪,狄金森常常在寫詩之前就擺出了一副已經死去了的姿態,也許這是她在對自己的死亡進行大膽想象和預測吧?她不知不覺地把未來加以無限制的延伸,把死看作是對未來之圖景的一種透視。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這種人超越了現在,并達到了真正的自我,從而在這未來之圖中認識到一種“永恒的生活”[10]。比如在《我的河在向你奔來》一詩中她寫道:“我的河在向你奔來———歡迎么?藍色的海!哦,慈祥的海啊———我的河在等候回答———我將從僻陋的源頭帶給你一條條溪流———說啊,接住我,海。”在這首詩中,詩人把人生比作河流,把死亡比作河流歸海,河流必然會流向大海。河流從無到有,直到淹沒在海洋中。這與存在主義的觀點不謀而合:人存在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一直在向著死亡推進。人存在最后歸結于空無,因為人存在必然會走向死亡,這是無法逃脫的。這首詩表現了詩人對待死亡的淡定心態。
對于迪金森來說,死亡也僅僅是存在的另一種形式,所以并不是什么讓人憂傷的事情。死亡不能阻止詩人對人生的熱愛,反而激發了她對人生的思考。死亡是來世的必經階段,精神的救贖要以肉體的毀滅為條件,活著的人不可能了解死后的秘密,依附于肉體之中的自我也看不見來世的光明。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兩位詩人的作品中都包含著存在主義意識。但在程度上又有著明顯的差別:狄金森的存在主義意識幾乎沖破了宗教觀念的束縛;而羅塞蒂則無法擺脫宗教對其思想的影響,讓自己的存在意識蒙上了一層宗教色彩。盡管如此,兩位詩人敢于尋找自我的勇氣,以及向死而生的人生感悟卻是一致的。她們的詩歌中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了一種參透人生之后的大徹大悟的境界。這也是她們之間最大的共性。盡管長期生活在相對幽閉的狀態下,但這并沒有影響她們對世間萬物的洞察和對人生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