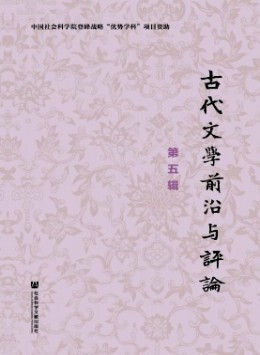古代文學(xué)文學(xué)感悟力思考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古代文學(xué)文學(xué)感悟力思考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中國古代文學(xué)學(xué)科從上個世紀(jì)初算起,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在中國文學(xué)的各門學(xué)科中是歷史最長、相對來說也最為成熟的學(xué)科。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文學(xué)所要具備的條件,比較清楚,如文獻(xiàn)的功底、理論的功底等。但是,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近年來被忽視或沒有得到充分的強調(diào),以至在古代文學(xué)研究人才培養(yǎng)乃至研究上,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這個就是對文學(xué)的感悟能力。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感悟能力,有楊義先生的大作論之甚詳。此處所說的文學(xué)研究中的感悟力,是指文學(xué)史家和文學(xué)批評家對于文學(xué)作品所蘊含的情感、思想、形象的意義和語言藝術(shù)的直覺的感應(yīng)、體驗、領(lǐng)悟和判斷的能力,以及對于文學(xué)現(xiàn)象的直覺感受和洞察的能力。
感悟力是研究文學(xué)作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不同的是,文學(xué)作品首先就是感性的存在,所有的思想意義,包蘊于形象之中,只有通過文學(xué)作品的形象,具體說就是敘事作品里邊的人物、故事、情節(jié),抒情作品里邊的情感、意象、意境、音韻、語言,作品的思想意義才能顯現(xiàn)出來。文學(xué)史家和批評家進(jìn)入作品的途徑是形象,進(jìn)入之后對作品的把握,則要通過感同身受的體驗,再現(xiàn)作品的內(nèi)容,這些都存在著感悟的過程。所以研究者對于他所研究的對象,能否有敏銳的感應(yīng),能否進(jìn)入到切身的體驗狀態(tài),會直接影響到對作品的接受與理解。中國古代文學(xué)歷來以詩文為正宗,在再現(xiàn)與表現(xiàn)的兩種藝術(shù)類型中,偏重于表現(xiàn)。中國文學(xué)的這種特征,使其成為一種重意蘊與藝術(shù)靈性的文學(xué)。在創(chuàng)作中,古人講靈機,所謂“方天機之俊利,夫何紛而不理”(陸機《文賦》);講興會,如顏之推所說“文章之體,標(biāo)舉興會,引發(fā)性靈”(《顏氏家訓(xùn)•文章》),要“隨興會所之為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三);講悟入,嚴(yán)羽《滄浪詩話》有著名的論述:“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
且孟襄陽學(xué)力下韓退之遠(yuǎn)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dāng)行,乃為本色。”又曾季貍《艇齋詩話》:“后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guān)捩,要知非悟入不可。”呂本中《童蒙訓(xùn)》亦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功夫中來,非僥幸可得也。如老蘇之于文,魯直之于詩,蓋盡此理也。”這都是重藝術(shù)靈性的突出表現(xiàn)。作為藝術(shù)靈性的創(chuàng)作,往往表現(xiàn)的是瞬間的感受,或者是神思的瞬間的勃發(fā)。雖然是瞬間的感受,或者是瞬間的勃發(fā),但是作品卻往往涵蘊著深厚的內(nèi)容或深刻的思想。所以評價作品也以文外重旨、韻外曲致為藝術(shù)的極致,因此意境與神韻理論大行其道,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的田園山水詩備受推崇,宋詞也以要眇的婉約詞為正宗。面對這樣的研究對象,研究者對于中國古代文學(xué)作品的把握,必須要有悟性,要有極強的藝術(shù)感悟力和生命的穿透力,才能參透詩旨,有所斬獲。歐陽修《六一詩話》記與梅堯臣論詩,梅氏以為:“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矣。”歐陽修問梅堯臣“何詩為然?”梅堯臣回答:“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這里所說的“會意”,就是讀者的感悟。梅圣俞舉詩例道其仿佛云:“嚴(yán)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tài),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于言外乎。”梅氏從嚴(yán)維詩而感受到春光駘蕩,從溫、賈詩品出羈旅愁思,都應(yīng)是感悟所得。又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云:“韻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韓退之是也;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此處所說的各位詩人不可及處,如“韻”,如“味”,如“意氣”,都非常空靈,非感悟不能得到。說到對詩的感悟,歷代讀詩人對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無題》及《錦瑟》等詩的解讀最為典型。如《錦瑟》詩因意象朦朧、指向不一的特點,解者紛紜,莫衷一是,其實都是解者個人的感悟,并沒有詩之外的史料來支撐。因此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只是無人作鄭箋。”如薛雪的《一瓢詩話》:“玉溪《錦瑟》一篇,解者紛紛,總屬臆見,余幼時好讀之,確有悟入,覓解人甚少。此詩全在‘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弦一柱,已足令人悵然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弦柱,令人悵然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弦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即達(dá)若莊生,亦覺迷夢;魂為杜宇,猶托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lán)田玉氣,恍若生煙。
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dāng)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嘆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薛雪對《錦瑟》的詩旨的理解顯然是傾向于年華之慨的,而他這一詩意的獲得,即來自他對作品的咀嚼感悟,如他所說是“悟入”的。古人如此,現(xiàn)在人也是如此路數(shù)。蘇雪林寫《玉溪詩謎》,認(rèn)為李商隱的無題詩表現(xiàn)的是李商隱一段人所不知的愛情,與宮女和女道士的戀愛,也是首先從詩里感受到了愛情的信息,而后在考證其生平事跡,寫成著作的。蘇雪林在1927年寫的六萬字的小冊子《玉溪詩迷》的引論里說:“千余年來義山的詩,被上述三派的人,鬧得烏煙瘴氣,它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認(rèn)。……因為歷來舊觀念蒙蔽了我的眼光,我也說義山的詩天生是晦澀的,不必求什么深解,……但后來我讀了《碧城》《玉山》等詩,便有些疑惑起來。因為這些詩里充滿了女道士的故事,若義山與女道士沒有深切的關(guān)系,為什么一詠不已,而再詠之,再詠之不已,而三詠四詠之呢?于是我根據(jù)了這一點懷疑的念頭,用心將義山詩集細(xì)讀了一遍,才發(fā)現(xiàn)了一個絕大的秘密。原來義山的《無題》和那些《可嘆一片》有題等于無題的詩,不是寄托自己的身世,不是諷刺他人,也非因為缺乏做詩的天才,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詞和典故,來炫惑讀者的眼光,以文其淺陋;他的詩一首首都是極香艷極纏綿的情詩。
他的詩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寫他一生的奇遇和戀愛的事跡。”所以文學(xué)研究的發(fā)現(xiàn)與創(chuàng)新,有的是要依賴于新的材料的發(fā)現(xiàn),有的就是來自于研究者對作品的感悟;感悟也是文學(xué)研究創(chuàng)新的重要源頭,一個人感悟力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作品接受與揭示的多寡。我在《不求甚解》書中討論到方管(舒蕪)對王維《鳥鳴澗》詩的體悟。詩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1949年《新中華》三期上發(fā)表的方管《王維散論》的分析很細(xì)膩:首先是分析此詩的靜:“夜靜而且山空,本來近乎荒涼寂寞了,可是,這山乃是春天的溫和的山,并非秋山冬山那樣蕭條死滅;何況到底還有月出,并非濃重的暗,到底還有月光下春澗中的山鳥的時鳴,也并非沉重的靜呢?”進(jìn)而分析王維的心態(tài)——其實是在詩的原意的基礎(chǔ)上,對人與物極其微妙的關(guān)系作了深入的發(fā)揮:“是因‘人閑’而桂花才落,還是因‘桂花落’而人才閑呢?是人閑了才看得見本就在落的桂花,還是桂花落了才看得見本就閑著的人呢?”詩人王維未置可否,似乎也無意于此,“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他把一切答案都融入在意象之中了。然而解詩的方管卻以自己的感悟,深入詩的內(nèi)蘊,進(jìn)而作了更具有他個人理解的生發(fā)。這樣的解詩,顯然拓展了詩境,對詩的內(nèi)容作了增量的發(fā)揮。以上所談的多是詩文,其實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戲劇,同樣也離不開研究者的感悟。而這種感悟與詩文不同,主要體現(xiàn)為對人物形象的價值判斷、人物心理的體驗、人物命運的推測,即通過生活的邏輯,把文學(xué)還原為自己熟悉的生活。而這個過程,因個人的生活經(jīng)驗、閱歷以及世界觀的不同,也是十分個性化的,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即此之渭也。對小說很多人物的不同評價、對小說主題的不同認(rèn)識多來自于此。比如對《三國演義》中的幾個主要人物,研究者的認(rèn)識就頗有出入。一般而言,都認(rèn)為劉備是典型的仁君形象,而曹操是奸雄形象,諸葛亮是智者的形象。
但是,魯迅卻從劉備的貌似仁厚中看出了偽詐,從曹操的奸詐中看出了豪爽多智,從諸葛亮的智謀中看出了近妖。他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中說:“至于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又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的第四講《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中評介《三國演義》的缺點:“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這就是說作者所表現(xiàn)的和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jié)果倒好像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jié)果倒像狡猾。”人物形象的復(fù)雜性,固然是因為作者描寫的原因,或有意寫出人物復(fù)雜多面的性格,或描寫動機與實際結(jié)果產(chǎn)生了矛盾,如魯迅所評。但是讀者和研究者能夠看出小說人物性格的多面,卻要靠他們閱讀作品的感悟,進(jìn)而概括為理性的結(jié)論。不僅如此,這種從閱讀中獲得的感悟甚至?xí)绊懙綄σ徊啃≌f思想傾向的整體認(rèn)知。一般認(rèn)為,《三國演義》這部小說的總體傾向是擁劉反曹,但也有人據(jù)作品所反映出的劉備的虛偽、狡猾而懷疑作者羅貫中是否真心擁劉,甚至得出小說從骨子里是反劉的結(jié)論,可見感悟會影響到對一部作品整體的評價。中國的古代小說,也頗重靈性。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云:“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蘇軾論文講心手交至,而在這里,還不過是程度稍高的圣境而已。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最高狀態(tài)是神境和化境,它超越了心手交至的臨紙狀態(tài),實則就是在進(jìn)入創(chuàng)作靈感時所呈現(xiàn)出的神思創(chuàng)作狀態(tài)。那么,讀者又如何才能從這樣無字、無句、無局的作品中讀出文字、文句、文局和文思來?當(dāng)然離不開感悟。金圣嘆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五評點此書時,即感慨“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賬過去。于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意處,轉(zhuǎn)筆處、難轉(zhuǎn)筆處,趁水生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后處,倒插在前處,無數(shù)方法,無數(shù)筋節(jié),悉付之于茫然不知。”這就是沒有或缺乏文學(xué)感悟能力的過。文學(xué)研究不僅要挖掘思想意義,還要分析藝術(shù)形式,總結(jié)藝術(shù)特點,那就更是離不開具體的感性的內(nèi)容。
就此而言,研究者能否具有敏銳的感悟力,在閱讀中迅速對作品水平的高低以及作品風(fēng)格作出判斷就至為關(guān)鍵。如敖陶孫《詩評》談詩人的風(fēng)格:“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fēng)流自賞;鮑明遠(yuǎn)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fēng)日流麗;陶彭澤如絳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fēng)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nóng)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云,核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yōu)工行鄉(xiāng)飲,酬獻(xiàn)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wǎng),綺密環(huán)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黃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fēng)之夢故在;梅圣俞如關(guān)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圣安禪,自能奇逸。”論魏晉至宋代詩人風(fēng)格,全是一種想象的譬喻,是以具體性格形象來描繪詩人的風(fēng)格。而敖陶孫對詩人風(fēng)格的獲得,很明顯就是感悟所得。今人對詩歌作品風(fēng)格的把握,與古人相比,已經(jīng)多了許多手段,如意象的統(tǒng)計、結(jié)構(gòu)的分析、用韻的把握等等,但是,對詩中情感的體驗、尤其是更幽微情感的捕捉,對詩歌意境的感受等,仍然不能離開對作品的感悟。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研究,離不開史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學(xué)史的范疇。史的研究的最大特點是要依賴于史料。文學(xué)作品產(chǎn)生的時代,作家的生平,作家的活動,一個時期、一個地區(qū)乃至一個家族的文學(xué)整體面貌,等等,都是文學(xué)研究必須涉及的。
但是,由于年代渺遠(yuǎn)、史料散佚等原因,研究者所獲得的史料永遠(yuǎn)是殘缺不全的、有限的,所以要還原文學(xué)史,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對于研究者來說,無論還原也好、建構(gòu)也好,每一個人都會把回到歷史作為他研究的目的或過程。這就需要研究者的感悟,通過合理想象和推理勾連起史料,回到歷史。吳承學(xué)、沙紅兵《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歷史想象》在論述文學(xué)史想象時曾引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上冊審查報告》中語:“吾人今日可依據(jù)之材料,僅為當(dāng)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jié)構(gòu),必須具備藝術(shù)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xué)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今明館叢稿二編》第247頁)所謂的“神游冥想”,實際上就是發(fā)揮想象重構(gòu)歷史的原貌,而這種文學(xué)史想象,誠如吳承學(xué)文章所說:“它又與一般的歷史想象區(qū)分開來,具有更需要神思感悟的文學(xué)特性。”其實文學(xué)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心靈史和情感史,而對于古代文人心靈和情感的把握甚至還原,殊非易事,研究者如果不能依據(jù)自身的情感體驗和心靈感悟是很難完成復(fù)現(xiàn)一個作家、一個時期作家群或一個地域作家群的心靈面貌、心態(tài)狀況和情感現(xiàn)象的。研究者的感悟力當(dāng)然有先天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還是后天的培養(yǎng)。一是有關(guān)閱讀。古代文學(xué)研究者,必須具有良好的文學(xué)修養(yǎng),而在文學(xué)修養(yǎng)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熟悉文學(xué)作品。所以熟讀作品是增強文學(xué)研究中感悟力的必備的功課。古人常常談?wù)撟x書對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司馬遷有著名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說。揚雄說:“能讀千賦則善賦。”(桓譚《新論道賦》)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些說的都是讀書對寫作的作用。其實寫作和研究是相通的。研究文學(xué)的基本功,更需要熟讀作品,才會增強悟入的能力。
嚴(yán)羽《滄浪詩話詩辨》對詩的悟入,特別強調(diào)熟讀領(lǐng)會作品:“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大歷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jīng),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朱熹治學(xué)也特別強調(diào)反復(fù)閱讀作品:“時時溫習(xí),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朱子語類》卷二十四)。只有這樣不斷溫習(xí),才會有新的心得。劉師培講古代作家研究,最講“浸潤”“:漢文氣味,最為難學(xué),只能浸潤自得,未可模擬而致。至于蔡中郎所為碑銘,序文以氣舉詞,變調(diào)多方;銘詞氣韻光彩,音節(jié)和雅,如《楊公碑》等音節(jié)甚和雅。在東漢文人中尤為杰出,固不僅文字淵懿,融鑄經(jīng)誥而已。且如《楊公碑》《陳太丘碑》等,各有數(shù)篇,而體裁結(jié)構(gòu),各不相同,與此可悟一題數(shù)作之法。又碑銘敘事與記傳殊,若以《后漢書》楊秉、楊賜、郭泰、陳實等本傳與蔡中郎所作碑銘相較,則傳虛碑實,作法迥異,與此可悟作碑與修史不同。”又云:“傅、任之作,亦克當(dāng)此。且其文章隱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滯,毫無痕跡;潛氣內(nèi)轉(zhuǎn),句句貫通;此所謂用典而不用于典也。今人但稱其典雅平實,實不足以盡之。大抵研究此類文章首重氣韻,浸潤既久,自可得其風(fēng)姿。”劉師培所說的“浸潤”,就是熟讀作品,從熟讀作品中,體會文章的“氣味”和氣韻。在古代文學(xué)研究中,有一十分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對風(fēng)格的研究。古人講作家,也多從“體”、即今天所說的風(fēng)格進(jìn)入。前面已引敖陶孫《詩評》論詩人風(fēng)格。又如:說“阮旨遙深,嵇志清峻”,唐代詩人李白豪放飄逸、杜甫沉郁頓挫,蘇軾自在雄渾,黃庭堅生新瘦硬,也都是風(fēng)格的概括與描述。嚴(yán)羽《滄浪詩話詩體》講了許多體:“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元和體、晚唐體、本朝體、元佑體、江西宗派體。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高達(dá)夫體、孟浩然體、岑嘉州體、王右丞體、韋蘇州體、韓昌黎體、柳子厚體、……”時之體就是時代風(fēng)格,人之體就是作家風(fēng)格。又楊萬里《誠齋詩話》:“‘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遙遙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縈。一溪和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fēng)聲。’此李太白詩體也。‘麒麟圖畫鴻雁行,紫微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xùn)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jīng)滟滪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dāng)其下筆風(fēng)雨快,筆所未到氣以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臺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fēng)光錯綜天經(jīng)緯,草木文章帝機杼。’又:‘澗松無心古須鬣,天球不琢中粹溫。’又:‘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詩體也。”風(fēng)格是我們研究文學(xué)越不過的范疇,尤其是古代文學(xué)研究,更離不開“體”的把握。但是對“體”的把握又談何容易。嚴(yán)羽只提出了某某體,未作具體解釋。敖陶孫對詩人風(fēng)格作了簡要的比擬,而楊萬里卻只引了詩人的幾句詩來說明此是某某詩體。無論是通過比擬,還是通過詩句來總結(jié)詩人的風(fēng)格,都要有研究者的個人感性的體驗和感悟。而作品讀的多少,讀的到不到家,熟不熟,深入不深入,會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感悟能力,進(jìn)而影響到他的研究能力,這里邊沒有捷徑可走。古人和現(xiàn)代一些優(yōu)秀的學(xué)者,多具備這樣功夫,即往往讀完一篇無作者姓名、甚至無題的作品,就能判斷這篇作品的時代,或唐或宋,或明清以下,甚而判斷出其作者。這種感悟的功力,沒有別的原因,只在讀書,是日積月累熟讀作品養(yǎng)成的鑒賞功夫。與此相反,在當(dāng)下的古代文學(xué)研究中,會發(fā)現(xiàn)一種常見的現(xiàn)象,缺乏對作品所在年代、作者以及作品藝術(shù)水平的判斷能力,甚至還有不分良莠、信口雌黃,究其原因無他,“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游潛《夢蕉詩話》),就在于作品讀的少,學(xué)力不夠。現(xiàn)在,計算機技術(shù)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高度發(fā)達(dá),為文獻(xiàn)檢索帶來了很大便利,然而計算機卻檢索不出思想的蘊含和情感的生動。因此,在古代文學(xué)的研究者培養(yǎng)方面,必須把讀書、讀作品作為培養(yǎng)的重要手段。不能用講課來代替閱讀;任何講課對文學(xué)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有限的,關(guān)鍵還在閱讀作品。
在博士生培養(yǎng)方面,有的培養(yǎng)單位安排了大量的授課,對此,我是不敢茍同的。我認(rèn)為必須把閱讀原典的時間安排充足,應(yīng)該要求學(xué)生讀完一個時期的重要總集、別集、一個階段所有的作品。最好是讀沒有經(jīng)過標(biāo)點的古籍。這樣做,不僅可以增強學(xué)生對文學(xué)作品的感受能力,同時也會加強他們對于古文獻(xiàn)的把握理解能力。然后才是同學(xué)間的交流研討和導(dǎo)師的指導(dǎo)。二是有關(guān)閱歷。在我國,文學(xué)從來都是修身之學(xué)、養(yǎng)性之學(xué),總是把讀者對文學(xué)的接受,與個人的介入融為一體,很少有西方那樣純粹客觀的觀照。孟子就有著名的“知言養(yǎng)氣”說,《孟子•公孫丑上》:“‘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何謂知言?’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所謂“知言”,是指辨別語言文辭的能力;所謂“養(yǎng)氣”,講的是個人內(nèi)在的道德修養(yǎng)。孟子雖然沒有直接的說明“知言”與“養(yǎng)氣”的關(guān)系,不過從這段話的邏輯上來看,顯然“知言”植根于“養(yǎng)氣”。也就是說人的道德修養(yǎng)會影響到語言文辭的辨別能力,直接影響到對文學(xué)作品的評判。由于文學(xué)本身寫人的性質(zhì),讀者或研究者對文學(xué)的接受,從來都受到接受者個人閱歷的影響與制約,包括人生經(jīng)歷、學(xué)識、思想意識、信仰等等。尤其是人生的經(jīng)歷以及由此而積累的人生經(jīng)驗,對于提升古代文學(xué)研究中的文學(xué)感悟力至為重要,甚至?xí)绊懙揭粋€研究者的學(xué)術(shù)個性。在古代文學(xué)研究界,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比比皆是。魯迅透過阮籍、嵇康等士人的出世與玩世,看到的是魏晉士人深刻入世的痛苦與悲哀,從陶淵明超然的田園詩中感受到的是他不超然,這種深入的感悟能力以及透辟的分析能力,毫無疑問與魯迅作為現(xiàn)代革命先鋒的人生閱歷密切相關(guān)。又如現(xiàn)代著名的學(xué)者李長之,從小就形成了獨立的性格,他在《社會與時代》一文中談到自己:“濃的興趣和獨立的性格,永遠(yuǎn)是我之所以為我了。”
再加之他在清華大學(xué)學(xué)習(xí)哲學(xué)時,又接受了德國哲學(xué)的影響,尤其是強調(diào)個人生命體驗的狄爾泰哲學(xué)影響,這種學(xué)習(xí)的閱歷,使他在李白的詩歌中,不僅看到了李白作為常人所應(yīng)具有的欲望,而且在其《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書中,還對其超常的痛苦作了深刻的揭示。談到閱歷對文學(xué)研究中感悟的影響,還要提到兩位特殊的《紅樓夢》研究者:一是寫了《紅樓夢人物論》的王昆侖先生,一是寫了《紅樓夢啟示錄》、《王蒙話說紅樓夢》和《王蒙評點紅樓夢》的王蒙先生。說其特殊,乃是因為他們都做過高官,但也就是他們豐富的人生閱歷,包括政治經(jīng)驗,使他們對《紅樓夢》有了獨特的感悟理解。用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去理解作品,再用作品的人生經(jīng)驗來驗證補充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寫出了不同于普通學(xué)者的研究著作。在我國當(dāng)代李白研究的專家中,已故的裴斐先生是一位既有突出成就、又極有個性的學(xué)者。當(dāng)古代文學(xué)宏觀研究中頗為流行情理中和之說、學(xué)者們紛紛強調(diào)中國的古代文化是以中庸為主的文化時,他卻鼓吹方的品格和狂狷精神,強調(diào)文人的人格應(yīng)該是方的而非圓的,認(rèn)為我國古典文學(xué)精華所在決非中和即中庸,而是與之相反的狂狷,對李白反中庸的狂狷性格給與了極高的評價。當(dāng)眾多學(xué)者認(rèn)為李白的性格和詩風(fēng)是豪放飄逸時,他又指出,李白并非一味的飄逸,一味的豪放,他的性格和詩風(fēng)是豪與悲。“其豪縱奔逸總是同深沉的悲感分不開,或豪中見悲,或悲中見豪,典型的李白個性總是包含著豪與悲兩方面。豪,出于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傲世獨立的人格力量;悲,出于對現(xiàn)實的深刻不滿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雙重矛盾、雙重痛苦。”
裴斐先生對古代文化和李白的獨特認(rèn)識,在我看來,即受了他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的影響。他的右派的不幸遭遇,改變了他的人生,但是也錘煉了他堅毅的人格,加深了他對社會人生的認(rèn)識與理解,從而也使他在從事古代文學(xué)研究中,從一個大家都不會注意或者忽略的視角,獲得對研究對象的感悟,從李白的飄逸中讀出悲與豪。因此,對于古代文學(xué)研究者來說,一輩子鉆到故紙堆里,不問世事,也不懂世事,未必能夠作出大學(xué)問,成為真學(xué)者。關(guān)注現(xiàn)實,洞明世事,與讀書互為表里,無疑能夠有效地增強其文學(xué)感悟力。提高古代文學(xué)研究中的文學(xué)感悟力,除了強化讀書和豐富閱歷外,還有必要建議學(xué)者嘗試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以提高文學(xué)修養(yǎng)。“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題》),親自嘗試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才會真正體會創(chuàng)作的甘苦,把握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真諦。因此曹植《與楊德祖書》說:“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認(rèn)為只有批評者自己是優(yōu)秀的作家,才有資格去評論他人的作品。古代詩文評不曾獨立,所以在中國古代,一般是作家即批評家,曹植此說自有道理在。現(xiàn)在文學(xué)研究已經(jīng)成為獨立的專業(yè),研究者雖然沒有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亦可以憑借良好的學(xué)術(shù)訓(xùn)練,深入作品,開展研究。盡管如此,從提高文學(xué)感悟力的角度來看,曹植的這句話卻也道出了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對于文學(xué)研究的重要意義。回顧一百年來的古代文學(xué)研究,在上個世紀(jì)出現(xiàn)了許多作家學(xué)者或?qū)W者作家,尤其是五四時期,作家學(xué)者往往不分,一些頗有影響的古代文學(xué)研究大家,同時也是著名的作家,胡適、魯迅、聞一多、朱自清、郭沫若、錢鐘書、林庚等等都是。這也證明,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確實有助于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深入,尤其有助于研究者對作品的感悟和理解。因此提倡古代文學(xué)研究者寫一點文學(xué)作品,對于他所從事的研究工作,一定會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