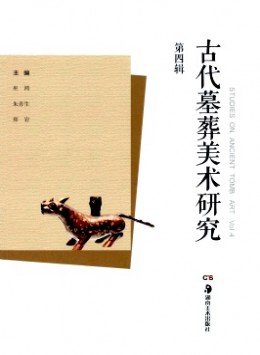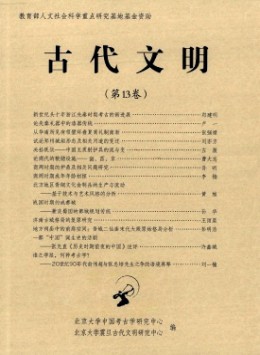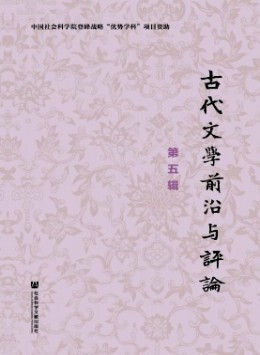古代文學研究價值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古代文學研究價值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內容意義與形式結構的中庸
古代文學研究說到底是文本的研究,而文本研究應該包括內容意義和形式結構兩個方面的內容。以詩、詞為最根本陣地的古代文學,其研究更無法回避這兩個問題。形式結構是指作者在作品中用以反映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手段的總和。內容意義是作品中所描寫的滲透了作家思想情感的社會生活。形式與內容之間體現出辨證統一的關系:沒有內容,形式無法存在,沒有形式,內容就無法閃現,二者各以對方為存在條件,不可分割。正是由于這種關系,作為文學研究,尤其是在以含蓄蘊籍著稱的中國古典詩詞的研究中,更是應該掌握好二者的平衡,既要析出其在布局謀篇中的妙處,又不穿鑿、拆散“七寶樓臺”;既要解悟作品真正的思想價值、審美意義、哲學思考、又不附會諸般“社會的”、“歷史的”、“美學的”風貌。舉個例子來講,北宋歐陽修有一首《蝶戀花》詞: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墟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這是一首情深意切的閨怨詩,但清代的張惠言卻在慎重研究后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遽遠也。‘樓高不見’,則王又不寐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也。‘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琦)、范(仲淹)作乎?”①全詞被整體肢解,形式之美蕩然無存;附上“微言大義”,又失卻詞中原原有的閨思閨怨的情腸。現今的詩詞研究者也常會做類似的事情,或是一首詩詞只剩下起承轉合、伏應斷續,或是要從一首小小的詩詞中“挖掘”出“深刻的哲學思想”、“重大的歷史意義”。應該說這樣的研究都是有失偏頗的,是對古代文學研究價值的破壞,對讀者鑒賞古代文學作品的阻礙。對古代文學作品形式結構和內容意義的研究,可以有所側重,也可以作一定的擴展和深挖,但前提必須是在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做出結論時更應嚴守中庸。
二、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中庸
佛馬克、蟻布思在《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一文中,將一個整體性的文學研究概念又細致分為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兩個側面。前者是一種解釋,有客觀的操作性,后者是一種闡釋,強調主觀的參與和制造,強調前見的主體在研究過程中的能動作用。這也就提出了文本研究中的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問題。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處理好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關系尤為重要。由于時間的久遠和流傳中傳抄、印刷及時代更迭時的校正等原因,古代文學作品文本的客觀性時常會受到質疑,需要研究者的考訂。但應當意識到,古代文學研究是為了挖掘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并利于它的傳播,以便對現代的讀者和作家的鑒賞與寫作提供指導。這就提醒古代文學的研究者,要把握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的“度”。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客觀應更多關注對文本本身的考察,對能夠幫助理解作品的作品的生成情況、作家的生平活動、思想狀況的一定程度的研究是可行。如對王之渙《出塞》一詩中是“黃河遠上白云間”還是“黃沙遠上白云間”,《紅樓夢》中黛玉吟誦的是“冷月葬花魂”還是“冷月葬詩魂”等的爭論直接關系到研究價值的立足點,無疑是必要的。但絕不能鉆牛角尖,像“紅學”研究中,對曹雪芹籍貫的考證,今天一塊碑,明天一個家譜,然后再大張旗鼓地爭論、打擂,除了成就幾位“專家”和專家所謂的“事業”,對《紅樓夢》研究本身幾乎沒有價值,甚至已經脫離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還有的研究者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分強調主觀,像出于個人的偏見偏好對作品價值的抬高或貶低,自以為是脫離作品實際的“×××的真故事”之類都無益于對古代文學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在古代文學的研究中,應該把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統一起來,“中庸”中追求對作品深刻、獨到又有價值的見解和認識。
三、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的中庸
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是在古代社會出現并流傳,在今天的社會中仍舊傳播并備受關注的古代文學作品。古代與現代,雖不是完全對立的,但必須承認,它們是截然不同的。無論是社會的狀況、思想意識還是讀者的范圍、接受標準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表現在文學研究中就出現了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的矛盾。如果單純考察古代文學作品的歷史情況,分析作品在其產生時的思想和藝術,就會與現代的讀者閱讀產生比較大的距離,無法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而如果一味地用現代的分析方法和視角觀點來關照古代文學作品,又會在某種程度上失卻古代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和真實趣味,同時會最終造成讀者的厭棄。比如,以下這樣的研究就會破壞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三言”中有一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寫的是商人蔣興哥與其妻王三巧本是一對恩愛夫妻,但蔣興哥出外從商時,三巧奈不住寂寞被人引誘與另一個商人陳大郎通奸的復雜的愛情故事。在對這一篇作品的研究中,學術界出現了若干種區別很大的觀點,其根本分歧就在于對文學傳統和現實需求的關系的界定。美國學者夏至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一書中,稱這篇小說是“明代最偉大的作品”,“是一出在道德上與心理上幾乎完全協調的人間戲劇”,寫的是“商人階級中三個普通又體面的青年人,他們會愛并且忠實于愛”,“三巧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情人正是她對丈夫的愛和思戀”,“愛既是情感的也是肉體的,具有雙重意義,正是這種愛,純潔了她的意識,以至于與處同樣情境的西方女性相比,她的徹底擺脫憂慮的坦然,道德上令人清爽……”②而徐朔方先生《論“三言”》一篇中,則認為,作品強調“少男少女,情色相當”,三巧與陳商之間的所謂愛情,只是“情色之娛”,不配作為愛情看待。這篇小說不是對禮教的否定,而是對愛情的否定。③前者的觀點是以現代的角度在考察作品,體現的是當代人對人性的認識,后者則立足于作品當時的道德和思想基礎,沒有現代接受的參與。兩者都失于偏頗,沒有能夠體現出一篇有著產生于古代而流傳于現代的雙重性質的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應當把握好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的中庸,做到既有歷史又有現實,掌握好歷史與現實的交流與對話。在現實對過去無止境的接受中,既體現古代文學作品作為歷史的價值取向,又以當代的標準發掘過去文學的意義。
四、作家與讀者的中庸
任何信息的傳播都是發送者、媒介者和接受者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作為文學,它的發送者是作家,媒介者是作品,讀者是接受者。文學作品的歷史地位決定于創作意圖與接受意識的統一。而文學研究的價值也同樣決定于其對作家和讀者的解讀是否是創作意圖與接受意識的統一,是否能夠在作家與讀者之間,在作品與讀者之間架起一座橋梁,使其能夠更好地溝通。尤其是在古代文學的研究中,這種溝通尤為重要。古代文學研究首先要能夠立足于作家當時的創作背景,從作家角度正確解讀其在作品中蘊含和宣揚的意識,而后要關注作品在長時間的流傳中意義與價值的轉換,然后立足現代體會新的閱讀角度、非專業的讀者可能產生的閱讀期待,最終找到古代的作家、古今并存的作品與現代的讀者之間的中介點。明確作家與讀者因古今時代不同而產生的意識差異,以及其間由于共同關注一部作品帶來的聯系,從而更好地發掘或引導讀者的閱讀期待,也能使作家的創作意圖被充分地理解。而要完成這樣的任務,古代文學研究者就應該有既客觀又主觀的身份定位,在作家與讀者中保持中立的立場,也就是嚴守中庸。否則,就與一般的讀者無異,無法完成作為研究者應該完成的任務。幾乎所有的古代文學作品,從它的誕生之日起,就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目的研究著。尤其是那些優秀的、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留存至今的古代文學作品,在其流傳過程中每時每刻都被研究著。這種研究對作品和作家來講是值得慶幸的,因為這是對作家勞動和作品價值的肯定,但對于現代的研究者來說,卻實在不算一件好事,再深刻、再宏篇巨制的作品也經不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反復咀嚼。要想不乏味,要想出新,似乎只有“華山一條路”,就是在某一立場上,鉆研到極致。但筆者認為,這樣的終極性研究恰恰是一條死胡同,堵住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繼續發展之路。因為這種方式無疑是為文學研究而研究,在結合作品分析的同時,反而把結論與作品推得更遠,實質上與作品本身是完全間離的,也就失去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應當發揮的作用。只有在內容意義與形式結構、對象客觀與主觀建構、文學傳統與現實需求、作家與讀者及其他許許多多古代文學研究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矛盾中,找到最佳的平衡點,也就是嚴守中庸的研究者,才能夠得到真正符合作品實際、作家實際、時代實際和讀者實際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