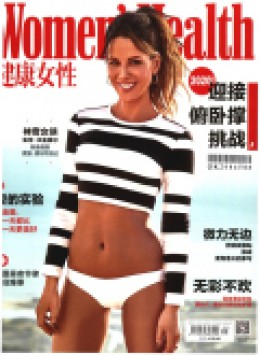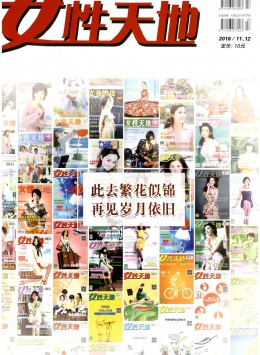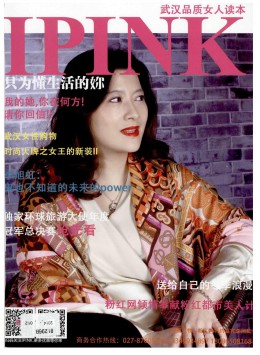女性文學與兒童文學教育的關聯性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女性文學與兒童文學教育的關聯性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現代兒童教育問題的重視與現在女性文學的發展密不可分,在歷史發展源頭上具有同一性,而女性期刊早期欄目的兒童文學設置以及女性作家對于兒童文學的參與,也使得現代文學中“婦女和兒童”問題得到了啟蒙者的重視。
關鍵詞:兒童教育;兒童文學;現代女性文學
伴隨著女性解放問題,兒童的發現與兒童的教育成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這種指征最明確的是震動寰宇的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正所謂“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①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對兒童教育問題的思考使得他成為中國第一位從“未來國民”的角度思考“開民智”“養新民”的人。而由此生發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于兒童問題的關注,魏壽鏞、周侯予合著的我國第一部兒童文學(教育)研究著作《兒童文學概論》中說:“這兩旁的不用說,年來最時髦,最新鮮,興高采烈,提倡鼓吹,研究試驗,不是這個‘兒童文學’問題么?教師教,教兒童文學,兒童讀,讀兒童文學,研究兒童文學,演說兒童文學,編輯兒童文學,這種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驚可喜。”②
這種對于兒童文學的關注也大量反映在當時的報刊、期刊當中,其實早在晚清時期兒童文學報刊雜志就已經開始出現,并出現了兒童文學叢書。1875年,美國教會學校清心疏遠創辦了《小孩月報》(后更名為《開風報》),1897年上海蒙學公會創刊了《蒙學報》,1902年,上海文明書局出版教科書《蒙學課本》(文言文),1910年孫毓修開始主編出版《童話》叢書,《童話》共計102冊,以譯述、改編為創作方法,其中包括29中中國歷史故事,包括《史記》、《前后漢書》、《唐人小說》、《木蘭辭》、《今古奇觀》等等,48種取材于西洋民間故事,如希臘神話、《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格林童話、貝洛童話、笛福小說、斯威夫特小說、安徒生童話等等。
與兒童期刊相對應的就是近現代知識分子對于兒童文學的翻譯、傳播、研究和討論,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兒童文學領域進行著初期建設和耕耘,在兒童文學翻譯方面,盡管當時沒有明確的兒童文學概念,卻出現了為兒童為主要閱讀對象的翻譯盛景:1888年張赤山翻譯的《海國妙喻》(《伊索寓言》)(繼1625、1840年的第三個中譯本,1907年放入《海外異聞錄》出版由天津時報館代印),1900年對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的進行了大量、多版本的翻譯,1902年2月到1903年1月,在《新民叢報》第2號到24號連載了梁啟超、羅孝高翻譯的《十五小豪杰》(法文原著名《兩年間學校暑假》),1902年11月到1903年9月《新小說》(1———7號)刊出的《二勇少年》(南野浣白子述譯),1903年徐念慈翻譯的《海外天》由海虞圖書館出版,190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臨沭、李世中合譯的《愛國二童子傳》,1905年包天笑翻譯的《兒童修身之感情》(1905年上海文明書局出版)及其1915年商務印書館初版單行本的《苦兒流浪記》等等不一而足,雖然這些作品有的秉持科學、有的秉持奇幻冒險,有的主旨在于教育,有的則著力于宣揚愛國主義,但比較明確的是其翻譯均有這樣的初衷,如梁啟超說“見這本書可以開發本國學生的志趣智識,因此也就把它從頭譯出”又如包天笑翻譯《兒童修身之感情》時說“此書情文并茂,而又是講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最合十一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口味”。③
對兒童文學問題的研究也開始出現在精英知識分子的思考視閾中,1912到1913年,周作人發表了《童話研究》《童話略論》等文章,才真正將兒童從“未來之國民”的身份還原到兒童的身份,不僅把兒童看作獨立的個人,而且要把兒童當作兒童,以兒童特質出發去研究兒童,這種主張是最切合兒童文學研究命脈的觀點。錢理群在對周氏兄弟的研究中,就極大肯定了周作人對五四時期“兒童的發現”的貢獻,并認為五四時期周作人對兒童問題的考察與其早年在紹興時偏重國家民族繁衍的立場不同,而是轉向了“人”的健全發展的角度,將兒童作為“人的發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錢也強調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所進行的兒童學、童話學、神話學研究在文學觀念、藝術思維方式等方面都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開拓。④
而另一位舉足輕重的兒童文學研究者翻譯者就是魯迅,魯迅的兒童文學翻譯占據了他120余篇翻譯的重要部分。早有研究者發現,從1921年左右魯迅與周作人的通信推斷,周作人從最初對安徒生童話全無興趣到后來成為“中國介紹安徒生第一人”的成長過程中,魯迅起了指導與啟蒙的作用⑤。就在《婦女雜志》上,魯迅也先后發表過翻譯愛羅先珂的《魚的悲哀》《小雞的悲劇》。與此同時,諸多知識分子也紛紛重視兒童文學,如知名學者趙景深、鄭振鐸、張梓生等人,他們不僅廣泛翻譯了俄羅斯、日本、歐美知名童話,還進行了專門的有關童話的學術性討論,如發表于《婦女雜志》八卷1號通信欄目的鄭振鐸《兒童世界宣言》、同期的趙景深、張梓生的《兒童文學的討論》、八卷7號馮飛的《童話與空想》、十六卷1號霜葵的《童話與婦女》、十七卷10號朱文印的《童話作法之研究》,趙景深還于1924年將有關文章會變成中國首部童話論文集《童話評論》。
那么,兒童文學類型又是如何與女性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呢?早在維新變法之初,梁啟超就已經將兒童教育的責任與女性的家庭教育相聯系,他認為,兒童教育的責任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師。而當時中國的教師“蠢陋野悍,迂謬猥賤”,“毀齒執業,鞭啟觥撻,或破頭顱,或潰血肉”,“導之不以道,撫之不以術”。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教師,才使得中國的兒童教育質量低劣,“是欲開民智而適以愚之,欲使民強而適以弱之也”而兒童教育的關鍵,百分之七十二歸于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梁啟超又特別強調母親對兒童的影響,但可惜的是:“中國婦學不講,為人母者,半不識字,安能叫人”,所以“女學衰,母教失”。⑥因此要發展兒童教育,就要發展女子教育。《女子世界》發刊詞中《女界鐘》的著名撰稿人金一也這樣去理解女性的“母體”功能:“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先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先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⑦可見在維新改革派及其觀點接受者那里,女性首先的屬性是母性,這里就孕育著母與子的天然聯系,而女性教養兒童成長的邏輯也由此而來,可以說這種女性與兒童的必然性聯系建立的基礎仍然是一種女性歸屬家庭的傳統女性價值取向,承認女性教育之功的前提一不是女性與男性的性別差異,二不是兒童自身的兒童發現,但是注重女性教育提升對兒童子女的教育,這本身確實起到了對女性參與兒童文學的創作推動作用。
兒童文學由此也進入了民國時期的教育體系,特別是女學體系中,1923年4月錢基博在其所擬的《三年師范講習科國文教學綱要》之“本科作業支配”中將“通解普通語言文字”、“自由發表思想”與“解悟小學教學法”作為師范教育的三項要務,并指出若要“解悟小學教學法”就要研習“兒童讀物研究”和“改文”兩類重要的課程⑧。1924年北師大附中高級部女子師范科課程標準中開列的科目有“模范文選”、“書法”、“文字學”、“國語發音學”、“語法”、“修辭學”和“兒童文學”。⑨張圣瑜在其所著的《兒童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的“例言”中寫道:“本編材料適敷師范科學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兩學分之修習,編者在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作為研究材料,復經邵鶴亭君于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采為教材。”教育系統尤其是女學教育內兒童文學的重視和固定化更為女性與兒童文學發展樹立了牢靠的思想接受基礎和現實儲備。
女性期刊發行之始就將兒童文學尤其是“童話”這一體裁納入到撰稿的視閾中。以《婦女雜志》為例,自1915年發刊始至1932中刊物終結,沒有中斷對于童話小說的刊發,在王蘊章主編時期,共刊發“余興”欄目(家庭俱樂部)童話41篇;章錫琛主編時期刊發家庭俱樂部“兒童領地”童話38篇;即使其后編輯屢經更迭,還發表了16篇。如此宏大的童話刊載量在現代報刊上的出現意味著幾個事實:第一,當時的知識分子(撰稿人、編輯者)充分認識到了兒童文學的重要價值和作用;第二,盡管數量巨大,但是童話大都來自于西方兒童文學資源的借用和翻譯,真正原創性的兒童故事仍屬少數,這恐怕也是民初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個現實境況;第三,童話體裁在女性期刊的出現印證了女性期刊在編輯話語時的天然的母性定位,將兒童、家庭統一歸納于女性事務范圍之內。女性期刊早期欄目的兒童文學設置以及女性作家對于兒童文學的參與,也使得現代文學中“婦女和兒童”問題得到了啟蒙者的重視。
注解:
①梁啟超.立法憲議•少年中國說[C].見:飲冰室合集(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5.
②張心科編著.民國兒童文學教育文論輯箋[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1.
③胡從經.晚清兒童文學鉤沉[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2:106.
④錢理群.第四講:兒童學、童話學、神話學研究與傳統文化的反思[C].見: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講.北京:中華書局,2000:48-64.
⑤藤井省三.魯迅與安徒生———兒童的發現及其思想史的意義[C].見:陳福康編譯.魯迅比較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⑥梁啟超.論幼學[C].見:飲冰室合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社,1989:45-60.
⑦金一.女界鐘[J].女子世界,1904,1(3):2.
⑧光華大學教育系、國文系編.中學國文教學論叢[A].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117.
⑨高級部女子師范科國文課程標準[J].北京市大周刊,1924,237(5).
作者:杜若松 單位:長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