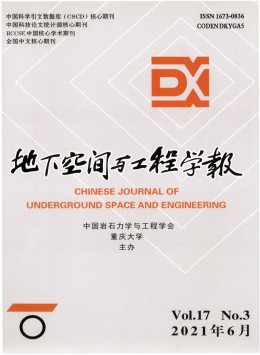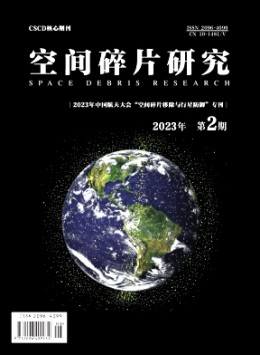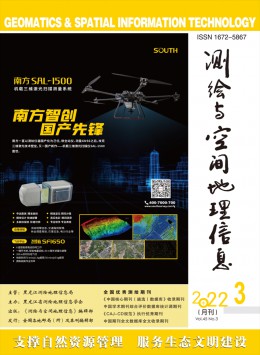空間隱喻五四兒童文學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空間隱喻五四兒童文學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物理空間: 確證兒童價值體系的中國境域
可以說,傳統的力量化為空間的秩序,將其影響延長到現在時段中來。在這種封閉和沉滯的物理空間中,外來文化訊息是無法折射和滲透進來的,兒童即使獲得了某些現代文明的信號,也難以真正形成自覺的意識,最終被習慣的規則和日常的秩序吞噬得無聲無息。當然,也有這樣一些兒童,他們能調節和整合自己的空間意識,他們的精神始終流動,在虛無的空間境地中綻出可貴的生命意志。在葉圣陶的《阿鳳》中,阿鳳對于婆婆的打罵始終保持堅忍的精神意志,在作家看來,“伊這個態度,有忍受的、堅強的、英勇的表情”。在趙景深的《紅腫的手》中,面對“我”的刁難,小全用“我不”、“我不去玩”、“我不跪”這樣的否定語言予以反抗,這在我看來有一種“英雄”的樣子。當然,兒童主體地位的確立是建構未來中國的第一步,如果兒童不能在現存的空間境域中彰顯作為未來國家的“人”的品格,那么其之于未來中國的價值也只能是缺席的。因此可以這樣理解,上述這種空間境域為兒童的主體價值的確立提供了檢驗的平臺,只有那些離棄了沉淪狀態,擁有自我獨立的精神品格,領悟未來籌劃的兒童,才能擺脫成為他人的影子和化身,成為未來國家的精神支柱。
二、文化空間: 透析中國社會分層的話語對峙
通過對物理空間背后文化意義的探究,為我們研究中國社會空間的文學分層提供了條件。物理空間與文化空間一起,構成了五四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重要畛域。伊夫•瓦岱說過: “傳統社會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特征,它的影響足以說明傳統思想體制特點( 我們也可以用神話思想一詞來概括它) : 這就是既存在于空間也存在于時間中的絕對基準點。”這意味著傳統的思想和精神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它會形成一種權力,滲透于主體存在的時空體中,以此來影響、規訓個人的行為,對個人的行為進行道德判斷和價值評定。在傳統文化的思想體系中,有形的空間位置的秩序是與無形的文化身份、價值秩序聯系在一起的,是具有意識形態話語權力和規范人言行的重要載體。在五四兒童文學作品中,“兒童”與“成人”的對立構成了中國社會結構中最為基本的關系網絡,他們擁有著不同的話語體系,其對峙與沖突表呈了中國社會分層的文化特質。五四知識分子意識到了兒童與成人的對立,并將其視為兒童文學內在文化構成的重要維度,予以審視。冰心以小孩子的口吻十分貼切地寫出了兩種群體的區別: “大人的思想,竟是極高深奧妙的,不是我們所能以測度的。不知道為什么,他們的是非,往往和我們的顛倒。往往我們所以為刺心刻骨的,他們卻雍容談笑的不理; 我們所以為是渺小無關的,他們卻以為是驚天動地的事功。”頗為相似的是,周作人通過對兒童游戲習性的考察,發掘了成人與兒童的重大分歧: “現在,在開化的家庭學校里,游戲總算是被容忍了; 但我想這樣的時候將要到來,那刻大人將莊嚴地為兒童筑“沙堆”,如筑圣堂一樣。
這些東西在高雅的大人先生們看來,當然是“土飯塵羹”,萬不及圣經賢傳之高遠,四六八股之美妙,但在兒童我相信他們能夠從這里得到一點趣味。”五四兒童文學中處處可見兒童與成人的對立,成人或者是家庭的主宰者,或者是學校的教育者,他們要么扮演不經意的“闖入者”,要么扮演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啟蒙者”。兒童與成人并非完全和睦相處,他們之間的沖突從未停止過。在《一課》中,葉圣陶指出,兒童最為核心的一種精神品質就是“動的生命”,主人公連上課也念念不忘隨身帶著的蠶,想著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泛舟的樂趣。在他的眼中,嚴肅的教育課堂只是正襟危坐的成人一廂情愿的安排,這一點也不適應于他。他的思緒隨著蝴蝶飛到了窗外,深密的相思開始了,在窗外自然之聲與室內沉滯之聲的對照中,“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聽窗外自然的音樂,那種醉心的快感,決不是平時聽到風琴發出滯重單調的聲音的時候所能感知到的”。在其另一篇小說《義兒》中,義兒不滿陳腐的教育,他與成人( 老師) 的對立是很直接的,他大膽地回擊成人對于他的無理斥責,公然挑戰教育體制。對此,顧頡剛指出,《義兒》是可以和《一課》合看的,“明明是很有生趣,很能自己尋出愉快的小孩,但社會上一定要把他們的生趣和愉快奪去了。甚至于最愛他的母親,也受了社會上的暗示,看著他的生趣和愉快,反而惹起了她的惱怒和悲感”。這種對立正如葉圣陶的《小銅匠》中根元的級任老師所認定的他與學生的關系: “我們與他們,差不多站在兩個國度里,中間隔著一座又高又厚的墻,彼此絕不相通。”那么,兩者能否有融通的可能呢?小說中有人接著提出“你先生何不把這座墻打破了?”此話一出,“大家默然”。由于對立的雙方都有一套自足的話語系統,都打上了主體意識的話語“密碼”,所以當兩套相異的話語碰撞時,對話交流常常以“中斷”收場。“雙向隔膜”的話語排斥力就產生了。擁有話語優勢的一方總是以壓制的方式規約著事態的進程,彰顯出符合話語權力者的價值取向。相反,兒童和兒童之間似乎有著能超越身份、地位的和諧關系。葉圣陶的《阿鳳》中有這樣一個場面: 當楊家娘當著我的三歲的兒子打罵十二歲的阿鳳時,“他終于忍不住,上下唇大開,哭了”。這里有“恐懼欲逃的神情”,更有兒童之間心靈的自然相通,“我從他的哭聲里領略到了人類的同情心的滋味”。
冰心《最后的安息》刻畫了兩個完全不同出身的小女孩,他們的友情和心心相惜勾勒了一幅美好的圖畫,與上述兒童和成人之間的關系有著極大的差別: “她們兩個的影兒,倒映在溪水里,雖然外面是貧,富,智,愚,差得天懸地隔,卻從們的天真里發出來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將她們的精神,連合在一處,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當然,這種美好的人際關系只能發生在兒童之間,一旦有成人的介入,一旦這種關系牽扯上更為復雜的社會網絡,就變得不那么簡單和純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特權兒童”身上的某種優越身份( 富庶家庭出身) ,使得他們的思維、行為、心理與一般的兒童有了區別,他們世俗味很重,頤指氣使,他們與成人一道虐待處于社會底層的兒童,自動地將自己與其他兒童區分開來。如毫無同情心地向另一個小女孩嘴里塞進劈柴刀把的青蓮( 徐玉諾《認清我們的敵人》) ; 又如隨意折磨、打罵貧困兒童小全的“我”( 趙景深《紅腫的手》) ,再如隨意支配阿美生活,把她當成玩耍工具的少爺( 趙景沄《阿美》) ……他們的行為完全缺失了兒童與兒童之間的心靈溝通,構成了成人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畢竟后者的關系更為直接和現實,也更為真實地體現當時社會結構的關聯。社會空間“允許某些行為發生,暗示另一行為,但同時禁止其他行為”[15。空間對個體的行為的規約和約束是始終存在的。兒童和成人的沖突往往會生成多樣性的權力關系,但是,這種空間位置的僭越是有界線的,僭越和界線相互依存,界線如果無法僭越,那界線的意義就不存在了; 同理,僭越如果毫無阻力,那它也毫無意義可言。在這種界限和僭越的雙向互動中,彰顯了彼此所表征的文化特質及社會現實境域。“兒童”的獨特意義在于其與“成人”的對立性,而且彼此互為他者。“他者”身份的確立為“自者”身份的建構提供了條件。“人類理解自我的方式就是要把自己所屬的人類群體劃出來,與先于自己的群體以及自己進化后脫離的群體相區別。確切地說,成人被理解為非自然、非獸性、非瘋狂、非神性———最重要的是,非孩子性。”
可以這樣理解,認知的最好途徑并非站在自我的視角上來理解自我,相反,從對立者的角度來反觀自我也許是一種相對深刻和理性的認知方式。兒童與成人的對立展示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層,兩者的張力對峙深化了兒童文學的內在涵量。一個顯見的道理,五四眾多知識分子對于兒童自然屬性的推崇,其實質是對于成人世界缺失了這種美好性靈的批判。豐子愷的話可能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心聲: “在那時,我初嘗世味,看見了當時社會里的虛偽驕矜之狀,覺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兒童天真爛漫,人格完整,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變成了兒童崇拜者,在隨筆中,漫畫中,處處贊揚兒童。現在回憶當時意識,這正是從反面詛咒成人社會的惡劣。”兒童與成人各站立于文化空間的一端,彼此相互參照。綜上,這種雙向力量的較量、抵牾,意向在空間中的糾合和參照,使得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視域有效地融匯在一起,從而生成出“包圍—突圍”的敘述空間。當然,在時間向度上,這兩條情節線以不同的速度、節奏和頻率糾合在一起: “包圍”折射了外在社會歷史演進的諸多訊息,打上了作家較強的社會歷史批評色彩; “突圍”所顯示的則是主體內在時間意識的價值取向,作家深刻復雜的意識流動從中得以窺見。在這種流動的空間里,意義可從多語義、多層面予以觀照、生成、展現,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有機地聯接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在五四情境中,盡管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有著較大的差異性和非對等性,但是它們最終還是融通于“想象中國”的宏大敘事之中。
三、空間的互動與文學話語的張力
五四新文學“拿兒童說事”直指“老中國”的思想文化體系,在破舊立新的邏輯中,開啟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偉大工程。如前所述,兒童與中國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建構與想象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探究五四兒童文學作品中所營構的兒童形象,揭橥符號表意系統呈示中國形象的可能性形態及精神表征,以此探究五四中國的現實境域與未來中國的文化走向。就五四兒童文學而言,兒童并非創作主體,他們只是成人知識分子觀照和審視的對象,正因為兒童作家的缺席,使得兒童沒法站在自我的角度上言說自我,兒童的書寫和言說只能依靠成人來完成。質言之,兒童形象的營構并非兒童“自塑”而是由成人“他塑”來完成的。這樣一來,圍繞著兒童主體的兒童觀念、兒童翻譯、兒童教育、兒童形象、兒童思維、兒童審美等范疇的建構是基于成人的自我考慮,即通過他者來確立自我。然而,即使成人設身處地地站在兒童的角度來言說兒童,也難以消除兒童與成人微妙復雜的差別。這使得這一時期的兒童作家陷入了難以平復的兩難境地: “一方面他們界定兒童、開創兒童世界就必須拉開兒童與成人的距離,強化兒童的非成人性; 另一方面他們要闡發成人的啟蒙理想又不能放任兒童超然的非成人性,必須再一次拉近兒童與成人之間的距離。”拉開兒童與成人的距離容易辦到,中國自古就比較漠視兒童的自主性,將其稱為“縮小的成人”,五四知識分子在肯定兒童的主體性的同時將兒童與未開化的原始人進行比照,肯定他們的自然天性。這種言論從生物進化學的知識上升到人類學的視野來考量兒童的心理、愛好、特質等問題本無可厚非,這也很好地為他們宣揚“兒童本位”思想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正是這種將兒童與原人的類比,順理成章地將兒童從成人主宰的社會網絡中疏離出來了。然而,這種疏離并不意味著切斷了兒童與成人的內在關系。
在啟蒙為主潮的五四時期,兒童與成人一樣,都不能脫離其所在的社會現實,兩者都承載著設計未來民族國家的使命,這要求成人作家將自我的理想與兒童的理想有機融合在一起,兒童的成人性必須彰顯,而這又與前面所述的兒童的非成人化發生了抵牾。可以說,兒童的社會化過程依賴成人的話語參與,成人教化和啟蒙兒童,也在此過程中確定了兩者的空間身份。兩者的生命形態也因空間話語的此消彼長而呈現出殊異的軌跡。時間與空間是始終扭結在一起的,談論兒童的時間意識實質上是兒童在特定社會空間及文化空間的時間感。這其中,兒童的生命感將時間和空間聯接起來: 兒童在空間中,但兒童不僅僅是空間的構成物,他有生命,時間才被呈現。兒童將其生命意識注入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才會具有兒童的時間性。五四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時間隱喻是通過空間場域中兒童的生命體驗、感知來呈現的。質言之,存在如下兩種截然不同的時空圖示:一是兒童生命被動地鉗制于既定空間,自身成為空間的一部分。這是一種不流動、靜態的時間形式,空間并未因兒童的生命存在而改變其所輻射的話語形態。在這個空間形態中,兒童生命是被動的,時間是被給予的,兒童的成長被吸附于僵硬的空間結構中而窒息。如那些麻木、無語的兒童庸眾,那些無助且無反抗的病態兒童,毫無痛感地接受了外在空間賦予的命運。由于他們的生命被他們的“奴性”、“愚昧”等消耗了,因此,生命是無時間性的,他們也不可能創造了自己的時間,他們的生命的時間靜止了、停滯了,最終完全變成空間性的。二是兒童生命反抗空間的吞噬,自我生命贏得時間。在個人和社會并立的空間中,兒童用成長去充盈和創造空間,通過其行為的沖擊去獲致時間的意義。與前者不同的是,它是一種流動的、可能性的時間形式。如那些不被命定的新兒童,他們在空間的壓迫和同化的情境下,意識到了本真存在的意義和絕境處境中的自我主體,或者“外突”,或者“反抗”,將其成長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動力。這時的生命就是時間性的,并孕育了創構全新的時間意識和生命形態的可能。應該說,五四兒童文學先驅對于兒童成長的考察源于其對于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全面洞悉。兒童的成長所隱喻的時間意識不僅是兒童社會化的表述而已,也是觀照兒童之外的民族國家精神氣質的話語資源。這使得兒童成長書寫超越了私人化的展示,而有了公共社會性的架構和文化內涵。
作者:吳翔宇 項黎棟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