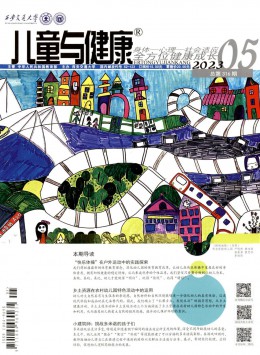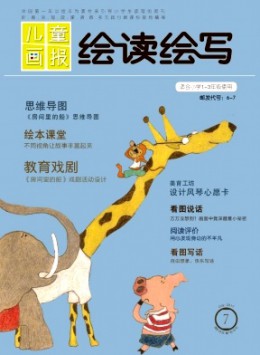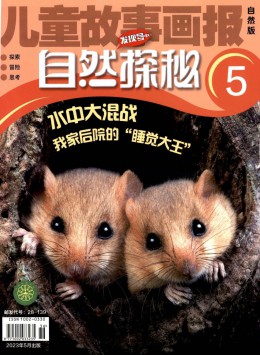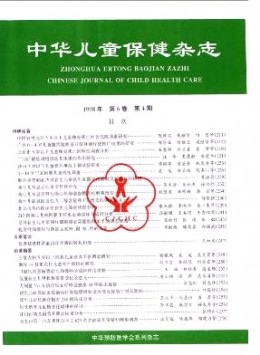兒童文學創作困境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兒童文學創作困境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人類社會對“兒童”的認識有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的過程。英國教育學家大衛•帕金翰的《童年之死》、美國傳播學者尼爾•波茲曼的《童年的消逝》都用相當長的篇幅闡釋了人類對兒童觀的認識過程:“童年不同于嬰兒期,是一種社會產物,不屬于生物學的范疇。至于誰是或不是兒童,我們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確的指令。”①在古希臘人看來,兒童和青少年兩個詞匯的含義是含混不清的,甚至可以包括從嬰兒到老年的任何人。而在亞里士多德時代里,人們對殺害嬰兒的行為也沒有任何法律和道德上的約束。由此可以看出,兒童觀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產物。人類社會兒童觀的轉折以文藝復興為界分為兩個階段。此前,兒童在人類發展歷程中是一個被忽視的存在,兒童的價值和權利不為人們所認可,完全是成年人的縮影。兒童的各種行為以成人為標準,還沒有構成完全獨立的個體化存在。在生活中,兒童被限制各種自由,包括游戲娛樂。文藝復興之后,西方文化走出了封建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困境,人文主義思潮日漸成為社會的主潮。人的主體性、人的價值越來越受到尊重,兒童也開始受到新的關注。人們開始關注兒童身心的和諧發展,將兒童視為有著特定人格的主體性存在。此后,英國哲學家洛克的天性“白板”的兒童觀、盧梭的“發現”兒童觀、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兒童中心論”等將兒童視為與成人同樣的人,開始兒童的個性和人格建構。
在兒童觀的發展過程中,媒介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刷術的發明,將人與人之間的知識差距拉大,有讀寫能力和沒有讀寫能力的界線將人劃分為成人和兒童。到了15世紀,學校的建立和兒童日益受到保護,讓兒童成為“未發展成形的成人”。此后,隨著電報、電視等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各種信息的數量和質量開始在全社會迅猛發展起來,兒童與成人之間界線的歷史根基發生了新的變動。中國兒童觀深受西方文學觀的影響,在發展進程上與西方兒童觀有著相似性,但又存在著自身的個性差異。王海英在《20世紀中國兒童觀研究的反思》一文中認為,中國的兒童觀在20世紀經歷了四個階段,即傳統兒童觀、現代兒童觀、國家兒童觀和世界兒童觀。如果我們對這四種兒童觀從“兒童”視角考察,就會發現這一演變過程經歷了一個“成人本位———兒童本位———成人本位———兒童本位”的歷程。在中國傳統兒童觀中,兒童往往被視為成年人的附庸,是成人的財產,是“縮小的成人”。“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②在西方文化和兒童觀的影響下,現代中國文化的“兒童本位”的兒童觀開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引介和發展起來,并首先在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中開了先河。解放后由于受意識形態影響,人們對兒童的認識又回到了成人本位(國家本位)上來,兒童成為受教育的客體。直到改革開放后,兒童觀才開始出現了新的轉向。“從家本位的兒童觀、國本位的兒童觀到兒童本位的兒童觀,世界本位的兒童觀,20世紀人們對兒童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跨越式的變遷過程。”③盡管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中國現代兒童觀逐漸形成并發展起來,但是強大的傳統封建文化和社會的影響依然存在。各種兒童觀念的沖突影響著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的創作、傳播和接受。因此,在當下文學中出現對同一兒童文學現象褒貶不一、爭論不休的現象是非常合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現代中國兒童文學觀的確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源自近代中國學人對西方兒童文學觀的引進。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大量引進西方兒童文學和文化思潮的基礎上,“兒童的發現”成為現代中國兒童文學的起點。受這一思潮的影響,當時的魯迅、周作人、鄭振鐸、葉圣陶、冰心、茅盾等文學家紛紛致力于兒童文學的倡導、創作和出版,現代中國文學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兒童文學經典,如冰心的《寄小讀者》、葉圣陶的《稻草人》、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在這些文學經典中,兒童不再是成人進行教育的對象,而是被作為與成人平等的朋友、知心人來參與故事敘事的。“先進的兒童觀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人的發現’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兒童文學。”④但是隨著后來民族危機的日益加重,當關注現實、關注時代、拯救中華民族成為時代的主題時,作家們開始將兒童文學寫作轉向對“現實批判”,因此革命兒童文學成為三四十年代文學創作的重鎮。葉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黃谷柳的《蝦球傳》等成為這一時期兒童文學創作中的經典之作。特別是《三毛流浪記》對社會現實的鞭撻、對善良樂觀的小三毛的塑造,贏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讀者的歡迎。解放后,兒童文學成為宣傳政治思想、教育兒童的工具,出現了《小桔燈》、《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寶葫蘆的秘密》等時代經典作品。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素,教化功能變得非常突出。到了新時期,伴隨著“文學的回歸”和“人的回歸”,兒童文學觀開始回歸“兒童本位”,各種不同的兒童文學開始出現在文壇。
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兒童文學的譯介和創作方面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創作領域出現了鄭淵潔、梅子涵、黃蓓佳、楊紅櫻、孫幼軍、沈石溪等重要作家,他們在創作中堅持“兒童本位”的文學觀,從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風格出發,創作出了大量為兒童喜愛的文學形象,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創作觀念。但是我們還不能說,他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觀和創作觀。縱觀新時期三十年兒童文學的發展歷程,兒童文學觀的建構性努力主要體現出以下幾種趨勢。
(1)“為人性”的文學觀。新時期以來文學完成了從“階級性”到“為人性”、從“工具”到“審美”的轉化,關注人、尊重人、探索人的心靈成為文學創作的時代主題。這一創作觀的倡導者和堅守者是著名兒童文學家曹文軒,他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一直堅持書寫兒童善良美好的心靈。在《文藝報》的一篇題為《文學應給孩子什么?》的文章中,曹文軒集中表達了自己的兒童文學觀,認為:“兒童文學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無論是道義感、情調還是悲憫情懷,都是作為文學打造人類精神世界的根本,因此也是兒童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講道義的文學是不道德的。不講道義的兒童文學更是不道德的。”曹文軒的“人性”文學觀強調的是一種美的存在,要用美好的人性去為兒童打造一個美好的“底子”。所以,他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兒童文學創作中的“人性”、“精神的底子”和“陽光寫作”等關鍵詞。在一次紀念丹麥作家安徒生的發言中,他對安徒生的童話創作做出了自己的解讀:“因為他為我們創造了美感,這恐怕是安徒生與其他作家有所不同的一個地方。他始終把美作為文學中一個重要的部分來營造。”①當然,這只是曹文軒依據自己的文學觀念做出的文學解讀,但這一觀念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觸摸到兒童文學創作的根本。
(2)“少兒本位”的文學觀。所謂“少兒本位”的文學觀就是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將少兒視為獨立的個體,以少兒作為創作的本體,而不僅僅是被教育的對象。新時期兒童文學創作中,堅守這一文學觀念的有秦文君、楊紅櫻等。秦文君在《小丫林曉梅》自序中說:“但愿這本書也能傳導我的文學觀,以少兒為本位。”秦文君的“兒童本位”文學觀就是懷著真誠的心靈去為少年兒童寫作,就是要“更多考慮少兒的視角,少兒的情調,少兒的喜怒哀樂,少兒的審美,少兒接受文學的規律”,“所有藝術上的探索都要圍繞這個根本,忘了本,所有的動力都變得微不足道。”秦文君的文學創作中,處在成長期的少兒有著鮮明的個性,有著自己的歡樂、苦惱和困惑,例如《男生賈里》、《女生賈梅》、《小丫林曉梅》等。楊紅櫻的“兒童本位”文學觀更多地關注兒童文學的趣味性和閱讀性。“她的寫作姿態放得很低,將自己放在與小孩子一樣的平臺上,用他們的眼光去觀察,用他們的思維去思考,用他們的語言去表達。”②例如“淘氣包馬小跳系列”,通過一個個短小的故事塑造了一個有個性、有創意、充滿各種奇思妙想的小學生形象。“我一直都保持著童心。孩子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孩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我對其他都無所謂。”③
(3)“超越童心”書寫。與大多數新時期兒童文學作家不同的是,鄭淵潔的童話創作完全是自學成才。這就意味著他的寫作更多地遠離了來自社會的影響,便于從兒童角度來思考他的文學創作理念,而不是接受了某一現成的文學觀點。在鄭淵潔看來,他的童話就是讓兒童在閱讀過程中發現自己;通過塑造一個虛擬的童話世界,讓孩子的天性獲得最大的舒展。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經歷所致,鄭淵潔的童話中對傳統教育觀念充滿了批判和挑戰。他只上過小學四年級,后來的學習完全是靠父母的指導才完成的。這種兒童觀反映在他的童話創作中,集中表現為作家對童話主人公那些充滿想象的各種奇妙思想所作的極度張揚和對現實世界中種種僵化體制的無情批判。鄭淵潔認為:“一個人在童年時期最重要的事情是玩,兒童是通過玩來認識這個世界的。”所以,鄭淵潔筆下的皮皮魯、魯西西、舒克和貝塔等形象,都是天玩好動,滿腦子都是奇思妙想,例如騎著竹竿上天、操作地球控制機、在零食王國檢閱零食大軍等。
在今天這個日益多元化的時代里,人們對兒童文學的評價也有著各自不同的觀點和思考。譬如批評界對楊紅櫻創作的爭論,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例。很多學者從純文學、主題設置、故事情節、出版傳播、商業化等角度對其創作展開褒獎或貶斥的評價,甚至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其實,這恰恰是兒童文學走向多元化格局的一種表現。“我認為兒童文學應該有一個多元化的批評標準體系。因為現在的兒童文學創作和出版已經日益多元,只有對于不同類型的作品施以不同的評價體系,當代兒童文學創作才可能得到公允的評價,兒童文學批評和創作之間的互動才可能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①當我們在為新時期兒童文學走向“兒童本位”而熱情歡呼時,那么,究竟何為兒童本位?兒童本位的文學觀在作家創作和文本中又是如何體現的?可是,如果我們對新時期兒童文學創作實績做一個整體評判就不難發現,兒童文學創作只能說努力朝著多元化前行,還未完全形成真正的多元。所以,對“回歸兒童本位”、人性美、現實世界和自我表現等文學觀念需要展開深入反思和做出建構性的努力,是今后兒童文學真正多元化發展必備的基礎。
首先,“回歸兒童本位”是否就是兒童文學的目標?新時期以來隨著“回歸兒童本位”的創作觀念的確立,文學創作中已經將兒童平等地視為個體性的存在,而不再是被教育被灌輸的對象。因此,我們的兒童文學出現了繁榮的景象。但是,“回歸兒童本位”是否就是我國目前兒童文學創作的最終目標呢?因為一方面,“回歸兒童本位”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在西方文學影響下的一種努力建構的趨勢,但是,如何在現代文化建設中形成中國文化獨創的兒童觀和文學觀,才是中國文化和文學努力的價值所在;另一方面,回歸“兒童本位”這一大的文學觀不同作家又有著自己的諸多創作取向,或者說,作家對如何建構自己的兒童文學世界有著自己的理解,因為無論是就作家對文學自身的理解還是就兒童的認知來講,彼此之間都存在著諸多的差異。例如作家楊紅櫻從兒童心理出發,更多的是關注小學年齡段的兒童心理和各種喜好,如《男生日記》、《女生日記》等;作為學者的曹文軒更加關注對兒童人性美的建構,特別是對未來一代民族精神素養問題的呼吁,如《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等;作家梅子涵持“快樂”的文學觀,認為“兒童文學需要徹底的真誠,需要樂趣和幽默。趣味性的追求應該成為兒童文學的第一要務。”②特別是后者,不同作家的文學創作實際上就是一個朝著各自努力的文學世界探索的過程。雖然他們有的創作觀還處于探索階段,或者說還沒有從自動寫作轉向自覺寫作,但是這種發展的可能性已經或正在影響著兒童文學創作的格局和傳播的現狀。
其次,書寫人性美是否是兒童文學觀的最終目標?一談到兒童文學,很多人就會很自然地想起文學作品所展示的真善美主題和對各種丑惡的批判,例如格林童話中的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故事。這種創作觀念本身沒有問題,問題的關鍵是不應當將真善美的文學觀與表現真善美和假惡丑的題材混淆,也不應當僅僅將兒童觀局限在人性美的層面上。在兒童文學敘事的過程中,作家一般盡量回避丑惡、暴力敘事,而是傾情于美好事物的書寫。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學雖然是一個虛構的世界,雖然書寫真善美是永恒的主題,但它同樣也是個“真實”的世界,是一個多種要素構成的復雜的世界。其實在創作中,我們對假、惡、丑的回避更多的是一種題材上的選擇。在文學世界里,表現真善美題材的選擇應該說與表現假惡丑的題材有著同等的價值,甚至超過了真善美題材的價值。例如《一千零一夜》中那些殘暴的國王、愚蠢的強盜,對于文學主題的表達和增添敘事藝術的表現力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在少年兒童的成長過程中,他們對社會價值的判定是建立在整個現實社會基礎上的,因此,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在不斷影響著他們的認知。兒童文學作家不應當僅僅停滯在對丑做出簡單的批判上,而是要對丑的東西做出深入分析,才可能創造出新的價值觀,才會在書寫過程中建構起更為復雜的形象。兒童觀從成人本位轉向兒童本位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停滯不前的。特別是以互聯網為標志的電子傳媒時代的到來,兒童的成長語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這就要求作家在創作時要不斷思考自己的創作觀和兒童觀,讓自己的創作更加適合現代兒童發展的需要。因為信息傳播的速度和覆蓋面已經大大超越了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現實生活中各種新現象新問題更是層出不窮,如果依然采用過去的觀念進行創作,就很難滿足當下兒童心理和審美的需求。實際上,今天在兒童文學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作家已經開始關注這些問題。例如鄭淵潔的童話寫作,就對現代教育體制產生了深深的質疑;楊紅櫻的小說中,那些搞笑、有趣的故事得到當下兒童的歡迎;孫幼軍的童話中,敘述了動物世界中那些欺騙、搶劫等不良現象。文學世界在弘揚人性美的同時,是無法躲避假惡丑的。一個健康的世界是不會躲避假惡丑的,所以既往的兒童文學禁忌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兒童文學創作觀的拓展和延伸。“寫作客體的話語禁忌,已然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繁榮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擾與阻礙,不僅僅影響著評論話語、編輯口味、作家思路,甚至在廣大讀者中也造成了許多刻板效應。兒童文學應該寫什么?怎么寫?要處理這個問題,開放的心態比什么都重要。”①這種“開放”的心態就是要打破既有二元對立的思維觀,對兒童世界有新的認知和思考。
第三,兒童文學是否只到現實為止?文學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但文學作為一門藝術更加注重對現實做出作家個人的理解和思考。作家要通過建立一個虛擬的文學世界來寄托自己的夢想。所以說,兒童文學不能滿足于到現實為止,而要滲入作家自己的理想和思考,建立起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黃蓓佳在談及自己的寫作時曾說:“我生活當中不能去夠到的東西,或者想了不敢去做的,我可以用文學來完成。”②兒童文學要致力于解決人的精神上的困惑。很多少年兒童之所以愛讀曹文軒、鄭淵潔、楊紅櫻、梅子涵等作家的作品,就是因為這些文本中所塑造的文學世界是他們現實中無法獲得的,是能夠給他們提供各種快樂和夢想的樂園。而作家和主人公能夠在文學世界里和他們進行平等的對話,讓他們有了知心的朋友。但是由于受到中國傳統寫實觀的影響,兒童文學在與現實世界的關系上依然離得太近,作家缺乏足夠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第四,“自我表達”的文學觀是否存在局限?兒童文學不僅是成人寫給兒童的文學,還有一部分是兒童寫給自己的文學。近年來,在兒童文學領域出現了一種被命名為“低齡寫作”的現象。例如六歲的竇蔻創作了《竇蔻流浪記》,十歲的蔣方舟出版了《正在成熟》,等等。假如我們拋開商業炒作的外衣就會發現,“低齡寫作”是兒童出于“自我表達”的需求而進行的情感展示。在今天的生存空間里,兒童的心靈變得比以往更加復雜也更加隱秘,因此,兒童的孤獨感和期待傾訴的愿望十分強烈。于是,他們就拿起筆來用那些毫無顧忌的文字來書寫他們的種種想法和期待。正如文學評論家錢理群在評蔣方舟的作品時所言:“應該說,小方舟寫著這一切的時候,并不含有自覺的批判意識。這是她與成年人的,以及高年級的學生的反諷寫作不同的地方:她只是以一種近乎游戲的心態寫下了她和她的小伙伴的真實的觀察與感受,或者如座談會上的一位朋友所說:她向我們成年人的世界做了個‘鬼臉’。”③
由于少年兒童缺乏社會經驗和文化積累,必然會對社會生活中的很多問題無法做出相應的判斷,出現種種認識上的偏頗。例如蔣方舟在一篇題為《正在發育》中:“世界上最有自信的人恐怕都沒有臉發這張照片。他站在一座大橋上,一看就是農村來的進口貨。眼睛要是再小一點就不知道還有沒有眼睛了。看他那樣子,穿了個大減價時買的襯衫。有一顆扣子沒一顆扣子的。我媽配‘才子’那簡直是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對歷史課本史實的課下調侃,對父母私生活的評價,顛覆父母、學校的各種教育觀念,消解傳統的友誼,調侃社會生活中那些看不慣的東西。雖然這種創作觀念會引起兒童讀者的共鳴,很容易產生轟動效應,但是由于缺乏對生活的深度理解,一味去做出一些淺薄的否定,會導致自己的創作成為轉瞬即逝的明日黃花。快意的調侃雖然反映了少兒時代的游戲心理和對現實的反叛傾向,但總是出于一種膚淺的情感快意的話語狂歡,缺乏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建構自己的文學觀,打造屬于自己的兒童文學世界,是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重點。兒童文學有著自己的發展規律,有自己特有的讀者群,特別是隨著現代傳播的迅猛發展,讀者受眾對文學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一些家長寧可選擇從西方引進的兒童文學,也不愿花錢購買中國作家的原創,不能不引起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反思。一方面,中國現當代文學自發生以來,普遍存在著原創性匱乏的尷尬。
中國作家一個多世紀以來始終處于西方文學或古代文學“現代性的焦慮”之中,對西方和中國古代文學的模仿、復制成為影響文學質量的關鍵。另一方面,作家在創作中是否努力創作出自己獨有的文學觀也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沒有這種主體意識的創作終歸是無法形成自己的創作觀的。反映到文學創作和傳播上,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以至于很多評論家認為中國目前還沒有產生自己的暢銷書作家。雖然暢銷不等于經典,但是暢銷書至少說明兒童文學創作在社會上所產生的影響。畢竟我們是一個有著三億少年兒童的國家,有著龐大的讀者接受群。
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一改過去單一的信息傳播方式,除了紙質媒介之外,廣播、電視、互聯網、電子圖書等各種媒介形式紛紛參與到兒童文化和文學的傳播。傳播語境的變革也極大改變著新時期兒童的閱讀心理和閱讀視野,當下的兒童比以往任何時候對自己的閱讀有著更高的要求,對傳統家庭和學校教育持有著更高的期待;他們追求個性自由,追求人格的獨立;他們向往新穎獨特的生活,厭倦了守舊閉塞。因此,作家文學觀的獨特性和文本世界的新穎性是促成兒童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陳舊的文學創作理念影響了兒童文學創新的步伐。傳統中國文學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功能,這種文學觀念大大影響了兒童文學對兒童心靈世界的關注和塑造。“好的兒童文學作品,都是在對世界和人生的思考,在對人情和人性的藝術揭示上有所專長。”①在大眾傳媒時代,愛玩的孩子們有著多種游戲的選擇,對于那些灌輸性的、說教的作品、沒有任何新意的作品產生抵觸情緒是非常自然的。兒童文學作家只有使自己的作品體現出兒童的真性情,符合兒童的真需求,其文學創作才能吸引被大眾傳媒包圍和浸染的兒童讀者。
文本的新穎性缺乏也是導致傳播不暢的重要原因。著名作家王蒙在回憶他的童年時說:“我回想小時候讀的作品,我記得最感動我的幾個作品,以至于大了還是在讀仍然還在感動的,往往都是由于它們能夠啟發人的愛心。”兒童喜歡通過自己的新奇發現來獲取更多的知識,喜歡在閱讀過程中受到文學敘事的啟迪,因此作家創作觀念的新穎性是解決兒童文學傳播暢通的關鍵。秦文君的“男生賈里系列小說”印數超過了100萬冊,被譽為“新時期少年兒童的心靈之作”。在這部小說中,賈里不再是一個十分普通的少年,甚至有時候任性、魯莽,做出一些傻事,說一些模仿大人的話,但是他又那么純真、誠實,對人充滿關懷和熱愛。正是這一人物不再像過去那些高大的人物以孩子們榜樣形象出現,而是與讀者一樣真實、容易溝通,所以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秦文君始終懷著一種單純、浪漫、寧靜的特殊的創作兒童文學的心境,有一種靈性質樸、毫無造作的理念。”②
好的兒童文學也可以是暢銷書和長銷書。兒童文學寫作和研究者應該做的事情是對這些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文本進行內在的分析,特別是對作家文學觀的研究,而不是僅僅滿足于表面的觀察和輕易做出的結論;滿足于以自己既有的文學觀發出種種不切實際且缺乏深度的評價,得出一些無法讓人信服的結論。因此,新時期兒童文學的發展和突破最為重要的一環還是要打破舊有文學觀的禁錮,從塑造兒童心靈的角度不斷探索兒童文學創作的新領域,為現代兒童心靈的建構做出新的探索。(本文作者:王倩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