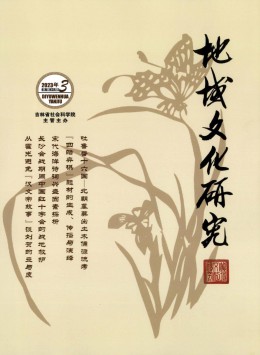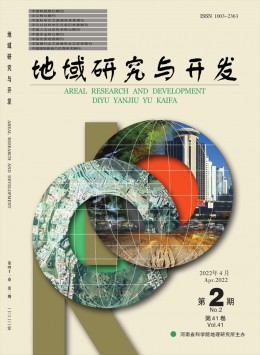地域文化視域下秦腔服飾藝術內涵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地域文化視域下秦腔服飾藝術內涵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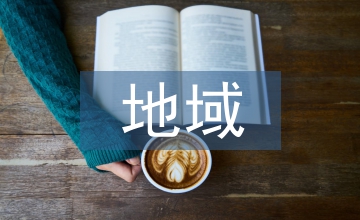
摘要:為了進一步探討秦腔服飾的思想價值和藝術表現內涵,以地域文化為視角,針對秦腔服裝的穿戴規制、款式造型、顏色搭配、裝飾元素等,從陜西關學思想、歷史文化符號及民間藝術等方面逐層分析秦腔服飾所受的地域文化影響.研究表明,秦腔服飾藝術在思想觀念上富含崇禮尚節的關學氣質;在藝術造型上注重寫意渲染,恣意張揚秦地民間藝術的絢麗;在創新運用上擅用歷史文化元素,激活藝術想象,彰顯厚重、深沉、質樸、務實的陜西人文精神.
關鍵詞:秦腔服飾;藝術內涵;穿戴規制;地域文化
0引言
所謂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特定人群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的總和”[1],不同地域內人們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不同,便導致了地域文化的差異性.這種地域文化差異性體現在語言、宗教、藝術、民風民俗等諸多方面.秦腔作為陜西地方戲的代表,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最直觀、集中地反映了秦地的歷史傳統、思想觀念和審美習慣.而秦腔服飾作為人物情感、性格以及劇情發展的外化標志,反映了地域欣賞心理和思維模式.所以,基于地域文化視角來解讀秦腔服飾,對于全面系統地理解秦腔服飾的藝術內涵有積極意義.目前針對秦腔服飾的研究,學術界有4種趨勢:秦腔服裝的發展歷史、類別的梳理,多是資料性的整理,如《中國戲曲志•陜西卷》、李明瑛的《秦腔舞臺美術》、楊興主編《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院志》等.秦腔服裝審美研究,如蘭宇的《秦腔戲曲服裝的裝飾性審美效果分析》,從戲曲服裝裝飾展現形式及審美效果分析秦腔服裝的裝飾[2];楊靜的《關于秦腔傳統服飾的研究》,側重從色彩和線條分析秦腔服裝的美學意義[3];趙紹強的《秦腔戲劇服裝的文化意蘊及審美特征的研究》,結合秦地文化關照秦腔戲劇服裝研究,較多側重于民間藝術[4].秦腔服裝某一行當、某一類別研究,如王會娟的《秦腔傳統劇目旦角服飾研究》,旨在探討秦腔傳統旦角服飾與古代女性生活常服及劇種風格的關系[5];周萌的《秦腔現代戲劇服裝的美學探析》[6],從美學角度闡釋秦腔現代戲劇服裝與秦腔傳統服裝及現代生活裝的異同.對秦腔某一劇目服裝設計進行賞析,如孫瑜《秦腔<大唐玄奘>服裝設計理念淺析》[7]等.從地域文化視角整體審視秦腔服飾的文章并不多見.本文結合調研心得,嘗試從地域思想觀念、歷史文化、民間藝術等方面對秦腔服飾加以關照,以求對秦腔服飾研究有一定促進.
1關學文化思想精髓的沁透
眾所周知,中國地方戲曲都屬于地域文化,每個劇種的風格、品性都與生養它的地域環境、地域文化傳統、地域民俗等息息相關[8-10].秦腔作為中國地方劇種中流播區域最大、觀眾范圍最廣、影響人口最多的地方劇種之一,它粗獷豪邁,蒼涼悲壯、慷慨激越,彰顯了陜西這個13朝京畿之地的蓬勃而又厚重的生命力和精神個性.秦腔雖然成為獨立成熟的戲劇形態時間較晚,但深受周秦漢唐正統儒家思想觀念的影響,更沁透著宋明以降關學文化思想的精髓,其幾百年來的發展,始終貫穿著明是非、知榮辱、辨善惡的價值尺度和人文情懷,這是秦腔具有雄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和不滅的生命力之所在.其中從北宋到明清盛行于陜西的關學思想對秦腔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價值理念上追求剛毅厚樸,恪守倫理綱常,重視道德氣節,崇尚禮治教化的關學氣質,還深深影響了關中戲曲的舞臺表現,主要反映在秦腔服裝的穿戴上.
(1)門風觀念濃厚
門風通常指一戶人家德行風氣,也是社會道德準則的一個窗口.門風的形成表面上看是一個家庭或家族的傳統、教育的影響,但地域文化卻是門風形成的土壤和基因,門風是地域文化的體現和豐富,不同地域的人們表現出不同的門風觀念,這不僅體現在人們現實生活中的言談舉止、衣食住行上,也體現在地方戲曲藝術中.在秦腔傳統劇目《柜中緣》中,即使小丑角色淘氣的著裝,也擁有鮮明的門風觀念.淘氣作為丑角,本是活躍氣氛,增加劇情笑料的角色,然而,秦腔中的淘氣略顯憨厚,年齡較成熟.以20世紀80年代肖玉玲演出版為例,淘氣上穿黑色對襟,下穿寬大紅褲,色彩對比夸張而不失古樸莊重,款式寬松自由卻不失保守,暗含人物所應承擔的注重義理、強調禮教的文化信息,體現了秦腔服飾穿戴在地域思想觀念方面的特殊寓意.而在其他諸如河南曲劇、山西蒲劇、河北梆子、川劇、彈戲和淮劇等六個劇種所演的《柜中緣》中,淘氣這個人物的服飾穿戴與秦腔相比,蒲劇在莊重性方面表現次之;淮劇中的淘氣無帽、光頭,孩子氣十足;川劇中的淘氣穿著一個紅色的裹肚,上場時,上衣沒有系扣,有不務正業的嫌疑;河北梆子中的淘氣更是“淘氣”不足,有點花花公子氣.從這一點來看,結合原劇作的意圖表達,劇情設置懸念是建立在擔憂門風敗壞來成就姻緣的,所以秦腔中的淘氣,在行為和語言上有和其他劇種相同的戲劇娛人、逗樂的傳統藝術處理,但在服裝穿戴上比較忠實于原作劇情,更能突出關中人濃厚的門第觀念.
(2)傳統穿戴規制下穿著方法特殊
穿戴規制就是戲曲演員運用傳統服裝以裝扮傳統劇目中的形形色色的劇中人物的基本規則或定例.這是戲曲藝術的程式性在服裝穿戴上的具體表現[9].龔和德在談論京劇穿戴規制時指出,演員運用穿戴規制向觀眾傳遞其裝扮意圖的途徑有五種,即冠服的款式、色彩、花紋、質料和著法…這五種途徑包孕著京劇裝扮的成套造型語匯[10].一般來講,傳統戲曲服裝具有象征人物性格、年齡、身份地位和所處環境的特殊功能.秦腔穿戴規制與京劇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款式、色彩等,但在穿著方法上也有不同于京劇的地方,如:同一人物在同一劇中穿不同服飾,賦予劇中人物特殊場合應有的寓意.如:秦腔劇目《轅門斬子》(又名《三換衣》),楊延景三次換裝所體現的人物心理變化.楊延景《頭帳》以三關元帥身份出現,戴帥盔、,穿帥服,有意擺脫家庭關系羈絆,以軍中公務為上,在母親面前表現出一股忠大于孝的楞勁兒.“二帳”中,楊延景穿綠袍花冠的駙馬服,以皇親身份面對八賢王時,表現出與八賢王分庭抗禮、不相上下的自信.在“三帳”面對英勇女將穆桂英時,因其是未來的兒媳,作為長輩的楊延景身穿黑色褶子,有渲染家庭氣氛,又不失莊重之意,其中不乏讓她歸順,承擔大破天門陣的重任,輔之于感情上的拉攏之意.此劇通過楊延景的三次換衣,從穿戴方面體現了對劇情的特殊處理,是秦腔服裝藝術個性的具體體現,彰顯了主人公忠勇而不失孝道,崇尚氣節,莊重寬厚而又直爽倔強的品質,是秦人形象的貼切描摹,同時體現了中國傳統戲曲服裝特有的文化觀和精神追求,也體現了西北地區特殊的地域文化觀念和藝術審美理想,迎合了關中人的審美心理.
2秦地民間藝術審美情趣的表現
民間藝術是各種民俗活動的形象載體,其本身便是復雜紛紜的民俗事象[11].民間藝術是普通百姓代代相傳的文化財富,是一個民族最為古老的名片,也是創造民間藝術的所在地域的一張靚麗名片.秦地民間藝術博彩紛呈,剪紙、繪畫、社火、皮影、刺繡等,其圖案、式樣色澤、工藝等,對秦腔服飾有深厚滋養,影響著秦腔服飾的款式造型、花紋裝飾和顏色搭配,使得秦腔服飾在尊崇傳統的基礎上,充分汲取關中文化的養分,恣意張揚秦地民間藝術的絢麗.
(1)等級觀念明顯
秦腔傳統著裝的上五色(紅、綠、黃、白、黑)和下五色(紫、粉或紅、藍、湖、香)深受我國古代服裝顏色等級的影響,上五色表示正色,在劇中一般用來標識主要人物;下五色表示副色,在劇中一般用來標識次要人物.紅色是我國傳統的喜慶顏色,中國古代女性的嫁衣多為紅色,秦腔服裝的用色習慣繼承了這一傳統,劇中角色婚嫁時都為紅色婚衣和紅色場景布置,象征熱情、活潑、興奮的紅色多是花旦的服裝顏色.唐代就有法律規定黃色為皇室專用顏色,黃色帔是秦腔中皇后、公主等皇室女性的專屬服色,更不用說黃袍加身的特殊意義.我國的喪服從周代開始已經使用白色(素衣、素裳、素冠等),古稱“素衣”,秦腔劇中吊孝的場景均是穿白色戲衣,如《祭靈》《秦雪梅吊孝》等.(a)《柳河灣的新娘》中的柳葉(b)《三滴血》中的李晚春圖1秦腔服飾中的刺繡Fig.1EmbroideryinthecostumesofQniqiangopera秦腔服飾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滋養還表現在裝飾物上.戲服上的刺繡圖案內容以喜慶、吉祥、祈福、納祥為主,在寓意上表現了中國人共同審美心理.如《柳河灣的新娘》中的柳葉在貧寒交加時,所穿服飾為梅花圖案,象征高潔素雅、堅貞自信.如《三滴血》李晚春褶子胸前就以彩繡為飾,來體現出閨門女性的清雅脫俗.
(2)地域特色鮮明
“歷代以來,陜西地區的服飾,以搭配對稱、均衡、工整、優美著稱于世,特別是民間流行的各種繡花工藝衣褲、圍裙、馬甲、肚兜、貓娃鞋、老虎鞋等至今盛行不衰.有名的鳳翔、千陽、扶風、韓城、合陽、長安、周至、大荔等地的刺繡服裝、貼花服飾,其色澤及式樣之精美,在三秦獨具代表性[12].鳳翔泥塑的憨態、馬勺臉譜的夸張,戶縣農民畫的平實,華縣皮影的抽象,紙扎藝術的傳神…都可以看出關中民間藝術的寫意、重彩、輕型的藝術特征.這些習俗、風格和元素對秦腔戲曲服裝的影響明顯.其中關中紙扎與其他區域紙扎藝術相比,鮮明的個性在于受關中習俗影響,不僅僅用于喪葬儀式、廟會神像,還影響到秦腔服飾的設計和使用.最典型的是陜西周至一帶,紙扎神像習俗在廟會上用于烘托氣氛,至今仍在流行.“神像主要包括菩薩、壽星、八仙、王母娘娘、黑虎、靈官等,整體造型力求嚴謹,與供奉的泥制神像一致.在整個紙扎技藝中,其制作工藝最為復雜,并且要求較高”[13]在這些紙扎神像中,與秦腔服飾關聯最為密切,且為秦腔服飾所獨有的是黑虎、靈官.黑虎即《黑虎下山》一劇中的趙公明.趙公明的服飾與關中紙扎相通之處在于頭飾的裝扮,頭盔上有扇子圖樣的折紙,材料為蠟光彩紙,顏色多為紅色和黃色.這種裝扮寓意在于其已成神靈,重在美化渲染其神通.筆者在采訪周至縣陳記三多堂陳樸福先生后得知,關中紙扎趙公明頭飾上的裝扮,當地叫“錢糧碼子”,只有神靈才戴,多用金黃色.秦腔戲曲服飾為追求演出效果,再添加紅色,折成扇子型,內側為黃色,外呈紅色.在采訪過程中,陳樸福先生介紹靈官紙扎與秦腔《打樓》(又稱《打臺》)折子戲關聯密切,趙公明的頭飾“錢糧碼子”也用于靈官.甘肅省西和縣秦腔劇團王團長也表示,作為戲臺必用儀式,該團還保留著此劇演出.據王團長介紹,趙公明神鞭上纏有的紙幡為“錢糧”,多用藍、綠、紫三色,表示其兵器神通廣大;趙公明頭飾物件為“碼子”,這與關中叫法略有不同,用法完全一致;靈官的神锏上也纏有此物,顏色與趙公明神鞭上“錢糧”相同.關中有“正月初二祭財神、正月初五財神巡游”的民俗,在眾多財神傳說中,影響最大、奉祀最多的是趙公明.關中的財神民俗、祭祀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秦腔服飾藝術與關中紙扎藝術.秦腔服飾對關中紙扎藝術的借鑒,是當地人們地域信仰和審美心理趨向所決定的.
3陜西歷史文化符號的融入與彰顯
陜西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和時間最長的省份.能夠代表陜西歷史文化的符號很多,兵馬俑、大雁塔、黃帝陵、西安城墻、秦嶺、半坡遺址、革命圣地延安、秦腔、碑林等,這些文化符號豐富了現代秦腔的舞臺呈現,也激活了秦腔服裝設計師的藝術靈感和構思.
(1)秦兵馬俑元素
秦一統六國,所創造的博大雄渾、開拓進取的秦文化帶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思考,尤其是兵馬俑,是對秦代短命而恢弘歷史的真實再現和無言詮釋,也給了藝術家們無限的想象空間.如:陜西省戲曲研究院秦腔團的《千古一帝》,劇中人物的鎧甲和頭飾元素,融入了兵馬俑的造型和裝飾元素,以衣服的象征意義,彰顯出秦所向披靡,橫掃六合的氣勢,歷史畫面宏偉壯觀,人物形象飽滿而富有歷史感.這種陜西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質,是其他劇種所無法具備的.
(2)漢代侍女服裝元素
漢代歷史對中國文化影響可謂深遠,且不說漢語、漢字等中華文化的核心元素,僅就西安漢陽陵所展示的漢代世俗化、生活化的場景,也是現代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漢服作為漢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其交領右衽、褒衣廣袖、系帶隱扣等特點不僅影響后世人們的主流著裝風格,也影響著戲曲服裝的設計.20世紀80年代易俗社演出的《卓文君》,劇中卓文君服飾就參照漢代侍女服飾,正如王保易所說“卓文君的造型,吸收了漢代侍女的形象特征”[14].
(3)唐代女性服裝元素
大唐盛世留給陜西的歷史元素更是不勝枚舉,其富裕和開放的程度表現在服裝上是雍容華貴、多彩多姿、張揚自信.秦腔音樂劇《楊貴妃》就較多參照了唐代宮廷服飾,如糯裙、長裙、腰裙、披帛、蓖、義髻、釵等,較好體現唐代女性服裝以胖為美、以露為美的審美心理[15].2008年,由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團推出的大型秦腔交響詩畫《夢回長安》,將周、秦、漢、唐歷史風云重新搬上舞,是融秦腔、交響、歌舞、舞美詩畫于一體的全新藝術演出,是用4D概念對秦腔藝術的大膽創新.其根據劇情特制的著裝達600多套,富有青銅紋式的“周服”,神秘、厚重的青銅器意象成為周代禮樂文化的符號;突出鎧甲戰袍的“秦服”,突出了糾糾大秦的氣勢;運用五谷豐登線條的“漢飾”寓意漢代休養生息而百姓倉廩充實的景象;奇異多姿、翩翩霓裳的“唐妝”則更是盛唐氣象的絕美展示.這樣的服飾效果,既有歷史感、地域性,又使秦腔藝術呈現更加時尚化,迎合了現代人的審美需求.這可謂對陜西古代歷史文化元素應用的綜合體現.
(4)革命歷史元素
《血淚仇》是秦腔現代戲的經典之作,其中王仁厚形象的塑造,在服飾運用上融入了革命文化元素,凝聚了特定歷史時期的記憶.此劇在延安時期上演時,王仁厚的服飾融入了陜北地域特色,頭上戴的毛巾裹扎的方式,帶補丁的褂子,這并不是有意的設計.據《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院志》記載,這是讓打前站的同志借好,有時向群眾以新還舊[16].此劇服飾雖然照搬于生活服裝,但卻記載了秦腔現代戲服飾融入革命文化元素的歷史.在20世紀50年代演出時,在服裝處理上增添了更多的補丁,以揭示被壓迫人民的悲慘遭遇.如王仁厚的服裝,多處補丁的上襖下褲,腰帶凌亂,還原了遭迫害人民的形象.20世紀80年代演出時,選用斜襟大褂,補丁減少[6].2015年三意社在紅色革命之鄉照金演出,服飾雖不見補丁,但結合現代審美觀念,較好保留了革命歷史元素的神韻,激發了觀眾對苦大仇深的底層百姓王仁厚的藝術想象.
4結束語
秦腔服飾雖然曾受到京劇等其他劇種的影響,但它畢竟長期得益于地域文化的滋養,在思想觀念和藝術想象上具有正穩、尚禮、深沉、質樸的地域欣賞心理和思維模式.陜西厚重的歷史文化和豐富的民間藝術也為秦腔服飾的創新性呈現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和藝術資源.所以,秦腔服飾的美不僅是色彩、款式、裝飾的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區域文化在道德與精神上的價值特點,秦腔服飾多年來的創新發展也啟發我們,戲曲藝術的傳承與創新必須和地域文化相結合,在包含中豐富,在豐富中創新,在創新中進一步彰顯地域文化.
參考文獻:
[1]張鳳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徑探析[J].浙江社會科學,2008(4):63-66.
[2]蘭宇.秦腔戲曲服裝的裝飾性審美效果分析[J].西安工程大學學報,2018(1):30-37.
[3]楊靜.關于秦腔服飾的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4:59.
[4]趙紹強.秦腔戲劇服裝的文化意蘊及審美特征的研究[D].西安:西安工程大學,2015:57-59.
[5]王會娟.秦腔傳統劇目旦角服飾研究[D].西安:西安工程大學,2016:61-62.
[6]周萌.秦腔現代戲劇服裝的美學探析[D].西安:西安工程大學,2016:25-48.
[7]孫瑜.秦腔《大唐玄奘》服裝設計理念淺析[J].當代戲劇,2016(6):62-63.[J].
[8]張阿利.陜派電視劇地域文化論[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10.
[9]龔和德.談戲曲穿戴規制[J].戲曲藝術,1983(2):84-90.
[10]龔和德.京劇穿戴規制[J].中國京劇,2003(5):28-30.
[11]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327.
[12]楊景震.陜西民俗[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13]張瑞超.陜西關中紙扎之陳記三多堂祭祀喪葬紙扎藝術[J].裝飾,2015(10):94-95.
[14]王保易.談秦腔《卓文君》的改編[J].中國戲劇,1987(7):24.
[15]鄭恩姬.唐代女性服飾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09.
[16]楊興.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院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6
作者:劉存杰 徐利蘭 單位:西安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