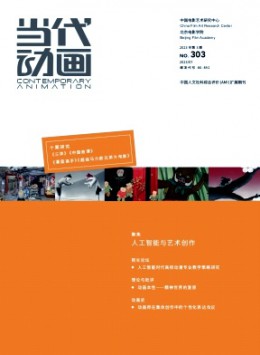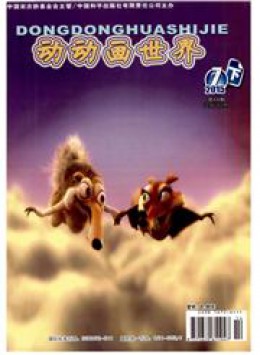動畫影像風格的建構與創(chuàng)新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動畫影像風格的建構與創(chuàng)新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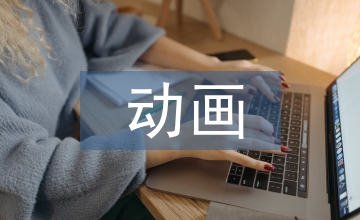
提要:當代中國動畫在消費及技術文化語境下不斷創(chuàng)新,同時也力圖追尋傳統(tǒng),探索自身風貌,建構中國動畫影像風格,但是仍然有很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因此,本文在梳理中國動畫傳統(tǒng)美學觀念及藝術方法的基礎上,深入剖析其與影像生產及敘事規(guī)律之間的矛盾,并嘗試探索當代中國動畫影像風格建構與創(chuàng)新的途徑。
關鍵詞:中國動畫影像風格傳統(tǒng)美學觀念敘事
一、傳統(tǒng)美學觀念及藝術方法
在中國動畫影像風格中的呈現影像風格從根本上說一種語言體系,是由特定文化孕育而生的影像形態(tài)所呈現出的穩(wěn)定面貌與基本特征。它不僅在表層上顯現為色彩、造型、構圖、聲音等,更為核心的是深層次的時空經驗模式。就中國動畫影像創(chuàng)造來講,盡管受到影像媒介和動畫藝術本體特征的制約,但創(chuàng)作者往往無法脫離民族文化和傳統(tǒng)美學、藝術精神之根,在形象塑造、心理刻畫、情感描繪、符號隱喻以及特定母題表達甚至是敘事法則上,都顯現出特定的喜好甚至迷戀。這些特點已經被許多研究者關注并探討過,但是本文想要進一步闡發(fā)的是,動畫不同于繪畫、戲曲、文學等傳統(tǒng)藝術,其本體性在于通過不同維度的影像和敘事來共同呈現意義世界。縱使中國動畫和其他傳統(tǒng)藝術形態(tài)一樣,致力于社會功能的實現,動畫往往也在平面上借助傳統(tǒng)繪畫中的線條、色彩元素及虛實、留白等方法,也像戲曲一樣強調情感的描繪性、符號的表現性等,但與這些傳統(tǒng)藝術形態(tài)不同,它更需要借助影像時空建構來完成故事的講述。因此,這里有必要先對傳統(tǒng)美學觀念與藝術方法中的時空建構規(guī)律做一下梳理。在筆者看來,傳統(tǒng)藝術中的時空建構,最為顯著的特征便是用時間性補充空間性。例如人物長卷、山水縱軸以及古版畫插圖中多個共時空間在同一畫幅里的并置,形成了一種流動的視角和“觀”的經驗。這種空間體驗模式注重的正是在全景式的舒卷自如的空間展開過程中,充分調動觀者的想象力和生命體驗,以時間為主脈來完成敘事。因此,這是一種典型的主觀敘事方式。當這種時空建構方式被運用到動畫中時,唯有類似于景深鏡頭和平行蒙太奇的影像語言才能與之相得益彰。由此,中國動畫影像風格便有了自身的基因與魅力。例如1963年創(chuàng)作的動畫片《牧笛》,便是這一影像風格的典型代表,其在構圖和取景、人物站位及景深調度等方面都極力制造出空靈的氛圍和時間流動的痕跡,而其敘事結構也與這種影調氣氛相呼應。誠如麥茨認為的那樣,各種表現手法都與敘事有關,因此可以說,敘事方式與影像風格也是內外合一的。羅蘭•巴特曾指出:“電影的特點正在于以一種‘文體’作為它的‘語言’”,(1)它與個人風格以及具體的語言相區(qū)別。在筆者看來,這里的“文體”指向的正是通過影像來完成敘事功能的特定影像生產形態(tài)。從世界各民族和國家的動畫影像生產來看,其影像風格無不是與敘事這一核心功能相輔相成、融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也只有當文化基因、審美觀念、形式元素與敘事方法結合起來時,影像風格才能得到完整的體現。從中國動畫影像風格來看,它呈現出的形式、空間皆與敘事無法分割,影像在呈現主體時空經驗的同時,也完成了對故事的講述;而這種“講述”方式,又進一步塑造了中國動畫影像風格。例如,《牧童》等作品在影像風格上注重意境的營構,在形象塑造上強調“物我同一”和意趣之美,流暢的音樂與人物的慢動作都頗具抒情色彩,彰顯出詩意的審美精神,整體上顯現出“中和”之美。在時空經驗上,它顯然是以時間統(tǒng)領空間,較少以具體的、寫實的空間形態(tài)來表達細節(jié),而是盡可能省略敘事成分。再如《三個和尚》等作品,充分釋放了符號與線條的敘事潛能,運用寫意方法勾勒了人性本真。總體來看,這些作品中的時空顯現、敘事主要不是靠視覺感知來完成的,而是借助虛擬性的空間和符號化表意來實現的。相較而言,日本動畫影像雖然也注重整體空間之美,但卻更強調生活細節(jié)和現實形象的唯美呈現,在空間處理上也十分寫實,注重光影等視覺效果。此外,鏡頭語言的運用具有更為直接的敘事功能。例如《驕傲的將軍》《大鬧天宮》《天書奇譚》等作品中有不少中、全景鏡頭,多將沖突角色雙方置于一個畫面內,而角色面部表情及身體細節(jié)等都游離于視覺中心之外,而這部分恰恰是格里菲斯通過近景、特寫來著力強調的部分,也是美國動畫的特色。全景深鏡頭則形成了較為復雜的畫面空間結構,觀眾在多層次的空間中也較易產生主觀感受與認知。再如,中國動畫中的平移鏡頭較多,在鏡頭調度上注重平面展開,如戲曲一般具有較強的舞臺性,而且這種畫面給人以舒緩、平穩(wěn)的節(jié)奏感,往往也使得整部作品在敘事上更顯悠長,呈現出一種詩性之美。此外,中國動畫中的空鏡頭不僅有助于虛擬空間的建構,像“留白”一樣為觀眾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想象世界,同時也能夠讓觀眾暫時脫離影像和離開劇情,體悟出那種似有似無、若即若離、難以言說的情感和主題。盡管從早期中國動畫創(chuàng)造實踐來看,造像、敘事等形成了較為和諧統(tǒng)一的風格,但是與傳統(tǒng)文學的詩性敘事或者繪畫、戲曲的意境呈現相比,影像創(chuàng)造畢竟有著自身的特殊規(guī)律,因此,當動畫電影在借鑒其他藝術創(chuàng)造方法的同時,其內部也就產生了矛盾。一方面,影像語言凸顯其形象化、直觀化、具體化特性,善于建構生動的畫面空間,這與“大音稀聲”“大象無形”等傳統(tǒng)審美觀念之間有著根本性的矛盾。在傳統(tǒng)的靜觀狀態(tài)中,主體的情思居于主動;而在觀影體驗中,主體更多沉浸在震驚狀態(tài)中,視像世界充斥于眼前,幾乎容不得主體片刻的思考,實質上消解了主體的想象空間。另一方面,影像語言特征也造成了影像敘事方式自身的特殊性,它具有時間性敘事與空間敘事相結合的特點,除了能夠按照創(chuàng)作者的意圖實現主觀敘事,也因豐富的鏡頭語言而生成復雜的詩性結構。與此同時,在消費文化與影像技術的發(fā)展下,影像語言不斷凸顯自身優(yōu)勢,主體需求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新的敘事模式和藝術方法必然隨之出現,這就進一步導致了影像風格與傳統(tǒng)美學觀念之間的分裂。
二、當代動畫電影的生產生態(tài)對傳統(tǒng)動畫影像風格的沖擊
當代中國動畫電影的影像風格,盡管受到各方面的沖擊與挑戰(zhàn),嘗試過不少轉型和突破,但始終沒有拋棄傳統(tǒng)美學觀念與中國動畫風格中的優(yōu)勢基因,力圖探索有別于西方的時空體系,追尋自身風貌。然而如前面所述,隨著技術文化與消費文化的全球化發(fā)展,新的影像風格與傳統(tǒng)美學觀念之間的矛盾也愈加凸顯,如何在與時俱進中守持民族特色,成為當代中國動畫創(chuàng)作者面臨的最為嚴峻的現實問題。從動畫本體來看,源自電影的特技和技術運用,始終是影響動畫美學的核心要素。從動畫的自律性發(fā)展來說,技術革新必然促使其在藝術方法和審美觀念上不斷嬗變,同時在內容上也趨向于與形式形成日趨完善的有機體,在敘事方式甚至題材上發(fā)生相應的變化。因此,如果說傳統(tǒng)美學觀念的生成因素是文化和社會,那么當代動畫美學的構成要素與推動力則是技術。影像技術是一種典型的全球化技術,它在媒介資本流動和影像傳播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各個民族和國家創(chuàng)作者及觀眾的審美趣味,也改變了動畫影像風格。例如,美國動畫影像風格的形成本就與技術美學密切相關,技術及其文化的不斷發(fā)展,以及技術與資本、市場的合流,最終催生了高技術影像美學,而它們又借助技術文化和資本的全球化,培育著世界觀眾的審美趣味與觀影習慣。因此,中國動畫電影美學及影像風格趨于被同化實際上是難以避免的。近年來,國內多數動畫影視作品往往在題材、符號上挖掘和利用傳統(tǒng)文化資源,但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化、形式化的層面上,其影像風格顯現出的美學特質,實際上與美、日等國動畫沒有明顯的差別。這期間,也不乏一些在美學上積極探索中國風格出路的嘗試,如《大護法》的水墨畫風極為美麗,但是暴力美學在影片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現,顯現出一種與《小蝌蚪找媽媽》《山水情》等傳統(tǒng)水墨動畫影像風格截然不同的審美趣味。與此同時,類型化生產也促成了多元混雜風格的誕生。例如,中國魔幻動畫風格、武俠動畫風格等,都屬于不同類型文化與美學融合產生的新風格形態(tài)。動畫藝術本就注重視覺變幻,追求形象夸張、自由、可變,在運動規(guī)律和設計上呈現出虛擬性特征,而當代審美文化偏重視覺感官體驗和對夢境、幻境等超現實時空的想象,加上數字技術的出現,為動畫語言和影像風格的成熟與創(chuàng)新提供了良好條件。早期中國動畫影像在技術與藝術之間尋求平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技術尚未成熟,而需要其他要素來進行彌補。但動畫及電影數字技術經過四十多年的發(fā)展至今天,我們已經迎來一個全新的數字影像時代,動畫制作更依賴于技術,而數字影像美學也為動畫美學帶來了新的元素。與機械技術時代的動畫影像創(chuàng)造相比,當代動畫影像創(chuàng)造一方面依托計算機CGI技術,可以逼真再現現實世界中的自然景觀和視覺奇觀,創(chuàng)造出美輪美奐的形象,由此沖淡了傳統(tǒng)美學觀念和審美趣味;另一方面,虛擬世界將理想與現實任意組接,創(chuàng)造出虛實共生的空間,不僅令主體的想象力被大大拓展,時空呈現方式得以進一步開掘,也改變了意象、意境的建構方式。從當代動畫敘事發(fā)展和類型化趨向來看,傳統(tǒng)影像風格的局限性也暴露出來。當代影視文本的主線往往是基于人與現實世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演化,大多圍繞著角色性格和行為動機展開復雜的情節(jié),而傳統(tǒng)影像敘事擅長的卻是回避社會矛盾根源、消解人與自然之間差異,呈現為一種象征性的、和諧的敘事形態(tài),這種影像敘事較適宜于表達情感的生離死別或者循環(huán)相因的世事沉浮,難以很好地講述復雜的現實故事。從《大魚海棠》來看,這種力圖將部分傳統(tǒng)影像風格與現代敘事方法結合起來的嘗試,顯然困難重重。此外,從跨文化傳播和接受來看,中國傳統(tǒng)動畫影像風格也面臨著窘境,因為身處異類文化語境下的人們并不認識這種語言體系的價值,便無法從語言的背后去探尋作品的意義世界。
三、傳承與創(chuàng)新:當代中國動畫影像風格的建構之路
面對上述困境,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來探尋出路。一方面,中國動畫影像需保持其審美特色,傳承優(yōu)勢基因。中國傳統(tǒng)美學觀念和審美范式具有濃厚的地域特征和社會人文內涵,是對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態(tài)的集中呈現,無論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國族形象塑造、文化復興、軟實力建構,還是本土大眾的精神家園建構,都需以這種文化基因為本色。與此同時,中國傳統(tǒng)美學觀念包含了對特定文化價值體系的肯定,在當代世界文化發(fā)展以及國際文化交流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例如,它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主張“無為”而非擴張和攻擊,顯現出人類對物質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對寧靜生活秩序的向往。其內在精神在總體上是平和的,審美風格也偏于靜態(tài),因此不習慣劇烈沖突與過度的感官刺激、令人目眩的瞬間變化等,而是在靜觀中體驗詩意的生存狀態(tài)。在當代文化語境下,中國動畫影像風格所具有的傳統(tǒng)美學特色往往能令人觸及童年記憶、反思科學技術對人類心智的異化,這種認知事物的模式與情感結構則顯現出一種珍貴的審美人格魅力。因此,中國動畫影像風格的建構應充分彰顯其優(yōu)勢,更多發(fā)掘影像的精神內蘊,強化影像風格整體上的象征意義,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傳統(tǒng)文化符號元素的借用上。誠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那樣:“趣味就是一種人們經由教育等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內在‘習性’”“趣味的表征實際上是對規(guī)則的一種無意識內化,它在潛移默化中成為人們的‘習性’。”(2)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趣味往往借助文化產品的美學風格柔性地顯現出來,讓大眾在審美實踐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自身的感覺方式和情感結構,形成相應的習性和趣味,最終接受和認同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所以,中國動畫不僅需要通過中國故事來書寫中國文化,也需要借助美學風格來吸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觀眾,更好地傳播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當然,如前面所述,影像風格的跨文化“涵化”復雜且不易,還涉及題材、敘事等多方面問題,需要依據具體情況而論。從《大魚海棠》《風語咒》等國內動畫作品來看,撇開敘事等問題,其空靈、超脫、詩意、唯美的影像風格與時空建構方式,的確將數字化時代的動畫“中國風”推向了新的高度,為后繼者積累了成功的經驗,但是如何將傳統(tǒng)美學觀念與當代審美文化對接,如何更好地解決技術與文化之間的矛盾,還有待于長期的探索。在這方面,《功夫熊貓》系列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融合模式。它借用數字技術成功地營造了頗具空靈與超脫之美的空間,在征服中國觀眾的同時,也促使其價值觀念得到認同,宮崎駿創(chuàng)作的日本動畫以及其他國家的動畫中也不乏此類經驗。另一方面,中國動畫影像風格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始終受到影像本體特征的約制,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影像語言上,還體現在敘事上。從根本上看,人類對于影像生產的價值訴求主要在于獲得“意義與快感”,成功的影視作品往往能夠讓觀眾通過消費敘事獲得愉悅感,同時把握世界的秩序。技術革新不斷賦予影像語言更加強大和完善的敘事能力,也促使空間敘事與時間敘事之間形成了更為復雜的關系,由此也拓展了文本的意義世界,不斷為觀眾帶來認知事物的新方式。因此,當代中國動畫也需要不斷探索意象、意境呈現與敘事之間的關聯,在傳統(tǒng)美學觀念與現代敘事方法之間進行巧妙縫合,使詩性結構更加符合敘事規(guī)律,才能重塑精神之維,建構起當代動畫影像風格。傳統(tǒng)動畫敘事如散文詩一般,強調抒情而淡化對立沖突、性格特征,但是當下以商業(yè)化、類型化為主流的影視消費,大多需要作品講出一個現實中的動人故事,戲劇化情節(jié)、板塊式結構、嚴密的因果邏輯以及儀式化段落、符號化的人物也應運而生。隨著敘事的密度與速度不斷增加,敘事節(jié)奏也顯著加快,加上復合類型敘事形態(tài)的出現,敘事線索日趨復雜,敘事容量日趨龐大,傳統(tǒng)敘事方式顯然無法滿足當代觀眾的需求。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內動畫也作出了積極調整,例如《麋鹿王》《藏獒多吉》《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等作品,敘事復雜,情節(jié)豐富,人物形象性格特征也很豐滿,但是影像風格卻未盡顯中國特色。《大魚海棠》等作品雖將寫意畫面與字幕組合,充分發(fā)揮聲音的空間感及環(huán)境音效的表意功能,但是這些并未有效彌補敘事斷層和情節(jié)空白。《中國唱詩班》系列則有了新的突破,其細膩雅致的古典畫風與視覺感受、生動的故事情節(jié)和傳統(tǒng)詩詞歌謠、對白與音樂、精致的細節(jié)處理以及富有中國韻味的隱喻,都較好地融為一體,鏡頭調度與情節(jié)也配合得恰到好處,在傳統(tǒng)美學觀念與當代影像空間及敘事的融合上樹立了典范。綜上所述,當代中國動畫影像風格的建構,不僅要把握自身文化命脈,還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傳統(tǒng)美學觀念與當代影像創(chuàng)造規(guī)律、敘事規(guī)律之間的矛盾,努力將各方面因素融合為有機整體。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中國動畫創(chuàng)作者的文化自覺與不懈探索,讓我們相信中國文化品格必將作為中國動畫的精神內核而被堅守,讓“中國風”具有永恒的魅力。
作者:鄒少芳 單位:浙江科技學院藝術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