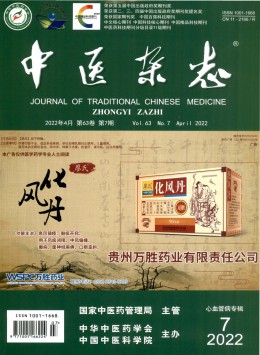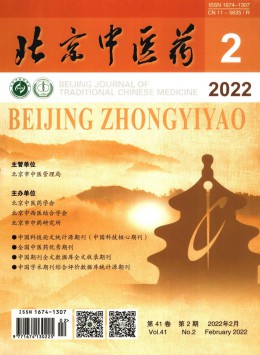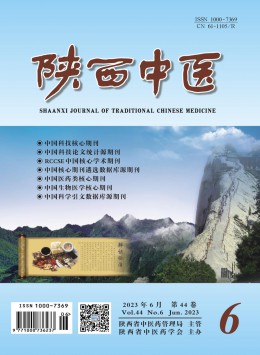中醫對藥物安全性風險控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中醫對藥物安全性風險控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中醫歷來重視用藥安全性,該文根據中醫臨床實踐過程,從中醫理論(理)、治則治法(法)、方劑配伍(方)、藥物應用(藥)以及特殊人群方面回顧了中醫傳統上控制藥物安全性風險的策略和方法,并簡要討論了現代臨床實踐和監管環境下,中藥安全性風險控制的進展。
關鍵詞:中藥;安全性;理法方藥;中醫理論;風險控制
1“理”和“法”
“理”是基于對人與自然、生理病理、疾病發生發展的認識,對通過四診收集到的患者癥狀和信息進行辨證和辨病,即在中醫基本理論的指導下,探討疾病發生發展的機理,并作出正確診斷。“法”上承于“理”,在辨證和辨病的基礎上確定相應的治則治法。中醫治療疾病,應當遵循中醫理論,先辨證,后論治。中醫的診治疾病的基本思想包括了辨證論治,以平為期,異法方宜,治病求本等[8]。《素問•移精變氣論篇》提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倒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即強調了正確辨證論治的重要性。中醫認為人體與外部環境、體內臟腑組織之間存在動態平衡,這種平衡打破了,就會產生疾病,而治療目的就是恢復或重建這種平衡,因此治療疾病時,注重協調平衡,即“謹察陰陽之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以平為期”的思想一方面重視治療的平衡性,提倡“中病即止”“衰其大半而止”等治療原則,反對過度治療,如《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食其正也”;另一方面也重視藥效和毒性的平衡,提出“不可過劑”,反對濫用重劑、峻猛之劑。異法方宜即制定治則時要強調考慮氣候、環境因素,結合患者個體因素,全面分析,具體處理,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提到:“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反映了根據季節氣候不同而用藥;《素問•至真要大論篇》提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傷寒論》中指出咽喉干燥者、淋家、瘡家、亡血家、汗家、酒客等均應慎用汗法,均反映了選擇治療原則應因人而宜。這些理論對于藥物安全性也有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如果不能準確辨證和辨病,或不能制定正確的治則治法,藥不對證,不僅治療無效,甚至可能引起毒副作用。清代名醫凌奐認為“凡藥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沖鋒于前,不顧其后也”,在其所著《本草害利》一書中,對于每一個藥物先言其“害”,后言其“利”,對人參、黃芪等傳統補益藥,關于“害”的篇幅遠遠多于“利”,充分反映了中醫對于藥物安全性的重視。因此正確診斷疾病,選擇恰當的治則治法,防止藥物毒副作用,一直是中醫臨床重要的指導思想。
2“方”
“方”是根據“理”與“法”,按照組方原則,確定藥物、劑量和劑型。“方”是連接“理”“法”和藥物的橋梁,綜合體現了從“理”到實施具體治療的過程。在中醫早期萌芽階段,一般采用單味藥,隨著對疾病認識的不斷深入,對藥物使用經驗的不斷積累,用藥也由簡到繁,由單味藥到多味藥配合治療,形成了方劑,多味藥配合應用中醫稱之為“配伍”。歷代先賢在臨床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藥物配伍經驗,對藥物與藥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有深刻的體會,認識到藥物的配伍應用能提高藥物的療效,同時也會增加或減少藥物的毒副作用。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更早,即形成了中藥組方和配伍的基本原則,歷經數千年,內容不斷豐富,從“增效”和“減毒”兩個角度出發,既增強藥物的療效,同時也力爭彌除藥物安全性的隱患。這些原則主要包括“君臣佐使”“七情相合”等。君臣佐使的理論出自《內經》和《神農本草經》,《素問•至真要大論篇》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指出藥物可按其在方劑配伍中所起的作用分為君藥、臣藥、佐藥、使藥。《素問•至真要大論篇》又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指出君臣佐使的配伍比例不同來區分成方的大小。《神農本草經》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下藥一百二十種為佐使,主治病;用藥須合君臣佐使”,則具體到了藥物層面。君臣佐使是從方劑組成結構出發,闡述不同藥物在一首方劑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中佐藥(佐制藥)用以消除或減弱君、臣藥的毒性,或制約君、臣藥峻烈之性,使藥(調和藥)調和方中諸藥[9],兩者具均有減輕藥物毒副反應的作用,從組方的角度控制了用藥風險,《傷寒雜病論》中大量的方劑用到了甘草、生姜、大棗,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起到了佐制和調和的作用。“七情相合”的配伍理論關注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出自《神農本草經》,書中提到:“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時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相畏”和“相殺”的配伍適用于彌減藥物的毒副作用,“相反”和“相惡”包含了降低療效和產生毒副作用的藥物相互作用,這四者都屬于現代藥物警戒的范疇。在“七情相合”的基礎上拓展出了藥物配伍宜忌,“宜”指藥物適合配伍,關鍵在于藥物配伍后能增效減毒;“忌”指藥物合用會產生和增強毒副作用、或降低和破壞藥效,在復方中不宜配合運用。配伍禁忌中最多提到的是“十八反”“十九畏”,尤其是“十八反”列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十八”之數,首見五代后蜀•韓保升《蜀本草》,其注釋《神農本草經》時提到:“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者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三十六種”。歷代本草著作有所增補,如《普濟方》記載有57種、48對,《本草集要》記載25種、19對,《中藥品匯精要》記載29種、28對,《本草蒙筌》記載25種、26對,《本草綱目》記載31種、29對。因此“十八反”已超出其數字意義,成為中藥配伍禁忌的代名詞。除“反”“惡”外,本草文獻中“禁”“忌”“勿”“不可”“不宜”等內容大部分都與藥物配伍禁忌有關[9-11]。此外,配伍禁忌還包括了服藥食忌,俗稱“忌口”,即服用中藥期間的飲食禁忌。《金匱要略》中提到:“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有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難療”。一般服藥期間應忌食生冷、油膩煎炸、辛辣刺激、海腥發物等食物,以免削減藥物功能,或產生不良反應。
3“藥”
“藥”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應用藥物,是組成方劑的基本單位,“方”“藥”常常并稱。中醫的藥性理論包括四氣五味、升降沉浮、歸經、有毒無毒等,是指導臨床合理用藥的基礎。中藥來源廣泛,品類繁多,很多藥物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甚至致命,如《神農本草經》提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殺人,一曰鉤吻,二曰鴟……”,并認識了一些藥物的中毒癥狀,如《諸病源候論》描述“著烏頭毒者,其病發時,咽喉強而眼睛疼,鼻中艾臭,手腳沉重,常嘔吐,腹中悶熱,唇口習習,顏色乍青乍赤,經百日死”。減少藥物的毒副作用,除了在組方時注重藥物配伍,避免配伍禁忌,在藥物層面,歷代醫家也盡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對藥物的毒性進行分級、藥物炮制、制劑、劑量、服用方法,以及解毒方法等[12]。《素問•五常政大論篇》開藥物毒性分級的先河,把藥物毒性分為“大毒”“常毒”“小毒”“無毒”四類,《神農本草經》運用到具體藥物,根據藥物的安全性注明有毒、無毒,并根據毒副作用的程度注明“大毒”“小毒”等分類,這種分類方法為以后歷代本草著作沿用,并出現更詳細的分級,如“微毒”“微有小毒”等,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采用了“大毒”“有毒”和“小毒”三級分類法。藥物毒性分級對藥物的臨床安全應用,避免毒副作用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炮制(或炮炙)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根據藥物的性質和治療目的,對中藥進行加工。由于藥物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因此藥物加工是減少毒副作用的重要環節,是中醫減少藥物毒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加工后的中藥制成飲片,便于制劑。早在南北朝劉宋時期就出現了我國第一部藥物炮制專著《雷公炮炙論》,經歷展,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藥物炮制的理論和方法。現在看來,傳統的炮制方法大多數有臨床實用價值,并經現代科學手段證實。例如巴豆含有34%~57%巴豆油,既是有效成分,也是劇毒成分,巴豆入藥前經過去殼、炒熱、研絨、榨去油、研霜等一系列炮制過程,加工成巴豆霜,使含油量控制在18%~20%或放在紙上不沒油跡為準,大大降低了巴豆油含量,既保證藥效,也提高了安全性[13]。中藥炮制一方面減少和去除了藥物本身的毒性和一些引起不良反應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制定了藥物來源、生藥加工、成藥生產的一些規范,從而減少因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品種誤用、加工生產不規范等因素引起的藥物安全性問題。中藥劑型以湯劑最為常用,因此煎藥容器、煎藥溶媒、煎藥時間、煎藥次數、煎藥火候和溶媒量對藥物的安全性也有影響,這在歷代中醫著作中有大量描述。例如煎藥容器不宜用鐵器;附子往往需要久煎,因為加熱可以破壞烏頭堿等等。對于一些毒性較高,用量較小的藥物,往往制成散劑,可以控制劑量,減少毒副反應。此外,中藥也有一些特殊的制劑方法,如服用時將芫花、大戟、甘遂這些毒性劇烈的藥物放入棗肉或桂圓肉內,類似于今天的膠囊劑,其目的也是減少藥物的毒副作用。古人很早就認識到劑量與毒副作用之間的關系,因此使用重劑、猛劑時往往采用劑量遞進的原則,反對孟浪用藥。《傷寒雜病論》中提到十棗湯:“強人每服一錢匕,羸人半錢……若下,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后,糜粥自養”,綜合反映了治療因人而異、劑量遞進的思想,以及服用峻猛藥物的善后。中藥服用得法,也可以減輕或避免安全性問題,如對胃腸道有刺激的藥宜飯后服;常山熱服容易引起嘔吐,故宜冷服等。除了減少藥物毒性外,歷代醫籍中對解毒方法也有描述,并不斷積累和沿用下來。如《神農本草經》認為甘草、豬苓、石蜜等藥材有“解毒”功效;《肘后備急方》中列有“治卒中儲藥毒救解方”“治卒服藥過劑煩悶方”等內容;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提到藥物的毒副作用也是有辦法可以解救的,“凡藥物云有大毒者,皆能變亂與人為害,亦能殺人。但毒有大小,自可隨所犯而救解之”;《新修本草》專列解毒篇,記載中毒解救之法。
4特殊人群的用藥安全性
妊娠用藥安全是我國古代醫家關注的重要內容之一,歷代將引起胎動不安、滑胎、墮胎等副作用的藥物列為妊娠禁忌藥或慎用藥。禁用藥多屬于劇毒藥,或藥性作用峻猛之品,或走竄性強的中藥,例如雄黃、斑蝥、麝香等;慎用藥則主要是一些活血化瘀藥、行氣導滯藥和攻下藥等,例如紅花、大黃、附子等。《神農本草經》記載了6種有墮胎作用的中藥,隋代《產經》最早直接列述妊娠禁忌,記載了82種妊娠禁忌中藥,宋•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系統完整地著錄妊娠禁忌藥,列舉了妊娠禁忌藥69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對妊娠婦女禁忌使用的中草藥和中成藥均有標注。除了重視藥物的禁忌外,針對孕婦還制定了專門的治療原則,如“有故無殞”“衰其大半而止”等,指孕婦不得“無故”用藥,倘若有病邪存在,雖使用峻烈藥物,是不會傷害母體,亦不會傷害胎兒的。用藥時應根據疾病輕重,謹慎用藥,不得過度治療。此外,也總結了不少適用于妊娠期間服用的中藥和方劑[14-15]。中醫學認為老人和兒童體質與青壯年差別很大,老人總體走向衰竭,血氣已衰,精神耗減,如風中殘燭;兒童生長發育未完全,身體脆弱,常用“稚陰稚陽”來形容,因此在治療上不僅僅是簡單的避免使用藥性猛烈的藥、減少藥物的劑量,而且結合患者年齡和生理狀態,即使相同的疾病,也可能采用與青壯年不同的治則治法和方藥,這樣既提高治療的有效性,也提高用藥的安全性。
5中藥安全性風險控制的現代進展簡述
中醫傳統上是非常重視藥物的安全性,對藥物安全性認識的廣度非常大,對中藥的毒副作用積累了豐富的知識,本草著作中記載的數千種藥物均有一定的安全性信息,這些安全性信息都是在臨床實踐中積累的,并根據臨床路徑,融理、法、方、藥于一體,從多方面、多角度減少藥物安全隱患,對臨床有很大的指導價值。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對中藥的安全性認識可能缺乏一定的深度,例如中藥雖然有毒性分級等安全性內容,但比較粗略,缺乏嚴格的客觀標準,每個醫家的認識和經驗都不同,這就造成對于同一個藥物的毒性描述和毒性分級會產生矛盾之處,造成歷史上對某些藥物安全性的爭議和困惑。隨著現代藥理學、毒理學、藥物警戒等理論和方法在中藥研究中的運用,從理論層面、方劑層面、藥物層面以及基于藥物警戒理論和方法的層面,對中藥飲片、制劑等進行安全性監測和評價[16]。近年對何首烏等藥物肝毒性的研究[17-18],使我們對中藥的肝毒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近日也《中藥藥源性肝損傷臨床評價技術指導原則》,旨在控制中藥用藥的安全風險,推動中藥新藥研發,從而促進中藥產業健康發展。另外,中藥注射劑是有別于傳統中藥的劑型,也已成為我國藥品安全風險主要集中區域之一,因此,也有學者提出生產廠家-醫療機構-政府部門“三位一體”的立體監控模式設想[19],也形成了中藥注射劑臨床安全性集中檢測的專家共識[20],這些新的理論、觀念和方法均有助于提高對中藥安全性風險的控制。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臨床實踐中也可以看到中藥本身成分復雜、中藥劑型多樣化、復方制劑居多,2015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共收載含毒中成藥474種,占成方制劑的31.75%。含毒性飲片的口服制劑、外用制劑、肌內注射品種分別為435(其中12個為既可口服又可外用的品種)、38、1個,分別占含毒中成藥的91.77%、8.02%、0.21%。含有1、2、3味及3味以上毒性飲片的成方制劑分別有318、93、32、31個,分別占含毒中成藥的67.09%、19.62%、6.75%、6.54%[21]。中藥臨床與其他藥物聯合使用多,而且多數中藥作用相對和緩,發生毒副作用可能無明顯臨床癥狀及體征,因此對于認識、判斷不良事件,以及判斷與用藥的關聯性帶來了困難。目前中藥的安全性監測和評價主要還是依靠自發報告,缺乏大規模的集中監測,缺乏設計良好的以安全性為終點的臨床試驗,藥物上市后再評價也有待加強;超過半數中藥說明書安全性信息缺失或風險警示不足;中藥不合理用藥現象突出;中藥與化學藥、生物制劑聯合應用非常普遍,但對這些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還缺乏認識和研究;中藥飲片、顆粒劑等產品的安全性監測仍顯不足;公眾對中藥的安全性還存在很大的誤區等,因此有學者提出建立“臨床監測-科學評價-風險防控”的一體化管理,完善科學的中藥安全性評價和監管體系[22],此外,加強中藥安全性監測網絡、優化中藥安全性評價方法,使之更符合中醫藥學科特點,使中藥安全性信息更好地應用于臨床實踐,提高公眾對中藥安全性的認識水平等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23-25]。
參考文獻
[1]蔡松穆,廖培辰.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石散[J].北京中醫藥,2008,7(4):273-275.
[2]邱少平.淺析魏晉服用五石散藥之原因[J].中華醫史雜志,2005,35(1):60.
[3]周榮易,王嬌嬌,韓新民.對中藥毒性問題的思考[J].時珍國醫國藥,2016,27(7):1679-168.
[4]孫喜靈,姜偉煒,劉琳,等.論中醫理法方藥知識創新的基礎與支點[J].中醫雜志,2013,54(4):277-279.
作者:劉靜 朱琰 朱琦 單位:上海市中醫醫院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 惠氏制藥有限公司(輝瑞制藥有限公司健康藥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