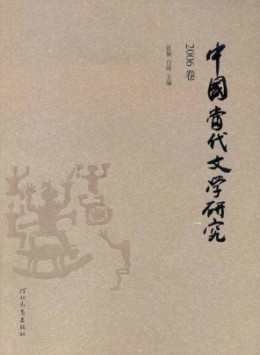當(dāng)代文學(xué)話語規(guī)范創(chuàng)建分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當(dāng)代文學(xué)話語規(guī)范創(chuàng)建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
1943年5月趙樹理寫出成名作《小二黑結(jié)婚》。《小二黑結(jié)婚》完成之后,受到了太行山區(qū)根據(jù)地共產(chǎn)黨高層領(lǐng)導(dǎo)的欣賞,還親筆題詞:“像這樣從群眾調(diào)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并刊載在1943年9月由華北新華書店初版的《小二黑結(jié)婚》單行本扉頁上。初版兩萬冊,與當(dāng)時“新華書店的文藝書籍以兩千冊為極限”的狀況形成鮮明對照。次年3月重排再版2萬冊,群眾還“自動地將這個故事改編成劇本,搬上舞臺”。[1]但讀者接受上的熱烈反饋并未在文學(xué)評論上表現(xiàn)出來,有評論文章稱:“當(dāng)前的中心任務(wù)是抗日,寫男女戀愛沒有什么意義”,并且“從此以后,太行區(qū)眾多的報刊雜志一律保持古怪的沉默”。[2]1943年10月,趙樹理又寫出《李有才板話》,兩個月后由華北新華書店出版。小說出版同月,在《華北文化》(革新版第2卷第6期)上發(fā)表了當(dāng)時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的推薦文章《介紹<李有才板話>》。這是最早提出評價趙樹理的核心觀點的文章之一。它提到小說表現(xiàn)了“新社會的某些鄉(xiāng)村,或某些角落”,提出“立場”問題、階級分析的方法和“接近群眾”的要求,這些都成為此后的評論文章衡量趙樹理小說的基本原則。聯(lián)系到評論界對《小二黑結(jié)婚》的冷淡反應(yīng),李大章在文章中批評那種“把寫給農(nóng)民看的東西當(dāng)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有意無意地抱著‘第二等’的寫作態(tài)度來從事它”的心態(tài),并非無的放矢。這是對“當(dāng)時根據(jù)地文化界大多數(shù)人看不起趙樹理的那種通俗化”[3]的側(cè)面反映。李大章進(jìn)而提出,是否愿意為農(nóng)民寫作“通俗淺近”的文藝作品,不僅僅是“態(tài)度”問題,其本質(zhì)是“為誰服務(wù)”的問題,“也就是立場問題”。從這篇文章的寫作實踐看,這種觀點應(yīng)該來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是1942年針對延安文藝界狀況做出的,傳播至各根據(jù)地則是次年10月。1943年10月19日即魯迅的忌日,《解放日報》正式發(fā)表《講話》。第二天,中共中央總學(xué)委發(fā)出通知,要求“各地黨委收到這一文件后,必須當(dāng)作整風(fēng)必讀文件,找出適當(dāng)?shù)臅r間,在干部和黨員中進(jìn)行深刻地學(xué)習(xí)和研究”。11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又做出“關(guān)于執(zhí)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指示“各根據(jù)地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yīng)該把同志所提出的問題,看成是有普遍原則性的,而非僅適用于某一特殊地區(qū)或若干特殊個人的問題”。[4]身為北方局宣傳部長的李大章,當(dāng)然是在最早的時間接到類似的通知,并從趙樹理的小說中辨識出了在《講話》中提出的要求,因此才可能在《李有才板話》出版的同時做出這樣的評價。當(dāng)然,在做出肯定的同時,這篇文章也依據(jù)階級分析的方法對《李有才板話》提出了批評:“作者的眼界還有一定的限度,特別是對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還不夠熟悉”,“特別是對馬列主義學(xué)習(xí)的不夠,馬列主義觀點的生疏,因此表現(xiàn)在作品中的觀點還不夠敏銳、鋒利、深刻,這就不能不削弱了它的政治價值”。———這種批評也恰好成了50年代批評趙樹理小說“缺陷”時的主要觀點。
二
1946年1月,《李家莊的變遷》由華北新華書店初版,隨后被多個出版社或書店再版。也就是在1946年,趙樹理在他不屑于擠進(jìn)去而要“拆下來鋪成小攤子”[5]的“文壇”贏得了巨大的聲譽(yù)。這一年有十余篇關(guān)于他的評論文章發(fā)表在《解放日報》(延安)、《人民日報》(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聯(lián)主辦)等重要刊物上,寫作者也絕非等閑之輩,而是周揚(yáng)、馮牧、陳荒煤等在解放區(qū)(尤其延安)舉足輕重的人物以及郭沫若、茅盾等國統(tǒng)區(qū)的左翼文藝界領(lǐng)袖。1946年7月20日,周揚(yáng)在中華全國文藝協(xié)會張家口分會的機(jī)關(guān)刊物《長城》上發(fā)表《論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以作家論的形式對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進(jìn)行了全面而系統(tǒng)的評述。郭沫若在讀到周揚(yáng)從解放區(qū)帶到上海的趙樹理的兩本小說集后,立即寫了熱情洋溢的贊美文章《<板話>及其他》,發(fā)表在8月16日的《文匯報》上。如同事后趙樹理的朋友史紀(jì)言回憶的:盡管《小二黑結(jié)婚》和《李有才板話》經(jīng)過了和李大章的介紹,“然而幾年以后,并未引起解放區(qū)應(yīng)有的重視”,“經(jīng)過周揚(yáng)同志的推薦,后又經(jīng)過郭沫若先生的評價,大家的觀感才似乎為之一變。”[6]趙樹理評價的這種“滯后”現(xiàn)象,似乎可以從一個側(cè)面看出當(dāng)時以“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文藝界和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政權(quán)之間的微妙矛盾。盡管的《講話》已經(jīng)作為整風(fēng)的“必讀文件”遍布解放區(qū)乃至全國的左翼文化界,并且對發(fā)動群眾文藝運(yùn)動做出了三令五申的指示,但對于趙樹理這樣一個文壇之外的農(nóng)民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銷行量廣泛的文學(xué)作品,文藝界仍然不能做出有效的回應(yīng)。這主要是因為,如何評價趙樹理的文藝作品,涉及“五四”新文學(xué)傳統(tǒng)與抗戰(zhàn)以來進(jìn)行民族和民眾動員時期的文學(xué),在文學(xué)觀念、創(chuàng)作的文化資源和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作家文化實踐方式等基本問題上的歧義和矛盾。對趙樹理作品評價上的分歧盡管沒有在具體的批評文字中顯現(xiàn)出來,但由筆者在它文中曾具體分析的“民族形式”的論爭,[7]由《講話》所倡導(dǎo)的“工農(nóng)兵文藝”的實踐過程所遭遇的矛盾和沖突,已可窺見其中端倪。在文藝界如何評價趙樹理的問題上,事實上最終是由周揚(yáng)的《論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做出了最權(quán)威的論證。周揚(yáng)這篇傾向性明顯的文章的發(fā)表,郭沫若、茅盾等無論在創(chuàng)作地位上還是政治地位上都屬于“資深”的領(lǐng)袖作家們的稱頌文章,顯然為趙樹理在文學(xué)界地位的上升并迅速提升到核心位置,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946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召開文藝界座談會,提出“今后要向一些模范作品如《李有才板話》學(xué)習(xí)”;10月,太岳文聯(lián)籌委會召開座談會,提出“應(yīng)學(xué)習(xí)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1947年5月4日,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聯(lián)和文協(xié)分會也提出:“我們的農(nóng)民作家趙樹理同志如此輝煌的成就,為解放區(qū)文藝界大放光彩,提供了值得我們很好學(xué)習(xí)的方面。”[8]1947年7月25日-8月10日,在中央局宣傳部指示下,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聯(lián)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趙樹理,這次會議的結(jié)論,由主持邊區(qū)文聯(lián)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長陳荒煤執(zhí)筆寫成《向趙樹理方向邁進(jìn)》一文,發(fā)表在邊區(qū)機(jī)關(guān)報紙《人民日報》上。陳荒煤以“我們”的全稱口吻,總結(jié)出向趙樹理學(xué)習(xí)的三點方向:他的作品的政治性;他所創(chuàng)造的“生動活潑、為廣大群眾所歡迎的民族新形式”;以及他“高度的革命功利主義,和長期埋首苦干,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于這樣的殊榮,趙樹理本人的反應(yīng)是:“我不過是為農(nóng)民說幾句真話,也像我多次講的,只希望擺個地攤,去奪取農(nóng)村封建文化陣地,沒有做出多大成績,提‘方向’實在太高了,無論如何不提為好。”[2]但此時趙樹理個人的意見已經(jīng)不重要了。一經(jīng)被選定為實踐《講話》的“杰出代表”,對他肯定與否也就與文藝思想本身的有效性聯(lián)系在一起。盡管趙樹理的文藝觀點與《講話》有許多內(nèi)在的契合之處,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其成名作《小二黑結(jié)婚》的寫作,并非是參照《講話》完成的;而就作品本身而言,也與《講話》并非全然一致。與其說趙樹理的小說是“文藝思想在創(chuàng)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1]或“最樸素,最具體的實踐了的文藝方針”,[5]不如說是左翼文化界選擇了趙樹理作為印證《講話》有效性的經(jīng)典。
三
但盡管如此,當(dāng)代文學(xué)在建構(gòu)其文學(xué)規(guī)范的過程中,規(guī)范的標(biāo)準(zhǔn)和內(nèi)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與解放戰(zhàn)爭時期更側(cè)重于強(qiáng)調(diào)“群眾文藝”和群眾立場相比,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尤其是隨著冷戰(zhàn)格局的明朗化而與蘇聯(lián)關(guān)系的密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為一種更激進(jìn)也被認(rèn)為更“高級”的原則得到集中的提倡。以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講話》為依據(jù)確立的“趙樹理方向”,也因此受到質(zhì)疑,并成為此后趙樹理抹不掉的“缺點”。1948年9月,為了“寫出當(dāng)時當(dāng)?shù)厝窟^程中的各種經(jīng)驗教訓(xùn),使中的干部和群眾讀了知所趨避”,趙樹理寫了中篇小說《邪不壓正》。在結(jié)構(gòu)方式上,小說以中農(nóng)劉聚財?shù)呐畠很浻⒌幕榧迒栴}作為線索,貫穿起下河村的全過程;而小說主題則被定位在批評不正確的干部和流氓,同時又想說明受了冤枉的中農(nóng)作何觀感。小說發(fā)表之后《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數(shù)篇讀后感和爭鳴文章①,對小說褒貶不一。在“趙樹理方向”提出不久,趙樹理在文藝界的地位趨于鼎盛的情形下,對他的新作產(chǎn)生如此明顯的歧義,一方面是此前文藝界對趙樹理創(chuàng)作異議的發(fā)露,同時也顯現(xiàn)出文壇關(guān)于當(dāng)代文學(xué)規(guī)范的內(nèi)涵并未獲得統(tǒng)一的認(rèn)識、而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對《邪不壓正》做出更尖銳也更符合當(dāng)代文學(xué)發(fā)展趨勢的批評文章,是竹可羽的《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9]以及《再談?wù)劊缄P(guān)于《邪不壓正》>》。[10]竹可羽認(rèn)為通過對照《邪不壓正》和《傳家寶》,“能夠說明一個創(chuàng)作上極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作者善于表現(xiàn)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現(xiàn)前進(jìn)的一面,在作者所集中要表現(xiàn)的一個問題上,沒有結(jié)合整個歷史的動向來寫出合理的解決過程”。這種說法既與“歌頌/暴露”的問題相關(guān),同時也與左翼文化界一個長期糾纏不清的問題相關(guān),即怎樣才算是“真實”地展現(xiàn)了“歷史的發(fā)展方向”,從“歷史”高度表現(xiàn)“新/舊”、“前進(jìn)/落后”之間的斗爭趨勢。這實際上正是1934年9月蘇聯(lián)作家代表大會在《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章程》中作為“基本方法”提出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所要解答的基本問題,即“要求藝術(shù)家從現(xiàn)實的革命發(fā)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xiàn)實。同時,藝術(shù)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wù)結(jié)合起來”。[11]就“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這一范疇本身來說,它是“一折中方案,其中包含一系列矛盾”,這些矛盾就是所謂“現(xiàn)實主義成分”和“浪漫主義成分”孰輕孰重的問題,以及作家到底是已然發(fā)生的現(xiàn)實生活的“觀察者”還是應(yīng)該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政策的“教育者或宣傳家”的問題。但要求作家“必須通過他的作品參與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宣傳,卻從來沒有放棄”。[12]也就是在《講話》中說的,站在歷史發(fā)展總趨勢的高度,“把這種日常的現(xiàn)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從而創(chuàng)造出“更強(qiáng)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文藝作品,以“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jìn)”。[13]從《講話》的“群眾路線”到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宣傳和教育原則,實際上是從“現(xiàn)實主義”更偏向“浪漫主義”,也是把文藝思想中那種“以先驗理想和政治烏托邦激情來改寫現(xiàn)實”[14]的“主導(dǎo)”方面凸顯出來。竹可羽的批評顯然是異常尖銳的。此后,在繼續(xù)把趙樹理作為一種“方向”來推崇的同時,批評他“善于寫落后的舊人物,而不善于寫前進(jìn)的新人物”似乎成了對趙樹理的一個定論,而“結(jié)合整個的歷史動向”來展現(xiàn)農(nóng)村兩條路線斗爭過程,也成了一個基本衡量標(biāo)準(zhǔn)。對于《三里灣》和《“鍛煉鍛煉”》的批評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1955年初,趙樹理根據(jù)他在山西平順縣底村農(nóng)業(yè)合作社的生活、調(diào)查、采訪所得的經(jīng)驗,寫成長篇小說《三里灣》,在《人民文學(xué)》上連載。小說發(fā)表后也引起了褒貶不一的評論。最有代表性的是俞林的《<三里灣>讀后》。[15]文章集中批評了小說雖然“真實地提出了問題”,但對問題的處理卻“沒有達(dá)到應(yīng)有的深度,而用不夠真實的大團(tuán)圓的尾巴把斗爭簡單的作了解決”。俞林提出,“當(dāng)前農(nóng)村生活中最主要的矛盾,即無比復(fù)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在《三里灣》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表現(xiàn)。———提出這樣的要求,顯然是依據(jù)激進(jìn)化的“兩條路線斗爭”的階級圖景,要求趙樹理的小說表現(xiàn)更“高”的階級立場,做出更符合“無產(chǎn)階級意識”的階級斗爭描繪。這一批評事實上也是依據(jù)“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提出的。如果按照“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wù)”的要求,最能表現(xiàn)出“社會主義精神”的無疑是處于激烈的階級斗爭中的無產(chǎn)階級英雄。《三里灣》對人物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的描寫,始終沒有脫離鄉(xiāng)村的倫理秩序,而人物之間的矛盾的處理方式,也是在鄉(xiāng)村人際關(guān)系許可的范圍內(nèi)展開。王金生對待范登高的態(tài)度和對是否擴(kuò)社的處理,就借助了鄉(xiāng)村倫理秩序而把社會主義精神融化其中,因而所謂的階級斗爭始終是在鄉(xiāng)村倫理秩序之中進(jìn)行的。這顯然沒有達(dá)到“社會主義精神”的純度和高度。1958年7月,趙樹理的短篇小說《“鍛煉鍛煉”》發(fā)表。這篇小說與趙樹理1949年后的其他小說相比,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以“批評”和“提出問題”為主,用趙樹理自己的理解,是典型的“問題小說”。小說一發(fā)表,就引起了相當(dāng)激烈的批評。批評文章都認(rèn)為《“鍛煉鍛煉”》所表現(xiàn)的問題是不“真實”的,沒有表現(xiàn)出“應(yīng)該有”的進(jìn)步人物、黨的農(nóng)村政策和對資本主義思想的“正確”斗爭,因而是在歪曲“現(xiàn)實”。顯然,這里“真實”、“現(xiàn)實”的標(biāo)準(zhǔn)并不是經(jīng)驗層面的,而是從“兩條路線斗爭”這樣的“觀念”層面出發(fā)在提出要求。從“經(jīng)驗”的真實發(fā)展到“觀念”的真實,其實正是《講話》、“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兩結(jié)合”這樣的理論本身的折中性和含混性決定的。如同洪子誠指出的:“《講話》的基本理論構(gòu)成,是一組對立的矛盾關(guān)系的展開。政治與藝術(shù),世界觀和創(chuàng)作方法,現(xiàn)實和理想,主觀和客觀,知識分子和工農(nóng)大眾,光明和黑暗,歌頌和暴露,普及和提高等等。《講話》本身留下的‘空隙’,和對對立項的不同側(cè)重,是不同歷史語境下,具有不同思想和知識背景的左翼作家關(guān)于《講話》的論辯的主要內(nèi)容”,[14]同時也是不同時期的不同評論家關(guān)于如何評判文學(xué)作品而進(jìn)行論辯的核心依據(jù)。對于《“鍛煉鍛煉”》的爭論也是這一爭辯的反映。
四
可以說,對趙樹理“問題小說”所提出的批評,是當(dāng)代文學(xué)規(guī)范內(nèi)部矛盾和沖突的具體表現(xiàn)。作為批評的依據(jù),則是更突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對“社會主義精神”的側(cè)重,也是把文藝思想中“以先驗思想和政治烏托邦激情來改寫現(xiàn)實”的浪漫主義層面凸顯出來。造成的后果,則是使左翼文學(xué)曾經(jīng)具有強(qiáng)大的現(xiàn)實批判力,并在經(jīng)驗層面與現(xiàn)實社會構(gòu)成對話關(guān)系的活力完全喪失,蛻化為語詞、概念和話語上的循環(huán)復(fù)制,完全拋棄了“現(xiàn)實主義”的因素。但這種批評觀,經(jīng)過50年代的反復(fù)之后,從50年代后期至“”,則成為文藝界占據(jù)主流位置的觀點。趙樹理受批判的命運(yùn)在所難免,并在1966-1971年達(dá)到高潮。曾被樹為工農(nóng)兵文藝方向的趙樹理,成了“修正主義文學(xué)的‘標(biāo)兵’”、“反革命復(fù)辟的吹鼓手”、“一貫鼓吹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作家”。1970年9月,趙樹理受到過度摧殘,含冤逝世,而對于他的批判卻并未停止。這不僅是趙樹理這樣一個作家的悲劇,事實上是所有或多或少地保持“現(xiàn)實主義”批判力的作家的悲劇,同時,也是已然被體制化的左翼文學(xué)本身被異化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