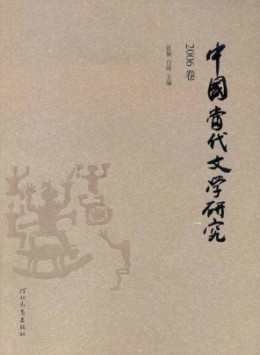當代文學發(fā)展歷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當代文學發(fā)展歷程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
1950-1970年代的當代文學,作為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嘗試,面臨著一個悲劇性的歷史處境,這從一開始似乎就決定了它的偉大成就與失敗的結局。在一個遠未現(xiàn)代化的社會要建立更現(xiàn)代的社會主義,這是俄國與中國所面臨的同樣的難題,這甚至也決定了列寧與會分享某些共同的焦慮,會具有共同的葛蘭西式的對文化的重視。但是,現(xiàn)實并沒有為新社會準備新的文化基礎。歷史不但未給新的文化準備條件,相反,新的社會還急需一種新文化來提供條件,只有這樣,才能完成落后的現(xiàn)代國家的最廣泛的組織與動員。這使社會主義新文化具有了某種超歷史的性質(zhì),從而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它的多舛命運與悲壯的結局。但是這與其說證明了新文化的本質(zhì)缺陷,還不如說證明了這場文化革命的艱巨性。新文化與新文學的這種悲劇結局,一方面和它缺乏基礎性的文化條件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如下的新中國的狀況聯(lián)系密切:在被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包圍的艱難局面下追求現(xiàn)代化,自我殖民所造成的結構性的內(nèi)部矛盾,以及先鋒政黨向社會管理者或一般性的社會精英集團的蛻變所造成的社會壟斷———這種不斷積累與演化的新現(xiàn)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理想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魅力,從而給建立新文化造成了潛在的障礙,并為舊文化的延續(xù)與復辟提供了民間的土壤。正因為建立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歷史條件的欠缺,反倒刺激了建立新文化的急切與激進態(tài)度,也導致了試圖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描繪新文化圖景的不得已的樂觀主義。在當代文學試圖超越現(xiàn)代文學的急切之中,我們不難看出在舊文化的壓力下表現(xiàn)出的偏執(zhí)化,和對舊文化過于強烈的排斥態(tài)度,如不斷強化的對革命的精神性純度的強調(diào),對具體歷史處境中的人的眾多社會性因素的驅(qū)逐,和對現(xiàn)實與歷史更多豐富性與復雜性的狹隘化處理,從而使文學的理想性過于強烈地壓倒了現(xiàn)實性。
事實上,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很多成功的當代文學作品,如《青春之歌》、《紅旗譜》、《小城春秋》、《三家巷》,包括更為通俗的《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烈火金鋼》等,恰恰是大量挪用了舊文學的資源,有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與舊文學相妥協(xié)的產(chǎn)物。當然,隨著“當代文學”邏輯的建立與展開,這種方向越來越受到壓制。應該說,在處理與舊文學的關系上,尚沒有獲得一種更具戰(zhàn)略高度的認識,比如,哪些因素是“當代文學”的核心價值?哪些因素是策略性的內(nèi)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如何能夠取得一種更有彈性、更具包容性的表達?如何容忍以及轉(zhuǎn)化其異質(zhì)內(nèi)容?當代文學另一個深刻的危機在于,出于對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強烈認同,把正在展開的現(xiàn)實秩序認可為理想秩序的現(xiàn)實展開,從而喪失了對新秩序的批判性的審視,喪失了對現(xiàn)實復雜性與內(nèi)在危機的敏感體察與文學想象力。可以說,1950-1970年代的文學的樂觀的理想主義恰恰是以它喪失深刻的超越現(xiàn)實的另一種烏托邦精神為代價的———馬爾庫塞意義上的烏托邦精神。當然,這種批判性的態(tài)度決不是指從舊文化或資產(chǎn)階級文化的方向上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否定,相反,那意味著是一種更深刻的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認同,它是對現(xiàn)實偏離理想的美學的質(zhì)疑與道義的糾正。因而它不表現(xiàn)為“寫人性”或“寫真實”式的批判。但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烏托邦氣質(zhì)逐漸被馴服了,其中既有文學體制的原因,也有作家主體的思想上的原因。當代作家,作為列寧意義上被組織化的文學工作者———這和各種改造與運動不無關系,似乎已習慣于與黨組織甚或其人格化的代表保持思想上的一致,哪怕它們已經(jīng)不具有抽象的黨的政治正確性。如“”組織的某些帶有幫派文藝色彩的創(chuàng)作,也不能一概認為其創(chuàng)作者態(tài)度不真誠。這就使文學喪失了原本應有的公共性質(zhì)。部分地和建立文化領導權的急切情緒相關,社會主義中國建立了更為“理性化”的現(xiàn)代化的管理文化的模式。而且,基于對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焦慮意識與危機感,1950-1970年代,形成了運用體制力量甚至政治暴力介入公共討論的傳統(tǒng)。
當然,在特定的情境下,自由討論有可能使舊文化(主要指更為成熟的資產(chǎn)階級文化)再度獲得優(yōu)勢,從而進一步威脅社會主義體制的建立,但這種過于酷烈的、一度常態(tài)化的批判體制卻在事實上損害了新文化的合法性,也取消了新文化在與舊文化的交流、對話與競爭中獲得成長的機會,以使它最終獲得歷史的勝利。事實上,對《武訓傳》、俞平伯(胡適)、胡風的批判在總體上完全具有歷史正當性,但這種批判的方式卻為后來新文化的結局埋下了伏筆———值得指出的是,恰恰是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率先對當代文學管理體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也構成了“三十萬言書”最閃光的部分。這的確是個困境和兩難。但是,如果能夠在先鋒政黨的引領下,通過自己對文化機器的有效控制而不是取消公共性的社會空間,情況或許會有所不同。在這一點上,先鋒政黨在1930年代與1940年代領導文化的經(jīng)驗值得回顧———雖然由于歷史情境的差異,這種對比不見得非常合適。事后看來,通過相對單純的文化批判來建立新文化的正當性,并通過更為完善地培育文學新人來提升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能力和經(jīng)典性,社會主義當代文學或許能獲得更大、更長遠的發(fā)展空間。
當然,對于文學新人的培養(yǎng)不能只是單純的意識形態(tài)或世界觀教育,它理應包括更為開闊的思想能力和文學訓練,無產(chǎn)階級的經(jīng)驗與社會主義的實踐,加上更為開放的思想與藝術的訓練,而不是狹隘地教條式學習,或許是社會主義文學新人獲得成長的一種可能途徑。在這一點上,浩然的成長道路是有偏頗的,他對革命觀念的教條式領會,試圖在黨的指導下進行文學寫作的單純意圖,極大地限制了這位出身純正的無產(chǎn)階級作家對現(xiàn)實的敘事能力———雖然他的典范意義是巨大的。但不容否認的是,“當代文學”的確在一種幾乎無所依傍的情況下進行了偉大的文學創(chuàng)造,它沒有對任何外在的、既定的、“普遍的”文學標準和普世文化價值的迷信與認同,也沒有去追求成為有特色的普世主義的中國的民族化版本,而是以勇敢的文化創(chuàng)造的精神,打破種種規(guī)矩(當然這并非沒有代價),自信地去創(chuàng)造一種文化與文學的新標準,或新的普遍性價值,這也是一個打破既定的文學定義,重新界定文學的過程。事實上,我們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史有意無意地無視了“當代文學”對世界的深刻影響。
以《白毛女》、《青春之歌》等作品為代表的文學創(chuàng)作對亞洲乃至歐美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尤其是對資本主義體制下進步的、有正義感的青年人有著異乎尋常的感召力,成為他們超越現(xiàn)實、思考新的未來、構想新“人”的精神資源———即使對于極端敵視新中國的西方主流社會來說,也不得不給予它敵意的重視和誹謗式的肯定。它所象征的普遍價值,對于世界與未來的文學想象,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是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所遠不能相比的———當今世界還有誰關注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文學?事實上,這也是喪失了真正的世界視野,依附在外在的普遍性或世界文學的標準下的“民族”文學的必然命運,試圖以“尋根”來披掛中國特色,走拉美式的諾貝爾獎捷徑的中國文學,充分象征了失去普遍性追求的中國文學的內(nèi)在渴望與虛弱本質(zhì)。這種文學即使在技術上再進步仍然是二流的,就不要怪顧彬式的漢學家對中國當下文學的奚落了吧,他只不過是把所謂西方或外部(包括民間)對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的輕視說得更直率露骨罷了。
二
1980年代以來的啟蒙主義的文學,重新接續(xù)了“當代文學”所否定的舊的現(xiàn)代文學的傳統(tǒng),以自由、美、人性為訴求,當代的中國文學完成了意識形態(tài)的轉(zhuǎn)向。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種非政治化的美學政治開始了新的意識形態(tài)實踐,但在形式上,它仍延續(xù)了1950-1970年代的文學體制———雖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這種延續(xù)采取了一種相對弱化的形式。可以說,1980年代以來的當代中國文學是以舊的文學體制,維護了對文學生產(chǎn)的有效控制———包括根據(jù)市場條件下的新環(huán)境,發(fā)展出行政與市場并重的雙重控制模式,從而維系了新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的再生產(chǎn)。這以1990年代以來的“主旋律”創(chuàng)作最為典型。
所以,1970年代末以來包括1990年代的文學多元化并不是沒有控制,這是一種更為隱蔽,也更為成功的控制,而且是新舊雜糅的控制方式,它呈現(xiàn)出更為自由的外表。“新時期”文學雖然在表面上沒有政治批判的威嚴,卻擁有著強大的合法性,它的成功正印證著、提示著“當代文學”體制的失敗———首先還不是內(nèi)容的失敗,而是高度集中的文學管理體制的失敗。事實上,如果沒有當代文學的歷史性失敗,1980年代的文學也沒有辦法獲得如此高的歷史合法性的起點,它正是在最初對“當代文學”富于革命性的挑戰(zhàn)中,獲取了自己的正當性與歷史價值———它的解放性當然是存在的。1990年代末期以后,尤其是進入所謂新世紀以來,在“新時期”文學坍塌的廢墟上,關于“新世紀”文學的想象又漂浮起來,形成了一團魅惑性的理論云霓。作為“大國崛起”意識形態(tài)的浪漫想象,以及即將成為現(xiàn)代化強國的自我意識的呈現(xiàn),“新世紀”文學卻只找到了些玄幻小說之類的世界文學流行市場的學舌之作,一些成為“世界人”的新人類的臆想與夢幻。不過,與此同時,新的文學因素也在開始出現(xiàn),比如“底層寫作”的潮流,盡管對此我們無法做過高估計。
因為,雖然其中的個別作品呈現(xiàn)了一種富于革命性的文學寫作的可能性,但作為總體仍帶有較多的“新時期”文學的色彩,這構成了它們歷史意義與文學價值的限度。另外,雖然某些“底層文學”有意識地試圖去接續(xù)革命文學或左翼文學的傳統(tǒng),但在這個無論從觀念上還是歷史實踐上革命都被祛魅的歷史處境中,直接地,不加反省地接續(xù)革命文學的資源是可疑的。底層文學還缺少真正有力量的對當下現(xiàn)實的批判能力和文學想象力,它的積極意義還更多地表現(xiàn)為對現(xiàn)實的直面與揭示,雖然,由于受到1980年代以來的美學慣例與某些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約,這種發(fā)現(xiàn)還是有限度的。但是,對“當代文學”的重寫畢竟已經(jīng)開始,以張承志、韓少功等為代表的具有思想能力和批判意識,同樣具有文學能力的作家的文學寫作已經(jīng)開始了這樣的嘗試。他們已經(jīng)放棄了經(jīng)典的文學體裁與成規(guī),這種文體革命和1980年代的先鋒沖動沒有關系,而是真正的文學與思想的自由對既有文學體制的漠視。他們的文學寫作已經(jīng)處在“新時期”之外,并形成了與當代批判性思想的有意無意地呼應和自然的暗合。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現(xiàn)象是,影視劇領域開始出現(xiàn)新的思想與美學因素,事實上,它有可能成為當代文學的一個新的場域。
由于電視劇必須面向當下與公眾寫作,它無法像所謂純文學一樣閉門造車。另外,作為新時代的重要主流媒體,這一寫作樣式也吸引了眾多寫作者,盡管它因商業(yè)性本質(zhì)也有著向世俗化的大眾趣味以及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妥協(xié)的一面,但也同時具有敏感于社會與人心的深層躍動,順應廣大民意的天然趨向。不可否認,對于那些試圖將文學寫作與現(xiàn)實建立有機、有效聯(lián)接,有抱負的文學寫作者而言,這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領域。應看到,創(chuàng)作主體的這種變化意義重大,這些人的參與正在部分地改變電視劇的文學品格,也在改變?nèi)藗儗﹄娨晞」逃械妮p視態(tài)度。一種革命性的變化正在出現(xiàn)———盡管在一開始還是極有限度的,在追求商業(yè)性的大前提下,電視劇也正在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值得重視的文學表達和個人風格的呈現(xiàn),《長征》、《星火》、《士兵突擊》、《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代表了這種變化。
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隨著文學閱讀者的銳減,電視劇的“高端”受眾數(shù)量卻在上升,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之視為一個癥候,表明了人們對當代文學喪失“當代性”的失望,這種閱讀期待被有效地轉(zhuǎn)移到具有某種“當代性”的電視劇中來。如何批判性地面對1950-1970年代和“新時期”以來的文學遺產(chǎn),反思其經(jīng)驗與教訓,在某種意義上,并不是一件外在于當下文學寫作的事情,它直接構成了這個時作的前提,內(nèi)在于每一個作家的寫作實踐。現(xiàn)在或許已經(jīng)來到了重新創(chuàng)造“當代文學”的時刻,它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當代文學”的政治性與“當下性”的自覺意識,文學寫作不得不是一種文化政治的自覺承當與面向當下并不斷地創(chuàng)造新當下的烏托邦實踐,與之相比,那種1980年代文學的純藝術迷夢,只不過是一種對當代文學寫作的政治化與當下性的不自覺與蒙昧罷了。當下性就是當代文學的本質(zhì),就是它的命運,也是它的活力與意義所在。